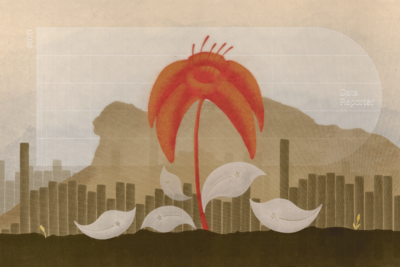「講阮暝日悲傷流目屎,希望你早一日回來⋯⋯」香港歌手黃耀明今年(2024)4月來台開唱,在滿場港人注目下,他卻突然開口獻唱〈望你早歸〉和〈港都夜雨〉兩首台語老歌,悲涼歌詞牽動著黃耀明本人的情緒,當他泫然欲泣,聽眾即使聽不懂台語,心仍被帶往四方,各自思念起那位不在現場的對象,是親友、情人,也可能是一座城市。
當最後一個音符結束,觀眾先是沉默,接著炸出掌聲,再陷入沉默,等待著黃耀明將說些什麼?此時歌者卻露出笑容。
出道40年來,黃耀明早已習慣在萬人體育館開唱,如今重返僅千人、百人大小的場地,他的巨星光芒絲毫未減,歌聲如畫、肢體舞蹈仍性感如昔。今年即將62歲的黃耀明說,在這個艱難時代,人們不能失去快樂的力量,他要盡力帶給人們快樂。
但台語老歌何其多,為何翻唱台灣民主運動中的兩首重要代表作,知道背後的意思嗎?當《報導者》詢問黃耀明,他再度笑了笑,回的隱晦:我知道,而且感同身受。

黃耀明和台灣、台語的緣分其實早有端倪。1986年擔任香港傳奇樂團「達明一派」主唱出道,黃耀明曾來台進行宣傳,當時留著叛逆長髮的他不知道台灣尚未解嚴,這世上竟存在藝人髮禁,也首次感受到政治如何影響文化。
而「台灣搖滾之父」羅大佑於九〇年代赴香港發展時,黃耀明是他的唱片公司旗下主力,羅大佑和作詞人林夕曾將台語歌〈雨夜花〉改編成粵語版〈四季歌〉交給黃耀明演繹,更成為他的代表作之一。
黃耀明坦承,唱歌久了難免疲累,演繹其他音樂人的作品,反而讓他找回活力。如此簡短的「久了」二字,卻可象徵香港的近代粵語文化史──身為歌手和「達明一派」主唱,黃耀明錄製過的專輯超過30張,在香港娛樂席捲全亞洲的九〇年代,他始終選擇和主流藝人不同的方向,成為粵語搖滾、迷幻、前衛音樂的開創者。
音樂這條路上,黃耀明取得的成就無數。多個香港、中國媒體自2001年起仿效美國樂壇最高榮譽葛萊美獎(Grammy Award)形式舉辦「華語音樂傳媒大賞」,在值得紀念的第一屆典禮上,黃耀明是最大贏家,榮獲最佳另類藝人之外,多首作品入選十大華語唱片及歌曲;而這年的競爭者包含張國榮、王菲、黃大煒等樂壇巨星。
一個理應被載入粵語史冊的名字,卻在2019年後逐漸從「兩岸三地」的娛樂界中消失。如今黃耀明已3年未在故鄉香港公開唱歌,原因不明。他多次租借場地遭廠商拒絕,2023年終於連演唱會的海報、日期、地點都決定了,又臨時收到廠商的退款通知。
「我知道這一天遲早都會到來的啊,當我開始參加很多社會運動的時候,我知道這一天早晚都會到來。」收到通知那天,黃耀明人在倫敦,他正進行「邊走邊唱」世界巡迴,前往各個住著香港人的城市開唱,從台北、倫敦、曼徹斯特、阿姆斯特丹到柏林。
「邊走邊唱」巡演名稱來自黃耀明1993年發行的經典曲目,它是首談離別的作品,歌詞圍繞一名情人對愛侶的互相傷害與懺悔,並重複唱著:「是我對你不起,沒法與你一起,但叫我遠走的偏是你。」
歌曲意境傷感,30年後的黃耀明卻換了角度詮釋,「我在台上唱,你在下面聽,我們能夠聚在一起的時候,其實那個是一個很快樂的時刻。」當黃耀明造訪各個國家,邊走邊唱的過程中,對語言的想像又再度昇華,他重新為台語老歌醉心。

擔憂有其原因。曾有一次黃耀明造訪新加坡工作,才發現星國自1979年起推行「禁止方言」政策,在媒體上不得播放粵語歌曲。接著2014年,中國廣東省禁止新聞台主播、記者在電視上說粵語,只能說普通話。種種經驗令黃耀明想起「台語在台灣的戒嚴時期也一度被打壓」,進而對台語產生更深認同。
「音樂已經是我的本能。我不能違背我的本能,如果我不唱歌,我就好像變成一個失能的人。我不會寫文字,不會做其他的事情,那我就通過音樂、通過唱歌說故事,無論是我自己的歌,或者是其他人的作品,」黃耀明認為,近期翻唱台語歌既是為香港人傳情,也為台灣人記憶。
替黃耀明製作〈望你早歸〉和〈港都夜雨〉單曲的音樂人王武雄則在錄音後分享:「因為歌有命,很多歌在出版之後,隨著時代的變遷,隨著與各種事件的連結,常常衍生出可能連原作者都料想不到的解讀。」
王武雄和黃耀明曾同是羅大佑旗下員工,兩人相識已久,1997年7月1日香港移交中國前一晚,王武雄便在唱片公司的大樓裡俯視維多利亞港,見證英屬香港最後一面。
「黃耀明的華語有較明顯的香港腔,別人我不知道,我自己很喜歡,這是我做功課時就已經決定的,我不希望他的台語發音失去他自己的特色。」本次專輯發行時,王武雄在社群平台上自抒。
黃耀明也感受到,九〇年代來台錄唱片時,製作人總要他「去掉香港口音」,近年卻發現台灣人對不同語言、腔調的接受度愈來愈高,「無論是我主觀的經歷,或者是我很客觀感受到,周圍都是一個比較包容的氣氛。」他希望這兩首作品跨越時代、語言,溫暖每個遊子的心港,「是一個香港仔對台語老歌的致敬。」
那粵語呢?當普通話教育成為香港主流政策,粵語的命運會如何?
「當我還在唱的時候,我還是會唱很多粵語歌的,所以反而沒有多想粵語會不會從我口裡消失?不會。當我還可以在台上開口唱歌的時候,粵語就不會消失,粵語歌一定不會消失。」
黃耀明依然選擇樂觀以對,他說只要有一支麥克風,一台電腦,他就會繼續唱下去。

今日台灣成為眾多香港文化人的歇腳地,而昨日香港,其實是台灣的長年模仿對象,諸如「屈臣氏」、「麥當勞」等外來品牌名,皆是台灣跟隨著香港譯名的使用,逐漸成為全民生活的一部分。旅居台灣6年的香港詩人廖偉棠便形容:
「粵語曾經是中文世界最摩登的,活著的語言。」
廖偉棠分析,香港自清朝末年受英國殖民後,長年是中文世界與西方交會的先鋒,「為了適應新出現的科技,時尚的事物,香港人會造很多詞,產生前衛的語彙。」但隨大量普通話流入,廖偉棠心中足以代表香港精神的各種「粵語」正在消逝。
2014年多名香港藝術家發起「探索霓虹」計畫,蒐集香港各地的老招牌、老字體,並做成線上地圖供人沿路造訪,廖偉棠的詩作〈從得如酒樓到麗泉桑拿,我們望天打卦〉,便是這趟文化之旅的起點誓詞。
「打卦」在粵語中意為占卜,廖偉棠在詩中寫道:「我們望天打卦,像六十年前從海港酒店,走出來的青年水手。」在他眼中,這些店家常取名吉祥、興隆、富貴,象徵早年香港人在貧困中對未來的期許;港式茶餐廳在菜單上常見的特殊字「丏(麵)」、「歺(午餐肉)」、「冬OT(凍檸茶)」,則代表這座城市在經濟奇蹟中追求效率、中西合璧的特色。
但面對主權移交,香港曾經的新潮成了古典,並從古典長出對「我城」的認同。廖偉棠認為,許多台灣人過去對香港沒有好印象,認為香港人自傲、頑固,他笑說「這些刻板印象完全沒錯」,尤其在當代時局影響下,堅持使用外來者看不懂的粵語,漸成一種態度:「好吧,我們(香港人)就不與時俱進了。」
「對舊文化的堅持,逆時代而行,成為一種懷舊卻前衛的宣誓,」廖偉棠說,粵語或台語都是。
廖偉棠出身中國廣東省新興縣,母輩講著粵語分支「新興話」,父輩則在四〇年代起赴香港留學和謀生,進而帶回了香港口音、香港用法的粵語,他從小聽著香港傳來的粵語兒歌錄音帶,裡頭有大量在廣東省已消失的「俗話」和純淨感。
其中一曲——〈鞋匠和小神仙〉令廖偉棠印象深刻,它用粵語詞彙改編德國格林童話的同名故事,小神仙即是台灣翻譯中的「小精靈」,敘述一名刻苦工作的鞋匠受到精靈幫忙,善有善報。
廖偉棠高中畢業才離開廣東,在他的童年記憶中,能夠公開傳唱的兒歌都與領袖、主義、愛國相關,「我昨天特地找回這首歌,我已經40年沒聽了,歌詞說天空星光閃爍不定,多麼安靜,多麼清澈明亮,這在我成長的大陸非常少見,它完全沒有意識形態,超越政治,只有純粹的美。」

文人自然對語言敏感,曾經歷中國愛國教育的廖偉棠深刻感受到,目前香港也正被一股「主流價值」席捲,混沌而生猛的文化不再,追求統一、和諧的詞彙取而代之,如同廣東省的粵劇強調字正腔圓,彷彿博物館中的展覽品,和香港粵劇保留粗話和黑色幽默形成強烈對比。
於是廖偉棠持續寫詩,堅持用粵語創作:
「作家有時候是一個招魂師一樣的角色,我給這個字招魂,我不把它拉出來,它就永遠被淹沒了。這樣的話,我們的口語會愈來愈貧乏,因為你只會講,不會寫的時候,你意識不到這個字本身是怎樣來的?」
但詩人畢竟不是政治家,廖偉棠經常在作品中假借他人之口,說出對粵語流逝的擔憂。2020年他以15首編年詩述說香港歷史,並和長期關注社會議題的台灣「再拒劇團」合作推出詩歌劇《說吧,香港》,吸引眾多在台港人到場。
劇末的閉幕詩〈我夢見一個未來的香港人〉,廖偉棠暗示自己老去,粵語已成了不能說的語言,直到一名年輕人對他開口:「爺爺,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這樣稱呼你,這樣,用粵語燒你,用紙花做你的地獄。」
廖偉棠上個月剛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末日練習》中,他又以「外星人學者」作為其中一篇故事主角:這位學者離開香港十數年,再沒說過粵語,也不再對外人提起自己為何移居、對外星文明的濃厚興趣。豈知多年後,一名外星人突然現蹤地球,並用粵語向主角問話:「我估,你心入邊既語言係廣東話?」(我猜,你心裡面的語言是粵語?)
「他(外星人)就用我自從流亡之後,十多年沒使用的母語和我交流。」廖偉棠如此寫道。
這些心情並非杜撰,廖偉棠在台灣同時從事教職,也積極參與文壇活動,曾有一名陌生長者來到講座現場,在滿場書迷下顯得突兀,於是廖偉棠問他對哪部作品感興趣?對方坦言「我不懂文學,但我想聽廣東話」,原來老先生已從台灣移居台灣數十年,長期因失語孤獨。
如同黃耀明對台語共鳴,廖偉棠在《劫後書》詩集的第一冊〈拓孤之地〉中,書寫台灣的白色恐怖和社會運動,對他而言,「詩是一種不會熄滅的沉默,是熊熊燃燒的暴雨,它將愛這個世界愛得更劇烈,無悔」,其作品不只談香港,也包含各個面臨困難的國家,如烏克蘭、緬甸。
《劫後書》第三冊〈母語辭典〉則回顧香港,廖偉棠重新思考語言如何形塑人的自我認同,尤以其中一首〈念〉,深刻解析中文本質,更寄託他對母語、故鄉的掛念:
「兒子問我:紀念的念字 是不是上面一個今天的今,下面一個心? 寫好之後 他說:念字好像 一個人痛苦地捂住自己的心,把臉別到一邊去。」

黃耀明62歲、廖偉棠48歲,那更年輕的香港人又如何思考粵語?香港樂團「絕命青年」主唱Soft提出另一觀點:
「港式英文、網路用語其實更能代表現在的香港。」
Soft和吉他手Soni旅居台灣3年,首張專輯《來一場冒險》便入圍2023年金曲獎「最佳演唱組合」,她們在香港的另一組樂團「雞蛋蒸肉餅(GDJYB)」也在2017年成為第一屆入圍金曲獎的香港樂團,在近年港、台非主流樂壇間互動成績亮眼。
即使Soni身為黃耀明「邊走邊唱」巡演的合作吉他手,但和前輩們不同,Soft和Soni的作品裡粵語僅是輔助,出道12年只有一首〈那天我們〉以全粵語演唱,並且大量使用香港人才能看懂的「口語」,例如:「佢哋一口一口咁蠶食,一次又一次嘅壓抑」(他們一口一口地蠶食,一次又一次的壓抑)。
在另一首敘述和價值觀不同的朋友決裂的歌曲〈我們不要再見了〉中,她們寫道:「因為你真係好on9啊」。on9是粵語髒話「戇鳩」諧音,又可譯為「硬膠」,起因是網路論壇禁止網友使用穢語,年輕人便用同音字「硬膠」代替,意指愚笨、難以溝通的人類。
香港粵語分為兩大系統:口語白話文、書面語,前者通常用在網路或港人間的快速溝通,將口語直譯成中文,書面語則是書寫正式文件、文學作品時專用。Soft認為,白話文更貼近自己的生活與音樂,像年輕人聊天時所用的「港式英文」也較少注重文法,更在乎效率,例如「人山人海」直譯成「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最後反倒影響其他華人,甚至成為世界通用詞。
乍聽不像香港歌,又要精準傳達香港故事,她們將心思藏在各個細節中,其專輯的歌名排列如下:「致留下的你、給遠走的你、等待、天始終會亮的」,壓軸曲目則叫做〈來一場冒險〉。
兩人並未名言其意義,只是淡淡地說,聽眾自然會有主觀感受,創作者不需每個字都解釋得那麼明白。
團體雖叫「絕命青年」,她們卻更傾向以幽默面對生活,在〈等待〉這首歌中,二人組把台灣電梯常播放的台語警示「六樓到了(la̍k-lâu kàu -ah)」和「電梯落樓(tiān-thui lo̍h lâu)」融入旋律。

Soft和Soni在台灣的住處,是在旅館裡上租屋網搜尋而來,她們向房東說了自己的故事、職業,當她們首次在台演出時,房東甚至和家人到場支持,這正是黃耀明心中最美的畫面。
今年4月18日,黃耀明和作詞人周耀輝久違在香港舉辦公開活動,雖然僅是簽名會,但仍吸引眾多樂迷到場,其中不乏中國歌迷,「那天我沒有唱歌,我就是簽名,起碼有7、8個吧,他們不是住在香港的大陸人,他們是從北京、上海、南京飛過來想見我一面。」
而在歐洲巡迴期間,黃耀明也常收到中國留學生寄信致意,「我必須誠實地說,收到這些粉絲寫信我都特別感動,因為他們要走過千山萬水才可以聽到我的歌。」黃耀明相信,堅持歌唱有其社會意義。
在音樂工作之外,黃耀明曾擔任專門資助獨立創作者的香港「文藝復興基金會」首任理事長,也和多名文化人成立公開爭取香港同志平權的倡議組織「大愛同盟」,多次來台參加同志遊行。對他而言,世界充滿壓抑與禁忌,「有些人就是想鎖住我們,不希望我們快樂,所以我們要透過唱歌得到自由,得到力量。」
於是,黃耀明總對世界各地的香港人說,不要怕大家聽不懂粵語:
「下次來看我表演的時候,你要帶一個當地朋友來看我,你們不要自己來,你們要帶台灣的朋友來看我。」
- 時間:6/27(四)19:30 - 21:10
- 講者:廖偉棠(詩人)
- 與談:許詩愷(《報導者》記者)
- 主持:李雪莉(《報導者》營運長兼總主筆)
- 地點:報導者第二基地(台北市中山區天祥路32號1樓)
- 報名詳情:https://www.accupass.com/go/never-forget-hk
- 時間:6/28(五)19:00 - 21:40
- 講者:黃綺琳(電影導演)
- 主持:陳怡靜(《報導者》特約主編)
- 地點:報導者第二基地(台北市中山區天祥路32號1樓)
- 報名詳情:https://www.accupass.com/go/never-forget-hk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