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六專欄【電影不欣賞】

從台北飛倫敦,下飛機直奔飯店放行李換衣服,再搭車趕往首映會,戲已開演,黑暗的影廳中,身旁的外國朋友對他說了一句話:「Oliver, it's just beginning.」Oliver Chen陳俊榮便放心下來,才剛開演,沒錯過太多,不枉費他飛14個小時專程來到倫敦。一個半小時後,電影結束,蕩氣迴腸,精彩無比,陳俊榮迫不急待要引進這部片,去找賣家的時候,覺得奇怪,為什麼其他台灣片商都沒上前競爭,顯得興趣缺缺呢?
回到台灣,在記者的提醒下,陳俊榮驚覺買錯了,《與狼共舞》(Dances with Wolves)的片長將近3小時,不是他原先以為的片長2小時。陳俊榮恍然大悟為什麼別人不敢買,西部片一向被台灣片商視為票房毒藥,更何況長達3小時,買了簡直找死,當時流傳一句話:「買騎馬的片子,小心跌到馬下。」不久奧斯卡金像獎入圍名單出爐,《與狼共舞》入圍12項,最後得到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攝影等7項大獎。原本被看衰的「騎馬片」,1991年在台灣上映的票房近2億元。
陳俊榮於1954年生於台中東勢,因母親在戲院經營小賣店,從小就與電影結下緣分。曾當過國小導師,經營過書局、數學補習班,1983年協助經營家族於東勢、豐原一代的戲院,因不滿於當時的經營模式,於1985年開始跑國外影展買片,1987年成立春暉電影公司,因買片眼光精準而建立起外片發行口碑;1992年擔任美商華納台北分公司總經理,1995年成立Sun Movie春暉電影台,亦投資拍攝國片。
在事業高峰期,陳俊榮除了同時管理華納和春暉兩家公司外,旗下還經營總統、梅花、頂好、新世界及絕色等戲院,並參與信義計畫區影城(今信義威秀)的規畫與建立,而春暉發展在當時可說是本土最大的獨立片商之一。其後因經營事務龐雜引發財務問題,春暉電影台停播,而春暉亦於2003年解散,僅留一小部分的發行業務。
即使電影事業經過大起大落,陳俊榮仍熱愛電影,並持續走在電影發行的路上;後曾任絕色影城總經理、兩任台北市影片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高雄市影片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目前為春暉映像總顧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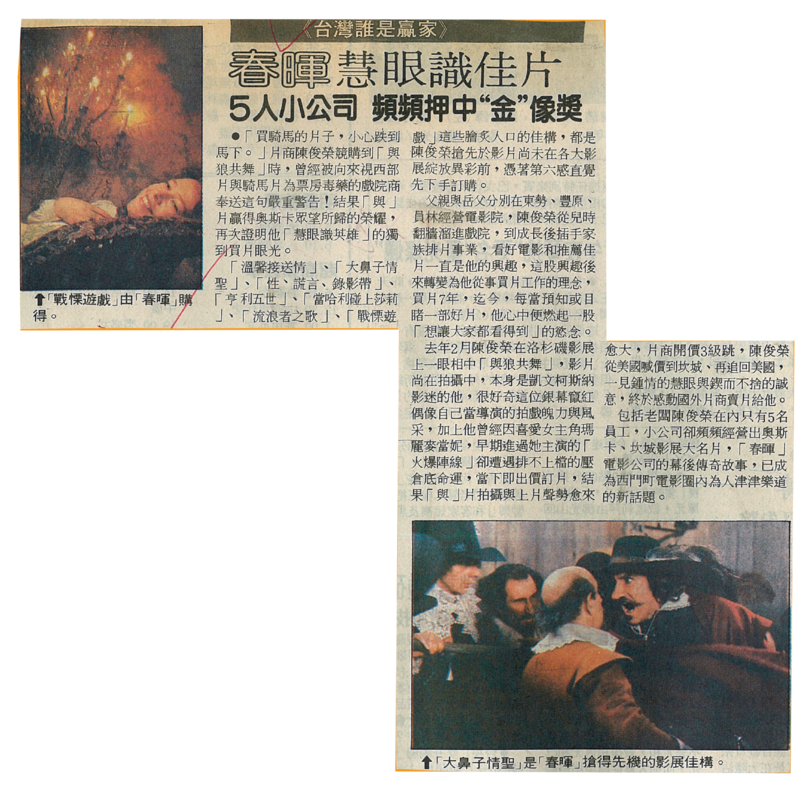
所有人都在問,買下《與狼共舞》的春暉影業是什麼公司?之前怎麼都沒聽過?Oliver Chen是誰?報導一篇篇出來,這家公司成立於1987年,一開始只有陳俊榮夫妻兩個員工。1989年春暉先是買了《性・謊言・錄影帶》(Sex, Lies, and Videotape)這部冷門片,摘下坎城影展金棕櫚大獎;接著又買下《當哈利碰上莎莉》(When Harry Met Sally...)。1990年買下《與狼共舞》讓春暉聲名大噪,後來又引進《溫馨接送情》(Driving Miss Daisy)、《戰慄遊戲》(Misery)等片,春暉這間迷你小公司,創下連續3年包辦奧斯卡最佳影片及最佳外語片的紀錄,以及三度事先猜中坎城影展金棕櫚大獎。陳俊榮買片的眼光精準,次次都讓他選對,用很小的籌碼換取莫大的報酬,有「外片小巨人」的稱號。雖然陳俊榮笑說自己是運氣好,但那些年頻頻猜中得獎片的勢頭,讓春暉這家獨立片商,幾乎可和美商八大公司平起平坐。1992年,美商華納台北分公司延攬陳俊榮擔任總經理,陳俊榮同時管理華納和春暉兩家公司,1993年的奧斯卡,春暉、華納包辦入圍的14部劇情片,佔了半數以上,風光無限。
今年68歲的陳俊榮回憶起30年前的往事,「『It's just“beginning”』除了剛剛開始,還有好戲正要上場的意思,我會錯意了。」盲打誤撞的結果,讓春暉從兩個人的小公司,擴張到300多人的企業集團,春暉除了代理外片、發行錄影帶,1995年在有線電視頻道開設Sun Movie(春暉電影台),1996年取得《ELLE》雜誌中文版經營權、代理《首映》(Premiere),並一度參與投資信義區華納威秀影城,1999年西門町絕色影城開幕,舉辦多屆絕色影展,春暉旗下在台北還有總統、梅花、頂好戲院。春暉的多角化經營,2000年還延伸到劇團,成立由郎祖筠擔任總監的春禾劇團。

說起這些「春暉旋風」,旁人會以為這是深謀遠慮、多角化經營的常規。陳俊榮的回答卻出人意表,這一大串事業不是嚴密的規劃,而是條連鎖反應,因為A而生出B,因為B而催生出C,因為C而有了D⋯⋯,稍不注意就從小樹苗長成枝葉繁茂的大樹。
1995年開播的春暉電影台,是資深影癡的共同美好回憶,在HBO的好萊塢大片外,提供給觀眾更多元的歐洲片、藝術片選擇。陳俊榮說:
「一開始根本沒想設立春暉電影台,要耗費的人力物力財力實在太大,做一個電視台要上億的資金,節目不能中斷,要準備6、700個小時以上的影片,我們畢竟不是HBO,要自己去談廣告、系統代理。」
成立春暉電影台有兩個原因,一是因為春暉引進的大部分是藝術片,「這類的電影必須要耐心看前面10分鐘以上才會進入狀況,產生喜愛」,陳俊榮希望藉由電視台的設立,培養愛看藝術片的觀眾,他認為一旦觀眾群建立起來,其中想先睹為快的人,就會走進戲院看電影。另一個原因,是因為春暉自製的一套戲劇《台北愛情故事》(1994年開拍、1996年播出)找不到地方播。春暉找來曹瑞原、易智言、蔡康永等6位導演,拍了30集。戲劇拍好,陳俊榮找有線電視台兜售,「他們的購買經費有限,最高20萬,我花5,000萬拍的劇,這樣根本血本無歸,只好成立自己的電視台來播。」

那為什麼想拍《台北愛情故事》?是為了向當時即將斷層的國片人才拋下一根救命浮木。陳俊榮答:「很多朋友告訴我,台灣導演快生存不下去了,他們要轉行。我們就去提供機會,找當時最好的演員,讓6個年輕導演發揮,拍最好看的電視劇。當時還為了爭一口氣,《東京愛情故事》很紅,為什麼沒有『台北愛情故事』呢?」
九○年代隨著西片拷貝數量以及映演廳數一再放寬,國片節節敗退,陷入低谷,一路長黑,直到2008年《海角七號》賣座才起死回生。1986年新聞局先是取消以往的外片配額制,九○年代初期,西片拷貝數量從8個放寬到12個,1995年已放寬到28個,到了1997年又放寬至50支拷貝、18家戲院映演,且一家戲院可以3廳聯映同一支影片。50支拷貝可讓一部好萊塢強片幾乎佔據每家戲院,多廳的影城還可以一次安排3廳,嚴重擠壓到國片生存的空間。
九○年代的全面開放,除了美方透過中美貿易談判、301條款不斷施加壓力,台灣也要為2000年加入WTO做準備。WTO談判時台灣的電影業被列為「服務業」,而不像韓國雖然也加入WTO,但電影採「文化免議」原則,可依照自己國家的文化發展適度保護,無須全面開放。台灣加入WTO後,2002年新聞局已完全取消西片拷貝以及映演戲院、廳數的限制,門戶洞開。
陳俊榮以及絕大部分的片商,在當時都贊成開放西片拷貝,他說:「這是時代的潮流,拷貝開放是必要的,要不然很多新的影城沒有電影可以播。可是在開放當中,要怎樣控制這個市場,當國片被欺負到這種程度,政府就要站出來,電影院要依一定比例演國片。但是滿可惜,在WTO談判就把映演比例拿掉,反觀其他國家,韓國電影能和好萊塢抗衡,就因為映演比例沒有拿掉。要問政府,開放的時候,保護台灣電影的心有沒有存在?」
對Oliver Chen這位美商分公司總經理而言,好萊塢的商業價值不是絕對。九○年代華納曾發行一部影片《閃靈殺手》(Natural Born Killers),送審前陳俊榮先看了片子,發覺劇情一直殺殺殺,共殺了51人。「我覺得這部片沒什麼意義,只是一直殺人,有害善良風俗,我直接跑到新聞局,說你們能把它禁演嗎?當時還有禁演制度,結果新聞局給它限制級,還是讓它演。我通風報信總公司當然不知道呀,你說我為什麼要這麼做?這是我愛護台灣的心!」
身在美商華納,陳俊榮心繫國片:
「藉著我在華納期間,我要讓台灣的電影更好,可以成長,這是我真正想要做的。」
陳俊榮說服美國老闆,在台灣成立「華納亞洲」(Warner Asia),投資華語片,也協助台灣的製片、導演,在兩岸三地拍片。華納亞洲發行楊德昌《獨立時代》(1994)到國際,入圍坎城影展正式競賽,走紅地毯,辦盛大酒會。還有王獻篪《阿爸的情人》(1995),該片投資四千多萬,工作流程比照好萊塢規格,拍攝現場有餐車,請來大廚。以及在宜蘭首映,請來林義雄致詞,白色恐怖題材的《超級大國民》(1994),也由華納亞洲發行。
「成績並不好,這3部戲的票房都沒有超過一千萬。《與狼共舞》拍美國原住民題材那麼成功,我找李道明拍台灣原住民題材,很可惜前三部不賺錢,華納不願意繼續投入。」陳俊榮說,「可惜我沒有抓準,如果當時再找一些有商業片潛質的導演,也許華納亞洲還會繼續到現在。」前人種樹,後人乘涼,華納亞洲雖然功敗垂成,但影響到後來哥倫比亞投資發行李安的《臥虎藏龍》,依循此模式,獲得巨大的成功。
與華納亞洲雙軌並行拉抬國片的,是春暉影業在1996年成立「國片部」,投資、發行華語片。春暉出資5,000萬拍攝《台北愛情故事》,出資4,000萬拍了兩季《作家身影》紀錄片,第一季拍攝魯迅、沈從文、張愛玲等12位五四時期的作家,第二季拍攝台灣本地的楊逵、呂赫若、鄭清文13三位作家。這是有拍完的,還有更多因故無法完成,陳俊榮要兼管華納亞洲與春暉這個龐大的事業體,分身乏術,常是投了錢卻無法盯著執行進度,「我常笑自己叫『拍一半』,太多例子了,用一大堆錢拍了一半,沒有完成。例如我特別飛到美國找白先勇,拿到《金大班的最後一夜》、《一把青》的授權,想拍成電視劇,結果還沒拍就停滯了。」陳俊榮沒有明說停滯原因,1999年的新聞記載,九二一大地震,陳俊榮老家在東勢、豐原一帶,親人在地震中逝世,投資電視劇暫緩拍攝。

在外商公司工作,陳俊榮太清楚九○年代電影產業的決勝點在影城。1997年位於信義計畫區的華納威秀影城盛大開幕,從此改變台灣的觀影習慣、引領連鎖影城風潮。許雲凱《華納威秀影城生產過程之政治經濟分析》指出:「多廳戲院從八○年代興起、大盛,進入九○年代,則紛紛與餐飲、電玩等娛樂業結合,改稱影城。」
陳俊榮在華納任職期間,是信義華納影城幕後的重要推手。「在台灣要把電影做好,有個目標一定要做:把影城建立起來。如果有一個自己可掌握的影城,發行商對自家的影片就更容易調度。」影城的種子最早在陳俊榮心中滋長,是發行《與狼共舞》,突然成為奧斯卡大熱門,戲院都來爭取,「第一次接觸到戲院跟戲院之間的鬥爭。」有時候是戲院不理不睬,看不上你所代理的影片,陳俊榮形容發行商像乞丐一樣,「一天到晚要拜託人幫我排片,明明是很好的片子,但要一直拜託拜託拜託,拜託到有一天,就覺得何必過這種日子呢?乾脆把春暉結束掉好了。」
陳俊榮坦言,一開始接下華納的職位,是想要結束春暉。「為什麼華納要我去當總經理?這是我建議的,本來是華納要買春暉,價錢沒談攏,我說我先來當總經理,邊走邊談。我背了一個擔子,春暉300多名員工要去哪裡?我希望把華納作大,春暉作小,春暉的人全部去華納上班。這是我錯誤的想法,沒認清美國人的做事方式,華納各個部門之間互相制衡,我想把台灣的幾個部門整合成一個部門,讓春暉的員工可以去上班,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九○年代不只西片拷貝大幅開放,美商八大等外資也積極地想在台灣投資大型影城。陳俊榮經常陪華納的老闆到各國考察影城,也在台灣考察可能的影城用地。1996年,經濟部通過美商華納公司的投資案,華納準備投資40多億台幣在台灣蓋影城,原先相中的是黑松汽水在復興北路的舊廠用地(今微風百貨)。1997年《經濟日報》報導,信義計畫區影城股東結構生變,「原先在台主導的春暉影業可能退出」,年底華納威秀影城開幕,由美商華納以及澳商威秀兩大外資合作,春暉影業確定退出。
許雲凱《華納威秀影城生產過程之政治經濟分析》提到,華納威秀影城原本分成兩個影城:「嘉年華信義影城」、「華納影城」。嘉年華影城由香港嘉禾與澳商威秀合資,華納影城由春暉影業、三僑實業、美商華納合資。最後的結果是嘉禾、春暉、三僑(後來經營微風百貨,有微風影城)都退出,由兩間外資華納、威秀攜手合作,在信義計畫區的A16、A17的兩棟建築間搭上天橋,合為一間華納威秀影城。
影城也是「做一半」,陳俊榮說:「華納威秀那邊是整個完成,包括冷氣都裝好了,我們不能經營。當時我為了錢,要把它賣掉,賺100萬美金。錢早上賺來,下午就沒有了,100萬美金要去補別的洞。本來華納要給我5%的乾股,我說不要,退就退了,現在想起來真是笨哪!」
華納影城,原本陳俊榮的規劃二樓是戲院,一樓是有450個座位的好萊塢星球餐廳,投了上百萬美金去買經營權利,還請Rockwell公司設計,卻所託非人,遇到中間的賣家破產,權利收回,竹籃子打水一場空。開星球餐廳的動機,和當初拍攝《台北愛情故事》的那股「不認輸」的情緒雷同。長期接待外國影星來台的Oliver Chen不服,台灣的票房市場明明在全世界排前十大,但大牌明星飛東京、香港宣傳,總是略過鄰近的台灣。陳俊榮說:「布魯斯威利斯、席維斯史特龍這些大咖每次都不來,我想說他們都是好萊塢星球餐廳的股東,我如果開在台北,他們非來不可,按規矩,開工破土來一次,開幕剪綵還要再來一次。」
陳俊榮對於大直影城的規劃,是20個廳加上一廳做Imax,為此他還特別跑到紐約考察Imax設備。當時正要跨入千禧年,21廳是21世紀的概念。「樓上是影城,一樓是商場百貨,地下室做劇場空間,比現在的美麗華還大,」陳俊榮說自己是劇場迷,對劇場很有想法,成立春禾劇團正是為此作準備,「我還計畫舞台劇可以透過衛星傳送在春暉的其他影城同步播出,觀眾只要買張電影票,就可以在電影院看舞台劇。總之我東想西想,想很多。」
陳俊榮說:「當時春暉台北有絕色、總統、頂好、梅花(戲院),還是不夠。要的話就要全省,威秀、國賓、秀泰現在各縣市都有,走的就是當年我們想走的路。當時想法太快、想做的事情太多,根本無法一個一個完成。原本預計台北有大直影城,台中有影城(現在的老虎城威秀附近),高雄也看中一塊很大的地,還計畫到成都、北京、瀋陽蓋影城。」
勾勒出完美圖景的大直影城,同樣無法脫離「做一半」的宿命,陳俊榮說:「大直影城我們動工挖土,也挖了地下室,挖了就停止了,也是做一半,很慶幸後來美麗華幫我把心願完成了。」
2001年夏天動工,新聞報導說明夏完成,到了2002年夏天,當然沒看到大直影城的蹤跡。2002年9月,陳俊榮將原來岳父經營的豐原總督影城重新整修開幕,要把台北經驗帶回家鄉。幾年後陳俊榮在電資館的演講回顧2002年的9月,他曾與死亡擦肩而過,過多的「一半」讓春暉的財務陷入黑洞,他站在歌林大樓的8樓窗戶旁,看著下面的巷子,想著跳下去就解脫了,他說:「要讓一個人垮,就讓他去做電影,電影是我最愛的行業,會讓我忘了自己是誰,只是去想自己可以去做很多事情。」
將陳俊榮的影城夢,置放在九○年代世紀末的時空環境,便可理解,這並非痴人說夢,也非不自量力的螳臂擋車。西片拷貝全面放寬,好萊塢大片大舉佔據各戲院,許雲凱的論文指出,美商八大掌握賣座商品,戲院為了利潤,院線盡歸外人之手,美商八大進一步掌握排片權、上片檔期,握有強勢影片又掌控龐大通路,逐漸長成電影巨獸。
美商等外資也投入巨資蓋影城,軟體硬體都讓跨國大財團壟斷,在全球化貿易的氛圍中,以及政府的放任無做為之下,本土電影商必須自行殺出一條血路。原本的電影重鎮西門町,由中影經營的中國戲院在2001年結束,新世界戲院在2002年停止營業,能播放國片以及藝術片的戲院只剩下真善美戲院,以及春暉旗下的總統戲院、絕色影城(1999年開幕,2003年停業,由他人接手)苦苦撐持。
資本市場的殘酷無所不在,陳俊榮要對抗的還有有線電視第四台的亂象,九○年代台灣有線電視興起,資本家以及地方勢力等都要來競逐這塊大餅。春暉電影台想找另一條出路,打算與太平洋衛視合作,轉型成DTH收費模式(direct to home),無需再透過第四台系統業者,而由衛星訊號直接傳送到家。這個想法並非不對,只是來得太早,如今的串流影音平台Netflix的成功,顯示這個方法可行得通。但在當年的時空,春暉與太平洋衛視合作,等於與第四台系統業者為敵,從64台被貶到93台,當年頻寬不大,90幾台之後被稱作「雪花台」,觀眾完全收不到,因此拉不到廣告。與太平洋衛視合作未果,想要再回到64台,陳俊榮投入大量金錢做了很多努力,仍被現實的資本市場吞噬,2001年10月1日,春暉電影台因不堪虧損而停播。
2022的這個夏天,九○年代的電影《少年吔,安啦》重新修復上映,影片中的小混混逃亡到台北,住在小旅館裡,打開電視,第四台正在播盧貝松(Luc Besson)的電影《霹靂煞》(Nikita),影癡們會心一笑,那還能有誰,是大家的共同記憶──春暉電影台。熬夜守候晚間11點過後的「影癡俱樂部」,就能等到沉靜蔚藍如盧貝松《碧海藍天》(Le Grand Bleu),以及英國導演賈曼(Derek Jarman)沒有一句台詞的奇片《藍》(Blue);或者喧囂奔放如巴爾幹半島庫斯杜力卡的《地下社會》(Podzemlje)、《流浪者之歌》(Time of the Gypsies)。為了讓1995年創立的春暉電影台能繼續下去,1996年陳俊榮就買下法國《ELLE》雜誌台灣代理權,成立春暉樺榭出版公司。陳俊榮說:「《ELLE》在當時是台灣傳閱率最高的雜誌,春暉代理的電影,春暉電影台播映的電影,都不是那種講究聲光刺激效果的大眾電影,要靜下心來才懂得欣賞,所以我買下這個雜誌來教育觀眾。」
春暉電影台成立之初發下豪語,以HBO為主要的假想敵,事實上兩者的立基點完全不同,系統業者將跨國企業HBO捧在手心,給予各種優惠條件,本土的春暉電影台要自力更生,和標榜無廣告的HBO不同,為了維持春暉電影台的運作,廣告營收是必要的。然而插入廣告,對不太能被打斷觀影情緒的藝術片是致命傷,陳俊榮說:「春暉電影台要做廣告,一直被罵,我只好說,廣告時間就讓大家去上廁所。」為了能與之抗衡,維持吸睛的新片量,陳俊榮跨出他原本熟悉的藝術片領域,買來許多好萊塢商業大片,由席維斯史特龍、布魯斯威利、妮可基嫚等巨星領銜主演,「錄影帶市場、春暉電影台都需要大片來撐,不能都是藝術電影。商業大片的價格一部要1、200萬美金起跳,再怎麼宣傳操作,票房也就2,000多萬台幣,成本怎麼拿得回來?」
投資國片、製作電視劇、大型影城計畫、購買商業大片維持春暉電影台的存續,製作3部戲的春禾劇團也賠了2,500萬,一個接一個的黑洞,互相加乘,終將讓陳俊榮的債務變成一個無底洞。2004年《聯合報》報導,春暉的債務曾經高達4億5千萬,陳俊榮變賣家產,從住陽明山開賓士車的大老闆,變成騎機車通勤的租屋族。陳俊榮回憶跌下深淵的過程:
「不能說哪一個計畫是黑洞,而是環環相扣,還包括我們有一顆想參與國片製作的心,那個去得更快⋯⋯」 「很多時候就會覺得市場的變化太大了,第四台的變化也很大,為了要讓春暉電影台活著,要犧牲很多東西⋯⋯」 「很多事情只能怪我自己做出莫名其妙的抉擇,因為我已經辛苦到根本不想再經營下去了!」

例如2000年,帶頭成立全方位網路票務系統,可在春暉e樂網訂票,統一超商取票。並推動全台戲院電腦化,由春暉旗下的總統戲院率先實施。如今在網路預訂電影票已很普遍,當時推行得卻不順利。陳俊榮說:「網路售票因為當時用信用卡的人還不是很多,要游說所有的戲院加入,不太容易。交1,000元加入台北市戲院公會會員,用電話語音訂票,大家還是習慣用這個方式。」
例如2002年,春暉和上海商銀合作共同發行春暉聯名卡,核卡就送電影票,是台灣第一張電影聯名卡,結果卻沒賺到錢,讓陳俊榮跌了一跤,「當時發行得不錯,有發行到3、4萬張。每個卡友一年有8張電影票可看,一張票成本150元,8張1,200元。我預估票卷回收率1成就很不錯了,通常會忘記使用,結果使用率很高,而且卡友選的都是美商的片子,例如《哈利波特》,當時應該要限定只能看春暉的影片,就能自己吸收,不用再付出成本。」
說起這些失敗經驗,陳俊榮找出手機裡的畢業證書照片給我們看,民國111年6月,他取得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財務金融商學博士學位,「當年在這方面失敗,就跑去讀書,想要補強這部分。」
源源不絕的點子,是激發陳俊榮對電影行業的無限想像?還是將他引導往失敗之路?陳俊榮說:
「當你愛一個人的時候,你會用很多點子在他身上,像我很愛我老婆,就會時時想著要怎麼對她好。同樣的,當我愛電影這個產業,就會想到很多點子,一切都是熱情,沒有Passion走不下去,如果沒有Passion,看到那些片子時只會想,沒有幾個人要看,那我引進來做什麼?」
「把人擊垮」的電影之路上,陳俊榮有不少回頭的機會,在1989年,成立春暉的前3年(1987~1989),陳俊榮跑影展買片買得相當開心,但不懂得計算成本,兩年半就把積蓄、房子貸款都賠光。1989年他的戶頭只剩下700多塊台幣,剛好有家錄影帶公司要買春暉代理的影片《第四次大戰》 (The Fourth War),「我拿到訂金,想說給自己最後一次機會,跑最後一次影展,在搭飛機時我甚至好希望飛機掉下來,這樣就有保險理賠兩千萬。我喜歡電影,為什麼會喜歡成讓自己變成這個樣子?」
最後一次影展跑對也賭對了,陳俊榮用很便宜的價錢買到《性・謊言・錄影帶》,中了金棕櫚大獎,好不容易能在西門町日新這種主流戲院上映。上映前卻還有關卡要過,因為片名中有「性」,想要宣傳登廣告處處碰壁,只能作罷;關卡二,上映前一天刮大颱風,陳俊榮的心情七上八下,文藝片碰到颱風天就穩死,他在心裡禱告:「如果神願意的話,請讓颱風轉向。」1989年9月9號,《性・謊言・錄影帶》在台北上映,這一天其他縣市都下雨,但在大台北上空出現雲洞,陽光普照,恍如神蹟。1萬多美金就買到的《性・謊言・錄影帶》,在台北賣出1,500萬的佳績。《性・謊言・錄影帶》是陳俊榮的幸運符,是春暉的轉捩點,從此繼續向前行。
陳俊榮笑著說:「觀眾衝著片名來,想看到『性』。結果觀眾的評語是電影裡頭都沒有性,講的都是謊言,而且是錄影帶的品質。」春暉引進的另一部《當哈利碰上莎莉》,票房與口碑雙收,梅格萊恩飾演的莎莉,在餐廳示範高潮的叫床聲,沒有任何裸露,在當時引起熱烈討論,吸引人進戲院,賣了3,500萬。
春暉影業成立於1987年,正是台灣解嚴那年,1988、89、90年街頭上仍有許多衝撞抗爭,是台灣社會版塊劇烈掀動的時刻。春暉引進的《性・謊言・錄影帶》、《當哈利碰上莎莉》顛覆傳統兩性關係,《與狼共舞》所觸及的美國原住民尖銳議題,正符合當下時空台灣社會的脈動。

回溯源頭,1983年,陳俊榮辭掉穩定的小學老師工作,接手家族的電影院,負責排片的工作。「我教書教得很好,校長勸我不要辭職,但我看不下去電影院的經營方式,我覺得電影不是這麼做的,一個人會去激發他的潛力,就是因為忍受不了現況。當戲院播到不好的電影時,觀眾為了洩憤把玻璃打破,把座位刺破,這與戲院何干?電影不好應該去找拍電影的人。我就覺得我應該要從最源頭的材料開始做。」
1985年,陳俊榮開始跑國外影展,一開始帶他的人,是發行《魔鬼終結者》的徐氏電影公司老闆,帶著陳俊榮去坎城。「我的英文原本不太好,所以才會誤會那句『It's just beginning.』。我的英文後來是怎麼練起來的?去華納當總經理,每天早上9點要和美國老闆用英文開會。後來我發現,去國外買片時,英文不好一點都不要緊。因為你是那個要付錢的人,人家就會很耐心聽你講的英文。」陳俊榮跑影展買了第一部影片,請徐氏電影公司幫忙發行,「我又覺得發行不應該是這樣,所以我才自己開公司來發行,春暉一開始就是我跟我太太兩個人。」
和電影緣分匪淺,怎麼走總會再繞回來,或許就因為陳俊榮出生在電影院。母親在東勢的電影院裡經營小賣店,「聽說我就是在小賣店出生。等到我3歲的時候,電影院裡會有布袋戲、脫衣舞,我都負責賣小板凳給大人,有脫衣舞的時候,大人都在最前面,坐在小板凳往上看。」
大學畢業後回鄉當小學老師,還在豐原開了一間書局給太太顧店,書局樓下會播放一些卡通片,消費滿多少錢就可以去樓下看電影,晚上這個空間變成補習班,陳俊榮在這裡教功文數學,「教一些原住民的子女,有時收不到錢,反正像我這種人太浪漫了。我一直很關心原住民,所以才會買《與狼共舞》,到現在我都還很喜歡摸稻禾,感受大自然。我的原住民朋友很多,他們下來我就請他們看電影,甚至把電影拿到部落去播。」
電影這條路,陳俊榮還在繼續走,他邀我們去看試片《探戈行不行》,春暉仍在發行電影。曾經大起大落卻也還是細水長流,面對如今的電影市場,陳俊榮樂觀許多,「現在市場比較成熟,當年很多東西都不透明,現在票房透明,投資者願意進來。我接受採訪是希望把經驗傳承下來,春暉以往單打獨鬥,自己的力量有限,承受不了幾次失敗,而且一定會有失敗。台灣需要大的製作、發行公司,應該有好幾家公司合作來經營,不要像以前春暉從頭到尾都是自己來。一定要有一些同好,屏除個人的意見,在電影的路上大家一起走,才能走得長遠。」
1992年陳俊榮接受採訪時說,「常有朋友笑我買片太瘋,勸我不要太率性。大概是看我敢進一些賠錢貨。我大學讀的是化學分析,我分析的結果就是,穩賠不賺,在公司還可以負擔的範圍下,還是要進這些注定賠錢的優秀作品,好滿足國內長期飢渴的影迷。」
我亦是那穩賠不賺的受益者之一,年少時深受撼動的《亂世浮生》、《此情可問天》,都是春暉代理進來,我至今仍能召喚回30年前的那個聲色空間,黑漆的電影院裡,這些光影是如何擊中我、捕獲我,是即使日後看修復版都無法取代的「最初」。1992年《亂世浮生》上映,我在現今已消失的公館大世紀戲院觀賞,上映的那個版本,陳俊榮說,當時新聞局規定,露第三點都要剪掉,於是劇情轉折的關鍵一幕,當「女」美髮師脫掉衣服的那一刻,必須要畫蛇添足加一句字幕「原來她是男的」,要不然觀眾無法意會過來。
※本文亦刊載於《Fa電影欣賞》第191期
電影從一道光束開始,映照出時代與生命的光輝與陰霾。無論光影或暗影,都讓世界與人產生共震與共鳴。然而,一部電影不只是一則文本,電影內外所含括的,除了自我經驗的投射外,更附帶著社會、文化與歷史的記載軌跡;於是,電影其實不該只是被欣賞,要探究電影之中更深刻的意義,就從「不只是欣賞」電影開始。
本專欄與「全國最悠久的電影雜誌」《Fa電影欣賞》合作,由國家影視聽中心獨家授權刊載,文章以觀點、論述、檔案、歷史、展示為經緯,陳述電影文化及電影史多樣性的探討。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