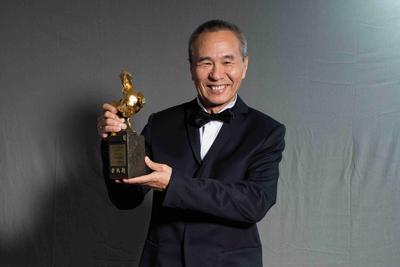週六專欄【電影不欣賞】

1985年,人在美國的賽菊蔻(Eve Kosofsky Sedgwick)女士,出了一本書叫《男人之間》(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書中指出一種homosociality(同性相聚)。看清楚,她說的不是那年代酷兒影評強調的homosexualiy(同性相愛)。她的目的,不止於同性戀的弱勢邊緣。
正好相反。她在書中挑戰的,其實是那些掌握位置的有權者,往往都只是同性之間的「惺惺相惜」。負面結果,最終只讓圈子變得緊密而不透氣,就有人以此暗諷其「腥」。賽菊蔻大概沒想過,這概念,也能用來形容遠在台灣(但她本人根本沒看過)的新電影。
同年,人在台北的楊德昌先生,拍了一部片叫《青梅竹馬》,片中展現一種criticism(尖銳批判)。看清楚,他拍的不是那年代文青導演耽溺的nostalgia(鄉愁懷念)。他想說的,不止於老異男好談當年勇。
正好相反。他在片中示範的,其實是那些掌握位置的有權者,時時都該有同輩之間的「互相漏氣」。正面結果,最終能讓圈子變得開放而能前進,卻有人聽到諍言就「氣」。楊德昌大概沒想過,這觀念,也能用來批判時至今日(但他本人根本沒活過)的新社會。
1980年代的前輩們,教會我們多少珍貴的道理,又留下哪些未解的問題?
《青梅竹馬》中的1980年代,來了幾個正要上位的新老闆,每個人都戴著類似的眼鏡。對於不同於西裝男士的女性,他們不願接受一個超出他們既存框架的「特別助理」,只想要你當他們的「祕書」,看看下面的風景。1980年代的現實台灣,倒也來了幾個正要革命的新導演。他們雖然跟片中新老闆長得一個樣,美學卻各異其趣。我其實很享受這群奇葩帶給台灣電影的風景。
美國來的賽女士(人家不姓賽!),精準地以homosociality捕捉臭味相投的男孩俱樂部。她指出這社會硬是會把「男子義氣」與「男同妖氣」的界線切得分明(相比於女性,從閨蜜到愛人,更具有光譜般的連續性)。這些臭雞雞組成的親近關係,就會特別展現出「恐同」甚至「厭女」的風氣。男人間甚至因此特別喜歡以彼此競爭追求其他女性,讓男人之間的「內情」能有「合理目標」轉移。
這概念後來會紅,一方面是習慣意淫異男們的酷兒,得以藉此重新摸索「男子義氣」內在具有的「可掰彎性」,試圖重新搭起光譜的連續性;二方面則更常被用以說明男人間如何因為這種「同類相聚」的「天性」,如公狗般建構出屬於自己人「神聖不可侵犯」的尊嚴和領地,讓其他「非我族人」不得接近。
台男狂八〇的新電影,就常是這種男人們彼此相聚,獻身甚至想霸道占據的「處女地」。有些人的個性與條件讓他們願意屈居小弟,享受在侯與楊下面幫忙吹捧的風景。直挺挺的侯與楊,早先站得也近:去美國回來的楊德昌,算是在《青梅竹馬》裡找了沒去美國的侯孝賢演他自己。不過,對台灣電影而言,應該能說算幸運的是,侯與楊根本沒那麼愛這種homosociality。他們固然樂於結夥革命,提攜電影成就路上的後進,但是他們始終更忠於自己的聲音,勇於講出跟同溫社會唱反調的批評。看《青梅竹馬》,我總感覺,對他們來說,那條沒人走過,甚至沒人想過該怎麼走的路,才是我們台灣人、我們電影人更該闖的路。
雖然後來兩人分頭走,看似可惜,但是正也是在「分手」後,兩人才各自交出自己在國際影評中最受吹捧的作品。兩人的「分手」,其實也打破在「新電影」時期的homosociality,後來我們就有了更多homosexuality的聲音,像蔡明亮和李安的作品,女性也更有機會在這領域發出聲音。只是昔日慣於待在下面看風景的小弟們,似乎仍不習慣criticism互相漏氣求進步的真諦,整個文化界仍瀰漫一股nostalgia的風氣。這一點,或許正說明了我們為何到2023年依然在不停緬懷「新電影」與「狂八〇」。
※本文亦刊載於《Fa電影欣賞》第194期
電影從一道光束開始,映照出時代與生命的光輝與陰霾。無論光影或暗影,都讓世界與人產生共震與共鳴。然而,一部電影不只是一則文本,電影內外所含括的,除了自我經驗的投射外,更附帶著社會、文化與歷史的記載軌跡;於是,電影其實不該只是被欣賞,要探究電影之中更深刻的意義,就從「不只是欣賞」電影開始。
本專欄與「全國最悠久的電影雜誌」《Fa電影欣賞》合作,由國家影視聽中心獨家授權刊載,文章以觀點、論述、檔案、歷史、展示為經緯,陳述電影文化及電影史多樣性的探討。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