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事情是這樣的(我發誓我沒有誇張),在福爾摩沙的山上(可說是窮鄉僻壤,這裡的白人少之又少),我們在路邊的一個涼亭停下休息。這涼亭是給像我們一樣的旅人歇腳用的,這裡有用竹管引過來的泉水。我們在此休息了幾分鐘。涼亭中央有一張淺色木頭做的桌子,你可以把手肘放在上面。四周的景緻很遼闊。我們的視線慢慢從遠方的山腰和翠綠的森林移回眼前的涼亭。突然我看到桌子上有字,這吸引了我的目光。那是用硬物刻在桌上的,而且這文字還很熟悉。上面用波蘭文寫著:J・謝斯基,來自澳門,1936年3月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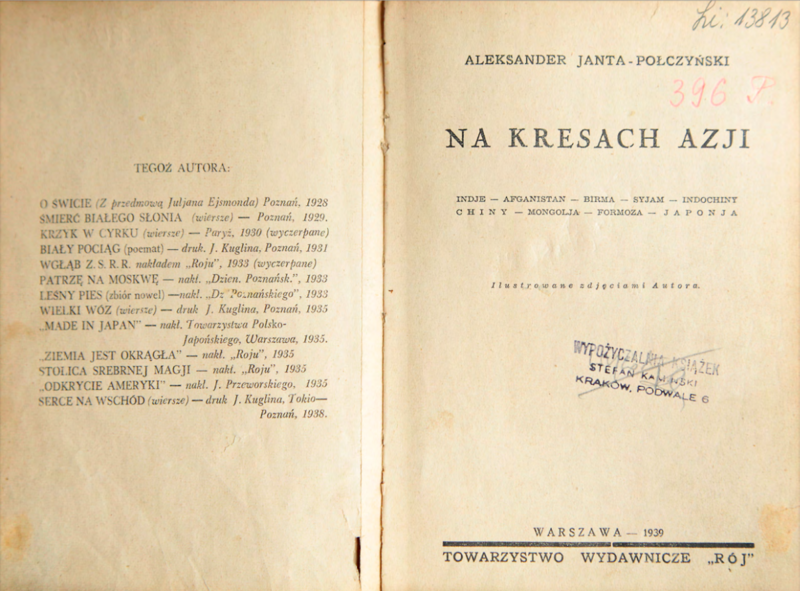
「那裡的氣氛根本一點都不維特。完全相反,那裡明亮、吵鬧、無憂無慮。從喇叭中傳出日本風的爵士,頗為感傷,沒有明顯節奏。那裡也有陪坐的小姐,她們有著天真的自信,口紅畫得很紅,看起來很好笑,但又有某種親切感。(⋯⋯)喝了一點酒的學生喧嘩吵鬧,不過,雖然他們在桌前和打開的窗口玩樂,卻滿節制的。11點後就沒有音樂了,12點遊戲結束,因為有宵禁。從這點來看,台北就像東京。福爾摩沙的異國情調要到別處尋找,到國度的深處。」(頁256)

長居日本的揚塔─普欽斯基可能會在不自覺中把台北和東京比較,他想要看到異國情調,而不是另一個日本的複製品。他在文中說:
「我們突然想到,我們想要遇見一些當地人。『當地人?但是當地人到處都是啊,』嚮導解釋,『你們只要知道,他們有兩個種族就好:廣東人和福建人。』」(頁254)

揚塔─普欽斯基進入的第一座深山是太魯閣。他用大量比喻,生動地描繪太魯閣,和寫台北的筆觸完全不同:
「福爾摩沙最大的特色是有著大理石的太魯閣峽谷。車子在峽谷入口停下,接下來就只有一條狹窄的步道了。在陡峭的峽谷底部,流著湍急的溪流,愈往深處,峽谷愈高聳。我們轉了幾次彎,如果往前看,會看到遠方一片彷彿屏風的岩壁,有著蒼白、翠綠、湛藍或是鉛灰的色彩。在我們頭頂,是一片濃密、多樣的植物,原始森林彷彿一頭毛茸茸的密髮,其中偶爾可見銀色的瀑布。」(頁260)
「我們瀏覽著這些面孔,有些面孔真的很美麗,但是大部分的面孔都是壞掉的。這些人由下往上看,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彎著腰(他們的工作是挑夫),但另一方面彷彿是因為恐懼,或是過於誇張的謙卑。後來我們比較了解他們後,就知道這舉止來自於教育。誰是教育他們的人?這一點不言自明。日式的鞠躬也是這樣的,同樣緊繃的身體,同樣把手放在膝上,然後用正確但膽怯的聲音囁嚅地說出:『Konni-ci-ua。』這是日文的『你好』。觀察了這裡的原住民幾小時後,我找不到其他的用詞來描述日本人對他們做的事:馴化(tresura)。即使在回答問題的時候,我也無法讓他們脫離『立正』的姿態,因為我不知道怎麼說『稍息』。」(頁261)
當他真的看到了被馴化(或者該說被強制馴化)的「野蠻人」,他又表示:「至少這比為了宗教目的或敵視外人而獵頭來得好。」揚塔─普欽斯基清楚知道日人為了掌控原住民,曾用武力鎮壓原住民部落(他後面有寫到霧社事件,霧社事件在波蘭也有被報導),但他依然為日本人緩頰,安慰讀者或自我安慰,說原住民也有從文明得到好處:
「我們本來要住在太魯閣峽谷斷崖上的巴達岡(Batakan)部落,住在警官駐在所,那是我們這次旅途的終點。不過當我們到那裡後,我們發現那裡有可供旅客住宿的招待所,而且設備一應俱全。不用說,台灣總督府這40年來的治理把這座島嶼整治得很好。到處都可以看到改變和便利,這對原住民來說一定也是很重要、很好的改變。就拿這些吊橋來說吧,它們可以讓原住民節省多少路途啊,以前他們只能走小徑,有時候走一走還會突然偏離主要道路,走到布滿地衣、夾在岩石之間的獸徑上。(⋯⋯)畢竟使用新道路、新橋、新設備還有水力發電的不只是觀光客,和觀光客比起來,山上居民人數更多。」(頁262)
日本人確實在太魯閣做了許多建設,但這些建造的目的並非為了便利原住民的生活,而是為了方便日本統治者監視、管理原住民,後期也是為了吸引觀光客。日本人對原住民的暴行不只是屠殺,也包括改變原住民的生活環境和生活習慣,把他們從山林的主人變成殖民者的奴隸。
原住民怎麼看待這一切入侵、改變他們生活的「文明」?揚塔─普欽斯基沒有對此作出評論,只承認自己也不了解原住民的心情:「接觸到另一個世界,從完全野蠻過渡到目前狀態,親身經歷這一切改變的當地人,他到底感覺到什麼?有什麼想法?不管是我們的攝影機之眼,還是我們自己的眼睛,都無法看透,也無法理解。」(頁263)在拍照的同時,揚塔─普欽斯基也有意識到攝影機可能會讓原住民不安:「這錢不好賺。你得克服多少恐懼,壓抑多少迷信,才能勇敢地直視那玻璃之眼,一動也不動地站著,在此同時,攝影機黑色、閃亮的瞳孔就瞄準你的臉⋯⋯。」

離開太魯閣後,揚塔─普欽斯基和旅伴坐上了火車,來到島嶼西部。他對台灣的火車讚譽有加:
「火車旅程非常舒適、愉快,讓人幾乎不想離開車廂。昨晚我們談到日本人把這島嶼建設得多棒,把這裡治理得多好。我們會談到這個,可能是因為在這長度394公里、寬度最多122公里的島上,鐵路就有811公里,而且以後還會更多。當然,這還沒有把汽車的道路算在裡面。我們可別忘了,福爾摩沙是有多座3,000公尺高山的多山島嶼。」(頁263)
「沒錯,許許多多的小島,在上面甚至可以耕作。它們沒有連到湖底,風來的時候它們會從湖岸的一邊被吹到另外一邊,島上有樹,風吹在樹上,彷彿在吹船帆。太陽出來時,從湖畔高處日式旅館的陽台上,你可以看到湖上有許多像船一樣緩緩漂移的島嶼,那真是一幅美麗的景象。你幾乎會感到遺憾,世界上其他地方看不到類似這樣但更大規模的景象,除了研究者記錄下來的,美洲大陸在幾千年來的漫長漂移。」(頁264)
除了拜訪日月潭的邵族部落,揚塔─普欽斯基也搭台車去了霧社。關於霧社,揚塔─普欽斯基是這麼說的:
「我們來到了被稱為Musia(霧社)的村子。這裡是日本殖民福爾摩沙下,最後一次(1930年)發生和原住民衝突的事件的地方。 這次事件的犧牲者(包括因討伐死亡的)有158名。村子很大,很有秩序,完全是個日本村子。 道路兩旁有一排排淺色的木造房子。在不遠處的山丘上有一座神社,隱蔽在蒼綠松樹的陰影中。種滿櫻花的道路穿過馬鞍形狀的山丘,通往更遠處的山丘。『現在不是開花的時候,』穿著黑色警察制服的官方嚮導近乎遺憾地說。」(頁265)
霧社事件在台灣如此慘烈,死了這麼多原住民(雖然死亡人數至今無法確定,但一定超過158人),而揚塔─普欽斯基竟然只用兩句話輕輕帶過,然後就去寫櫻花了。之後,他寫了小商店:
揚塔─普欽斯基對總督府理蕃政策的陰暗面輕描淡寫。他寫的是他想、他願意看到的原住民,同時也是台灣總督府想要、願意向外國觀光客展示的原住民。
揚塔─普欽斯基的遊記最大的亮點,在最後一段:
「在福爾摩沙的最後一天,最後一夜。明天我們就要坐船回日本了。這島嶼充滿自然之美,當你想念陽光、自然氣息和寧靜,你就會想要回到這裡這美麗的世界一角。就像印度是大英帝國的珍珠,福爾摩沙在日本統治40年後,也可被認為是日本眾多為了武裝、防禦目的而建立的殖民地之中的第一顆珍珠。」(頁273)

〈在福爾摩沙〉是目前我所知道的、篇幅最長的關於日治時代台灣的波蘭文報導,可以告訴我們當時波蘭知識分子怎麼看台灣,又在台灣看到什麼。雖然其中有些獵奇的想像令人不適,但它也讓我們看到當時的波蘭人對台灣有什麼刻板印象,是用什麼樣的眼光在看台灣。那樣的目光有其時代背景,但不用因此就接受這樣的看法,更不必用他們的眼光看自己。面對刻板印象和歧視眼光,我們也要有無畏的、瞪回去的勇氣和自信。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