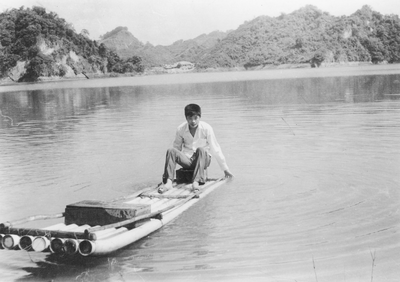閱讀現場

本文為春山出版社總編輯莊瑞琳,和《靈魂與灰燼: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主編之一童偉格,在2022年6月1日的線上對談整理,由春山出版授權刊登。
《靈魂與灰燼: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精選47篇作品、43位作者、總共近90萬字,以截然不同的視角切入白色恐怖歷史的肌理,區分為繫獄作家、青春、地下黨、女人、身體、特務、島等7大主題,將這些受挫、受辱或者心靈扭曲的主體放置一處,也涵蓋加害者與協力者,並注重多元族群包括外省、原住民與離島馬祖、外國人的經驗,使他們共同發聲,像是一個巨大的人性劇場。
本場對談,援引其他外國作家真實的受難人生和寫作經驗,冀使聽者與觀者在這個令多數人直觀驚怖、畏懼、迴避的人性劇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與啟示,找到與這些歷史的聯繫,更創造出能產生新思考的方式。
- 陳 列/無怨 (朗讀者:蕭定睿)
- 葉石濤/一個臺灣老朽作家的五〇年代[節選](朗讀者:李英立)
- 張光直/蕃薯人的故事[節選] (朗讀者:蕭定睿)
- 吳聲潤/二二八之後祖國在哪裡?[節選](朗讀者:李英立)
- 黃素貞/我和老蕭的抗戰和地下黨歲月(朗讀者:林涵柔)
- 唐香燕/心內彈琵琶──回憶蘇慶黎和蘇媽媽蕭不纏(朗讀者:林涵柔)
- 季 季/行走的樹:追懷我與「民主臺灣聯盟」案的時代[節選](朗讀者:林涵柔)
- 蔡德本/蕃薯仔哀歌[節選](朗讀者:陳余寬)
- 李世傑/調查局黑牢三四五天[節選](朗讀者:李英立)
- 唐培禮/撲火飛蛾──一個美國傳教士親歷的臺灣白色恐怖[節選](朗讀者:張心哲)

童偉格(以下簡稱童):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靈魂與灰燼: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的協同主編童偉格。這次的講題是「創造能產生新思考的條件──《靈魂與灰燼:白色恐怖散文選》的內擴與外延」,首先對應的是有聲書這個新載體的發行。希望這個載體,能以相對親近、輕量的方式,將這些關於白色恐怖的體驗送到大家的面前。另外是,《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最後的成果總共5卷、47個篇章,加起來90萬字,裡面有相當多的獨語、傾談,當然也存在著相當多的對話。我個人的盼望是有朝一日,這些真的都可以成為在場各位的集體記憶、或感知的一部分,也希望這些記憶跟感知,在更遠的未來,真的能夠創造出新的思考條件。
因為我個人的關注是在文學創作,所以所謂內擴跟外延,首先對我而言,指向了文學創作的可能性。於是接下來的說明,其實是給我自己的個人備忘錄。之所以會連到普利摩.李維的書寫,是因為在編選散文選的過程中,李維確實是我常常想起的作者。
李維是一位義大利的文學創作者,或者大家其實更熟悉他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倖存者。他大概在1944年2月被送往了奧斯維辛,1945年1月因為奧斯維辛解放,所以留在現場的他也就一併獲得了自由,展開了非常漫長的歸鄉道路。李維實際上在奧斯維辛的時間算起來不到一年,但在集中營的時間感,跟我們真實生活中的時間感是不一樣的,因為這不到一年的時間,事實上是密度相當高的時段。在集中營惡劣的環境裡,人能夠活著看過幾次季節的轉換,其實是相當不容易的。李維的經驗對我們而言,成為相當重要的見證,因為他相對全景地告訴我們,在奧斯維辛那個生活條件非常惡劣的地方,他所經歷的種種炎熱、酷寒或是饑餓等,所有這些經驗的細節。
李維成為我在想《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編選邏輯中一個重要參照,首先是時間性的問題。走出了奧斯維辛集中營以後,在1946年,他就寫出第一部奧斯維辛見證錄《如果這是一個人》。之後的時間,好像都是重寫這個見證錄的時間。如此一直到1986年,也就是他過世前一年,他出版了在省思上面具有總結意義的《滅頂與生還》。從1946年算起,到1986年,是漫長的40年光陰,40年的寫作。某個意義上李維對我說明了一件事:也許確實在人的生命中,會有一種東西極度逼近永恆,那就是像生命限度那麼長的始終不渝,類似像這樣的意志。也因為40年是李維生命的三分之二,所以他其實是將自己的奧斯維辛省思,更為永久地刻印進關於自己生命的描述裡了。我的好奇或困惑,其實是一個事關倫理的問題:
在什麼樣的思考下,一個人會基於倫理自願去承擔重複的見證?以及重複的見證,它所對應的基本困難到底是什麼?
如果從結局說起,李維帶給我們最大的困惑,應該是他最後選擇自殺。在1987年4月11日,就是1986年《滅頂與生還》出版後不久,李維就從他出生的房子──他除了去奧斯維辛以外,很少離開的房子──的樓梯井跳下來自殺了。他的自殺,形成了對現當代文學經驗而言相當顯著的一個事件,因為我們可以粗淺地說:他的自殺,多少證明了這樣的文學寫作,或文學寫作自身,所具有的療癒功能事實上是有限的。這樣的寫作救不了這個作者。有人會說,40年後奧斯維辛還是追捕到了普利摩.李維。但有些人對這樣的說法感到憤怒,因為40年已經是一段逼近生命限度的時間了,在這樣艱難的寫作過程當中,事實上在每一次的書寫現場,李維已經生還過無數次了,而且確實也已倖存過了很長一段時間,而自殺是人的自由選擇。
李維的寫作,包括最後的《滅頂與生還》,都在嘗試告訴我們說,其實帶給他痛苦的不是過去的奧斯維辛經驗,或者不僅是奧斯維辛經驗而已。帶給他痛苦的是在那之後,非常善於遺忘的世界。反覆揭開自己的傷痕需要意志力,這個意志力不是來自於受創者本人對於傷痕本身的自戀或是愛,相反的,這其實是普利摩.李維自我選擇當中倫理上的承擔。比發生過的奧斯維辛經驗更令他痛苦的事情是,在相當多年以後,不管他如何表述、如何描寫,人們還是會去質疑「這樣的事真的發生過嗎?」所以使人痛苦的不是受難的事實,而是這樣的事實,非常輕易就被遺忘了。
這是我讀李維時所感覺到的矛盾,以及恆久刻印在他的寫作與肉身上的痛苦。讀李維時,你會看到一種始終堅持的、相當純真的憤怒。這種憤怒如果延續了40年沒有消減,我個人認為這已經是一種記憶的形式了。這種憤怒如果沒有消減,而且每次都在表達當中重複琢磨、一再深思的話,某個意義上,好像是在告訴我們一個相當困難的悖論,意思是長久的憤怒、長久地憎恨著什麼,也可以換得永恆的東西。這是愛的反面,但也許,也是另一個形式對於同類之人的愛。因為存在著「我所記住的,願你也能夠深刻記住」這樣的群體連帶感,於是才會對人的輕易遺忘,有一個始終純真的憤怒,包括對於所有先於他選擇自殺的人的憤怒。這不代表他不知道受難是什麼,正好相反,他知道受難經驗是什麼,且知道背負著這個死難經驗而活有多不合道義、多辛苦。正是因為這樣,他無法輕易地放下所有先他一步選擇自殺的人。
著名的例子,是李維在散文集《他人的行當》(L'altrui mestiere)當中,對於保羅.策蘭(Paul Celan)的評語。李維直接指出保羅.策蘭的詩在他讀來接近謊言,就是「獨自赴死之人的語言」。意思是其中的晦暗、蕭瑟,一切相當負面的修辭,讓李維讀來格外痛苦。前面說過,不是因為不理解,正好相反,因為他理解,於是這個獨自赴死之人的語言,才成為他一生想要拒絕的語言。這也許是人類史上,對保羅.策蘭的詩最嚴厲的評語。
另外,如果大家讀過《滅頂與生還》,一定會記得李維花了整個章節,在為一位朋友做自殺分析,這位朋友是哲學家讓.埃默里(Jean Améry)。哲學家在《獨自邁向生命的盡頭》(Hand an sich legen)裡,主張自殺是人通向自由的合法道路,也在《罪與罰的彼岸》(Jenseits von Schuld und Sühne)裡,將集中營視為人去觸及「死去」(Sterbe)經驗的空間。他嘗試描述人傾向於死亡的意志。這讓李維感到同樣的憤怒。李維認為埃默里的深思在某個意義上也接近謊話,他直接指出在集中營那樣局促的環境中,自己沒有心思去思考任何跟死有關的事,他一心只想爭取再多活一點時間,用這樣的意志,度過漫長一年的集中營。所以可以看到李維來得及完成的寫作,都費力在抗拒死亡,或抗拒自死。於是李維自主的死亡,對我而言是一個需要重新回答的問題,是一個在文學空間裡結成的基本悖論:當這個人以寫作,不斷地抗拒可能對自己有吸引力的選項(即自死),且當這樣的抗拒,最後跟他的現實選擇相反時,我們有沒有可能用一個更為複雜、立體的方式,來解答這個當代文學事件?這是我自己特別想要封印下來的一個基本矛盾。
另外,李維的寫作位置也讓我相當好奇,因為在許多篇章裡他都曾經描述過,對他而言,為集中營的死難經驗代言這件事,其實是被迫的代言。他不認為自己具備足夠的資格去書寫受難經驗、並承擔起這樣的代言。他被迫接受一個可能有的副作用──因為代言死難經驗,他的整個生命狀態,也遭到一定程度的簡化。這個基本矛盾讓我覺得需要再想想,或需要找一個方式更好地描述。
李維終身更想做的,是一名科幻小說家。如果沒有奧斯維辛受難經驗的話,李維可以更自在寫他想寫的作品。但當成為集中營受難經驗代言人時,某個意義,好像他所寫的所有事,都跟受難經驗有關。這是我們理解他的方式。好像他所有更私密、更內在、自己更想望的創造、所有千言萬語,無一不指向他置身過的奧斯維辛現場。從集中營出來後,在1952年他完成了一篇科幻小說。這篇小說是友誼之作,想要回應朋友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的作品。卡爾維諾是一位義大利小說家,同時也是李維著作的編輯。這篇科幻小說叫作〈冰箱裡的睡美人〉,寫在很遠很遠的未來,在太空時代,所有地球人都離開地球了,只在特定節日才會返鄉。德國人回到柏林之後,聚在一起參加儀式。這個儀式是去觀賞一個被儲存在深度冷凍裝置裡的女體的解凍過程。這篇小說除了回應卡爾維諾之外,我們還會在後來,譬如說川端康成的《睡美人》,以及賈西亞.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的《憶我憂鬱娼婦》裡,看到相似構想。
某個意義,李維其實是用自己的方式,來跟文學系譜對話。在〈冰箱裡的睡美人〉中,那些未來的德國人,當他們返鄉回到柏林,當他們旁觀這個定期被解凍的冷凍裝置裡的女體時,他們就在旁邊開宴會,很開心喝得大醉,故事大概也就這樣結束了。就像一個寓言,往往不會只有單一寓意,〈冰箱裡的睡美人〉也許想說的,其實就像臺灣北海岸神明跳港儀式那樣,是人定期將酣睡的神叫醒,讓祂浸冷水,然後用嘉年華的方式,來確認自己跟家鄉神靈的距離。也許,李維在說的是一個「倒反過來的創世論」,因為這些未來德國人的基因,都來自這個被反覆冰凍、反覆解凍的女體,他們參觀這個對自己而言,具有「始祖」意義的女人,觀看她如何甦醒、如何再被凍結進睡眠裡面。觀看曾經創造過他們的、這近於神一般的存在,如何被他們保留下來。觀看祂如何成為看守他們家鄉的神靈。這可以是一則無信仰年代裡的創世論。
但因為李維的受難者位置的關係,所以幾乎所有人讀到〈冰箱裡的睡美人〉時,立刻想起的就是集中營,想起納粹如何對人的屍體、人的生命缺乏敬意。這是一個隨李維的生命,一併理所當然被簡化的創造。被封印在這樣的簡化當中,似乎是後續李維創造的前提了。李維也許因這樣被簡化的事實而感覺到哀傷,於是當有人問他「你死後除了名字以外,在墓誌銘上面想要刻什麼?」
李維說,就簡單的兩個古希臘詞彙,在《荷馬史詩》當中,用來形容流浪者尤里西斯的兩個詞彙,「pollà plankte」。意思接近「大錯特錯」或「離鄉背井」。
這是李維最想要的、關於自己一生的考語。但是很遺憾,這個希望沒有得到尊重,最後李維的墓碑上,除了自己名字之外,只刻了一組號碼──他在奧斯維辛作為囚犯的編號,174517。
最後的最後,當人們需要選一個標籤去tag他的時候,人們遺忘了對自己的生命,他更愛的那個說明。也許他一生竭盡所能,像卡夫卡(Franz Kafka)寓言〈獵人格拉胡斯〉裡的獵人那樣去扮裝,去自願承擔一種以錯誤作為前提的考察,也在錯誤的前提下,極力想要挽留真實記憶。但對他而言,所有這一切,很明確是關於倫理責任的自我選擇,因此對他而言,扮裝永遠無法去除。他希望人們最後可以理解:也許我們認得的、或我們記憶與珍惜的李維,不是李維認為的最真切的自己,但他願意接受這個錯誤。他希望人們可以理解這個非常豐富的錯誤。但最後,我們還是認為曾經銘印在李維肉身上面的刺青,那個編號,更好地說明了李維。
我自己在讀伊恩.湯姆森(Ian Thomson)所寫的《李維傳》(Primo Levi: A Life)時,在這裡停了很久,我在想李維想要被記得的那個自己,為何最後終究還是被他作為一個政治受難者的形象給壓過去了?李維自己會怎麼想這件事?這變成一個開放性的問題。

想著這件事的時候,我又想起了捷克小說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因為這是一個跟墓誌銘有關的問題,所以我不由得想起昆德拉最著名的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其中的一個篇章叫作〈偉大的進軍〉。在所有昆德拉文本中,它最直接地解釋「媚俗」這個概念是什麼。昆德拉認為媚俗有兩種,一種是媚極權政治的俗,一種是媚商業市場的俗,而昆德拉在描述的,是對這樣雙重媚俗的抵抗。可是如果大家耐心把〈偉大的進軍〉讀完,其實會讀到昆德拉更想說的一件事,他其實是用很繁複的方式為我們證明,媚俗是我們身而為人難免的宿命。因為直到最後,不管我們經歷了怎樣的人生,不管從怎樣的受創經驗當中再站起來,然後活過一生,當置身那個死難現場,某個意義我們的生命形式就已經死過一次了。在那之後,只是更漫長的逃亡,這樣一直努力逃亡,直到最後,第二次死亡來帶走我們。昆德拉告訴我們,不管我們怎麼逃、也在逃亡路上活過了怎樣繁複的生命時間,最後,我們一定會不免成為某個墓碑上面的墓誌銘,而這墓誌銘通常是簡化後的話語,不是我們希望的,而是其他人更希望記憶我們的方式。我們最後,都會活成一小段簡化過後的考語。像這樣的墓誌銘,就是我們終身無法逃脫的媚俗,因為媚俗就是對個人生命的收納、簡化,然後用絕對不容更改的字詞,來對我們的存在做絕對的肯定。所以〈偉大的行軍〉說:
「媚俗,是存在和遺忘之間的轉運站。」
媚俗,是我們不知為何被給予的存在,跟我們最後難免都要走進去的遺忘,這兩點之間的轉運站。將生命收納成一行墓誌銘,是為了要被人更好地遺忘。
如果將這件事反過來想,也許我們可以更好地說明,李維是如何在漫長的40年之內,承擔一種見證寫作,同時也承擔這種寫作必然的結果。首先,他得先願意接受自己可能正冒著一個危險──他會終身被簡化成一個政治受難者。這是寫作的前提,同時也是倫理的責任,因此,他得以展開關於更多人的、更多元的受難經驗的描述跟討論。這麼想吧,也許李維在1987年4月11日、從自己家中的樓梯井跳下去之前,很長久的時間,已經不為人知地置身在一個小小的、非常寂靜的墓園裡面了。某個意義,他接受自己的生命形式已經隨集中營告終。接受了這樣的前提,站在這個非常寂靜的墓園裡,他才開始發出聲音。為什麼要不斷反覆地發出聲音?為了呼求更多元的理解。所謂的理解,我會把它標注為包括《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在內的這麼多話語,所共同結成的一個夙願,一個請求。前面說過,媚俗是存在和遺忘之間的必然轉運站,於是,呼求「理解」的意思是,邀請大家背向人總難免的遺忘,面向人的豐富存在。
從李維所開放的這個可能性來看,我衷心認為所有受難經驗的描述,都是非常珍貴而難得的。因為它們都是從一個非常寂靜的位置所發出的聲音,而發聲之所以可能,首先因為作者願意接納自己生命終將被簡化的這個事實。這個事實,很奇怪地在文學空間裡,卻該是成為作者的條件,而不該是寫作的阻礙。由此來看,我認為包括李維在內的所有受難經驗書寫,都不僅是要我們理解受難經驗而已。而是以受難經驗作為出發點,以這些被簡化過的作者位置,所發出去的聲音共振,指向人更為豐富的存在。所以理解李維的寫作,其實就是接受這樣一種悖論式的思考:李維的紀實寫作,也同時是事關解讀論與創作論的建議。因為李維常常描述紀實寫作的極限或不可能,對我而言,這其實就是虛構的邀請,他的書寫也就因此,成為一個現當代的文學事件。
如果要很簡單說明李維所封印的悖論,可以只講兩件事。第一個是關於言說資格的問題,這是李維念茲在茲的,最後也明確封印在《滅頂與生還》裡面的字句。他認為個人記憶並不可靠,但無奈的是,關於集中營受難經驗,我們只有倖存者的個人記憶可以倚靠。他明確說明,最有資格去言說受難經驗的人其實是死難者,因為他們是更為純粹的受難者。而在集中營能夠倖存下來的人,其實都接受了某種特權,以便換得更舒適的生活環境,讓自己的倖存率更高。這意味著,關於死難確實發生過的最好證明,其實是死難者那絕對的沉默。這是寫作之所以令李維不安與痛苦的基本原因。因為每一次對沉默的打破,這個言說之人也必須理解,自己其實不符道義。
總結說來,個人記憶並不可靠,集中營也不是最好觀測集中營的位置。所以這個被迫的代言,指向一個無可奈何的事實:不幸的,「我已身在集中營裡面了」;更為不幸的是,「現在只剩下我倖存了」。於是所有書寫,變成一個更為艱難的自我審核。我也是以這樣的方式,來看待《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裡的這90萬字,來思考它所背負的倫理難題。或者,去猜想當這些記憶幸運逃生之後,透過解讀,我們說不定可以更具體地理解那種背向沉默的基本痛苦是什麼。這是李維所留存的第一個悖論。
第二個悖論是關於「集中營宇宙」裡,所謂「灰色地帶」這種空間的描述。李維是一個正義感十足的人,是非對錯在他心中非常重要,不容混淆。但李維也用更多書寫來對我們說明,集中營宇宙最大的創造,是它確實開發了一個空間,分隔了受害者跟加害者。在這個混淆的中介地帶上面,站滿了各式各樣立場曖昧的人。李維認為,在這個中介地帶存在著很多人,是他窮盡一生也無法揣摩他們心靈結構的人。於是他留下索引,要求更多人以詮釋或想像去介入那個地帶。因為這是集中營宇宙最大的創造,所以重述它、定義它、能夠描述它,等於才能解開集中營宇宙對我們的殺傷力。意思是說,這樣的灰色地帶值得分析,不是因為這些曖昧之人相當深邃、很吸引人,而是因為當這樣的人存在時,人的價值將遭到全面的混淆。李維的陳述與留白,其實也就是《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而言,相當具體而明確的編輯建議。這大概是為何最後散文選的架構會這樣生成的一個重要原因。
莊:謝謝偉格老師,我想大家很想繼續再聽他講一個小時的普利摩.李維。我們最近在做《無法送達的遺書》增訂版,其中有篇文章叫〈記憶的艱難〉。這篇文章談到,隨著轉型正義這些年的開展,我們重新經歷了更多對記憶艱難的體會,順著偉格在提李維的書寫所帶來種種對李維個人的挑戰,我們值得去深思關於記憶這件事情,這裡頭除了書寫者個人記憶的倫理、記憶的承擔,也有他記憶的艱難。還有對於準備去承接這段記憶的人或後代,或者是所謂的群體社會,記憶的位置到底是什麼?記憶的政治又是什麼?
《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這些作品,光是書寫者的位置就非常多元。有類似李維這樣位置的當事人,是很多被槍決難友中倖存的那個。有些人是家屬,或是對這個事件關心的書寫者。有非常多不同位置構成。我覺得愈到後面的時間,記憶會有更多重的意涵,也有更多重的困難。最近在做《無法送達的遺書》增訂版的時候,因為新增了一個案例,聯繫上家屬。從跟家屬或再下一代的討論會發現,即便是當事者的家庭,記憶都已逐漸破碎掉了,它就是一個再被拼圖的過程。我經常覺得,到底在這個時代有誰可以為這些破碎的記憶寫一篇完整的敘述?我們是否有資格?我們是否真的確信我們的理解是完整的?而且企圖用一種完整的方式寫成文章傳遞給大家?這是我愈來愈感到困惑或愈來愈自我提醒的事情。
這次我特別想談杜斯妥也夫斯基,因為他是一個帝俄時代的政治犯,跟後來大家認識的蘇聯、現在的俄羅斯,基本上是不同的俄國了。我為什麼覺得約瑟夫.法蘭克(Joseph Frank)所寫的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傳記,令人非常想要繼續看下去,是因為我看到其中一段,讓我想到了陳列老師〈無怨〉的最後一段話。
杜斯妥也夫斯基怎麼書寫他被監禁以及流放的這10年,看年表會發現,杜斯妥也夫斯基在1860年結束監禁跟流放的歲月之後,已開始在寫《死屋手記》,某種程度上可以視作對他過去被監禁歲月某一種以小說方式所寫的作品。裡面幾乎都可以比對出來角色真實的名字,傳記作者法蘭克就有比對出來。

杜斯妥也夫斯基入監的過程是這樣的。他寫完第一個作品、開始有點名氣的時候,跟一個叫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朋友來往,他們經常聚在一起討論社會改革。他們應該是屬於俄國開始受到法國社會主義影響的一群知識分子。杜斯妥也夫斯基還有一群更小團體的朋友,是更激進的,會用出版品、小冊子的方式去改變社會。所以沒多久警察就注意到他們,他們之中還有一個臥底的人,於是警察經常在他們聚會的地方的對面監視。沒多久他們就被逮補,經歷審判。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假死刑事件」。「假死刑事件」是發生在一個叫謝苗諾夫校場的地方,其實沙皇尼古拉已經決定不判他們死刑,但是用假死刑的事件去震撼他們。所以當被判刑的15個人被帶到謝苗諾夫校場的時候,他們真心覺得要死了,而且有3個人已經被綁在柱子上。這個「假死刑事件」是後來在討論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時候一定會討論的事情,因為這個場景不斷地出現在他的作品裡,在《白癡》就有一段,在談到底人面對死亡前的5分鐘會想什麼?
這對我來講非常震撼,因為我們在做《無法送達的遺書》跟《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時,經常透過這些被槍決的政治犯留下的遺書,想知道他們人生最後一哩路在想什麼。但我們永遠會有一個空白是:他寫完遺書之後,到真的面對死亡的來臨,也許是6個小時、也許是1、2天,每個政治犯經歷的時間不一樣,有的人是寫完後的6小時就被槍決,有的人是隔天,有的人是隔了好幾天。但是那段時間,對所有想要記憶這段事情的人,包括他們的家人來講,就成了一個記憶的艱難。
直到看杜斯妥也夫斯基他們所經歷的假死刑,那所謂的5分鐘,對我來說好像才第一次感覺到:原來面對死刑的人可能是這樣。有趣的是,其實杜斯妥也夫斯基跟他的同志、朋友被拉到刑場上時,還跟朋友講悄悄話,說他昨天還在想一篇小說要怎麼寫。在《白癡》裡面則是透過小說的方式寫,在那5分鐘,他有2分鐘想要跟他的同志、夥伴告別,有2分鐘對自己的一生反思、反省,那最後1分鐘要做什麼呢?他想看看他即將要死的這個地方四周是什麼。然後他看到遠方有個像教堂圓頂的東西沐浴在陽光下,他覺得大概1分鐘後就要成為這景色的一部分了。這就是杜斯妥也夫斯基後來用小說的方式所寫的死刑前的5分鐘。
第二個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杜斯妥也夫斯基後來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他在那邊受到非常溫暖的對待,因為他遇到了前一代政治犯的家屬。這批政治犯家屬因為被流放,永遠沒辦法回到莫斯科,所以整個家庭就只好住在那裡,形成了一個小的菁英社群。這群人不斷關心後來的政治犯,並想盡辦法去監獄見他們,甚至在聖經裡面縫紙幣。知道他們要去下一站的時候,就站在路邊送別。
杜斯妥也夫斯基經歷過這些流放歲月後,還是沒有放棄寫作夢想。事實上,他被監禁時幾乎沒辦法讀到任何一本書,他一方面焦慮自己還能不能寫作、還能不能讀書,但是從來沒有放棄。後來他回到聖彼得堡之後,分批出版了《死屋手記》。我覺得很有趣的是,即便杜斯妥也夫斯基留下了跟哥哥的書信,也以作者的方式寫了一本《死屋手記》,可是傳記作者法蘭克是這樣說的:
「在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生平中,沒有哪個階段比監禁歲月中的這一段更難滿意地描述。不是缺乏材料──相反,他的書信、同時代人的回憶錄、數年後《死屋手記》所做的全面描繪似乎提供了足夠的文獻。儘管有顯然如此豐富的證據,但仍有揮之不去的神祕,很難弄清期間究竟。無論是《死屋手記》還是書信,杜斯妥也夫斯基這位偉大的心理學家都沒有分析過他的內心狀態,只是閃爍其詞。」
所謂的材料或是當事者的書寫見證這件事情,其實還是有很多空白是無法被填補的。甚至這個空白可能是當事者刻意造成的,或者是不經意造成的。
法蘭克又有一段在分析,關於杜斯妥也夫斯基在勞役營裡面的4年拘禁,許多事情也只能猜測,甚至如何理解他關於這段生活的作品,也還是一個問題。法蘭克覺得杜斯妥也夫斯基其實重新安排了他的經驗,去跟藝術的目的相符合,所以絕對不能視為日常生活的簡單複製。因此,杜斯妥也夫斯基不管他對過去的關照或者記憶如何修飾或強化,這樣的改進,方向都是一致的。也就是說,他確實知道自己是在一個創作的狀態寫這些東西,所以有更多藝術跟象徵的意味。這讓我們進一步理解到,經驗是不可完整傳遞跟表達的,或者說經驗或記憶,會造成修飾和扭曲。這是一個悖論,但文學卻用這樣的方式讓我們保留某些東西,讓我們可以靠近它。同時,它雖然是一個人最孤寂的墓園,卻又可以容納最大多數的閱讀。同時我覺得文學也是一個停戰之所,它可以盡量容納許多多元或是互相衝突在書寫裡面。
傳記作者法蘭克跟我們一樣都是20世紀以後的人,透過參照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人生與作品,他怎麼去理解那麼久之前的政治犯杜斯妥也夫斯基,以及小說家的杜斯妥也夫斯基?因此看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傳記,或者重新用當代轉型正義去理解他的時候,給我滿大的衝擊。透過杜斯妥也夫斯基150年前的時間尺度,我們應該要去思考,到底「政治犯」這件事情的意義對我們而言是什麼,或者說,因為政治事件而受難的經驗是什麼意思?
林傳凱在〈記憶的艱難〉一文有處理到,對家人而言,要如何記憶他們的家人是怎麼樣的人,為什麼他們要為了政治理念而付出這麼大的生命的代價?是很難去決定立場的事情。所以對後世的我們來講,到底要怎麼去思考政治犯的意義,跟我們現在去看跟政治犯相關的書寫或是更多作品時,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去理解,假設有一些空白是我們抵達不了的,起碼我們可以在客觀的結構上去想:如今我們為什麼要理解他們?我覺得第一,我們必須理解國家權力是怎麼被展示,它的管制方式什麼?不只是國家決定要逮捕哪些人而已,而是它為什麼要如此監禁、刑求一個人,或者是培養線民來監視一個人?甚至它為什麼決定你該不該死、該不該被判死刑。不是任何人生下來就想要變成錯誤生命的那個政治犯,一定是在他生命的過程裡有什麼樣的事情對他來說必須參與或瞭解,有需要面臨改革的體制。也就是當我們在看每個國家、每個時代的政治犯的時候,即便是同一個國家不同時期的政治犯,一定是有不同的意涵。臺灣1950年代有偏左派或地下黨的政治犯,1960年代後期一直到1970年代開始出現所謂臺獨政治犯,這都是不同背景下造成的體制問題,所以人有不同的政治行動選擇。體制的變革問題其實也是社會長期累積的問題,150年前的杜斯妥也夫斯基,他們那時面臨的是帝國最後50年的掙扎,大概再過半個世紀左右,帝俄時代就結束了。但是在1850年前後,這個制度已經有非常多問題了。
其實不一定要把這90萬字都讀完,可能只要讀其中幾篇,或許就能體會我剛剛講的這些問題──極權統治的形成,它是怎麼全面覆蓋,不只是社會性的覆蓋,還包括對人的肉體、精神、靈魂、生死、價值等哲學面向的覆蓋,而且到現在可能都還存在,它不是一個事件而已。這些傷害或記憶仍在傳遞著,沒有消失,以某種方式繼續存在。這大概是我從杜斯妥也夫斯基所體會到的一些事情。
還有我在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書信裡還體會到人性的問題。杜斯妥也夫斯基在經歷「假死刑」的震撼後,寫了一封信給哥哥描述這個事件,我覺得有個部分讓我看了非常感動,他跟哥哥說:「我既不會消沉,也不會沮喪,生命不管在哪裡都是生命,生命在我們自己身上,不在外部。」他說:「我的身邊(西伯利亞)會有人,要在人群之中做一個人,始終如一,不灰心、不放棄,不管發生什麼樣的不幸──這就是生命的意義,這就是生命的任務。」然後他說,我開始意識到這個想法進入了我的血肉。傳記作者法蘭克接下來寫了一段話,也解讀得非常好,他說:「因此,努力保持人性,『不管發生什麼樣的不幸』,就是如今生命的主要任務。堅決將『外部』放到次要位置,絕對優先的是,無論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個體都有責任堅持他人性的完整。」
我看到這段話時簡直覺得這就是陳列老師〈無怨〉的最後一段話:
「許多日子以前的某些時候,我常自以為已無法再感受歡愉的滋味了,人與物都顯得疏遠而難把握,甚至於天空和草木的爽新之美也只徒然加重愴然感覺而已,並認為此生將這樣地在憤懣裡走著、咳嗽、老去。現在雷雨聲中的恬靜裡,我卻已曉得,我不應該因為過去通過歪扭的媒介走入世界就變得落寞。當天地間萬物貫注於生長的時候,似乎其他的什麼都不值得怨恨和記掛了,最該珍視的是自己的完整。因此,我開始自覺得如此溫柔,如此強健,如此地神。」
我覺得他們基本上幾乎是同一個精神。在150年前的杜斯妥也夫斯基身上,這個關鍵的受難年代轉變了他的整個寫作。突然之間好像小時候半懂不懂讀的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有了很不一樣的感受。
今天剛好是6月1日,官方促轉會昨天已結束任務。臺灣這幾年有了官方的促轉會,某種程度可視作對轉型正義的討論好像有了某種成果,我們有法律依據去徵集更多檔案,做更多調查,甚至有更多直接的討論,譬如中正紀念堂的存廢問題。但同時在開展這些討論的時候,我們同時會立即感覺到困境,有很多價值的思辨即便是徵集再多檔案都無法克服。在當代的社會條件中,到底要如何重新定位這些政治犯?即便官方給予平反,但社會如何討論?是否仍舊有大多數人覺得不需要去回憶過去的事情?這種種的爭論都還存在社會中。其實在杜斯妥也夫斯基之後的蘇聯,一直到蘇聯解體後的這些國家,還有現在正在經歷戰爭的烏克蘭,都一直跟我們一樣處於社會的糾纏跟死結。
我最近在看蘇聯解體後的各國包括烏克蘭、哈薩克等,關於它們轉型正義的研究。跟我們的狀態非常像,共產黨一直是棘手的問題。很有趣的是,臺灣過去號稱自己是Free China,但其實是威權體制,我們的社會對於處理過去所謂的共產黨,始終有無法面對的尷尬感覺。但即便是這些前身就是共產國家的國家,它們也非常難面對跟共產黨之間的關係。
以烏克蘭來說,它們在2001年與2019年兩次在憲法法院裁決到底應不應該對共產黨下禁令,新獨立的國家跟共產黨的關係到底是什麼,以及現存於烏克蘭的共產黨是蘇聯共產黨分部嗎,還是一個全新的共產黨?如果大家都承認俄羅斯對於烏克蘭的克里米亞有很大威脅,那是否該正視這個事實、是否要禁止共產黨活動,甚至不能讓共產黨人參加選舉,以及沒收它們的財產?因為它們的財產在蘇聯時代都是不義所得。這些種種模稜兩可的討論,某種程度跟臺灣現在的處境很接近,陷入了一個價值與現實威脅的泥淖當中。
如果現實容易陷入一種荒謬劇,有很多東西是不能用速成的方式處理跟解決,我們在文學或是書寫的空間裡面去討論這些事情的時候,可能格外地有另一種力量。回到《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為什麼我非常願意投入,因為這是用一種更細緻的方式,回到對經驗的理解,然後讓它在紛亂的政治討論中作為一個特殊的存在。或許在令人非常厭倦的這種反覆、沒有結論的記憶政治的難題當中,我們還有另外一種安放記憶、靠近記憶的方式,這樣或許才能慢慢走出荒謬的記憶政治。
童:莊總編剛剛引用的杜斯妥也夫斯基傳記,書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受難的年代,1850-1859》,這是五卷本杜斯妥也夫斯基傳記的第二卷。身為「杜粉」,我強烈推薦這部傳記,它是我讀過最詳盡,觀點也最為完備的杜斯妥也夫斯基傳記,也熱切期待有一天它會有繁體中文版。
莊總編談杜斯妥也夫斯基在受難年代的經歷,以及經驗承擔,跟記憶自身的艱難。其中有兩個對立的時間尺度。第一個是非常微觀的時間尺度,也就是人面對死亡前的5分鐘。關於這點,我只有一些細節要補充。

當時,杜斯妥也夫斯基是作為政治犯,被關在涅瓦河心的一個軍事要塞。因為他是春天被補,所以穿的是春天的衣服,但到了假死刑現場時,已經是冬天了。這些囚犯還穿著春天的衣服,然後被帶出軍事要塞,每個人都凍得發抖,這是被帶出來時,最初始的肉體震撼。有個善良的獄卒送他們厚襪子,那是他們身上唯一禦寒的衣物。所以,每個人長得都像盆栽一樣,腳肥肥的,身上非常輕薄,就這樣被送上了謝苗諾夫校場,成了假死刑大戲的演員。這場戲的編導是沙皇尼古拉,囚犯當中有人也叫尼古拉。這個尼古拉受驚過度,當場瘋掉了。這樣的巧合讓杜斯妥也夫斯基內心非常震撼,因為他好像也覺得從假死刑之後,那個被送往西伯利亞的自己,其實也堪稱是某種贗品。
杜斯妥也夫斯基是一個格外複雜的文學案例,在這整個大戲當中,除了剛剛莊總編所描述的領悟以外,其實還有一點讓人傷心,因為它是比較晦暗的存在經驗:從受到驚嚇以後,杜斯妥也夫斯基就變成沙皇熱情且忠誠的擁護者了。這需要另外的理解跟分析,也是那個相當微小的時間尺度裡面,還待解、並需要更豐富的文學書寫來解說的謎題。
相對於此,是宏觀的時間尺度。杜斯妥也夫斯基大概在1860年返回聖彼得堡,之後,才開始寫幾部重要的長篇小說。如果將他60年的人生拆開來看,你會看到包括受難年代在內的40年,對於一個文學創作者而言,好像是一個相當漫長的準備,因為他只剩下20年,去從事文學寫作了。從《死屋手記》開始,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寫作說明這個無奈的事實:文學準備必要的時差與漫長。我猜想,這是莊總編把杜斯妥也夫斯基的陳述,類比於陳列〈無怨〉書寫的原因,因為他們共同回應的主題,其實就是所謂「自己的完整」。承擔記憶的責任、找到語言,然後重新敘述,這整個過程,其實也就是找出如何活下去的可能。像這樣的準備過程,可能是所有政治受難書寫,共同回應的一個厚重的主題。一個關於主體修復的問題。這也是《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第一卷,我們標注的主題。
《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第一卷後半,還集中呈現關於青春主體的受難經驗。這件事情延伸看來相當複雜,因為客觀說來,除了比較立即的回應、除了死難者的見證錄之外,其實社會大眾不會很想要回憶集體的政治受難經驗。包括德國,也是在1960年後才在文學上,對集中營經驗、集體受難經驗有一番省思;日本也是在1960年代以後才有對戰爭經驗的省思。
所有這些寫作是由誰啟動的?你會發現主要負擔著記憶責任的人,他們在戰爭年代基本上還是小孩子。比方說德國小說家鈞特.葛拉斯(Günter Wilhelm Grass),他生於1927年,戰敗時還是一個青少年;比方說日本小說家野坂昭如,他是《螢火蟲之墓》的作者,在1930年生,也就是說1945年終戰時,他只有15歲。所以記憶的艱難同時也指向一個問題:這些以青春狀態度過整個戰爭時期的人,在當時,他們沒有成年人的立場,或對戰爭行為有成年人的責任,但他們又已經在場,所以不能完全宣稱自己是和平時代的原住民。意思是說戰爭還是跟他們有關,而且跟他們更近身地相關。因為這個戰爭經驗,就是他們的啟蒙經驗。
這些人後來長大成人,到了跟在戰爭年代的長輩們年齡比肩的時候,你幾乎可以說,去探觸記憶的艱難,同時也是去實踐關於記憶的自主承擔。他們像是代替父輩去思考──我們的行為責任在哪裡?而在文學寫作上,奇特的雙面性是,他們的思考,常常也都跟自己的成長經驗牢牢地綁在一起,永遠無法再被移除了。這是一個更深刻的捲入也說不定。
以日本小說家野坂昭如的小說為例,如果大家讀過,一定會對其中的青春肉身經驗充滿印象。他描述一個孤兒,父母都在戰爭中走了,帶著一個比他更小的妹妹,在戰爭年代裡成為更純粹意義的孤兒。因為他們沒有人際關係,無法加入村落互助組織、無法獲得食物。他們不在食物配給名單裡面,所以更為饑餓,而那整個饑餓的身體體驗,就是他們成長經驗重大的一部分。這個男孩最期待的就是美軍空襲的晚上,好像在他的感官當中,整個戰爭體驗事實上跟成年人是反過來的。為什麼最期待空襲之夜?因為空襲之夜村落裡面的所有人、家家戶戶都會去防空洞避難,這時候少年就像夜遊神一樣,在村落裡面晃蕩。他可以任意打開任何對他關閉的家門,他可以潛進去,因為都沒有人,他就自由地像穿牆一樣走,走在那個地獄之火正在降下的無人村落裡,開始翻箱倒櫃到處找東西吃,找到的所有東西他都全部吞嚼入腹。這是無法阻擋的、相當狂熱的饑餓感,即便是沒有煮過的白米,他也用自己的牙齒,好好地全部咬碎,然後一口一口吞進去。這個青春主體,生命狀態這麼孤絕,可是很奇特的是,他的肉體非常好客。這個封印戰爭受難、死難經驗的肉體隨著他的發育,長進他後來的歲月裡,所謂「饑餓」就變成一個具體又形而上的概念。因為它永遠在這個肉體裡面,他會一直挨餓,就算吃飽了也還是餓。好像這個肉體在更久的未來,長成了一個總是在反對他的靈魂。這個肉體所封印的那個像獸一樣的經驗,就是他對受難最為深切而且難以移除的體驗。
我也一直在想一個跟聲音有關的問題。剛剛莊總編提到關於政治受難經驗對我們的意義,包括國家權力是怎麼被展示的這個問題。我想繞遠一點,很想要推薦一本書,這本書是當我在揣摩跟受難有關的肉身經驗到底是什麼的時候,會一再想起的書。就是張娟芬的《無彩青春》,它記錄的是蘇建和案。從1991年3月24日蘇案的命案現場被發現,一直到2012年8月31日蘇建和等人無罪定讞,檢方不得再上訴。在這21年當中,牽涉在內的3個無辜的年輕人,他們從19歲長到了40歲,他們的受難經驗,也被封印進了成長年代裡面。當能夠從受難經驗當中脫身而出的時候,他們已經是半生都被國家浪費掉的人了。
國家權力怎麼對他們展示?其實就是一連串跟聲音有關的密室。對蘇建和等人而言,這些跟聲音有關的密室,包括警方刑求的房間、檢察官到場採證的房間、不公開的法庭與法務部的法醫研究所──那個將所有一切的勘驗知識,全部變成祕密的法醫相驗所。總是這樣一個具有時代徵兆的場景,老是日照不明,然後這些人老是在非常驚恐的情況下聽見一些聲音。這些聲音,好像就是關於受難經驗持續最久的記憶形式,而它也是最脆弱的一種記憶形式。我總感覺在那些暴力現場,聲音是有形狀的,且它其實已經隨著暴力碎落一地了。這樣說也許太過抒情,但我還是會永遠記得──包括像是崔小萍的獄中日記,崔小萍一直在描述一種聲音,就是她在相當驚恐的情況下、被拉到法庭的時候,庭上有一位法官,老是怪怪地笑。他有一種玩世不恭的笑聲,好像發生在他面前的這些事情都無足輕重,太好玩了,所以他發出非常不莊重的笑聲。這種笑聲,帶給親臨那個聲音密室的受難者崔小萍,很大的痛苦。如果是莊重的聲音,她知道如何回應;如果是徹底的緘默,她知道如何自重。但問題是這個法官坐在執法者的位置上,老是發出非常滑稽的笑聲。崔小萍也許在問:「這個法官是怎麼回事?是什麼東西、什麼狀態允許他發出這種笑聲,成為我最為持久,但卻說也說不清的受難記憶呢?」
法官是試圖反抗嗎?在做某種內心流浪嗎?意思是說,他自己也不太情願做這個法官,但他已經在這個位置上了,於是就發出不受節制的笑聲,以此來自我反諷嗎?或者,一個讓人更為深刻痛苦的可能性是:法官其實就真的不在乎。因為他知道,更多更多年以後,反正這些密室都會被忘記。這種笑聲,作為非常隱密的印記,被記在這個受難者的心中,我總是猜想,它有點像是剛剛莊總編所說的,是一個相當微小的時間尺度,但又好像是一個非常盛大的時間尺度。但無論如何,這些好像都要更漫長的等待,才會有寫作者來予以展開。這當然也是在完成了《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之後,也許是一個備忘、一個提醒,然後希望:也許真的,在非常久遠的未來,文學寫作有能力回憶,像這樣不可記憶的事情。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