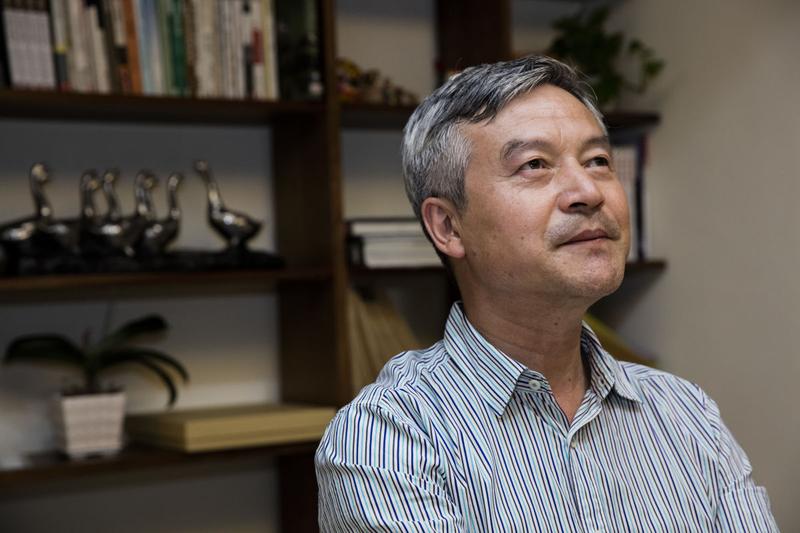評論

有一個笑話說,第一個中國太空人登上月球時,竟然發現已經有維吾爾族人在那裡賣羊肉串了,由此可見維族人頗有做生意頭腦,以及足跡遍布整個中國甚至更廣。
但現在,要在我所生活的城市,吃到正宗新疆人烤的羊肉串,已經幾乎不可能。仔細回想,這樣的情況持續時間差不多已經有兩年。我個人的旅程和消息所及之處,狀況也是如此。
最近一段時間,全世界都關注到了新疆的「再教育營」,但幾乎所有討論都忽視了一個前提──如果維吾爾族人仍然可以在全中國的範圍內自由出行甚至自由出境,那麼無論多麼嚴苛的集中營,都不可能將他們「一網打盡」。
烤羊肉攤消失的原因,不僅僅是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以拆除違建的名義,驅趕「低端人口」──雖然在經濟上處於弱勢地位的少數民族,必定受到波及──各地政府對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等少數民族在當地的住宿都採取了嚴格的限制。
這一年多來,中國對於賓館的入住要求愈發嚴格,除了每一個入住者都需要查驗身分證之外,通常還要經過人臉識別系統的審核。但一個維吾爾族人,即便是拿著本人的身分證,想要隨意在外省的賓館住宿,也會被告知:「請前往指定接待的賓館。」如果工作人員「不慎」收下了維吾爾族客人,那員警很快就會出現在大堂,然後要求賓館每天安排人去派出所報告這位住客的動向。
那如果想要透過租房的方式長期留宿在外地呢?恐怕結果是,房東會聯絡維吾爾族租客說,自己的房屋有別的用處,願意提供一筆不錯的違約賠償,請他盡快搬離。當然,房東並不是真的要拿房子派什麼用處,只是接到了「有關部門」要求清退若干特定少數民族租客的通知。至於節外生枝產生的賠償,也只能由房東自己「買單」──以上這兩種狀況,目前並沒有流出的「紅頭文件」可以佐證,但確實都在我身邊的親友身上發生過。
於是乎,在中國各大城市,市民們已經很久沒看見戴著白色的帽子販售羊肉串或者切糕的「新疆人」了。

2008年,我的一個朋友去北京看奧運會,收到入住的連鎖賓館發來簡訊,其中強調不歡迎新疆人、西藏人入住,朋友吐槽賓館怎麼可以發出如此「政治不正確」的內容。但總體而言,對於維吾爾族人被事實上剝奪了自由出行的權利這件事情,漢人社會是無感的,甚至有一部分是支持的。
在中國的大部分城市裡,生活環境幾乎完全是漢人的世界。對於長相、穿著、口音都和自己不同的維族人,漢人通常會想到兩個詞,一是能歌善舞,二是民風彪悍,雖然有刻板印象之嫌,但也不能說完全錯誤。
我的一位同學就曾說起,大學裡與她同班的維族女同學總是很不願意參加同鄉會的活動,因為去了常會被同族的男生霸凌,回寢室時,往往已經哭紅了雙眼。
對於城市裡的治安問題,漢人們常常責怪警方處置不力,造成了這種恐懼的加深,這其中最為著名的例子是2012年的「天價切糕(維族人稱瑪仁糖的特色食品)」事件。2012年前,漢人中就流傳著維族人不誠實經營的說法,諸如買切糕之前,對方說×元人民幣一兩(50克),切完又改口說×元一克,不掏錢就可能被一群維吾爾族人暴力脅迫。
2012年12月3日,湖南省岳陽市公安局發布微博稱,「村民淩某在購買新疆人核桃仁糖果(指切糕)時,因語言溝通不暢造成誤會,雙方口角導致肢體衝突引發群體毆打事件」。最終,淩某需承擔的各項賠償總計為15.2萬元人民幣。在那個「圍觀改變中國」的年代,網民們相信,官方的消息證實了「天價切糕」這一傳說的存在。
不管當時是非曲直,現在無論你是想要吃地道的烏魯木齊羊肉串,還是對販售切糕的維吾爾族商販心存忌憚,他們似乎突然在漢人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
流散在全國各地的維吾爾族人無處可去,再加上他們不容易申請到護照出國,最終只可能有一個選擇──回到新疆。以今日的「後見之明」來看,中國政府應該早就規劃好了整盤棋──待他們悉數回家,進行「集中管理」,或者說「一網打盡」。
從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開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和「五大山頭」(北京、天津、上海、重慶、廣東)的「一把手」一樣,位列權力最中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現為25人,其中包括7名政治局常委),屬副國家級領導人。2016年8月,原自治區黨委書記的張春賢退出權力中心,之前主政西藏(圖博)的陳全國,調任新疆。
美國喬治城大學教授米華健(James A. Millward)曾撰文指出:「陳全國將檢查站、派出所、裝甲車和不間斷巡邏的網路系統帶到了新疆,這一套是他此前在西藏任職期間完善的,共產黨相信他在那裡使一個難以駕馭、對共產黨的統治感到不滿的族群平息了下來。陳全國在新疆上任的第一年,已經招募了數以萬計的新安保人員。」
幾年前仍是張春賢主政之時,我曾去過新疆。大巴車進入烏魯木齊時,全車人要下車接受安檢並檢查身分證,安檢的隊伍排得很長。但可以明顯感到,對漢人的檢查相對較鬆,通關速度要比少數民族快得多。

如今再看,當初的那些安保措施,實屬「小兒科」。如今走在烏魯木齊的街頭,每隔幾百米就可能遇到盤查身分證的員警,不帶身分證出門很可能寸步難行;維吾爾族人購買的菜刀上,需要打上有身分信息的QR-Code;手機上則必須安裝政府所指定的監控軟體;街頭裝滿了監控攝影機,彷彿布下了天羅地網。在這些事情上,海外媒體的報導和我們在國內看到的新聞、聽說的「小道消息」是可以互相映證的。
被不少海外人士呼籲美國政府對其實施制裁的陳全國,讓很多人想起了綽號「王鬍子」的王震。王震是中共開國上將,1950年率部隊佔領新疆。作為鄧小平時代的「八大元老」之一,在天安門事件中,時任國家副主席的他屬主張武力鎮壓的強硬派。王震主政新疆時期,同樣以鐵腕著稱,以至於流傳著當地人用「王鬍子來了」,嚇唬不聽話小孩的說法。
一位出生在烏魯木齊的朋友,曾以懷念的口吻說,「王鬍子一拍桌子就喊殺,讓維族人沒脾氣。」一直以來,都有人認為在新疆應該延續王震的鐵腕政策。如今,很多人在陳全國的身上,依稀看到了「王鬍子」當年的影子。
但全國範圍這麼大的一盤棋,並不是陳全國一個人所能決定的。他也只不過是待中國各地將維吾爾族人驅趕回原籍全面完成之後,在新疆一地衝鋒陷陣的「馬前卒」而已。
新疆在清代再次併入中國版圖,乾隆特意為烏魯木齊取名「迪化」,意為「啟迪教化」。雖然期間有一段時間,新疆脫離中央政府控制,但掌握當地的軍閥如盛世才等,也並非維吾爾族人,大多是漢人,也有同為穆斯林的回人。中共關於統治新疆最初的想法,恐怕主要是擴大版圖(占全國總面積的六分之一),還不涉及後來常被提起的資源問題──塔里木油田的勘探和開發是1980年代後期才開始的,較早的克拉瑪依油田也是1955年才發現的。但將漢人移民到新疆以穩定邊境的政策,卻是貫穿始終的。如今在北疆,漢人已經從「少數民族」變成了「多數民族」,烏魯木齊的維吾爾族人口只有12%左右。
我曾詢問過一些人,新疆有沒有當地的漢語方言,得到的答案均是否定的,因為在新疆的漢人來自全國各地,至多只有一些當地特殊的表述方式,比如問路時,對方回答「一直往前走」,「直」字的發音長短,表示距離的長短。
這些年來,漢人堅持認為是自己幫助了新疆的發展(就我所見,當地的公路網確實修得不錯),但很多維吾爾族人則始終認為自己被漢人掠奪去的資源更多。各持己見的思維定式,讓兩個民族無法真正互相理解。
當然,中國各個少數民族之中,都不乏中共的鐵桿支持者。在我們這些外人看來,在南疆不同民族的官員相處得頗為和睦。有人問一位維族官員,你們維吾爾族人都是穆斯林嗎?他回答說:「我從10幾歲就開始當兵,有30幾年黨齡,你說我怎麼可能信那個?」但也有漢族官員私下說,雖然看起來彼此關係不錯,但民族不同所造成的隔閡始終存在,維吾爾族的共產黨員、幹部私下信教的情況也不少見。而當地醫院的心理醫師則透露,遇到過不少維吾爾族黨員幹部前來諮商,因為「被同族認為是『維奸』,心理壓力很大」,甚至擔心受到報復傷害。
在少數民族政策上,中國政府很長一段時間採取的是軟硬兼施的措施。一方面,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觀念之下,漢人對於少數民族,尤其是藏族和維吾爾族從來沒有百分百的放心,始終暗中提防。另一方面,出於宣示「56個民族大團結」的需要,在高考(類似於台灣的學測)等方面,給予了少數民族以優待。此外,因為「民族宗教問題無小事」,所以以往對於諸如盜竊等刑事犯罪,打擊也並不十分嚴厲,以至於又招致漢人社會不滿。
回溯之前的軌跡可以看出,中國政府至少在4、5年前,仍然有某種「懷柔」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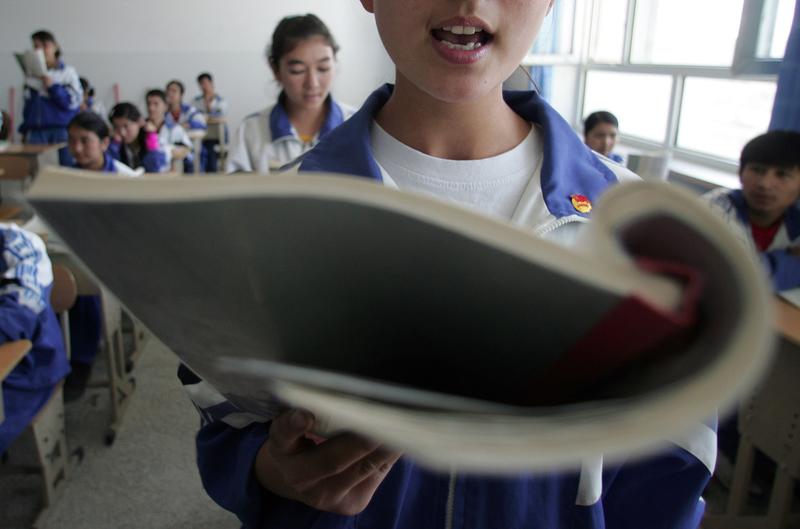
2014年5月26日,習近平主持政治局會議,提出要「南疆全面實行高中階段免費教育」(即12年免費教育)。而在中國的其他地方,除了西藏以外,即便是經濟最發達的地區,義務教育也只覆蓋9年。
但是政府的政策,往往並沒有戳中維吾爾族人的痛點。以12年免費義務教育為例,其實很多維吾爾族家庭,子女較多,不太可能讓孩子念那麼久的書。
即便是旨在促進民族融合的學校裡,不同種族的同學可能會在同一個教室裡上課,但還是可以輕易地發現,漢族和維族學生,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兩個不太往來的團體。而在同一所學校,漢族學生考試60分及格,維族學生只要30分就能及格。這樣的狀況,既讓漢族學生覺得不公平,也讓維族學生因自覺被歧視而不滿。
再比如,在全面開放二胎政策之前,政府就允許南疆的維吾爾族家庭生育3個子女。但是,「超生」的現象仍然十分普遍。對此,相應的「懲罰」措施是,超生的子女不允許上戶口、辦身分證,但這樣反而又造成了更加混亂的對人口失去控制的狀況。即便遇到官員前來查驗人口,在家的子女拿出其他兄弟姊妹的身分證,漢族官員通常也無法識別。
在陳全國之前,兩任主政新疆的官員王樂泉和張春賢,並沒有祭出太過激的手段。
2009年造成至少197人死亡的「七五事件」,發生在王樂泉的任上。1995年開始主政新疆的王樂泉是山東人,曾有與之長期接觸的人士對我說,王樂泉人很好,每次都是價格不菲的好酒好菜招待他們。
「七五事件」之前,廣東省韶關市發生一起鬥毆事件,起因是維族人騷擾漢人女子,有兩名維吾爾族人在鬥毆事件中喪命,這引發了維吾爾族人在烏魯木齊舉行街頭示威。但當地政府並未引起足夠重視,甚至在官員中流傳一個說法是,「『七五事件』發生時,王樂泉正在和他的山東老鄉喝酒」。他們認為,維漢間的殺戮和報復,造成了數百人的死亡,讓兩個民族之間結下了「血仇」,更讓新疆的情勢急劇惡化,王樂泉難辭其咎。
一位維語很好的漢族官員曾告訴我,自己出生在南疆,從小和維吾爾族孩子一起長大,很長一段時間裡,漢族人、維族人互相到對方家裡吃飯,都是很平常的事情,穆斯林也不會特別在意漢人家裡的伙食不夠「清真」。但在「七五事件」之後,一切都變了。雖然見面彼此還會寒暄,但是作為漢人和維吾爾人的自我認同變得十分強烈,到對方家中吃飯這種事變得無法想像。
2010年,張春賢從湖南調任新疆。我去新疆時,官員中對於他詬病最多的是2014年2月開始推行的「下基層」活動,要求20萬名機關幹部分成3批,到最基層蹲點,「一竿子插到底」,每批為期一年。
中低階的官員,對這樣一項「討好中央」的做法提出了不少批評。比如下鄉的初衷是希望幹部深入維吾爾族群眾,緩和矛盾,但很多漢族幹部不通維語,無法與維族群眾交流,蹲點毫無意義,甚至還要專門安排人保護纖弱的女性。
回頭來看,無論是王樂泉的不以為意,還是張春賢的形式主義,都未能使新疆擺脫民族宗教問題的泥潭。
在新疆推行12年義務教育,可以算是中國政府最後一項明顯的「懷柔政策」。
政策出台前一個月的4月27日至30日,習近平唯一一次以國家領導人身分到新疆考察、調研,並且深入維吾爾族人聚居的喀什地區。最後一天,他在烏魯木齊接見了勞動模範代表。也是在那一天,烏魯木齊火車南站發生了暴力襲擊事件,造成3人死亡、79人受傷,官方稱此案為「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恐怖組織所為。
在那之後,我曾到過習近平在喀什下榻的賓館。它是被鐵絲網完整包裹著的,門口有荷槍實彈的武警24小時站崗守護。幾個省市的援疆指揮部也在這道鐵絲網內,較可以保障各地援疆官員的安全。
至於各級政府門前,擺設著防衝撞的金屬設施,更是司空見慣,儼然一個個隨時可能發生戰鬥的陣地。
一位漢族醫生曾經告訴我,他們有時會下鄉去維吾爾人的聚居村落巡診,「但是那時候常會覺得慚愧,我們去看病,老鄉載歌載舞歡迎我們,但我們身後就跟著端著槍的武警。」

火車站的那場襲擊,難免讓人心有餘悸。我們無法揣測,在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心中,是不是從那時開始,決定要在拋出12年義務教育的「胡蘿蔔」之後,不再手軟,用以暴制暴的國家恐怖主義,對付版圖內的異族。
中國政府將新疆所發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歸結為「分裂主義、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的三合一。一位主管民族宗教事務的地方官員曾私下表示,「藏獨」雖然有一定的國際影響,但實力有限;與之相比,「疆獨」則要有威脅得多。他甚至透露,1990年代,就曾有疆獨分子,襲擊過新疆境內的一處祕密軍事基地,導致該基地200餘名解放軍全部犧牲,但政府一直沒有對外公布此事。
但新疆的暴恐事件真的如中國政府所宣稱的(雖然最近兩年並未再公布恐襲事件的次數和造成的人員傷亡數)那樣多發嗎?也未必。當地官員舉例說,曾經有一次導致多人死傷的衝突事件,最初只是停車糾紛,雙方各自找了人幫忙械鬥,最終鬧出了人命。因為其中一方是維吾爾族人,當地官員便在向上級報告時宣稱彈壓了一起暴恐事件,以此增加政績。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中文網近日一篇報導稱,「文件顯示,在習近平訪問新疆後的一年(即2015年)中,中共開始建造『教育改造』營地,警告穆斯林少數民族宗教狂熱和民族分裂主義的危害。官員講話及報導顯示,當時拘禁營規模較小,許多被拘禁者僅被關押幾天或幾週。」
我們在國內聽到的消息與之基本相符,比如「再教育營」設立之初,「入住率」並不高,但如今已是住得滿滿當當。至於被投入其中的人,是否真的有百萬之眾,恐怕除了中國官方,外界很難判斷其準確與否。
而中國政府則只是宣稱,外界所說的「再教育中心」是為維吾爾族人提供就業培訓和法律教育的,其目的是「治病救人」,並在10月9日匆匆修改了新疆的一些地方性法規,對其進行「合法化」。
9月28日,在與美國前財長魯賓(Robert Rubin)對談時,中國外長王毅表示:「新疆有2千萬民眾。他們現在都非常贊成政府採取的做法,因為他們感到安全,他們晚上可以安心地睡覺。」王毅說,基地組織和IS滲透新疆,透過暴力影片吸引無業青年成為恐怖分子,讓新疆變得非常不安全;為了保護新疆人的生命財產,中國政府才依法採取行動,令這1、2年新疆都沒有恐怖事件。此外,政府也宣稱,因為情勢穩定,今年新疆的旅遊收入十分可觀。
按照學者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說法,民族與宗教所造成的矛盾是一種「文明的衝突」。而在中國政府看來,如果要在「維穩」和不侵犯人權之間做一個選擇,一定會果斷選擇前者──這恐怕也是與世界主流治理理念涇渭分明的一種「文明的衝突」。可是,在一個人並未實施乃至計畫進行犯罪之前,政府真的有權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嗎?
9月27日,烏魯木齊旅遊局突然發布公告稱,因「旅客列車運行圖調整」需要,停售10月22日以後進出新疆的鐵路車票。外界推測,列車將被用作「再教育營」人員的祕密轉運。而從10月初開始,已有傳言說,路上出現了一些拉著黑色窗簾的大巴車,或駛向烏魯木齊,或去往甘肅等周邊省分。
沒有人知道,這些被送走的維吾爾族人,何時才能回到他們的故鄉。
(閱讀英文版,請點: How The Uyghurs Vanished From Daily Life In China。)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