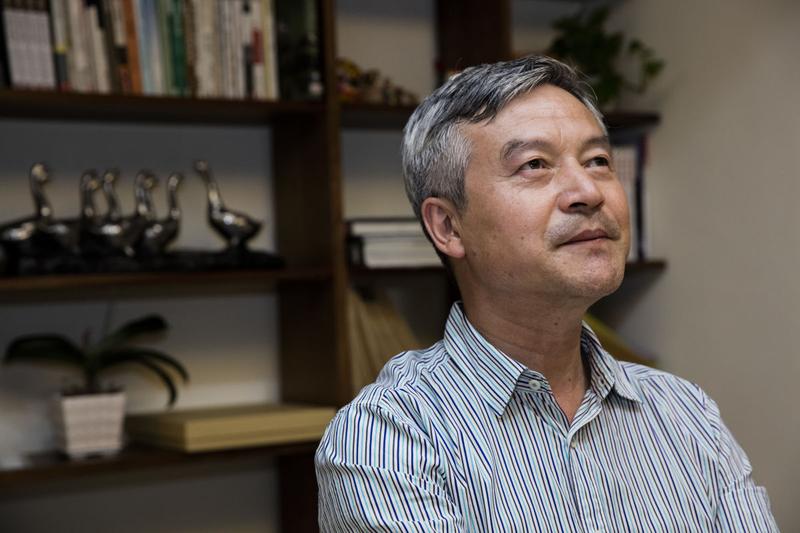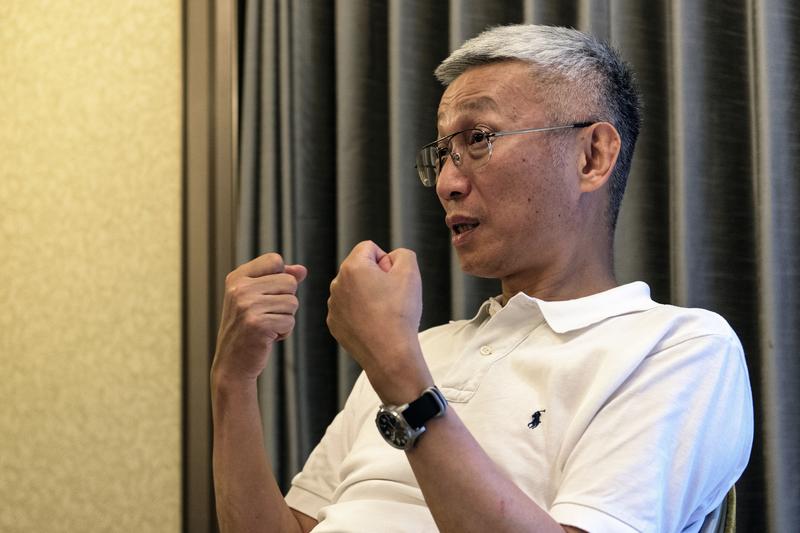
60歲的裴敏欣是當代重要的中國問題專家,他是美國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政府學教授、凱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Keck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主任。他的研究主軸是專制政權與威權體制的轉型,國民黨過去在台灣的威權體制,曾是他關注的課題。
而這位知識份子,從年輕時就展現他的氣度與銳利。他童年碰上文革,求學時中國剛改革開放,他對政治十分感興趣,為了瞭解中國政治,赴美後學習政治學;1989年,民運點燃烽火,北京學生上街,裴敏欣熱血澎湃,他積極在美國的留學生圈子中,發起支持中國學生的募款以及活動,甚至為要求美國政府對中國政府施壓,成為中國學生中,出席美國國會聽證的第一人。
在學術上,他接受哈佛政治學教授杭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的啟蒙。杭廷頓以「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觀點為世界帶來極具影響力的思潮時,裴敏欣正是他的助理,無論在學術理論,還是個人的職涯發展上,裴敏欣在《報導者》訪談中細述了杭廷頓對他的影響。
近日他受龍應台基金會的邀請,出席思沙龍演講,同時介紹他的新書《出賣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的起源與共產黨政權的潰敗》。在專訪、演講以及書中,他多次提及中國獨裁體制的崩解,「我認為就是10到15年」。他說,當中國菁英從分贓與聯盟,到現在的內鬥,過去從抱團取暖,到現在的你死我活,菁英不團結,威權政權的可持續性就降低很多。從中國目前的經濟及教育水平,已經達到民主轉型的標準,他強調,「中國需要民主化」、「也必定民主化」,現在的中國顯現許多問題,未來必然經歷一場政治改革。
對於蔡英文上台以後,兩岸關係冷卻,李明哲事件、巴拿馬與台灣斷交,台灣感受到來自對岸的壓力有增無減,他也在專訪中表示,習近平的「全面強硬」容易導致僵局,而在美台關係間,他認為台灣只能「影響」但無法「決定」美國政策,台灣能做到的是島內先團結。
以下是裴敏欣接受《報導者》專訪紀要:
報導者(以下簡稱報):你自1988年成為第一批來台灣訪問的大陸留學生,來台灣多少次?在這近30年的時間,你對台灣民主化的整體觀察如何?
裴敏欣(以下簡稱裴):我一直感到有一種很親切的感覺。我從第一次來台灣到現在,這段時間來了台灣很多次,至少12次。因為我當初來的時候是台灣民主化起步,我現在來,看到台灣的民主不僅是進步,基本上是進入了民主鞏固階段,更是感到,就是說,一種滿足感,替台灣感到驕傲。
報:你在到美國留學前,中國政治社會情況如何?為什麼你當初想到美國唸書?什麼契機讓你出國讀書?
裴:我1981年從大學畢業了,我當時是提前畢業,3年就把4年的書讀完,畢業之後工作了3年半才去了美國。因為80年代,中國是剛開放的時候,我們這一代年輕人的求知慾很強,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夠有機會到世界上教育條件最好、資源最豐富的國家去讀書,那就是美國。這是唯一的考慮。
我是文革之後第一屆通過考試進去的大學生,1977年考進去、1978年進入很有名的上海外國語學院就讀。我們這種出身普通家庭,在國外沒有親戚,大學剛進去從來沒想過出國唸書,能夠出國唸書,感覺就像是上天堂。
當時教育部給了兩個名額公派出國,不知道遴選機制是什麼,總之輪不上我,後來是經由學校的美國教授的幫忙,他認為,我們這些學生很優秀,應該到美國去學習,他在匹茲堡大學給我找到獎學金。我出去之後,所有學費、生活費都是美國人提供的。
1984年出國,因為大學本科讀英語,我一開始去美國能拿到的獎學金是「英文創作寫作(Creative Writing)」,我在匹茲堡大學讀碩士,但讀的過程當中,我感覺到英語只是個工具,我對政治學比較有興趣,所以開始一方面讀英語創作寫作,一方面讀政治學。
回想起來,我們這一年代人,經歷過中國非常政治動盪的年代,我的童年時期碰上文化大革命,所以我對政治十分感興趣,因為想要瞭解中國的政治,就去學政治學了。
報:1980年代,中國內部民主浪潮興起,直到天安⾨事件受到劇烈打擊,當時你正在美國攻讀政治學碩⼠,那段時期當中你有什麼記憶以及經驗?
我算是很積極的份子,我是第一個以大陸學生身份到美國國會作證,要求美國政府對中國政府施加壓力的人,我主張中國政府不應用武力來對付學生;我又主持捐款活動、又寫文章、又做演講。
因為我算是曝光率很頻繁,去國會作證兩次,上了許多次電視,不像許多人參與沒有留下紀錄。所以我很長一段時間不能回中國,我也不敢回去。中國是個不透明的國家,你猜自己做了那麼多事情,應該是上了黑名單,但是,你根本就沒辦法確定。而且1990年代,我在美國是個窮留學生,那時候又有了孩子,如果回去給逮住了,不放出來,那麼家庭怎麼辦?所以當然就是不敢回去。
報:你在哈佛大學的老師杭廷頓教授,在學術⽣生涯中對你的影響是什麼?
裴:我到哈佛大學時,他正好是65歲、66歲的時候,正值學術成就的頂峰時期,我對他最大的印象是,從個性來講,他生性非常低調,不太說話,是一個很靦腆的人。
我選他的第一門課,就是「比較政治學」,當時我所讀的第一本他著作的書是《變遷中社會的政治秩序》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y),我一看,覺得這不得了,這是天才的書!那本書,可以說是改變我的學術軌跡,原本我應該是要學國際關係,但他的書中有許多比較政治分析、解釋、理論,特別是現代化國家的政治穩定、政治變革,他的見解是天才性的,讓我十分佩服,使我感到學比較政治更有意思。
他待我很好,我學他的課之後,他就雇我做他的助理,他教一門「民主化」的課,他又雇我做他的助教,所以我跟他接觸很多。他等於是我們這種人的一個楷模,他是我的榜樣。我要做學問就要像他那樣做。
杭廷頓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學者,他講文明衝突、美國認同問題,都比人家看得很早。他一直在研究政權的建立、政權的轉型,他在寫《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時,同時在教「民主化」那門課,我是他的助教,我自己對民主化也很感興趣。所以我寫的第一本書《從改革到革命:共產主義在中國和蘇聯的消亡》,他是指導教授之一,就是講共產主義的轉型。
我的學術軌跡上,他對我個人幫助很大,我的論文出版,他特地寫信到哈佛大學出版社去推薦,我找工作,他為我專打電話,因為他學生遍天下,我一生當中他幫我很大的忙,我的第二本書《中國被困的轉型:專制制度發展的限制》(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是獻給他的。
報:杭廷頓教授做學問的方式在哪些部分影響到你?
裴:最大的影響是兩點:第一點,是找到重要的問題。學術可研究的問題很多,但大部份問題都是不重要的。像杭廷頓教授,他選的題都是最重要的,而且他有前瞻性,許多十年之後成為很重要的問題,十年之前他都看到了,這個特質是沒人可比的,他是天才。
第二點,是他根據事實說話,你如果要研究某個問題,你必須要有足夠的證據,這是他對許多學生的影響,他為學生樹了很好的學風。
報:你撰寫關於杭廷頓教授新威權主義的文章的背景是什麼?
裴:當時是80年代末,他的《變遷中社會的政治秩序》一直被認為是鼓吹威權主義,你當然可以這麼解讀。但他是說一個國家最主要的是「政治秩序」,政治秩序的來源是一個「強而有力的政府」,但怎麼形成強而有力政府?許多人解讀成,發展中國家實行威權主義,能夠提供一個強而有力的政府。但他其實並沒有給一個清楚的答案。
1988年,中國正好是威權主義盛行的時候,我跟他做了一個很長的訪談,訪談裡他沒有講到必須是威權國家才能提供政治秩序,因為實際上來說,威權國家不能提供政治秩序,大部份威權國家是失敗的國家。這篇採訪在1988年12月刊出,登在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上,因為中國當時很開放,但八九之後報社就被關掉了。
報:研究敏感的中國政治問題,對於研究者而言會不會有壓力?
裴:當然。你就是說話要很當心,像我們華裔背景的中國學者,需要回到中國去訪問、工作、探親,你如果說話過頭,以後就不可能拿到簽證。我認為這可能是最大的顧慮。
上一次是2015年回去參加一個會議,後來工作忙就沒回去。這次新書回去訪問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本書不是政治正確,是有爭議的。《出賣中國》這本書算是敏感議題,但是我為什麼研究?因為這是重要的議題。
我們是做學問,說話是比較謹慎,幾件事情你不能做。你不能對中國領導人進行個人攻擊、你不能參與中國內部的黨派之爭、不能支持薄熙來或反對誰,就是你不能有政治偏向,不能參加組織活動,這是中國政府最在意也最忌諱的一點。其實明白人心裡都知道。
報:「中國是否崩潰、何時崩潰」⼀直是研究中國制度變遷涉及的焦點,1989年後許多學者預測中國將會崩潰,2012年的權力交接、2015年反腐運動,許多學者也接連預測中國崩潰,但卻未⾒結果成真,你的看法是什麼?如何看待這樣的現象?
裴:這類東西沒法預測,但是你可以說這些政治經濟體系是「不可持續」的,但是到哪一天結束,是沒法預測的,這是小概率的事情,根據學者研究,每年每個專制政權崩潰的概率大概只有2%左右。政治學者關注的是「過程」,不是關注終極點的「事件」,比如說,前蘇聯1991年崩潰,政治學者關注改革之前出現的許多矛盾,及改革後出現的許多問題。

但是中國是否會崩潰,這個問題有許多人思考過。第一個歷史原因,是因為蘇聯崩潰了。接下來看下去,中國的一黨專制跟蘇聯體制很像,受到八九衝擊後它的確危機四伏,所以崩潰並不是空穴來風。第二點,90年代之後全球民主化浪潮,許多專制政權都以各種不同方式垮台,許多人感到這類專制政權不可能長壽。再來,許多人用西方理論或是西方眼光,看中國政治經濟體制,有許多不合理的地方,覺得不合理的東西怎麼能持續。
報:相對其他已垮台專制政權,中共政權為何至今屹立不搖?
裴:你要了解中國,你必須了解世界。
如果你光看中國,你只能看到中國的某些特點,但是你了解世界,你對許多問題會看得更清楚一點。像是中共這類「一黨制」的專制體制是最長壽,而且這個一黨制一定要是「高度組織」,對社會控制滲透能力很強,能把社會菁英籠絡起來。世界上最長壽是前蘇聯共產黨,現有的是國民黨,還有墨西哥的革命制度黨。
國民黨在大陸時,中國共產黨就十分務實,毛澤東時代之後,它變得十分靈活,它很會學習,很會做戰術上的調整。特別是蘇聯垮台之後,它悟出一點,「意識型態」對統治中國社會人民失去效用,因為共產主義整個意識形態體系都垮台了,唯一能夠使人民認同政府的,就是要提供「經濟表現」帶來的「合法性」,這一點,雖然簡單,但是許多威權政權做不到。這可以解釋,為什麼在過去二、三十年當中,中共成功的生存下來。
報:中國「權貴資本主義」是如何形成的?中國政治內部的貪腐是否帶來中國崩潰的可能性?民主體制是否有利於解決這樣的問題?
裴:八九之後,中共做了很大調整,在內部,中共把國有資產的控制權大大的下降,一下子使許多共產黨的基層幹部,最低到縣級幹部,對國有資產有了支配權,基層幹部有能力和有錢的資本家進行交易,這就是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
中國過去也有貪腐,但都是小打小鬧,因為你不偷財產再貪也貪不到哪裡去,但是你一旦擁有土地、礦場、工廠,一夜間可以暴富,那才是真正的資本主義。而其特色是金錢跟政權結盟,使小部份人成為權貴。
目前中國政府的打貪,只是針對這個權貴資本主義收賄、權勢交易的表面現象,但是沒有針對權貴資本主義的「根」:第一,是國家掌握很多資源,一旦政治權力可以支配經濟資源,腐敗土壤就會形成,政治權力不受監督,沒有反對黨,沒有媒體,沒有獨立司法體系監督,更加變本加厲。
民主體制是否能解決貪腐?民主只是有利條件,但嚴格講不是必要條件。民主體制也有腐敗,享受腐敗的人多得不得了,例如在印度是多數人的腐敗,但每個人收的錢不多;專制體制下的腐敗,是少數人的腐敗,但個人量大,一個人能收到5,000萬美元。解決貪腐要多管齊下,民主體制下還要使政府管得錢少,並有獨立透明的程序機制,不然政府逮了人,無法說明那人是真的腐敗還是因政治鬥爭被逮,因此還要媒體、民間社會的力量來監督。
報:中國現在是否具有民主化條件?
裴:中國現在經濟社會發展程度,跟台灣80年代中差不多。中國民主化客觀條件已經具備,根據世界銀行資料,中國是「中等收入群」裡面的中高等收入國家,此外,中國13億人口中,25歲以上人口受教育的平均時間是7.5年。所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東風」,就是政治菁英的角色。
如果中國政治菁英認為,挽救共產黨最有效且長期能夠持續的方法,是讓共產黨跟別人競爭,改變遊戲規則共產黨還同樣能掌權,它會做這樣的「戰略決策」。國民黨80年代做的戰略決策,使國民黨至少延長了二十幾年壽命,這是不得了的,因為一般這麼年紀大的一黨專制政權,要維持30年是很困難的。
中國民主化契機目前還看不到,因為政治菁英的價值觀,還是覺得民主不好,戰略判斷上,威權體制還可以靠高壓政策,或是靠經濟增長繼續提供合法性,當然不會進行民主改革。
報:你曾提及專制政權民主化很重要的一點是「資訊的流通」,但是中國政府近年實施各種「實名制」,並對媒體加強收緊,是否民主化希望更加渺茫?
裴:「民主化」跟「專制政權的維持」永遠是一場遊戲,或是一場鬥爭。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中國政府通過技術手段,降低信息革命對政權的威脅,是鞏固了政權。但是,世界上沒有免費午餐,它的代價肯定是信息流通少了,但是信息是有價值的,雖然你控制了對政府不利的資訊,同時也控制了對社會有利、經濟有利、對社會創新有利的資訊,那代價是無形的,專制政府在什麼情況下會垮台,都是一個「綜合性」的因素。
為什麼東歐要有世界上一流的秘密警察,因為它面臨了「綜合危機」。「綜合危機」必須經歷一個漫長形成的過程,「綜合危機」發展到一定程度,威權政權是沒有人會出來保護他的,因為威權體制講人治,危機到來時人的鬥志都已經沒有了。顯然中國現在是沒有這樣的「綜合危機」,只是苗子都在了,還沒有匯集到一起,有的苗子,也還是很嫩。
報:中國現有體制還可以走多長?
裴:我認為就是10到15年,為什麼這樣看,第一,靠經濟增長維持政府的合法性,這條路恐怕已經快走到盡頭了,中國高速經濟增長的時期已經過去,要維持中國的經濟增長,需要很困難的改革,特別政治上的改革,但現在看不出中國政府會進行這樣的改革。「危機綜合症」有一個發展過程,一般而言危機的發展,就是10到15年。
八九之後中國政府的一套「後天安門體制」的生存戰略有幾個特點,第一,是「菁英分贓」、「菁英聯盟」,但是現在菁英不聯盟了,因為分贓機制沒了,菁英團結不起來,變成菁英內鬥,以前是「抱團取暖」,現在可以說是「你死我活」,菁英一旦不團結,威權政權的可持續性就降低很多。再來是,中國外部的國際環境已經改變很大,在後天安門時期,中國在世界上是「韜光養晦」,現在是「鋒芒畢露」,這又帶來了很大的變數。
報:中國的世界經濟地位正在取代美國?「經濟發展卻政治收緊」將帶來什麼後果?
裴:對。但這不一定對中國是好事還是壞事,很難講。弄不好,中國為了在國際擴大自己的影響勢力範圍,投資過多,可能就犯了跟前蘇聯一樣的毛病。
你要搞經濟改革,政治上必須放權,中國的經濟還是被政府管得太多。但共產黨政權如果對經濟資源放棄了,它的政權的根基就不穩固了,因為它是通過對經濟資源的支配來維護許多人的政治忠誠,政治改革會把它的基礎給摧毀。
而經濟發展的短期效用,對專制政權的生存還是有用,因為它有合法性,有更多資源籠絡人心、加強社會控制;如果沒有錢,怎麼雇那麼多網路警察,裝那麼多攝像頭。但它的代價就是,使專制政權的長期生存受到威脅。
我們可以設想人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自由,都要一定程度的安全、法律的保障,都希望能夠上網不受管。這些價值觀是跟教育水平、經濟水平的發展是正相關的,經濟及教育水平提升,人們越會不認同現有政治體制的權威,開始覺得「你憑什麼管我?你不是我選的!」
報:中國需要什麼形式的政治改革?中國若有機會民主轉型,反對黨從何而來?
裴:這很難預測。但可能的有三類形式。第一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菁英「改良」。就像是蔣經國,他看到長期國民黨是沒有前途的,非得通過改變遊戲規則,才能給國民黨帶來新的政治生命。這種改革不能太晚,要在「綜合危機」到來之前,反對力量還不是那麼強大,人民對你還有希望,太晚「改革」肯定會導致「革命」。
第二個改革類型是自下而上的「革命」。革命聽起來好像令人鼓舞,但實際上成功率很低,我做過研究,因為專制政權有絕對暴力上的優勢,一般來講,只有在幾種情況下人民會起來造反,一種,是選舉不公正,例如台灣的「中壢事件」,導致人民上街大多是因為掌權的威權政權在選舉舞弊,菲律賓、烏克蘭都是例子。第二種,是國家打仗打輸了,老百姓很生氣,例如希臘、阿根廷。再來,就是經濟危機、銀行崩潰,這種是少數。
第三個類型是「改良」導致「革命」,政府一開始是要改革,但是改革釋放出來的革命勢力,往往是因為改革改得比較晚,政權已經比較虛弱,正好讓革命勢力起來,像是前蘇聯。
而中國最大的課題就是,他是否已經喪失了改革的時機。
至於反對黨很關鍵。一般來講,在一黨專制的社會裡,反對黨的出現都是舊的統治菁英的分裂,他們可能是黨內政治權力鬥爭當中的輸家,薄熙來就很可能像這類人物,像是前蘇聯的葉爾辛,搖身一變變成民主派。時間一到,他們會像是雨後的蘑菇一樣,到處都是。
報:十九大後,習近平會繼續打貪嗎?怎麼看打貪目前的成果?
裴:打貪,我估計很難再繼續,因為中國政府先是「破」,然後要「立」,成天都是破,你沒業績啊!打貪只是解決了過去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問題,所謂「立」,特別是經濟改革,讓人民有新的方向,「中國夢」還是比較含糊的事情,因為中國一般的民眾最關心的還是生計問題、教育問題、醫保民生問題,這都跟經濟發展有關,涉及到新的政策出台。
習近平的第二任裡面一定要「立」,因為以前所謂「九龍治水」的時代,九個政治局常委的權力過份分散,中國政府辦不了事情,但現在是「一龍治水」,大權一人在握,大家就要看你的政府是否能夠辦事。
而打貪在中央一級層面,有清除異己的政治效應,但使共產黨整個官僚機制變得「消極」。許多規章制度使中國官員感到不可接受、感到繁瑣,他們不幹活了;再繼續下去,沒人給你幹活你怎麼「立」?他一定要使中國官僚機制的積極性可以重新調動起來,最起碼就是,打貪不能再打了。
報:習近平上台以來強勢作風,對台灣都有一定程度的震盪。這樣的趨勢下,你認為台灣社會應該如何應對︖
裴:習近平是一個很強勢的領導,他肯定要在台灣問題上顯示出個人權威,不僅是台灣問題,香港問題也是一樣,他是全面強硬的,這種局勢下去就是導致僵局。中國的影響在過去10到15年裡擴大了不知道多少倍,北京有更多資源能力在國際空間壓縮台灣,你說承認九二共識是投降了,放棄九二共識門檻也很高,你說引進外力,美國恐怕不太可能,在這個問題上,川普不是很關心,也不是很懂,他的言行都是受很偶爾的因素影響,就像是他做其他事情一樣,沒辦法事先做判斷,不可預測,所以我說僵局。
報:怎麼看台灣公民社會的發展,對中國公民社會的影響?而你怎麼看待中國「網路愛國主義」對公民社會交流的影響?
裴:台灣公民社會是一個很發達、很健康的社會。台灣就是一個「典範」,台灣自己做的事情傳到大陸去就是影響大陸,人不用過去。「網路愛國主義」實際上起到的效果是「網路賣國主義」,國際形象、外交政策會受負面的影響。「小粉紅」去年台灣大選之前到蔡英文臉書留言,起的效果是適得其反,就像中國有個詞:「愛國賊」。
報:中國崛起,國際上越來越多國家不承認台灣的存在,但台灣的主體性又日益堅強。台灣不同世代對兩岸關係的判斷有些落差,年長者感到悲觀,年輕一代傾向宣揚台灣民主,主張台灣優先,你怎麼看台灣內部世代間想法落差?
裴:我是這麼解讀,中國政府的政策不一定能達到它所希望的效果,就是使兩岸人心向背,有許多是它控制之外的,它怎麼來使台灣的年輕一代認同中國,這,很難啊。你不可能靠高壓政策,我看北京至少現在是找不到出路。
外部壓力越高,人們對自己的認同越強,這是很自然的。但這只是一種心理上的反抗,在實際層面上是實力之間的較量,僵局要靠實力突破,而不是靠情緒或一廂情願來突破,我想,對兩岸最好的忠告是:「謹慎」。
做任何事情都要謹慎,當然這話對北京來講比較難一點,因為它認為它有很多實力跟空間做它想做的事情,台灣更主要的是保持島內的團結、穩定,使台灣的民主成為一個很成功的民主,這是台灣自己能做的事情;在台灣控制之外的,是美國政府的台灣政策,台灣雖然有辦法去影響,但是沒有能力來決定,台灣能做到的是島內先團結。
台灣的命運跟中國的命運是綁在一起的,不管你對它感興趣、不感興趣,現實要求你不得不對中國有一定基本程度的瞭解。我想年輕人的樂觀,也許部分來自大陸今後的經濟發展,最終還是能夠導致政治變革,只是在這之前,台灣能起到自由民主法治的作用,他們那一代,可能會看到更光明的兩岸關係。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