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年多前,台南地方法院前發生一件震驚社會的殺人案:男子洪當興將談完離婚的妻子與其律師撞死。該案一、二審皆判處死刑;2020年中,最高法院發回台南高分院更一審獲得減刑,改判無期徒刑,「逆轉免死」引發輿論譁然。然而,更一審法官前所未有的在我國死刑案件中,聆聽孩童的聲音,判決書中不僅呈述洪男與受害前妻未成年小孩的心聲,並透過詳細的量刑前社會調查,完整建構孤立的「犯罪人」之外,一個活生生「社會人」的樣貌,更在司法的末端嘗試架起一座修復與療癒創傷的橋梁。
近年來,重大刑事案件死刑與否的判決,常因量刑標準不一致而飽受外界批評,人權與正義孰輕孰重的兩極觀點,幾乎使得相關議題的討論難有交集。暫時放下二元的價值對立,洪當興案開展出一個重新面對社會、家庭結構與對話的可能。(2021.1.21更新:最高法院三審無期徒刑定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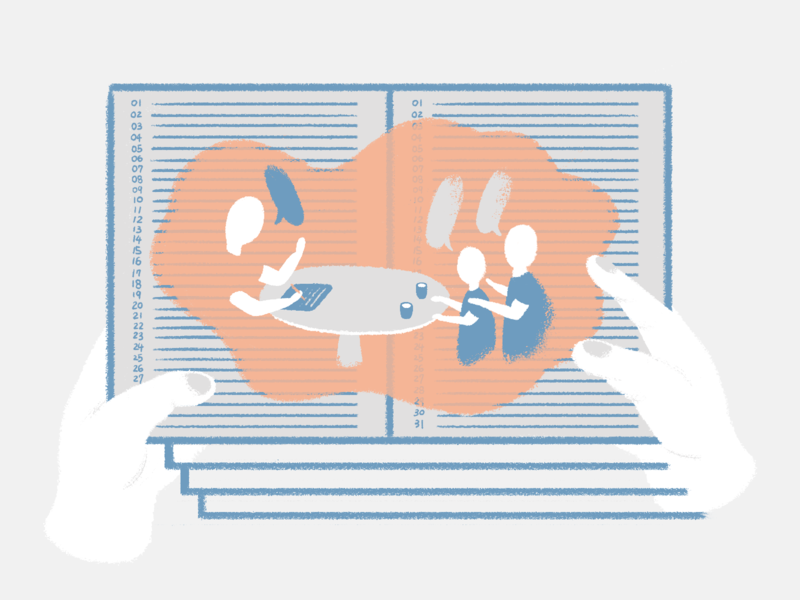
「若是爸爸真的被判(死)刑就再也見不到爸爸了;反之若沒有被判(死)刑則覺得對不起媽媽。」
D甚至無法說出「死刑」這樣的字眼,停頓多次,最後以「不能再見面」來替代。
判決書(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8年矚上重更一字第18號刑事判決)中,被告一雙未成年子女用單純的語言,訴說著面對這起家庭悲劇的矛盾心情。這是台灣死刑案件中,首次聆聽被告子女的聲音。
「爸爸殺掉媽媽,然後國家再把爸爸殺掉,孩子等於永久失去雙親,國家有沒有權力做出這樣的決定?在媽媽、爸爸、國家之間的關係裡面,什麼才是符合孩童最佳利益?」律師李晏榕說。
負責審理洪當興案更一審的台南高分院,為了執行沒有任何前例的「兒童最佳利益」鑑定事宜,委託熟稔家事案件的李晏榕籌組鑑定專業團隊,她同時也在司法程序中擔任兩位未成年孩子的代理人。
2017年7月17日下午3點30分,洪當興和前妻在台南地方法院完成離婚調解程序後,開車輾斃正要走出法院車道的前妻與其律師,兩人當場死亡。律師光天化日下在法院門口被害身亡,創下全台首例,引起司法實務界極大衝擊,一、二審皆被宣判死刑;被最高法院撤銷發回後,2020年8月台南高分院更一審改判無期徒刑,現正等待最高法院就此定讞或再次發回。
「聯合國的《兒童權利公約》(CRC,簡稱《兒權公約》)揭示,在任何有可能影響到孩子的司法判決中,理論上都要進行『兒童最佳利益』的鑑定跟評估,包括了解孩子的生活關係、社會關係、照顧者、現在生活狀況等等;在死刑案裡,沒有比洪當興案更適合進行此項評估,」李晏榕表示。
「家裡出了一個殺人犯,在媒體上呈現出來的家屬常會有『連坐』效應,經常遭受輿論的攻擊,像是『怎麼沒把你的小孩教好』,小孩可能也會承受許多汙名⋯⋯剛好藉這個機會,我們第一次這麼親身接觸到加害人的家人與孩子,可以感覺出來他們也有很多、很多話想說,」李晏榕表示。
「他們也承受非常大的痛苦,自己的兒子、弟弟、爸爸殺人,造成的創傷可能不亞於親人被殺掉,他們都是從電視上看到,會一直不斷地問自己『到底為什麼?』那個問號是從事情發生當天就開始,震驚之外也會自責,怎麼沒發現他的婚姻狀況、沒能做些什麼阻止這個遺憾發生。」
案發後,寄居在親戚家的姊弟倆,害怕黑夜,即使大人同睡,時常在半夜裡驚叫,開燈到天明。去看守所探視時,眾多親人圍繞以及時間短促無法多言,見到父親流淚不止。
從2019年9月到2020年5月,鑑定團隊耗時近9個月,從開始擬定計畫、法院程序、建立關係到執行訪談與撰寫報告,完成了這個史無前例「聆聽殺人犯子女」的任務,像是為兩位孩子開了一扇窗,得以直面巨大的問號。
「一開始就很清楚表示我們的角色是協助他們表意,把他們的想法清楚呈現,讓他們的需求被了解、受的苦被聽到;原則上用開放式的問句:『你怎麼想、希望怎麼樣』,不會講『怎麼樣好不好?』這樣可能會預設立場或有引導作用,」鑑定團隊成員、心理師蘇淑貞解釋進行訪談工作的原則。
「一直壓抑著不談,所受的創傷就很難過去,若開放的談,有時能重新認識這些痛苦, 而逐漸調節情緒,做較具建設性的修補。」她強調。
透過詳細的鑑定報告,洪當興的女兒傳達希望有機會與父親面對面,說清楚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並瞭解爸爸那邊的家人是否曾疼惜母親、是否不再把錯歸在母親身上,「也有個信念,有問題必須開放溝通才能解決,很希望家人間能開放來談,期待帶來情緒的平復。」
而弟弟則一度表示要寫信給法官,但受限於表達能力,鑑定團隊成員、 心理師張嘉紋替他具體擬出3種可能情況:
1. 若爸爸(被告)不在了,影響或感覺為何? 2. 若爸爸仍在世界上但是無法一起生活,影響或感覺為何? 3. 爸爸仍在、且能夠一起生活。
承審法官侯廷昌在判決書內如實引述弟弟的回答,毫無修飾地讓孩子訴說出內心深處的聲音:
1.若是爸爸(被告)不在了,會覺得最親的人都不見了,而且以後自己也沒有父母了; 2. 會比較不難過,因為至少還能見到面,並認為若能夠兩個月探視被告一次,雖然無法一起生活,但是內在的感受仍是較好的; 3. 認為爸爸仍需要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因此此種狀況較難以想像,但若是年老後一起生活,認為自己會照顧被告⋯⋯知道被告因為犯錯而需要付出代價,只能期待有一天可以跟爸爸同住,並明確表達不希望自己在世界上無母也無父,相信自己會持續探視被告,保持聯繫。
脫去艱澀的法律術語與道德譴責的窠臼,在不可挽回的悲劇之後,透過理解孩子們的惶惑與傷痛,司法最末端的判決跨越罪與罰的高牆,猶如搭起一座理解與對話的橋梁。
「相對於剝奪案父的生命而給孩子們留下一個大大的未竟事宜(unfinished business ),使其內心終身都卡著一個未解之結,且造成之巨大創傷性更難將相關歷程處理完整,個體傾向壓抑或迴避相關記憶,卻又因未完成而常常縈繞心頭,不如在專業協助下,給予孩子機會及時間與被告做深入開放的溝通,處理他們的困惑,調節他的情緒,更能夠讓他們減免因之而來的情緒困擾或適應困難 ,使學習的狀況較為穩定,心理素質愈強愈穩定,日後更有力量面對外界風風雨雨,處理解決自我情緒及人際關係等方面之困擾。」
兒童最佳利益鑑定報告的結論如此寫到。然而,在透出強大的療癒希望之中,現實仍有其無可迴避的局限。
「對法院來說,案子判完這件事情就結束,但這個家庭、孩子們生活都仍舊是持續下去;我們做完報告後,看到這個家庭需要很多支持,連照顧者都深受創傷,很希望有人可一直陪伴他們,要持續讓他們充分表達想法與感受,學到新的互動方式。遺憾的是我們好像開了頭,但後續的資源接不上,」鑑定成員之一的社工師李姿佳表示。
鑑定人被賦予的任務僅止於盡量中立、客觀搜集證據,難以再跨入治療或諮商的角色,在現行並無相關制度性做法的情況下,鑑定團隊只能無力地看著大人與孩子在往後漫長歲月等待彌合的傷口,即便相較於更多的受刑人,洪家已經擁有相對豐厚的支持網絡。
另一個缺憾是, 在進行對各方人員訪談階段,被害人家屬因感受強烈傷痛,未能接受團隊訪談,而少了部分被害人家屬的聲音,使得訪談拼圖有了缺角。鑑定團隊無法獲得所有相關人士意見之全貌。
「整個過程中可以明顯感到,法官扮演push(推動)的角色,希望大家都進來,有點像修復的概念,但已經被一個框架給架住了,就是兒童最佳利益,」被害律師家屬的告訴代理人趙培皓說。
「自覺心裡的痛到死都會帶著,其若給被告機會,那麼誰給其機會」,法官在判決書的「量刑審酌事由」中,引述被害律師妻子的話,如往常一般買早餐送丈夫出門、聯繫上車開會事宜的她,再次見到的丈夫是「已經整理過的遺體,沒有最後一面,沒有最後一句話」,夫妻倆許多共同的夢想與計畫都無法實現,使其頓失人生意義,再多的探問甚至心理諮商,也可能是另一種折磨,掉進更深的漩渦,獨自承受失去摯愛的失落與無助;被害前妻的父親,更幾乎無法用言語表達對於心肝女兒的不捨與心疼,「選擇透過沉澱及收藏的方式來處理失親之痛」。
「當事人的直覺反應是,為什麼要做這個(鑑定)?每個人療傷的方法不一樣,他們就是覺得不想要談了,不想要再揭開這個傷口,這就是療傷的方法,為什麼還硬要我再把它割開一次?另外從整個判決書可看出來,法官很大篇章在講被告及他的孩子,被害律師的遺孀好像不見了,就告訴代理人的角度,對被害人不平衡,」被害妻子家屬的告訴代理人林媗琪強調。
由於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是以被告為主體,被害人家屬猶如法庭中的邊緣人,最關鍵的調查證據,訊問證人、鑑定人或被告,上訴權,都只能由檢察官進行,即便2019年底三讀通過加強被害人訴訟參與新制,有學者認為其在法庭中弱勢的地位並無改變。
更一審因自首認定與考量兒童最佳利益,「逆轉」成無期徒刑的結果,家屬無法接受,檢察官提起上訴,主張要維持前兩審的死刑。

「你很危險,內向的人很危險,我建議你看一本書:《教出殺人犯》。」
在話筒雜訊與周遭探親家屬重重交織的聲浪中,洪當興的聲音傳到耳際,以「過來人」的姿態鄭重對前往採訪的我提出忠告:「某次出版社到看守所辦書展時,看到書名就想買下這本書,因為我就是殺人犯。」他如此強調著,話裡沒有任何自嘲或玩笑的意味。
更一審後被羈押在台南看守所,等待最高法院定讞或再次發回前夕,我隔著會客室第13號窗口的金屬欄杆與透明壓克力板,感覺已經認識另一頭的洪當興有好些時日。
口罩遮住大半臉龐,仍可看到眼角露出的笑意,擠出一道道皺紋,像是倒垃圾時會在巷口遇見的鄰家中年大叔,親切、靦腆且過於平凡,完全難以連結起3年多前令人髮指的犯行。
在短暫10分鐘的會客時間裡,我盡可能快速描述過去數月透過判決書細節,看見一位台灣男性跌跌撞撞的成長經驗與走進婚姻後的困境,並表明由於這幾年也進入婚姻並生養兒女,對此深有所感──從以往的採訪經驗中深知,有時候必要的自我袒露是取得受訪者信任的重要步驟。
「反覆讀著這本書,一邊想著為什麼自己變成這樣子?為什麼從小就這麼害羞、不愛說話,是不是小時候某些經驗造成的影響?習慣一直壓抑忍耐,等到受不了時就會出現很大情緒,暴怒什麼的,很堅持自己認為對的價值觀,比如我會要求自己不隨便在路邊停車,若別人不這樣想或做不到就會很氣⋯⋯。」結婚初期,洪當興就曾因故砸鄰居車窗,由岳父母出面道歉賠償和解。
那天在家事法庭調解離婚的現場,洪當興完全沒有預料到太太會帶著一位律師前來。一路上沒有尋求任何專業協助、自行寫訴狀的他,聽到律師用強勢的語氣代表當事人陳述意見,更感到憤憤不平,一個外人怎能了解多年來他處在婚姻生活中的不堪與痛苦?甚至當面對著律師脫口而出:「你是她的『客兄』嗎?」等討論到兩個孩子到底要跟誰,雙方更陷入高張的對立情緒。
已和太太分居將近兩年,即便處在失業的焦慮中,洪當興仍花許多心力照顧陪伴兩姊弟、時常帶他們一同露營出遊,非常在意小孩應該維持原有的生活,始終不同意妻子此前一人一個小孩監護權的提議,他深知兒子很黏姊姊,要將他們分開是滿殘忍的事情,所以堅持不能拆散姊弟,兩方為此遲遲無法達成共識。但為人母思念小孩心切,又唯恐他們跟著失業的爸爸恐無法獲得好的照顧,因而在調解時臨時改變主意,爭取兩個小孩的監護權。
儘管過程不愉快,洪當興完成了分居後一直想離婚的心願,僵持不下的監護權問題,則只能未來交由法官裁判解決。然而,這段日子以來獨自帶孩子的身心壓力、對妻子不分擔撫養開銷的怨懟,加上方才律師不顧及他感受的言談⋯⋯種種不滿逐漸擴大難以消解,在他的內心累積到臨界點。
二審法院委託的其中一份司法精神鑑定報告中,嘉南療養院主治醫師郭宇恆具體指出被告內向性格與犯案動機之間的關聯:
「須將自己的家務事呈現在不熟之人之前,如調解委員、律師等,與洪員的內向個性可能有所衝突⋯⋯且個性內向者,對外界刺激較敏銳,故在強烈或長時間的社會活動後,內向的人容易感受較深⋯⋯待調解結束,洪員看到律師與其妻在路邊交談,律師的肢體語言顯得很得意,又想到調解過程中,無法暢快表達自己意見,自覺遭欺壓⋯⋯想報復而發生本案。」
案發後的訊問筆錄中,洪當興坦言開車正要從法院離開時,連續經歷失業、分居、搬家、一人獨自帶兩個孩子的沉重壓力與無人了解的心酸,無處宣洩的情緒滿溢:「那時開車到接近他們後面時,就是腦海中想到很多事情,想到自己的家庭、婚姻生活不是很如意,小孩子可能又不能在身邊,又工作上、生活環境種種一些許多不如意。」
近乎重複過往婚姻關係中易怒、容易失控的行為模式,只能採用攻擊的姿態來因應內心不知所措的挫敗感,洪當興有股強烈的衝動,要「嚇嚇」妻子與律師,遂降檔、加速,駕車偏往人車道路面中間位置前進,只是這次握著老舊廂型手排貨車方向盤的手,再也無法回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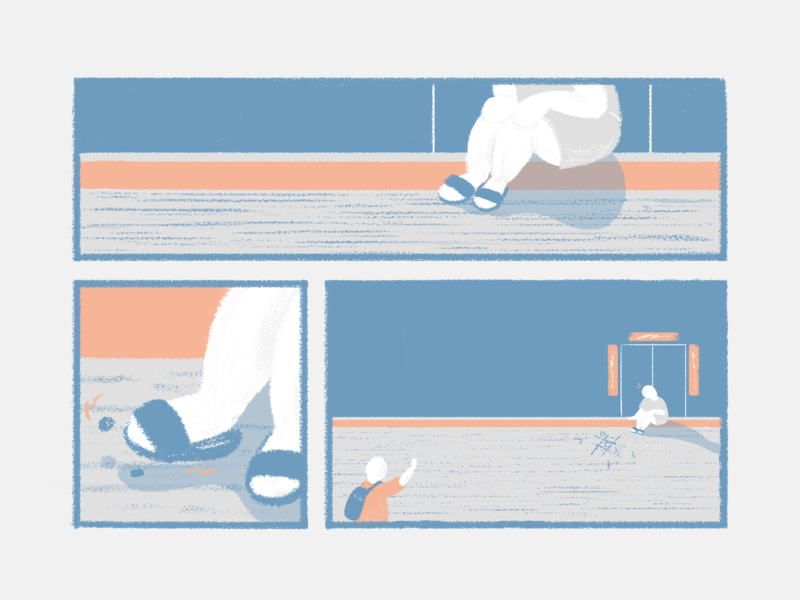
我爸媽他們去田裡不在家,然後我回來的時候,他就坐在那個門檻,然後門是關著⋯⋯等我們下課回來,他就是一個很文靜的小孩子,他不像別的小孩子,會亂衝亂跳,或是到處找不到小孩子那種,他就是安安靜靜那種。(0502訪談 ,大姐)
若非此案2019年底被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承審法官侯廷昌(時任台南高分院法官,現為最高法院刑四庭法官)重新針對被告的生命歷程做深入的調查,我們沒有機會窺見洪當興除了犯下最嚴重罪行的「犯罪人」之外,他過往生命歷程的真實樣貌。
1970年代,洪當興出生在彰化二林的家庭,是四個孩子中最小的,識字不多的父母在傳統農村靠著耕作與從事各種勞動工作拉拔四名兒女長大,父親雖偶會賭博但在困苦環境中仍努力工作養家,樂觀開朗是眾子女對其共通的形容,母親則是逆來順受、一切以先生為重的傳統婦女,雙親可說都在他們的能力與智識範圍的極限中盡力照顧家庭。
手足間感情良好,洪當興從小就是個內向害羞的小弟,親友間習於以閩南語稱他為「啞巴的」,「國小三年級時在學校遊戲斷手也不敢主動與老師說明,老師發現後才送醫院⋯⋯可能一 、二年級開始就有近視,某一個時間點開始看不清楚黑板,生性害羞不敢說。」報告中回溯他幼時的生活細節,生動反映其性格中不擅表達自我需求的一面。
但另一方面,他也從不令家人擔心,循規蹈舉在體制中一路考試升學,高中聯考考上彰化地區第一志願彰化高中,大學雖曾被退學但又重考上世新大學,是家族中唯一的大學畢業生。出社會後面臨不同工作的轉換階段時,未有懈怠地上課進修,取得微軟系統工程師認證(Microsoft Certified Systems Engineer, MCSE)後,朝向當時整體社會主流公認最有前途的資訊業發展。
2005年洪當興進入當時聲勢如日中天,以股價232元首度超越聯發科技、登上股王寶座的宏達電,不久後公司要在南部設立新的辦公室,更主動請調台南,看似即將在新的城市充滿希望地拓展未來事業。
10年過去,隨著市佔率連年衰退、股價持續探底,2015年中宏達電宣布全球裁員15%──該公司首度也是至今最大規模裁員,洪當興成為當時兩千多名被資遣者之一。
外在產業環境與工作變化的同時,家庭內部的婚姻關係也急劇惡化,他於訴請離婚書狀中用強烈的措辭寫道:「因生活理念與個性不合,婚姻生活曰益磨擦,致惡言相向,如同敵人。(民國)104年7月原告因服務公司營運不佳遭資遣,被告(其妻)旋即搬離雙方住所,留原告獨自撫養兩幼小子女,且被告也不願意負擔子女之生活及就學費用。雙方分居久未共同生活,已成路人,甚於仇人,實無維持及回復婚姻之可能。」

「法官在法庭上問我:『他們會吵架的原因到底是什麼?是夫妻失和、婆媳問題、還是教養或用錢觀念?』,對我來講真正的原因只有一個:兩個人安全感不足,使用的修復策略是錯的,安全感足夠的話,這些都不是問題。可能一般人都希望找到一個明確的原因,隔了幾分鐘,法官又繞回來問,『所以你認為真正的問題是什麼?』」
從廣泛的訪談調查中,宋旻諺從發展心理學的「依附理論」,將洪當興的性格界定為「逃避依附型」──從小就不習慣分享生活事件的他,對自己與他人情緒的接觸或感受程度都很低,傾向阻斷 、隱藏自己情緒的狀態,對於身旁的人而言,就是個一天到晚不知道在想什麼的「悶葫蘆」。
我們那群就是,也是要喝個小酒才彼此認識嘛,然後他就不喜歡講話,以我來推論啦,他就想和他老婆離婚,懸在心裡憋好久好久。(0513訪談,郭友)
家庭裡的許多重要決策,都是自己說了算,例如2008年在宏達電工作期間,因厭倦於「北部事情很多又很累,人又很多,就不喜歡在那邊跟人家有的沒的,有些摩擦」,沒有跟前妻討論就逕自請調到「天氣溫暖、環境單純、車子不多」的台南,到了隔年妻子與小孩才南下同住。自以為很不錯的決定,卻完全只是站在自我中心考量,連同種種生活瑣事,都讓前妻感覺到沒有「被在乎」。
加上洪當興與原生家庭關係緊密,婚後只要有空,都會回彰化二林的老家住,是眾人眼中乖順的孝子,但卻常常忽略太太的感受與需求,從訪談孩子的眼光中,爸爸通常不會站在媽媽這一邊,看到的媽媽是可憐、有許多委屈的。
「我在想,這個太太在生前一定很不快樂,在這個家她覺得孤立無援,」宋旻諺說,從旁人零星的印象,太太常表現出來的是脾氣不好的形象,高院二審其中一份由凱旋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王富強主責的鑑定報告中記載:「案主曾表示,對於前妻容易情緒化及某種動作、表情(教小孩不會時,會拍桌子、抓頭髮的動作)⋯⋯案主對前妻的某些情緒化動作感覺厭惡的。 」洪當興從早年成長過程中,就沒有學習發掘與表達自己內在真實情緒,在面對另一半情緒時的反應,不是也跟著一起生氣暴走,就是採取逃避或迴避的模式。
我是沒有聽到實際的話啦,但在我們聊天中,我覺得他被他老婆糟蹋到很累啦,因為我也是過來人啦,因為她就會講一些,「你也沒工作啦,你也沒路用啦」怎樣又怎樣「啊你兩個小孩是要怎麼養啦」。(0513訪談,陳友)
「這是造成夫妻關係失和的滿典型因素之一,雙方感情生變或外在壓力變大的時候,有一方積極想解決問題,表現出來比較嘮叨、惹人厭、容易怪罪別人,另一方希望息事寧人、日子能過就好,沒有不努力,只是不擅表達,」宋旻諺說,「要說誰對誰錯,表達含蓄好像是錯,因為沒讓對方知道自己的感覺,可是積極那方也是,沒有讓對方知道自己的不安,對方只是感受到壓力與憤怒而已,所以積極那方也是常常做錯事情。」
宋旻諺針對洪當興成長歷程的訪談與鑑定中,深刻著墨婚姻關係中,「一方愈攻擊,使一方愈防衛;一方愈防衛,使另一方愈攻擊」無限惡性循環的互動,打破男方=加害者/女方=受害者的二元對立,將一件每隔一段時間就可能出現在社會新聞角落的「失控莽夫家暴案」,還原成關係中的實況:兩個人是彼此的加害者,也是彼此的受害者。
「其實雙方都有表達自己脆弱的片刻,當太太講出內在感受,先生視為抱怨,聽不進太太內在孤單,就不會去回應,其實那時候太太需要被支持、被理解、被擁抱;先生有時透露感受時,被太太拒絕,先生也會覺得妳不能諒解、支持我,陰錯陽差之下,雙方一直漏接。」

「以前認為只要乖乖上學,吃飯睡覺守秩序,維持正常作息就好,卻忽略了孩子內心的感覺,沒有聽他們在想些什麼。我希望他們不要害怕,有任何煩惱或問題都要跟姑姑、或其他大人說,及時向外尋求幫助。」
此刻在我面前的洪當興,是一個充滿懊悔的父親,即使鑑定報告及判決資料裡面一再強調他是如何的深愛孩子,但只有他自己知道,那只是表象──這個社會賦予父親的角色就是要盡力看顧孩子生活起居,然而在衣食無虞之外,他未曾好好傾聽他們真實的感受,因為他連自己的聲音,都不懂得要如何察覺。
經過這段日子以來鑑定人員的密集訪談以及自己閱讀後的反思,他從法官眼中的「桀驁不遜」,甚至二審時聲稱不想浪費社會資源當庭解除律師委任,到現在願意面對過去,與當年那個被叫做「啞巴」的小男孩對話,問自己是如何走到今天。
更一審後被收押進看守所剛好滿4個月的這一天,洪當興提筆寫信給他的孩子,「我想跟他們懺悔,請他們原諒我這個爸爸。」
(2021.1.21更新)
最高法院於1月21日以109年度台上字第4461號判決駁回檢察官及洪當興之上訴,全案維持更一審判決,以無期徒刑定讞。最高法院新聞稿指出,更一審已詳細查明,警方在尚未釐清肇事原因以前,被告即主動自首,表明故意駕車逼近恫嚇,導致被害人遭其所駕駛之自用小客貨車撞擊,且其自首之舉出於真誠悔悟,非貪圖僥倖的狡黠陰暴之徒,依《刑法》第62條規定予以減輕其刑。
最高法院判決摘要並認同更一審量刑標準,除了以《刑法》第57條檢視一切相關情狀之外,還納入具內國法效力、包括兒童權利公約等國際人權公約,作為量刑考量因子。在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犯罪行為的嚴重程度與被告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犯後態度及其他有利及不利等一切情狀後,最高法院認為並無選擇科處有期徒刑之餘地,因而量處減刑後最重本刑──無期徒刑,並宣告褫奪公權終身。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