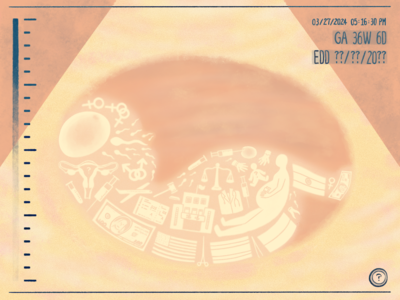長期以來,台灣未開放代孕,卻也不曾在《人工生殖法》中明文禁止;現實裡,有償代孕契約屢次因違背公序良俗,被法院判決無效。「不開放」不等同「不會發生」,即便多數代孕需求轉往海外,仍有少部分遁入更隱蔽的台灣角落,甚至形成一種詭境──由於欠缺明確法規可循,若有女性從事地下代孕並遭受剝削,不易尋求保障與救濟。
踏上代孕求子路的準家長同樣進入一場賭局,遊走其中的仲介及跨國業者,以及與代孕緊密糾結的人性幽微,再再牽動法律、人權與倫理危機。在孩子身世曝光與社會道德批判的壓力下,無論成功或受騙,家長傾向祕而不宣,資訊難以流通,給不良業者可乘之機。《報導者》獨家揭露橫跨台灣、泰國、烏克蘭等多地的代孕仲介糾紛,訪談多對在異國或台灣透過地下代孕求子的家長,為何涉險求子?付出什麼代價?亦爬梳台灣近20年的代孕相關判決,看見台灣本土代孕者的身影與心聲。
※為保護及尊重受訪者意願,以下多數受訪者以化名呈現。
「(海關)問小孩是誰的?媽媽是誰啊?」R太太(化名)回想,先生和寶寶被異鄉海關攔下的那天,她就像電影《不能沒有你》中的主角李武雄,內心盡是與法制交手的無奈、親子恐被迫分離的焦慮,以及,在孩子非法代孕出生的情況下,她無法回應自己是媽媽的心痛。
《報導者》近半年採訪發現,前往代孕非法國家的準家長從未間斷,可一旦踩入灰色地帶,下一個問題是如何讓寶寶安全、合法地返台。R夫妻就收過其他求救訊息──也是到非法國家代孕的家庭,在仲介遊說下竄改代孕寶寶身分文件,雖然出入海關順利,但文件瑕疵導致寶寶無法定居台灣;其中一對夫妻求助台南立委,只能一再申請延長寶寶的居留期限,避免孩子遭遣返回出生國。
而這一切,都是從仲介的「掛保證」開始的。

幾年前,R夫妻出世不久的孩子發生三度腦室出血,面臨未知後遺症,兩人決定不再搶救,「我就答應他(孩子),一定會再把他生回來。」然而,惦記著對已逝孩子承諾的R太太,卻被醫師判斷為高危險妊娠族群,在台灣代孕尚未合法化之際,夫妻將希望轉向海外代孕。 「本來想去烏克蘭,但沒有亞裔卵子,她(仲介)說,不然你們要不要考慮東南亞國家?」R夫妻透過幾個關鍵字搜尋,找上白菜寶寶協會,理事長吳素慧對他們如此提議,「我們問,那有合法嗎?她說沒有合法,但很快會修法,就會合法了。」
自身代孕經驗不僅成了吳素慧最強大的保證,她掛在自宅客廳的那張「政府認證」──白菜寶寶協會於2021年取得的內政部社會團體立案證書──更是R夫妻等委託者信任吳素慧的關鍵。
就這樣,R夫妻透過白菜寶寶協會,開啟了海外借卵代孕之旅。當時的他們還沒意識到,寶寶如何從代孕國出境,將成為最大考驗。
代孕寶寶的出生證明和DNA鑑定乍看之下,就像是R先生與外籍女子產下的非婚生子女。但因該國地下代孕興盛,這樣的「非婚生子女」數量不少,甚至在R夫妻入境前,警察才在當地飯店查獲非法委託代孕的外國人。「其實他們(代孕非法國)在抓,海關的立場就是,我一眼就看得出你是代孕,雖然沒有證據,但我的職責就是不讓你走,」R太太說。
帶孩子離境時,R一家果真被海關攔下,吳素慧及吳合作的當地仲介則建議「賄賂海關」,吳同步要求R夫妻簽切結書,聲明孩子滯留海外與協會無關。「(吳)拿到自己的利潤之後,不會去幫她的個案回家,但這不是她們身為仲介應該做的事?」R先生回想,其實吳的異樣早有端倪,接受委託前聲稱自己對流程很熟,問起寶寶返台文件要怎麼填寫,吳卻要他去問別人。
進退兩難的R夫妻,耗時兩個多月才終於從另一個機場將寶寶帶回台灣。兩人當時也做了最壞打算──如果無法返台,只好把孩子留在當地,等長大點再試著出境,「但這樣的話,孩子根本就認不得我們了。」
《報導者》採訪多位海外代孕委託者後發現,白菜寶寶協會的爭議不少,除了被指控轉介民眾到非法國家代孕,導致寶寶差點進不了台灣,或回台後無法入戶籍;不少委託者更在有求於吳「好好辦理代孕流程」的壓力下,借貸給吳數萬到百萬不等,許多款項至今尚未歸還。
「那是我個人(的借貸),不是協會的名義,」吳素慧回應,因為跟委託者彼此信任,才以「朋友」名義借款,且都有簽借據,並會加上利息歸還。吳素慧更喊:「不順利的(委託者)都會講,成功的都不會講。」
吳素慧強調自己只是分享經驗,但她也說,若有準家長確定做海外代孕,她會推薦委託者至合法國家,牽線讓委託者跟當地診所、仲介簽約,代孕款項不經她手,直接進到醫院或仲介戶頭,「我沒有(跟委託者)簽約啊,有任何人出示我跟他的合約嗎?我只說你(委託者)小孩的護照,到時候我會協助。」由於寶寶回台需辦理多項文件認證、驗證,吳表示自己僅在委託者提出需求時幫忙代辦,「我收錢是他們(準家長)委託我辦文件,我在莫斯科、波蘭都有代辦人,我要付錢給他們,我郵寄也要錢。」
曾與吳素慧打過交道的準家長Alex(化名)觀察,吳素慧在泰國主要與一名中國仲介Scarlet合作,還有一名華僑協助對接。由於吳素慧在2021年曾因仲介烏克蘭代孕,被法院依違反《人工生殖法》判處有期徒刑3月定讞,Alex與一名曾加入群組的民眾指出,吳現在用詞特別小心,會以「分享會」、「代辦/諮詢費」迴避法規,萬一準家長在國外出事,就以「自己只是提供諮詢」規避責任。若有準家長在群組提出對吳素慧的質疑,則會馬上被吳踢出群組,變成群組永遠只有講她好話的訊息。近年,仍不乏準家長指責她大幅墊高代辦費或向合作仲介收取回扣。
《報導者》接觸到的海外代孕受害者,其實不少是具備一定社會經驗與財力基礎的人士。他們為何願意將求子大事交託給素昧平生的仲介?前往代孕灰色地帶國家、發覺有異時為何未及早抽身?
「我當初也是這樣,會認為『我付了這麼多錢,你(仲介)就會想辦法』,」Alex曾在與不同仲介交手過程吃過幾次虧,他表示,在距離、語言與各國複雜的法規隔閡下,若仲介用熟悉的中文講出看似可行的流程,已是接近準家長的第一步。最關鍵且具說服力的第二步,是拿出「成功案例」。
「(問題仲介)他們的手法有點像詐騙集團,讓一、兩個人先成功,其他人看到他們抱回孩子,就覺得這國家可行。等付了錢,仲介再跟你說『不好意思這國家現在抓得很嚴』,要嘛繼續等,要嘛轉到別的國家做,這時你的錢已經被扣住了,」Alex說,「你會覺得怪、你會懷疑,卻又開始自我安慰,覺得應該不會被騙,就像詐團受害者最初也認為自己不會被騙一樣。」

對於欠缺可靠諮詢管道的準家長而言,網路上星羅棋布的仲介,成為隱密與即時性兼具的諮詢對象。仲介普遍態度親切,不分日夜在線回覆準家長的焦慮,亦有人強調自己也曾透過同一間機構成功代孕,能深切同理諮詢者的心情。久而久之,準家長無法向他人開口的問題,唯有對這位素未謀面的陌生人傾訴。居心不良的業者,此時悄悄張開心理陷阱。
在同家會的協助經驗中,極棘手的情況是在外國非法代孕,孩子生了卻帶不回來。黎璿萍表示,代孕牽涉到非常多親權轉移的法規,台籍家長帶著當地婦女生下的孩子出國,在沒有合法親權判決的前提下,極易被認作人口販運,海關要攔合情合理。有仲介表示會讓代母簽署放棄親權文件,但親子關係豈能用一張紙輕易解除?且就算這做法在其他國家行得通,在台灣不見得適用。「萬一失敗,仲介能幫你什麼?可是許多家長會心存僥倖,或聽曾鋌而走險的網紅分享,就覺得明明他可以,為什麼我不行?」

律師許秀雯就曾聽聞一個四處求助的案例。準家長赴海外代孕,礙於經濟壓力選擇非法管道,將代孕過程的各階段分散到不同國家進行,導致文件不實及缺漏,孩子好幾歲了還無法回台。許秀雯表示,很多個案是出了事才來到律師辦公室,「但如果有先開口問我的,我都一定會建議,要代孕就去合法的地方,如果有風險,或可能會傷害別人的事,我就會跟你說不要這樣做。」
雖多數代孕需求已轉往國外,但國人的求子路上,一直能見到本土代理孕母的身影。

民眾黨立委陳昭姿28年前開始推動代理孕母解禁,收到眾多想徵求或想成為代理孕母的信件。她將信件分類,發現各有200多封,「願意幫忙的人,跟需求者的人數是對等的。」自願代孕者樣貌多元,有希望在助人之餘增加收入的上班族母親,也有醫事檢驗背景的家管媽媽。陳昭姿那時會給需求者、自願者對方的聯絡方式,祝福她們有好的開始。
如今社群媒體成了撮合供需的平台,曾有網友開出120萬元徵求代理孕母,有些備孕、試管嬰兒社團裡的民眾,則會接到陌生加友與訊息:
「你好,有不孕的困擾嗎?我想當代理孕母,幫忙不孕夫妻的求子夢,可私訊找我詳談。」
《報導者》循線接觸兩名有意替人代孕的台灣媽媽,皆年約30歲,一人自稱已成功代孕一次,另一人表示正同時與3組準家長接洽。她們皆清楚無法在台灣植入胚胎,提議可到美國、或代孕仍屬非法的中國植入,再回台生產,期待的酬勞為新台幣150萬~200萬元不等,但在記者表明身分後皆未同意受訪。
自願代孕者還有其他主動應徵的管道。打開幾個簡體中文的代孕生殖網站,網頁寫著斗大的「代孕媽媽召集令」,透過電話或填線上表單就能完成報名,進入中國業者的資料庫。
也有自願者找上仲介毛遂自薦。「有3、4位台灣媽媽主動找過我,都是北部婦女,」在美國第三方輔助生殖公司任職的台灣人Hanna(化名)說,她接觸過的自願者,通常是有一定學歷與知識的女性,只是因為家有幼兒,暫時不適合朝九晚五的工作,才想代孕賺奶粉錢,希望至少實拿150萬元。
但Hanna清楚對台籍代母的需求不曾斷絕。有對和孩子一起諮詢的台灣老父母,才剛向她探詢找台灣人代孕的可能,這是因為想在代母孕期就近「照顧」。從同業口中,她知道台灣人會透過中國生殖中心、仲介找台灣代母,甚至有原本要捐卵的台灣女性接受條件改做代孕。
「沒有合法管道,這些(想找台灣代母的)人就會找非法管道,」Hanna說。
正在學走路的樂樂(化名)在客廳裡跌跌撞撞,全家的目光都繞著這孩子轉。樂樂藉一名台籍代理孕母誕生在男同志情侶Alan與Grey(皆化名)的家,喜悅的不只是兩個爸爸,還有Alan的父母。
Alan求學時期就對家人出櫃,爸媽要Alan試著跟女性交往,但性向不能勉強,許多年後,Alan帶著Grey回家,兩老不再反對,卻浮現兩個擔憂:「一是傳宗接代壓力,二是怕(兒子)他們老了,一個先走,另一個會孤單。」Alan爸爸說:「結果Alan告訴我們沒關係,就生一個,我們(聽完方法)馬上答應。」
生孩子原本就在Alan與Grey的成家規畫中,他們參加數場海外代孕講座,發現經濟能力無法負擔合法的美、加代孕,去非法國家又怕帶不回孩子。直到在網路上找到一位中國仲介,對方剛好認識一位台灣代母小蔚(化名),他們想,若能在台灣生產,就不會有小孩回不了台灣的問題。

確認僱請小蔚代孕前,雙方只碰過那次面。Alan後來跟小蔚深談,才知道她有債務。
小蔚流產後,Alan對阿媽說起此事。「阿媽說她村子裡有個人或許願意幫忙(代孕),她去幫我們談。」
阿媽為兩人介紹同村的女性小鈴(化名),由於小鈴不想提起過去,兩人對她的背景了解有限,只知道她30歲、有生育經驗。那時因COVID-19疫情無法出國,兩人先幫沒有穩定工作的小鈴租房子,隔年疫情趨緩,Alan與小鈴循相同路徑飛到泰國植入胚胎,返台待產。
「到小鈴懷孕中期,和她相處久了,覺得有些地方不太對勁,」Alan感覺小鈴的社交與認知能力顯得薄弱,孕期間持續在菸味瀰漫的麻將場出沒,多次不按照醫囑服藥,且難以溝通。他們原先按月支付小鈴餐費,後來擔心她把錢花在不該花的地方,改成直接幫她備餐。
當樂樂出生,從醫院社工口中,他們發現這已是小鈴第五次生產。在前幾段不知是戀情或其他原因的孕產歷程,最終都是小鈴離開與男方的同居處,男方留下小孩,或小鈴出養孩子,以政府的生育給付與生育獎勵金生活,然後再次懷孕。
Alan想起一件事。小鈴一開始就知道他是男同志,卻在懷孕期間到處跟村民說她是Alan家的媳婦。這是小鈴混淆了自己的角色,或她其實想在一段段懷孕生子的關係中找到她的「家人」?或她從一開始就沒有選擇其他生活方式的能力?
這樁交易是否對等也有待商榷──小蔚與小鈴確實答應委託方提出的金額與條件,但她們的心智狀態適合代孕嗎?同意前,是否全然理解代孕是怎麼回事?
Alan與Grey坦言,他們不是要惡意占人便宜,但他們接觸到的代理孕母,經濟與認知能力確實相對弱勢。在即便法規未解禁、有意為之的人仍會透過管道找台灣代母的情況下,Grey支持將代孕入法,尤其是自願者的生理、心理、智能與經濟狀況要審慎評估跟照顧。
最為隱蔽、卻也同樣不曾消失的,是協助國人施行代孕手術的醫療院所。
據現行法規,若代孕手術發生在海外,頂多負責招攬的台籍仲介被依違反《人工生殖法》懲處。若手術發生在台灣,委託者、代孕者、仲介與醫師都有法律責任,其中以施術醫療機構的罰則最重,醫師甚至可能被吊銷執照。但在記者為期半年的採訪期間,無論是台灣、中國、烏克蘭代孕仲介、台灣生殖診所與準家長,都對我們證實台灣依舊有極少數診所願進行代孕手術,除非經熟人介紹,或先與中間人洽談確認身分,否則無法輕易接觸。
由於《人工生殖法》適用對象僅限於「不孕夫妻」,而且妻子能以其子宮孕育生產胎兒,醫療機構為代孕者施術即為違法,可處10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行為醫師依《醫師法》移付懲戒;主管機關並可就人工生殖機構限定其於一定期間停止實施人工生殖。
此外,醫療機構實施人工生殖,依法不得應受術夫妻要求,使用特定人捐贈的生殖細胞。因此若機構接受委託者要求,使用代理孕母或特定人士的生殖細胞,可處醫療機構2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
仲介方面,若一併介紹精卵或胚胎捐贈者,即涉及生殖細胞及胚胎仲介行為,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2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金。
由於若沒有受術者與代孕者的行為分擔,醫療機構不可能自行違法,因此要求醫療機構進行手術、有犯意聯絡的受術者仍有可能依《行政罰法》,「依其行為情節之輕重,分別處罰之」。不過在目前公開的判決書中,未看到受術者遭罰的案件。
先天無子宮的民眾黨立委陳昭姿,收養兒子前也曾私下找過兩次代孕。當年她出面呼籲解禁代理孕母,眾多需求者請她幫忙介紹能做代孕手術的醫師,「我一律說我幫不了忙,你(委託者)要如何讓醫師相信你跟代理孕母都不會惹出麻煩?你趁沒有其他病人在場時自己去求,醫師信任你,就可以做。」
現在還有這樣的醫師嗎?陳昭姿毫不遲疑地說:「還是有,但要彼此信任。誰說不孕的不會輪到醫生?其實如果是同行(找代孕),大家會比較幫忙,因為信任你嘛。」
中南部一名不願具名的診所醫師,5、6年前就碰過在大醫院服務的同業,替親友向他詢問私下代孕的可能,「在大醫院是領薪水,為什麼要扛這個風險?所以大醫院是不可能有醫生願意做的。會做這個都是比較小的診所,都是大家Under Table(祕密地)講好。」也曾有患者跨縣市來到他的診間,「他(患者)就吞吞吐吐啊,說醫師能不能幫我?他們自己都找好(代理孕母)了。」
這名診所醫師推估,目前全台應該僅有零星幾間診所,還會私下進行代孕手術,「聽到風聲啦,不會很多,90%不願意做。簡單來說就是吃力不討好,賺一點點錢,但是要冒很大的風險。」

審理時,蔡姓夫妻強調自己不曾要求醫師植入這麼多胚胎,傅也否認違規,但法官認為唯有醫師能決定如何手術,認定傅有賠償責任,蔡姓夫妻免賠。台中市衛生局召開醫審會,傅保住醫師執照,其他裁處細節,衛生局表示已難以查詢當時的紙本公文。
記者致電傅嘉興,他說自己已70、80歲,想不起此案細節,僅透露當年這類私下的代孕請託「是非常多的」。在這通簡短的電話中,他最後深嘆一口氣:「(這類案件)醫生常是受害者,好的時候是(當事人)他們好,不好的時候是醫師不好。」
蔡姓夫妻與劉姓代母仍有案外案,據判決書,當時蔡、劉雙方約定以孕期每月2萬元報酬代孕,植入胚胎後,劉女極度不適,雙方改以口頭約定將報酬提高到120萬元,前期60萬懷孕第5個月前付清,後期60萬在產後支付。劉女懷胎3個月流產時僅拿到25萬元,因此對蔡太太提起民事訴訟,要求支付剩餘的前期代孕金額35萬元。
劉女的告訴代理人、律師邢建緯表示,《人工生殖法》未明確規範代理孕母,是立法機關的懈怠,可是沒規範不等於禁止。並主張:
「禁止(代孕)並不等於不會發生,尤其本質並非唯惡之行為,禁止情況下,只會讓當事人在更沒有保障的情況下祕密進行,對於所有當事人更為不利⋯⋯國家基於對人民基本權之保護義務,應積極立法確認各項相關之法律關係,以減輕可能發生之爭議,而非以駝鳥心態視而不見。」
時任新竹簡易庭法官陳順珍認為,代孕契約的產生,是基於順應生兒育女的基本欲求與需要,代理孕母是以此為動機而尋求醫學協助的產物,固然無可厚非,《人工生殖法》也確實未明文禁止代理孕母;但藉助人工生殖技術將生命誕生商品化、價格化並進行交易,的確悖於倫理道德。因此以違背公序良俗認定契約無效。劉女無法獲得她主張的剩餘報酬,也未再上訴。
這份判決,彷彿台灣數十年來關於代理孕母應否合法的論證縮影。在法律的模糊空隙,或許仍有大同小異的情節繼續發生,只是更替著人名與地點。
2024/12/4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2024年12月5日排審《人工生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代理孕母是否與開放單身女性、女同志適用人工生殖脫鉤處理,成為攻防焦點。衛福部長邱泰源指出,部版《人工生殖法》將代孕脫鉤,草案底定後,將送性別影響評估,擬於12月底送行政院。
本次各委員各黨團一共擬具16版本《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當中5個版本包括開放代理孕母,提案者為國民黨立委陳菁徽、王育敏、謝衣鳳,以及國民黨團、民眾黨團。除了交鋒最激烈的代孕,亦討論人工生殖子女身世知情權、代理孕母醫療風險等議題。台灣反代孕行動小組與多個民團在立院大門集會,指代孕將成為剝削女性的人權災難,要求退回代孕法案。
衛福部於2024年5月公告部版草案,開放單身女性、同志配偶適用人工生殖,且開放利他代孕。該草案採專章規範代孕相關事項,包括志願代孕者應通過身心評估、孕期間身體自主權、產後2年得探視代孕子女、有權依《優生保健法》終止代孕等權利。但身心評估程序與標準、中介機構資格等細節,仍有相當多細節是由「主管機關定之」,民團擔憂恐淪為空白授權。
草案公告以來,衛福部國健署均對外表示「無預設立場」,但12月3日下午突然改口脫鉤代孕。邱泰源答詢時指出,收到600多則對部版草案的意見,大約8成反對代孕。由於代孕尚無社會共識,衛福部希望多討論,故優先處理較無爭議的單身女性與女同志適用人工生殖,因此約在3週前就擬定脫鉤代孕,並向行政院報告,並未像外界所言的「急轉彎」。
民眾黨立委陳昭姿痛批,時任立委的總統賴清德,在2002年就提出代孕修法,時任立委的副總統蕭美琴還是連署人之一,民進黨昨是今非,是否為反而反?反對者口口聲聲保護孩子,但現在不乏家長尋求海外代孕,當環節出問題,代孕子女回不了台灣,難道這是對孩子好?
國民黨立委陳菁徽指出,政府及執政黨委員應提出脫鉤後的做法:會不會提出代孕專法?何時要提出?還是反對代孕到底?請衛福部不要永遠停留在凝聚共識,請民進黨對全國不孕女性以及有生育需求的男同志言明立場。
民進黨立委林淑芬表示,即便代孕議題歷經公民審議會議,但時日已久,當時的資訊未盡充足,不能以少數參與者代表多數人意見;昔日代孕電話民調的問題設計也有誘導開放之嫌。她強調,代孕形同轉嫁孕期的健康風險,若非經濟弱勢,誰願出借子宮?她不否認有女性願意協助代孕,但多數的「同意」,是在不平等下給出,生育權論述不能推導到開放代孕,也並非所有需求都要被滿足。
值得注意的是,對於捐卵、捐精子女的身世知情權,國健署長吳昭軍答詢時指出,知悉權是兒童權利公約的規範,衛福部也正研議「雙軌制」,捐贈者可選擇具名或匿名捐贈,精卵捐贈子女成年後若有意追溯,可在雙方同意前提下相認。
2025/1/10
2025年1月,行政院證實未納入代孕的「脫鉤版」《人工生殖法》草案已送入行政院審議。衛福部國健署長吳昭軍表示,由於代理孕母正反意見眾多,因此優先處理較具社會共識的女同志與單身女性適用人工生殖,且需保障子女最佳利益。對於代理孕母議題,修法、另立專法、擱置皆有可能。國健署將藉公聽會、專家會議等聽取各界意見。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