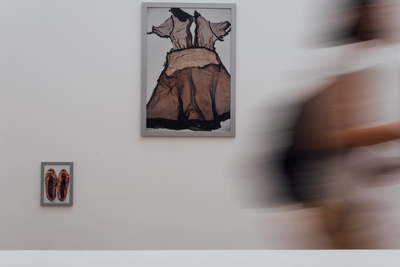在中場休息,意識還沒回神時,多位漠然表情的女性,倏忽從旁包圍觀眾席,彷彿身邊陌生的觀眾開始打架,他們拼命肉搏、扭打、纏繞,難分彼此地將身體肌肉扭攪一起,狠狠以近身戰毆打對方。之後出現多位披著藍色布卡罩袍的人們,不時團聚進行儀式性動作,並舉起藏於罩袍的槍。現場猶如發出槍鳴,雷射光在中山堂四處流竄,仿若人間煉獄,到處都在發生事件,有些女性蹲著躲避、有些倒地、有些則是逃難般牽引坐在座位上的觀眾,有人拿著石頭在觀眾席間對倒下屍體進行哀悼儀式。
一場戰爭沒有預警的席捲而來,雷射燈像槍擊軌跡般穿梭在觀眾席,演員、燈光、聲音、中山堂空間,與觀眾共同捲入沒法一目瞭然又不知所以地混沌風暴。
暴動之前與之後
在席捲台下的暴動之前,《不知邊際、不知所謂事件》以傳統鏡框式舞台的形式,邀請陳以文表演著冗長、毫無戲劇性、缺乏敘事性、沒有情感連結的現場口白,有如讀稿機般在講莫名其妙的台詞文本(例如「夢在尋找身體」)。口白同時交錯著同樣沒劇情、音畫不同步(時而抽掉現場收音)的巨幕運動影像——展示著異域人物的身體片段,人極簡地如同物件靜止,皮膚如雕塑般冷冽,鏡子裡曝光的攝影機,不時舉行一些單調重複的儀式姿態(玩弄鬍子眉毛頭髮、群體跑步繞圈、雙人對坐咀嚼洋芋片、抱貓咪),最終字幕揭示這是關於墨西哥「女性殺害」(Femicide)的殘忍事件鬼丘鬼鏟在墨西哥駐村的實驗影像作品《BUENOS DIAS MUJERES》(2019)以曖昧方式討論當地
女性殺害的問題。對照來看,
藝術家黃亦晨《最後身影之後》(2021)用攝影為主要媒材處理台灣女性在暗巷「被消失」的情殺案件。但黃的操作更加暴力直觀(例如鞭打底片);而鬼丘鬼鏟則是塑造相較模糊詭譎的體驗。
狂亂暴動後,回歸之前鏡框式舞台的疏離形式,口白與影像再次在台上交錯出現。但是觀者在看這些影像時,卻有了不同於第一場表演的感受,更加有精神地關注中場休息後的表演。如果說暴動之前瑣碎的口白與影像,讓人意識鬆軟地昏昏欲睡(很多觀眾睡著);那暴動與之後的場景則是讓人難以入睡,更緊張與專心地投入現場(腎上腺素爆發?)
什麼是「現場」?
8月,在台北藝術節登場的鬼丘鬼鏟《不知邊際、不知所謂事件》 ,以暴力為核心,碎片為操作,重新質問到底什麼是「現場」?近年來,不管是視覺或表演藝術,大量出現「現場藝術」(Live Art)的討論,如果說線上展覽的形式讓大家不在現場也能觀看,那現場展演則更關注觀眾「在場」的身體感。然而,「現場」絕非只是現場表演,而是一種「重新操作」的方法,重新分配觀者習慣的「感知」,讓我們不只是被動接受訊息,而是在特殊的情境營造中主動發生「改變」。
如果說傳統劇場的演員以戲劇化形式表現情感,試圖以眼神、口音、腔調、姿勢的人性姿態感動觀眾,吸引觀眾進入劇情。那前衛藝術到當代電影與劇場的演員,則是採取疏離、斷裂、碎片化、機械化、重複方式,讓人難以入戲以意識到舞台框架,沒法順著框內敘事走。例如濱口龍介電影中的角色,往往面無表情、單調跟機械,甚至在電影《在車上》(2021)的排練橋段,更直接要求演員不要抑揚頓挫的情緒渲染,單純唸台詞(當中主角亡妻在錄音帶不斷重複的台詞聲也是抽離情緒當代攝影也有冷面疏離的一脈在拍攝地景,也是不走感傷情懷,更不是私寫真的當下熱情,而是保持距離的延遲觀看。
陳以文角色的碎裂疊影
然而,陳以文不是扮演著西島秀俊,而是導演李奧森(敘述著拍片的過程),同時也是演員自身(探討演員的角色),演員與導演,兩者交錯並置,互相的影子重疊與轉化。可惜的是,我能理解李奧森想與陳以文形象重疊,借陳之口說出自己的話(濱口龍介之於西島秀俊)。但陳像木偶一樣蒼白的口白,成為導演喃喃自語文本的附庸,文本抽象詩意地連結「導演經驗」與「演員本身」的概念,卻較少進一步擴展「陳以文形象」(藉知名演員之口說話,但這口是「誰」都無所謂)。此外,冗長的碎片話語,再加上沒字幕,雖然去除視覺元素讓觀眾耳朵打開,更專注「聽」他到底在講什麼,但是因為太同質化的詩意操作反而讓觀眾感到倦怠。
碎片化的口白文本,讓人想到超現實主義的遊戲「精緻屍體精緻屍體為:摺紙遊戲,包括由多人完成的一句話或一張畫,所有人都不知道先於自己的合作內容。其中經典的例子是通過這些手段生成的第一句話,不僅成為經典,還是這個遊戲命名的出處,「精緻的—屍體—將會飲—新—酒。」
除了文本內容,鬼丘鬼鏟拍片中導演「不介入」,只給予演員一點提示,即興發展的方法;以及暴動中除了互相打架外,還有對觀眾展示拳擊、翻筋斗、體操莫名聚在一起等古怪表演;再加上超現實的場景佈置與詭異動作。這些荒誕的隨機組裝都讓人想到「精緻屍體」的方法。
夢、潛意識、暴力、荒誕、黑色幽默、政治行動等超現實主義的前衛幽魂,纏繞著鬼丘鬼鏟。鬼丘鬼鏟也「跨地域」地連結墨西哥與世界上各式各樣的暴力;末尾播放的影片《我可以瞌睡數百萬年》(2021),更是「跨時間」地將沉睡的人(拿槍的施暴者)與石頭並置,人在睡著時也像石頭/雕塑/屍體,而非殘忍虐殺動作與瘋狂近身扭打,沉睡「靜態」讓人與物(睡了數百萬年的石頭)的生命平等,彷彿透過影像定格,永恆地如同嬰孩安眠。
吞噬的死亡共同體
人類再怎樣瘋狂進行屠殺運動,還是「平等地」需要休息睡眠,以及必須面對靜滯死亡。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提到的「死亡驅力」,也揭示了人不只是有想求生的慾望(強調個人主體性);同時有一種想回歸無機物(影像中石頭)的毀滅慾望(毀滅主體,投入黑暗,交互溶解滲透)。
讓我們把時間拉到暴動後的「轉場」,在觀眾席之間瘋狂運動的表演者,並沒有離席,而是在燈光昏暗後,跟觀眾一起坐入觀眾席,一起觀看第三場的口白與影像,帶著身體互相交融在夢境般地影像與口白裡。暴動中拿槍的蒙面人、死去的屍體、漂浮的幽靈、影像中的石頭、沉睡的人、陳以文站在台上的身體、觀眾在場的身體,也相互在黑暗的環境中成為「死亡共同體」。然而,這並非是排斥非我族類,所建立的認同共同體(不是墨西哥人、台灣人或日本人的國族共同體)。而是屍體的、死亡的、暴力的、身體的、混沌、潛在的共同體,我們邁向死亡,投入黑暗,沉浸於「吞噬性體驗藝術史家碧莎普(Claire Bishop)在《裝置藝術:一部批評史》〈模擬性吞噬〉也探討裝置中死亡與消滅主體的驅力,我們不只是想保存主體,也有想被黑暗吞噬的慾望。碧莎普(Claire Bishop)(張鍾萄譯),《裝置藝術:一部批評史》,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21。
舞蹈理論家勒沛奇(Andre Lepecki)曾區分「觀看者」跟「目擊者」差異,觀看者只是消費被動和安靜地獲取各種訊息;目擊者則是更為倫理性與政治性地行動與轉譯現場Andre Lepecki. Singularities: Dance in the age of performance. Routledge, 2016.
王世偉精彩的《群眾》(2021),也有被迫參與現場的混沌調性。他們都不是友善邀請觀眾,而是不給予線索地讓觀眾突然被迫捲入風暴。只是說王世偉更傾向於表現街頭抗爭暴亂的身體情境;鬼丘鬼鏟則是把暴力的無意識、黑暗跟模糊性呈現出來。關於群眾與社運的討論可以參考我的文章
《為什麼我們要起身?藝術與運動》。
觀者也不止於現場劫後餘生的目擊者而結束(暴動不是最後,而是在中間),在最後一段倒地的死者與生者「重新做為觀看者」。觀看者不是被動地獲得資訊,也不只是主動行動介入,而是在影像與口白的交織中「既被動又主動地」體驗著共同的黑暗、暴力、夢境與死亡。
愛的間離:從影像批判到情境空間
劇作家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以降,乃至於導演高達(Jean-Luc Godard)與法洛基(Harun Farocki)在電影中運用的「散文體」,可以看到他們大量採用「間離效應」(Distancing effect),運用智性批判,讓我們擺脫劇作或電影對觀者意識的操控,透過知識分子的滔滔雄辯不讓人入戲,拆解劇場或電影後面的意識型態。
然而,鬼丘鬼鏟的文本與操作,幾乎沒有智識的批判,更接近個人獨白場景。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在討論黑暗空間與身體的文章《走出電影院中》提到的「愛的間離」,不只在個人智識運作,批判影像意識形態的操作,而是關於周遭的整個環境:影院、黑暗、房間與其他人的存在Roland Barthes. ‘Leaving the Movie Theater’, in The Rustle of Language, trans. Richard Howar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pp. 345–349.
不可見的暴力與睡眠政治
今天數位時代的暴力,不再是過去可見屠殺的血腥鎮壓,也不是對他者的排斥,哲學家韓炳哲在《暴力的拓撲學》中提醒我們暴力轉化成更加不可見、無限擴張與不斷強調功績效率的肯定主體。暴力不再是壓迫者跟被壓迫者的二元對立,而是二合一地「自我剝削韓炳哲確實指出現代人在網路上自我剝削的新暴力,然而在烏俄戰爭或香港抗爭的例子上,還是可以看到集權血腥鎮壓的傳統暴力模式,對他者的鎮壓並沒有消失。韓炳哲(Byung-Chul Han)(安尼 / 馬琰譯),《暴力拓撲學》,中信出版社,2019。
喬納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許多 / 沈河西譯),《24/7:晚期資本主義與睡眠的終結》,中信出版社,2015。
長期以「睡眠」作為方法的泰國藝術家阿比查邦(Aphichatphong Wirasetthakun)作品中也有許多暴力橋段,他不是直接展示可見的暴力,而是透過不可見的暴力聲響、煙霧與裝置,間接訴說軍政府的屠殺。鬼丘鬼鏟的暴力也更偏向情境的營造,而不是直接給觀眾看暴力的殘忍畫面關於處理暴力手法的另個極端,對照柬埔寨導演潘禮德的散文紀錄片《惡之三聯畫》(2020),重口味引用大量屍駭、腐爛肉身、殘肢破體的大量影像,讓觀者視覺感到難以承受的暴力,同時透過影像串連世界戰爭與屠殺的暴力史。鬼丘鬼鏟則更關注暴力不可見的模糊與幽微氛圍,他不是丟出屍橫遍野的奇觀,而是讓我們回頭看待平靜「日常的暴力」。
鬼丘鬼鏟運用去中心化、碎片、讓人沒法一目了然的方式,觸及無以名狀的暴力,啟動觀眾另類的感知,觀眾被迫吞噬於黑暗中,與各種不同物種(屍體、施害者/受害者、石頭等)交織與沉睡。
然而,今天的網路平台跟虛擬貨幣助長地運作方式不也是去中心化的碎片嗎?我們不也跟大數據互相交織嗎?碎片化的劇場形式如今還有抵抗性?大數據不也是把我們變成情感過溢的殭屍嗎?為什麼我們要不斷在社群媒體發表?為什麼我們要不斷更新與優化自我形象?在看似自由、多元表達、肯定積極、不斷活躍、碎片化地數位永生情境中;為什麼我們不可以一起重演死亡、一起抱著石頭入睡?
以餘生哀悼死亡
鬼丘鬼鏟不是以一種苦情、強調正義、替弱勢發聲、剷除暴力的方式站在道德高位說教;而是以模糊、曖昧、無邊無際的「美學」讓人「體驗空氣中暴力的無以名狀」。跨地域與時間地連結行星普遍存在的暴力(不只探討特殊地域的暴力,如台灣之於白色恐怖),與人類內在的毀滅傾向(在黑暗空間的集體消融)。
導演諾蘭(Christopher Nolan)的《黑暗騎士:黎明昇起》(The Dark Knight Rises)2012年在美國科羅拉多州奧羅拉市(Aurora)的16世紀戲院(Century 16)首映時,昏暗的電影院發出響聲與火光,子彈隨機朝觀眾席射去,現場一片混沌的血腥味,影像跟現場的界限徹底混淆。《不知邊際》雖然在中場休息時突發暴動現場,但最後並不是鼓勵行動,反而是透過影像跟口白,引導我們閉眼入眠,面對無法預期的暗黑未知。在黑暗中解構「導演/演員/觀眾」涇渭分明的控制關係,劇場中固定位置的身分開始變得模糊,我們聚集、擺放石頭儀式、一起用身體睡著,抵抗大數據經濟無孔不入的精神控制。
我們在槍林彈雨後的餘生,共同哀悼16世紀戲院的死者、墨西哥女性殺害事件、烏克蘭戰爭的屍體、演員本身、劇場觀眾還有潛藏於日常角落的種種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