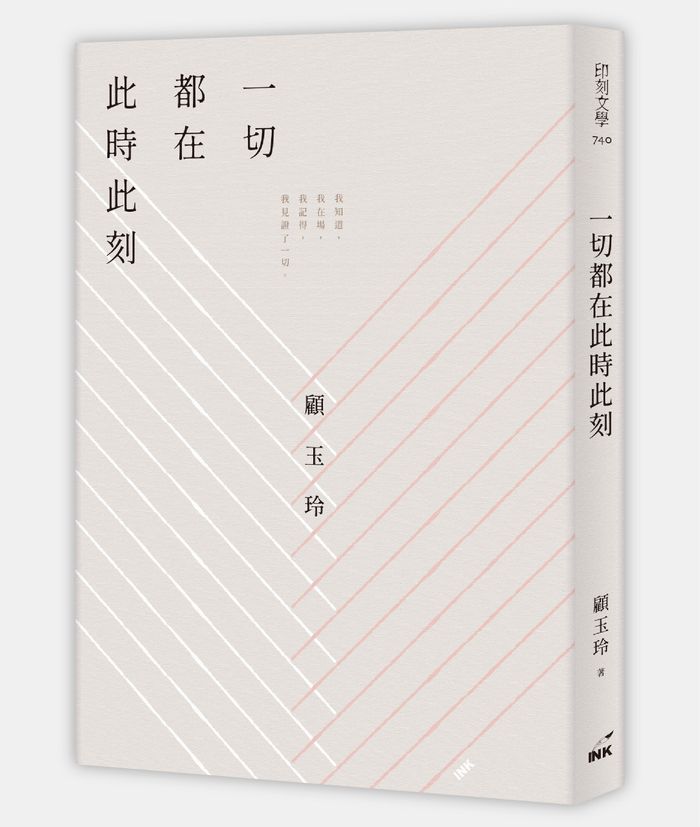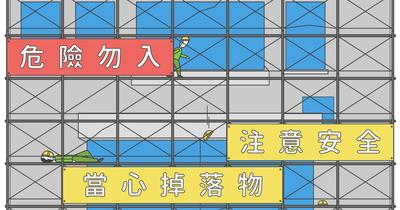精選書摘

台北藝術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作家顧玉玲曾任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祕書長,著有非虛構作品《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與《回家》、長篇小說《餘地》,並主編《木棉的顏色:工殤顯影》、《拒絕被遺忘的聲音:RCA工殤口述史》等書。在其新書《一切都在此時此刻》中,從各種極限勞動環境到職災細節,她顧及性別、階級、族群的多重面向,親證還原組織現場、勞動狀況與工傷後的修復之路。
本文為《一切都在此時此刻》之〈死了一個原住民臨時工之後〉部分節錄書摘,由印刻文學出版授權刊登,記述一個東埔部落布農家族的工傷故事──史家6個堂兄弟中,就有2個職災死亡,1個終身殘障。原住民「意外死亡」比漢人高出一截的機率背後,真的是那些「酗酒、打架、低學歷、不穩定就業」刻板印象與成因嗎?
史文秀和史亞山是堂兄弟。國中畢業後,他們一如部落裡許多年輕人,都曾經到台中、台北打拚,在住商大樓、地下道工程、環山公路等營造工地流轉,販賣勞力以賺取生活所需。
九○年代初,政府以缺工為名,開放企業主大量引進廉價移工,原住民更被推上失業浪潮的峰面。文秀和亞山退伍後,城市已然不容易找到工作了,他們先行撤離,回到部落,和同村的布農女孩結婚、成家,共同面對偏鄉生計的窘境:投注全家人終年辛勞的農作,在不平等的產銷結構裡,被中盤商一再削價抽成。市價高昂的優質高山茶,兌換進入茶農口袋裡的,連基本維生都有困難。
亞山父親留給他的三分地,全年種茶所得不到11萬元,「還不包括肥料、人工費用。」亞山說。
回到部落後,他們的身分被納入勞動統計高達30%的「原住民從事農、林、漁、牧工作人員」,彷彿就此安身立命。事實上,農作價賤的事實,逼使部落原住民不得不兼打零工以維持生計。但官方資料中,大量部落原住民身分轉換為「務農」後,就輕易地從失業率的分母數刪除了,享有農保的福利,也同時意味著不得在打工時加入勞保。也就是說,當下原住民失業率較平地工人高出兩倍的數字,掩藏了太多「不完整就業」的黑數;而部落農民的工傷,也無法呈現在勞保的統計數字裡。
農閒時分,東埔部落的青壯男女,常態性地等候在臨時工市場,待價而沽。一旦有漢人做不來的高地勞動,就有小包商到部落裡找人,按日計酬。
「揹重物走山路,漢人是不行的啦!」東埔一鄰的鄰長柯進平說,下意識流露出布農獵人不擅誇耀的得意與自信。
1969年,交通部氣象局在玉山北峰海拔3,858公尺處,設立全台最高的氣象觀測站,之後又增設太陽能板,自立發電以維持觀測運作如常。許多登山客都知道,若要攀爬玉山,塔塔加是車行最終站,再來就得徒步上山,起碼要花上4、5個鐘頭的路程,才能抵達北峰。即便是搭乘直升機,北峰機坪距氣象站台也有幾十公尺的陡峭山路,重物搭機直上山頂,卸貨後仍需要人力負重攀行長路。
崎嶇山路上,多依賴擅負重、走山路的布農族人,將太陽能電瓶及配件分批扛上北峰。基於地緣之便,東埔一鄰最常受氣象局徵召,將觀測站所需要的物資、食材補給,以獵人的登山鋁架裝載妥當,一次次送抵最高峰。
1998年4月間,鑫閃公司承接北峰氣象站太陽能電瓶運輸工程,山上積雪未融,工程早已落後,緊急透過氣象局官員至東埔部落召募臨時工,一天工資3,000元。彼時春茶才剛收成,部落裡的人多數沒有自己的烘製廠,只能將高品質的茶葉論斤賣給漢人經營的製茶廠,偶爾再受聘於工廠充當曬茶、揉茶工。或者,就是不定期的登山揹工、公路修道工。忙完春茶,文秀與亞山就應聘鑫閃承包的氣象局工程了。
上工第三天,文秀和亞山天未亮就從東埔一鄰開著農用小貨車,直抵塔塔加。凌晨5點開始工作,他們將重達70公斤的太陽能電瓶,一支一支地扛上直升機下的大型吊籃,運載至北峰再交由另一組工人們揹著電瓶,走最後一段路程。從塔塔加停車場到臨時機坪,一人一電瓶,彷彿是兩個體重相當的人扭在一起搏擊,扛著走,走著扛,汗水滴落機坪都來不及被日光曬乾又濺上新的。他們一路忙到下午2點,山上起霧了,領班宣布停工。
從塔塔加返回東埔的下山車程中,副駕駛座上,文秀已然疲憊陷入昏睡。亞山開車,順著山路滑行一個多鐘頭,即將經過和社時,小貨車突地打滑,橫越馬路,撞上對向車道旁的電線桿,跌入山溝裡,整個車頭都壓扁了。亞山胸部嚴重挫傷、右腳踝粉碎,文秀則傷重身亡。
當時任職於南投家扶中心的競中,每月一次開車上山進入東埔部落,為淑娟家兩名稚子送上低收入戶的扶助金各600元。偶爾,競中和亞山一起沿著聯外道路散步,他們各自眺望沙里仙山谷,久久不曾交談。一年後,競中辭去社工員工作,北上投身工運組織,積極連結工傷協會、工委會關注原住民勞工議題,尋求改變現況的可能。我們於是共同上山,繞行6個多小時的車程,進入國家公園深處的東埔一鄰,趕在兩年職災求償期限前,和族人們討論職災勞資爭議與相關行動。
真的可以爭取嗎?依法有據嗎?沒勞保的臨時工也可以求償嗎?
「我很怕,怕遇到警察,怕又要上法院,怕亞山又要被關。」美珠原本是退縮的:「我看還是算了吧。都已經兩年了。」
倒是亞山說了:「我自己,慢慢可以走路,可以工作了。可是伍淑娟太辛苦,如果還可以爭得到什麼,就為她爭吧。」
淑娟不在場,她在家裡照顧婆婆吃藥。雙胞胎雅瑟、雅各從屋裡跑到屋外又跑進屋,和亞山的孩子們追逐玩鬧。

「東埔一鄰那件事啊,死了一個原住民對不對?」
問清楚職災是發生在下班後途中,與提供直升機的廠商沒有關連,中興航空公司的經理明顯鬆了一口氣。他很快地調出了直升機起降紀錄、相片、飛行員簽到本、收據,並熱心地佐證:「工程都已經延後了還發生這樣的事,實在很麻煩。收工下山時出的車禍對不對?原住民工人一定是喝了酒。」
相同的「原住民工人一定是喝了酒」的說法,後來在氣象局、勞委會、立法院,一再地被官資雙方提及。漢人刻板印象中閒散的、耽酒的、不負責任的原住民,出了事怎麼能怪老闆呢?人們不約而同,不假思索,順手就拿起汙名便利貼,阻擋進一步探究。
偏偏亞山不喝酒。部落裡人人都知道,亞山不但不喝酒,連菸都不抽。
事發一年多,鑫閃公司早已易主,原合約上負責直升機運送的台北航空公司也已搬遷,相關資料與相關人士幾乎是一片空白。輾轉找到鑫閃借調直升機的中興航空公司,我們在布滿漂亮機型相片的松山機場辦公室裡,查閱1998年4月10日的飛行紀錄:機型BK-117的直升機一早6時抵達塔塔加,2,382公斤重的貨物上了飛機,再飛北峰。
競中代理亞山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後,南投縣政府輕鬆轉來一紙公文:「資方表示⋯⋯車禍應找肇事者求償。」要求亞山出具醫生證明、警察局筆錄,及勞雇關係證明等。
美珠嚇壞了,車禍的肇事者就是駕駛的亞山啊,難道又要遭法院傳喚出庭嗎?一般包商到部落找臨時工,怎麼會有「僱傭證明」?口頭契約要如何舉證?直接與包商接洽的工頭就是文秀,死無對證怎麼辦?
「最倒楣的就是我,你們原住民以前在山上打零工,還不是都沒有勞保?只是剛好這次被我遇上了。」鑫閃公司新任的孫老闆完全不清楚狀況,也確實自覺冤枉。他接收這個新公司,還沒來得及賺到錢,就要處理前債未清償的惡果。他攤開雙手,不疾不徐地說:「之前的馮老闆到大陸作生意去了,我也找不到人。這件事我根本不清楚。」
中央氣象局的反應雖然客氣,卻也推得一乾二淨:「發生這樣的事,我們感同身受。若要我們成為勞資爭議對造人,那就抱歉了,氣象局又不是資方。」
我們在南投縣勞工局、勞保局、中區勞檢所、鑫閃公司、航空公司、氣象局、交通部、勞委會四處碰壁,多方函文、找證據,重新拼湊事件的經過。氣象局官員不高興了:「這件事我們當初就知道了,也沒有人有意見,事情過了就過了嘛,都一年多了,那個工程早結案了,工程款也都結清了。你們幹嘛把事情弄得這麼複雜?勞民傷財,我們還得花錢找律師出席調解會議。」
「氣象局長期找我們去做工,出了事卻完全不管我們的死活!」東埔一鄰的朋友們終於生氣了。
他們都是部落裡少壯年輕的一代,也是當年與文秀、亞山上山工作的同伴。他們都到過都市工作,又回到部落務農,眼看著部落裡土地、水源、產銷等問題無法解決,現在更意識到大量的工傷原來不該獨自吞忍。他們自行組織起來,成立非正式的「東埔布農文化促進會」,想為東埔一鄰做點事。不料第一件差事就直接對上交通部氣象局。
晚上,我們坐在亞山家的客廳,仔細討論相關法令與困境時,促進會的朋友們都趕來開會了。書面請願無效,依法調解無效,不得不集體遠赴台北抗爭時,大家認真盤算:週三農會開市,不好動員;5月剛收完春茶,6月整地施肥告一段落,8月要剪夏茶,9月收成番茄與敏豆,11月偶有狩獵需求⋯⋯都是天大地大的事,都要避開。抗爭時序奇妙地配合山上農作的生長,採收時節幾乎動彈不得,作物天天熟成,晚一兩天都老了,賣相差口感差價錢更差,一季的辛勞全毀了。
偏鄉赴首都的抗爭成本高,往來花費更要仔細考量:要想辦法排除教會長老的壓力,爭取部落群眾的支持,向教會借兩輛九人座可以省下交通費,晚上借住工委會辦公室以節省住宿費,吃的不愁,部落婦女會幫忙製作糯米糰、水煮玉米、火烤番薯⋯⋯。如此精心策劃,時間要捉得很精準,行動要設計妥當,一次北上就要接連兩天抗爭與談判。若沒有結果,就返回部落商討下一波,下一次的農閒時機。
促進會發言人美秀說:「這不只是為了你們,也希望以後原住民不要再受到這樣的漠視與傷害。」她是來自台東的阿美族人,嫁入東埔的布農部落,落地生根,成為集體的發言人。
「受害者代表史亞山先生,你要不要說幾句話?」冷氣房裡,西裝筆挺的勞委會官員在作出總結前,客氣地訊問。
之前一個多鐘頭,立委、氣象局、交通部、原民會、勞委會等各部會官員反覆進行了職災的法律釋疑,冷硬,抽象,不容反駁,來自外太空。
「謝謝大家努力的討論。」一直沉默不語的亞山,總算抬起頭了,他拿起放在桌下的吉他,客氣地說:「我想唱首歌,表達我們原住民的心聲。」
未經演練,20幾名來自東埔一鄰的布農族人都抬起頭了。他們或站或坐,自然地形成聚集的氣流,順著吉他的前奏,齊聲歌唱:
我在靜靜的夜晚裡,思念我失去的朋友, 心裡的傷痛,不知如何好, 誰能安慰我的傷痛? 主耶穌,懇求你憐憫我, 醫治我心裡的傷痛。
亞山的眼淚毫不掩飾地掉了下來。適才的法律爭辯,像是被劃開表皮,揭露內裡的蒼白失真、自以為是,而布農族人回應以優美誠摯的歌聲。官員們面面相覷,主席不知如何制止,倉皇失措。原本百無聊賴的攝影記者們,紛紛亮起鎂光燈,快速連拍。
〈傷逝〉這首歌,是文秀死後,哥哥文雄為紀念他而創作的。史文雄是部落裡唯一正式受僱於氣象局的工人,全年有一半的時間待在北峰山頂,維護並記錄觀測站的運作。史家的客廳牆上,掛滿了文雄攝影的山景。「玉山真的好美啊,」他總是這麼說,「怎麼拍都拍不膩。」〈傷逝〉帶著複雜的傷痛,正是文雄在北峰值班時,使用太陽能板蓄積的電力,思念亡故的弟弟。不知如何是好,不知如何是好,那也許才是最痛的部分。
在〈傷逝〉唱進最高勞動行政機構之前,我們還沒能長出即興歌唱的自信,讓真實的情感帶動抗爭主軸。雖然也曾在行政院前舉行布農獵人的喪禮,跟著阿浪牧師吟唱聖詩,但那畢竟是排練好的行動步驟,突出工殤死亡的嚴重性。之後的談判也多沿襲過往模式,準備大量的事實證據與法律知識,一步步沙盤推演。屢戰屢敗,屢敗屢戰。
7月16日,第一次的抗爭行動從勞委會前的「原住民走投無路記者會」展開。族人們半夜3點從海拔1,000多公尺的高山部落出發,他們慎重穿上布農族的傳統服飾,20幾個大人小孩擠在兩輛九人巴士裡,連夜趕赴台北。披星戴月,長途奔波,他們都早有心理準備,沒料到卻是進入市區竟迷路繞行了兩個小時,都市叢林簡直像迷宮一樣。
急壞了的他們抵達勞委會時,已然遲到半小時了。遠遠看見鮮豔的布條、聲援人潮、眾多的媒體時,亞山還疑惑著:「又弄錯地方了嗎?這些人是誰?」直到聽見數十名平地工人、外籍勞工喊出聲援口號:「工人鬥陣,車拚相挺!」,亞山才定下心來:「是的,這就是我們的工人團體。」
一跨出車門,美秀就哭了:「想不到有這麼多漢人來幫我們。」她以手背抹去淚水,接過麥克風,大聲說:「我們是來自南投東埔的布農文化促進會⋯⋯」
淑娟帶著兩個孩子,雙手緊緊捧住文秀的遺像,毫不畏怯地直視相機鏡頭,快門聲此起彼落。我繞到布條後面,幫兩個孩子繫上抗議頭帶,淑娟側過身對我點頭示意,笑了。我發現,她的後背早被緊張的汗水濕濡了一大片。

7月底,氣象局的函文總算來了:「鑫閃公司並未承認史文秀及史亞山為其員工,其勞資關係未明,當事人應提出工作證明以憑認定,否則一般人發生車禍,均要本局負連帶責任,本局將無法負擔。」
史文雄立刻請了假,連夜從北峰趕來台北:「氣象局的人都知道啊,包商就是透過氣象局請我向部落召募人手,文秀出殯時我的同事還送奠儀來,怎麼說是『勞資關係未明』呢?」
東埔部落的大人小孩在工委會打地鋪,又睡了一夜,隔天一早就到交通部去抗議了。亞山和治中認真排練街頭行動劇,大布條寫著:「氣象局保平安,原住民拉警報」,諷刺多颱風的台灣,各地氣象觀測台的指示,成為民眾防颱保平安的指標,可是全台最高海拔的玉山北峰觀測站的背後,長期為氣象局擔任電瓶裝運的原住民臨時工,卻拉起死傷累累的警報。
一向羞怯的淑娟也拿起麥克風說話,她背了一晚上的稿子,聲音發著抖:「史文秀是我的先生,因為我們那裡種水果、種菜的收入不夠養家,他常常幫氣象局打零工,揹很重的東西爬山⋯⋯」
抗爭帶來協商的機會,族人們總算進入交通部的會議室,在空調得宜的屋內,有來有往地對話,並留下正式的會議紀錄。
負責接見的航政司官員,好整以暇地說:「你們要求以後外包工程要強制承商為工人加保,意見很好,我們會好好研究。」
「我們原住民都死了人了,你們還在研究!」
美秀率先把話截過來,直接打斷浪費時間的官腔:「臨時工是我們原住民無法擺脫的命運,我們根本沒辦法靠農作過活,一定要打工才能送小孩上學。北峰氣象台所有的工程,都是我們東埔布農族建起來的,可是你們感謝過我們的付出嗎?史文秀墳上的草都長很長了,你們還是不聞不問!」
憤怒像陣雨感染了每一個人,平地的工會幹部、職災工人也接連發言。砲聲隆隆中,美珠開口了:
「我們原住民不是來討錢的。」
她氣得握不住麥克風:「淑娟帶兩個孩子來,不是要氣象局可憐她、幫助她。她要的,她要的是原住民的權利,是職災勞工應該拿到的賠償。」
午餐過後,我收到一封電子信函,來自氣象局員工。他說他不便出面,不能具名,但請我代向亞山和淑娟致意,他們贏得了他莫大的尊敬。稍晚,這名公務員在上班的空檔前來當面致意,提起7月1日氣象局才剛辦過50週年慶,非常不以為然:「啍,50週年表揚的全是局裡辦公室的職員,沒一個是山上的氣象員!」
隨後數日,來自花蓮、新竹各地原住民,主動打電話給布農文化促進會,為亞山和淑娟加油:「要堅持到底!」大家都知道,這是眾人之事。
鑫閃孫老闆私下對我說:「硬要玩法律,我問過律師,你們是玩不過的。沒有僱傭證據嘛是不是?而且這個公司根本沒剩什麼資產,你們就算花個3、5年打贏官司,也要不到什麼錢。可是,」他搖搖頭,嘆了口氣:「可是我在氣象局看到史文雄,這樣一個根本不會說謊的人,寧可丟掉工作也要來抗議。我要為了這點錢,一輩子讓這些老實人心裡怨恨我,值得嗎?」

最後一次抗爭,〈傷逝〉的歌聲帶動所有人的情緒,勞資官三方暫停協商,原本的對峙張力,似乎有了隱微的流動。是什麼被鬆動了呢?也許是歌聲,也許是媒體壓力,也許是累次抗爭成果的積累。討價還價,鑫閃承諾拿出近期一筆工程頭期款,勞委會、原民會各自出具慰問金,勉強拼湊出合乎《勞基法》的職災補償金額。氣象局則提出,內部員工已針對亞山和文秀的工傷,主動發起募捐,總計16萬元。那些匿名的鼓勵郵件,必然也在其中。
亞山與淑娟都說:「盡了力就好,謝謝大家。」
氣象局員工的捐款,基層互助的心意,該怎麼分配呢?我請官員先離席讓我們私下討論,有人建議對半分,有人主張亡者多一些,亞山和淑娟一直靜默不語。
走出勞委會,亞山特意留著和我並肩走,他平視前方,慢慢說:「捐款就全給淑娟吧,她太辛苦了。你去說,她比較會聽你的。這是我對文秀的一點心意。」
帶著孩子們到國父紀念館玩,淑娟也主動去找競中了:「你去跟亞山說,我說了他一定拒絕。募捐的16萬都歸他,美珠要照顧3個孩子,沒辦法下田。亞山的身體還沒好,跛腳不好走,又常生病。我自己還好,還能下田,而且當初文秀留下的意外保險金還夠我們用。」她紅著臉,簡直是不好意思的模樣,怕說不清楚,怕傷了亞山的心。
過往的爭議談判,臨到利害關頭時,無非是捉緊個人盤算不放。東埔的布農族人在貨幣上如此匱乏,卻沿襲著獵人文化的傳統,成果公平分享,以需求衡量所得。後來,他們也不吝惜地回捐部分金額給教會、促進會、平地的勞工團體。工人秋鬥遊行,布農朋友們也不忘借車子趕來參與,每一次,還是半夜出發,每一次,還是在都市叢林中迷路多時。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