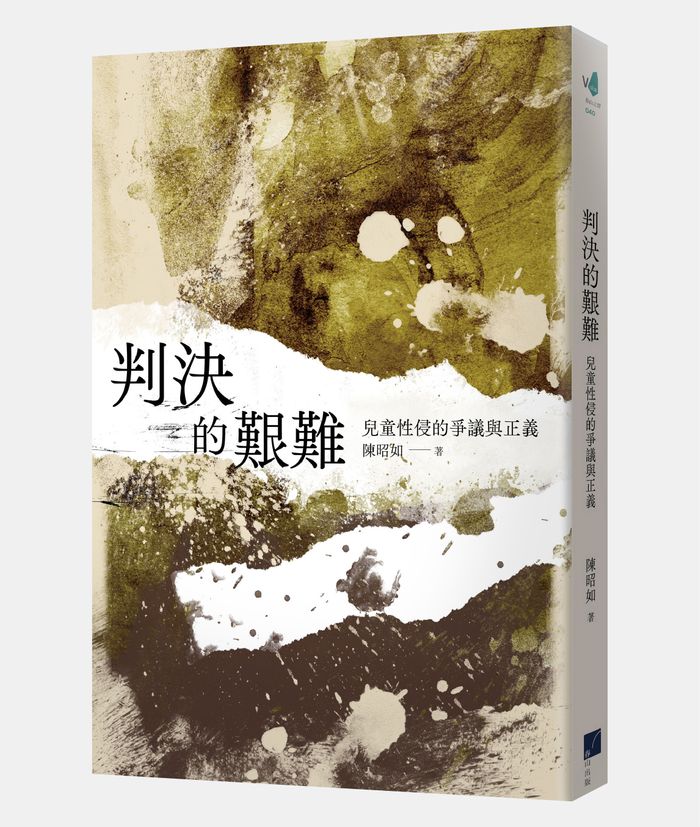精選書摘

本文為《判決的艱難:兒童性侵的爭議與正義》章節書摘,經春山出版授權刊登,文章標題、內文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所改編。
性侵害案件通常發生在密室,少有直接明確的人證或物證,如果事後雙方說詞迥異,被害人又是認知與表達能力有限的兒童,如何斷定發生了什麼事?執法者是否可能因個人隧道視野、迷信科學證據、過度依賴單方證詞而造成錯誤──無論是縱放了真正的犯人,或是誤判了無罪的被告?
陳昭如長期關注性侵被害人的處境,亦深入理解性侵冤案的來龍去脈。這次她挑戰探討兒童性侵害案件認定的兩難,並指出無論是眾聲沉默的性侵案,或是被迫消音的性侵冤案,都是在性(侵)是羞恥的文化之下,讓「不可說」的氛圍製造出驚人的黑暗與混沌。她在本書中訪談被害人、家屬、社工、檢察官、律師、法官、NGO等多方角色,呈現他們的所見、所思、所為。期盼每個人都反躬自省,側耳聆聽,瞭解這個議題的複雜性,讓不同角色的痛苦被聽見,透過不斷的思辨與說理,往解決的方向前進一步。
本篇書摘接續〈陳昭如/兒童性侵的爭議與正義(上)──「法院認證」的雙面刃〉一文,提出在正義之外,「復原」的重要性常被忽略,是整個社會都該思考的問題。
看了HBO描述一起性侵疑雲的紀錄片《伍迪艾倫父女之戰》(Allen v. Farrow)。
說明一下事件背景。伍迪.艾倫(Woody Allen)與米亞.法羅(Mia Farrow)結婚時,法羅已有8名養子女,包括曾經流浪首爾街頭的順宜(Soon-Yi)。1991年,米亞.法羅在伍迪.艾倫的公寓發現裸照,主角就是順宜,伍迪.艾倫自認「沒有任何道德上的問題」,順宜也表現出對她「社會性父親」的全然支持,沒有任何猶豫。1992年,小兒科醫師懷疑他們的另一名養女迪倫(Dylan)被性侵,主動提出通報才讓事件曝光。
30年來,這起性侵案件一直有兩個版本:其中一個版本,是養父伍迪.艾倫侵犯了7歲養女迪倫,另一個版本,是養母米亞.法羅唆使迪倫誣陷自己的養父。前面這個版本,是米亞.法羅和她的支持者提出來的,後面這個版本,則是伍迪.艾倫和他的支持者說的。耶魯紐海文醫院的兒童性虐待診所聲稱迪倫沒有被猥褻或性侵,但康乃狄克州警局卻指稱迪倫所言句句屬實,絕無捏造。這兩種說法明顯相互矛盾,你要相信哪一種?
《伍迪艾倫父女之戰》大量訪問相關當事人,公開許多首次曝光的法院文件、迪倫自述被性侵的影片、還有數量驚人的證人現身說法。至於事件的主角伍迪.艾倫則是拒絕受訪,並稱「這部紀錄片對事實不感興趣⋯⋯在虛假的資訊裡拼湊惡毒誹謗」。
看了這部片子,我仍無法百分之百確定1992年康乃狄克州農莊的閣樓裡發生了什麼事,或者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不過承辦該案的康州檢察官法蘭克.馬可(Frank Maco)的說法,特別引起我的注意。他說,當年他有相當理由(probable cause)可以起訴伍迪.艾倫,可是他沒有這麼做,因為他想保護年幼的迪倫。他以米亞.法羅拍攝過一卷錄影帶記錄迪倫是如何描述出事的情節說:
我不接受任何人說「迪倫是受到母親操控才捏造出性侵」的說法,如果你看過錄影帶,看看小孩怎麼說出這些事的,這些都不是被母親操控說出來的,而是孩子真實說出來的話。米亞.法羅只不過是一位關心孩子的母親,沒有跡象顯示這是一個捏造出來的故事。
法蘭克.馬可說,決定不起訴伍迪.艾倫是很艱困的決定。他很在意事實真相,但更在意迪倫的未來,「她的神智完全被抽走了,臉上只有冷冰冰的眼神,根本完全不看我一眼。」他不想讓這個脆弱的孩子經歷嚴酷的審訊,萬一法官質疑她為什麼不拒絕?為什麼不馬上告訴大人?是不是媽媽要她撒謊?這些問題對一個7歲的孩子來說,實在是太過頭了。
無論真相是什麼,外界的紛紛擾擾,已讓迪倫的世界產生驚天動地的變化。她每次出門,就連上學都一樣,必須從後門溜出去,上了車,用毯子遮住頭,避免好事者或媒體發現她的行蹤。她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吃不下,睡不著,那時她只是個小學生而已。
30年來,伍迪.艾倫始終否認他對迪倫做過踰矩的事,可是迪倫從來沒有改變過她的說詞,外界對她的攻擊與質疑亦不曾間斷。人們提起迪倫時的反應是,喔,就是那個被發狂媽媽要求誣告自己爸爸的小孩。
我一頭栽進了法庭紀錄,以及所有我能找得到的書面資料。根據迪倫7歲時所做成、後來也一再明確複述的筆錄,艾倫把她帶回我們康乃狄克老家,並在地板下方的一處爬行空間裡用手指侵犯了她。事實上在這之前,她便已經向一名治療師抱怨過艾倫對她有不當的碰觸(但這名由艾倫僱用的治療師直到後來上法庭,才把真相說出)⋯⋯艾倫通過一個由律師與包商所組成的人脈網,僱用了根據某律師估計達10人以上的私家偵探,他們的任務是跟蹤執法的官員,蒐集他們酗酒或賭博的證據⋯⋯法蘭克.馬可後來描述那是「阻撓檢警辦案的行動」,而法蘭克的同事表示他不堪其擾。
我無意自詡我處理起姊姊的故事會有多客觀──我既關心她,也支持她──但我仍主張她的說詞是具有可信度的性虐待指控,而這類指控卻經常被好萊塢的業內媒體跟更廣大的新聞媒體給忽視。「這樣的沉默不僅在是非上有虧,而且還非常危險,」我寫道,「這傳遞給被害人的訊息是咬牙站出來一點也不值。這也讓大家看清了我們是什麼樣的社會,我們會視而不見哪些事情,會忽略誰,看誰重於泰山,誰又輕如鴻毛。」
如今,那個7歲女孩已經35歲了,她與白髮蒼蒼、退休多年的法蘭克再度見面時,《伍迪艾倫父女之戰》記錄了這一刻。迪倫感嘆:「我很自責,我當時還不夠堅強!」法蘭克告訴她:「迪倫,我不希望聽到你這樣說。你那時還只是個孩子,如果有的話,請怪我,那是我決定的,我選擇的,你可以指責我『那個檢察官沒有起訴』!」說時眼角泛著淚光。
法蘭克.馬可沒有起訴伍迪.艾倫是否是個錯誤?沒有人知道。他同理迪倫,傾聽迪倫的聲音,站在迪倫的角度為她設想,或許這樣,就夠了。
被害人是否非得透過訴訟才能得到正義?我問過潔晧這個問題,他說,他不特別關心這點,他更在意的,是被害人是否有權決定要不要提告。
「今天小孩子進入通報系統,他的選擇權是什麼?很多小孩子進入通報系統,是在無預期的狀況之下被通報,這是法律的規定,也是保護網的一環。這種做法忽略了小孩子已經離開傷害環境一段時間,進入復原的階段,他決定說出自己的經歷,是想尋求復原的資源,沒想到卻進入無法預期的司法流程,而這個流程是不考慮復原或小孩子的意願,是不讓他選擇的。」
「受傷的本質是生命被剝奪了自主權,無法控制自己的身體。當小孩子離開了被傷害的環境,對生活再度有了主導權,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可是當他決定說出來,卻被迫進入司法系統,再度被剝奪了生命自主權,這是很不公平的事。兒童性侵害是自主權被剝奪的問題,受害的小孩子應該擁有控制生命主體的決定權,不能假司法之名,剝奪他們對自己的掌控!」
進入司法系統是由誰決定?被害兒童本身?監護人?還是國家?追訴期有沒有可能延長?是否可讓兒童成年之後再行決定是否提告?潔晧與思寧有很多疑問,因為他們覺得這是為了兒童的安全(例如他們的生存條件必須仰賴加害人,這種情況尤以家內性侵最多),也是尊重他們的生命主控權。
《兒童權利公約》第十二條規定:「一、締約國應確保有形成自己意見能力之兒童有權就影響其本身之所有事物自由表示其意見,其所表示之意見應依其年齡及成熟度予以權衡。二、據此,應特別給予兒童在對自己有影響之司法及行政程序中,能夠依照國家法律之程序規定,由其本人直接或透過代表或適當之組織,表達意見之機會。」當相關政策或措施影響兒童權益時,決策過程就該將兒童的意見納入其中。監察院在調查某國中棒球教練性侵學生案時發現,在全班學生幾乎悉數被害的情況下,只有兩位家長願意出面提告,其他家長則拒絕被調查。至於被害兒童的意願是什麼?他們的聲音在哪裡?我們不清楚,因為沒人問過他們的意見。
潔晧與思寧還提及一個鮮少被關注的問題,就是透過法律框架理解性侵害,反而可能降低兒童對不當性接觸的敏感度。目前「性猥褻」與「性侵害」的罪刑有所差距,應是立法者認為後者是侵入性行為,罪刑應該更重。性猥褻對孩子身心造成的戕害,果真比性侵害來得輕微嗎?思寧不認為如此:
「根據我對文獻的閱讀,以及對兒童被害人生命經歷的瞭解,小時候就算遭遇性猥褻,不是性侵害,傷害是一樣大的,但有的大人會說,陰莖沒有插入,所以不算太嚴重。我們經常收到信件問我們說,我小時候被人家做了什麼,我不確定這樣算不算性侵?如果我們不用『性猥褻』或『性侵害』這樣的字眼,而是換成『性虐待』的話,他們同樣都是被害人!」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性侵害犯罪」是指《刑法》中的性交犯罪與猥褻犯罪。依照《刑法》第十條,「性交」不只限於用性器插入陰道,肛交、口交或是性器之間的碰觸,利用手指、其他身體部位或物品、器具插入陰道、肛門,也都算性交行為。至於猥褻則是指性交以外,足以使一般人興奮或滿足性慾的色情行為,例如強摸他人胸部、私密部位等。換言之,性侵害犯罪不只限於有插入行為,觸摸、碰觸或其他猥褻行為,也都算是性侵害犯罪。許多人不瞭解這點,仍以陰莖插入與否作為判斷嚴重與否的指標,會不會是誤解?
「我們一直在思考,法律上對『性侵害』的定義,或許是從大人的性互動而來,所以很在意有沒有『插入』,忽略了成長中小孩子的特殊性跟脆弱性。他們對性的理解與互動,是跟大人不一樣的,不應該以大人的標準套在他們身上。有些大人在教導小孩子保護身體的時候不瞭解這點,反而讓小孩子對別人觸碰身體的敏感度很低,只要沒有接觸到性器官,或是性器官沒有插入,好像就不是那麼嚴重的犯罪行為,這是我們比較擔心的地方。」思寧這麼告訴我。
某次參加研討會,我注意到後方有名男子神情格外專注,那麼哀傷的眼神,那麼絕望的表情,我想,應該是被害人吧。果然,趁著中場休息,他怯生生走向我,說,有時間聊聊嗎?我領他走到場外無人一隅,毋須太多暖身或開場,他兀自語無倫次、片片斷斷說起一段傷心的過往。
「有人說我那樣不叫性侵,你覺得呢?」他問我。 「你覺得是不是?」我反問他。 「我不是很確定。那時我還很小,什麼都不懂。」 「可是你很不舒服,覺得很受傷,對不對?」
他沒出聲,但他的眼神告訴我,他覺得是。
「那個人不該這麼對你,不管那樣算不算性侵。」 「如果那樣不算性侵的話,或許我就不會那麼痛苦了。」 「不管他做了什麼,他都不該那麼做。他傷害了你,你當然會感到痛苦。你有告他嗎?」 「沒有。」 「你現在想告嗎?」 「告不告,已經沒有意義了。」
我們靜靜站了好一會,沒有人開口說一個字。
「我從來沒想到,我可以活到現在⋯⋯」他長嘆了一口氣,「很難想像喔?」 「你很勇敢啊,我說真的。」
沉默再繼續,空蕩蕩的會場外,隱約傳來場內的發言聲。他收起滿漲的情緒,露出一抹慘淡的笑意:
「嗯,我也覺得我滿勇敢的。」
過去我認為被害人出面指控是值得鼓勵、是增能的表現。聽了這位男性的故事,我才發現或許保持緘默,選擇隱蔽,也是他們的權利。站出來揭露真相,或許能得到正義,若是無法、或不願說出真相,也該得到絕對的尊重。沒有人能預測說出來的結果會是什麼?人們會怎麼想?哪些人會支持?哪些人會不同意?既然沒有人知道後果,當事人決定怎麼做,外人無庸置喙。
被害兒童選擇緘默,有時不是自願,而是被迫,因為知情的大人假裝沒這回事,不願出面處理,迫使孩子沉默了。這點在澳洲皇家調查報告裡一目瞭然。
2017年,澳洲政府公布皇家調查報告,指出從1950年至2000年,澳洲有超過17,000名兒童受害,讓外界看見性侵害的各種樣貌及影響。這份厚達17巨冊的調查報告最引起我注意的地方,是被害兒童發現原本信賴的師長視而不見,或分明知情卻不願伸出援手,很容易產生強烈的自我懷疑及嚴重的焦慮、身心解離與創傷症候群。這不只讓他們易於再度受害,影響他們接受法律、醫療等各項服務的機會,無疑也會增加其他人被害的風險。
為什麼大人寧可選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也不願積極處理?這牽涉到成人對兒童權利與認知發展的成見。兒童在成長過程中,經常被教導「不可以挑戰成人」,若是說出成人不願相信的事,不是被當成隨口說說,就是被視為挑戰權威。當兒童從成人的反應發現性侵害是不能說出口的,或是說了也沒人相信,強大的矛盾、迷惘與不安讓他們再也無法敞開心房。相反的,如果有人願意真誠的傾聽,而且是在溫暖安全、沒有曝光之虞的條件下,他們是很願意說的,而且是毫無保留的全盤托出。
根據我有限的經驗,被害兒童大多聰慧而敏感,懂得選擇適當時機與對象傾訴。他們最大的痛苦未必來自性侵本身,而是沒有人傾聽的痛苦,我能做的,只是陪伴與傾聽,相信他們的感受,接納他們的情緒。至於說或不說,這是他們的權利,外人無權以任何理由(像是「你要勇敢一點,說出來」「說出來,才能救其他人」⋯⋯難道「不說」就代表「不勇敢」?難道其他孩子被性侵,是他們的責任?)如此要求。
我們期待被害人勇敢現身(聲),控訴不義,好像唯有如此才是被害者的「本分」。我們用「勇氣」鼓勵被害人將不想訴說的傷痛公諸於世,彷彿只有透過這個途逕,外界才能認可他們被害的身分。公開受害事實,走進司法,是最好的選項嗎?他們的傷害與苦痛會得到緩解嗎?或者這只是旁觀者的一廂情願?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