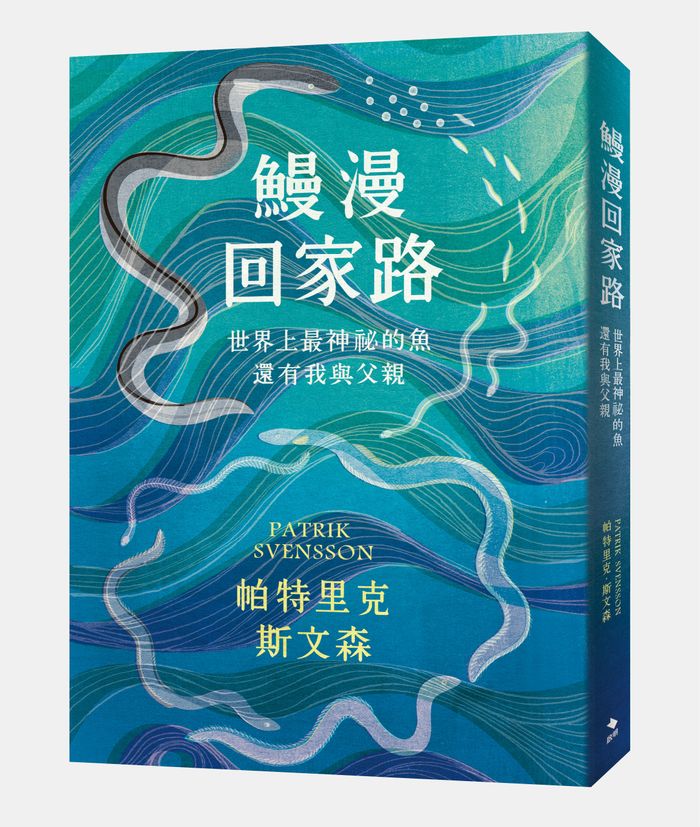精選書摘

本文為《鰻漫回家路:世界上最神祕的魚,還有我與父親》部分章節書摘,經啟明出版授權刊登,文章標題、內文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改編。
鰻魚從哪裡來?牠究竟是什麼生物?為何一生分為6個階段,從體型到體色都顯著改變?是什麼驅使在淡水居住數十年的牠們,泅泳數千公里,回到誕生的海域繁殖、然後死去?幾千年來,許許多多的科學家和哲學家們都沉迷於「鰻之謎」。即便到了科學發達的今日,謎團尚未解開,鰻魚卻已面臨嚴峻生存威脅,不只來自於自古即有的捕撈,還有整個環境的變動⋯⋯。
本書作者帕特里克.斯文森(Patrik Svensson),在瑞典「鰻魚海岸」附近的小鎮成長,從小與父親釣鰻魚、聽父親述說關於鰻魚的一切,他把自己與父親捕鰻的經驗結合現代海洋生物學、歷史與文學中關於鰻魚的研究。
這是一個關於鰻魚與傳承的故事,帶讀者探索鰻魚的起源、神話與瀕危,以及牠們在人類與自然世界中的位置。
什麼樣的人會選擇成為捕鰻人?鰻魚能提供這些人什麼?職業與收入是最簡單的答案,但還不是故事的全貌。誠然,鰻魚在歷史上向來是歐洲大部分地區的重要食物來源,但牠一直很狡猾,難抓、難懂、神祕,很多人就是不喜歡牠。牠迫使捕鰻人開發特殊的方法與工具;鰻魚自己怪異的行徑也讓捕鰻業無法擴大,儘管需求極高。牠不能如鮭魚般養殖,事實上,牠也不可能在圈養中繁殖。作為營養來源,鰻魚對很多人來說至關重要,但牠完全不願意配合。到了今天,吃鰻魚的人愈來愈少,漁獲量也逐漸萎縮,何必要當捕鰻人呢?
如果你問瑞典鰻魚海岸的那群人,大部分會得到的答案是:這從來就不是個選擇。大家天生就是要吃這口飯,在世代傳承中,你不知不覺就培養出師了。當然沒有什麼大學課程或專業培訓單位會訓練捕鰻技術。捕鰻人擁有的知識從來就不是在教室或實驗室取得的。它經過了好幾世紀的嬗遞,正如一個仰賴口耳相傳、從來都沒有人費心書寫的古老故事。如何製作捕鰻陷阱、替鰻魚剝皮、判讀海象與天氣、詮釋鰻魚在水面下的活動:這冷僻專門的知識是通過實際行動傳遞下來的,是超越了歲月與時間的共同經驗。因此,捕鰻常常是家族事業,代代相傳。只要是捕鰻人,必然流著捕鰻的血液。只要是捕鰻人,全都將這行業視為比捕鰻活動更為神聖的事:這是文化延續,這是傳統與知識的繼承。
在歐洲,捕鰻業最興盛的地區很少是那些超級有名的大都市,鰻魚之都與人類毫無相干,相反地,它們都是一些很奇特的地方,住民也特色迥異,個性頑強驕傲,就像住在瑞典鰻魚海岸的那群人,他們不只從先祖那裡繼承了事業,也因艱苦的工作與簡陋的環境塑造了不一樣的人格。他們讓工作成為自己的認同,於是,就像施密特一樣,堅持乘風破浪捕鰻,不顧一般人的勸阻,儘管常識也提醒他們不要這麼做。這群人多半養成一種邊緣人的性格,質疑權力。於是,在瑞典鰻魚海岸外的許多捕鰻人,就這麼自成了另一種生物。
- 卵期(egg-stage):位於深海產卵地。
- 柳葉鰻(leptocephalus):在大洋隨洋流長距離漂游,此時身體扁平透明,薄如柳葉,便於隨波逐流。以海洋雪為主食。
- 玻璃鰻(glass eel):在接近沿岸水域時,身體轉變成流線型,減少阻力,以脫離強勁洋流。
- 鰻線(elvers):進入河口水域時,開始出現黑色素,卻也形成養殖業鰻苗的捕捉來源。
- 黃鰻(yellow eel):在河川的成長期間,魚腹部呈現黃色。
- 銀鰻(silver eel):在成熟時,魚身轉變成類似深似深海魚的銀白色,同時眼睛變大,胸鰭加寬,以適應迴游至深海產卵。
距離奧里亞河口往內陸沒幾公尺的小村莊阿吉納亞,居民不過600人,卻有5家捕玻璃鰻的魚公司。在這裡,專業知識同樣古老,也是世代傳承。玻璃鰻在寒冷黑夜,趁滿月或新月時分,天空稍有烏雲時,隨著潮汐進來。牠們漂浮在遼闊淺灘附近的水面,就像一大片銀白色糾結的海藻,船上捕鰻人來回撈捕著;船首燈光映照在活跳跳的玻璃鰻群上,他們持著長棍,棍上繫著圓網,然後徒手將玻璃鰻捕捉上岸。
玻璃鰻在巴斯克地區被視為頂級佳餚,現在只有那裡珍視牠了,不過,歷史上享受這脆弱透明狀態下的鰻魚的情況其實相當普遍。在英國,玻璃鰻曾經在塞文河被大量捕獲。牠們被拿來和培根一起炒,或做成歐姆蛋捲,所謂的「精靈蛋糕」。在義大利,人們在西部的亞諾河及東部的科馬基奧附近捕玻璃鰻。當地偏好用番茄醬燉煮,撒上一點帕馬森乳酪。在法國的一些地區,也流行吃玻璃鰻。不過如今這傳統已經式微。隨著游進歐洲河域的玻璃鰻魚數量急劇下降,以牠們為主的漁業活動也不再存在。到現在只有巴斯克人民還頑強不屈服,堅持拒絕放棄。
當然這一切都有合理解釋。首先是財務考量。人們在這裡抓玻璃鰻由來已久,據說牠們過去大規模地在奧里亞河載浮載沉,數量多到農民們可以從河岸撈捕,拿來餵豬。但正因為如今牠們數量稀少,生存威脅增加,更讓玻璃鰻成為搶手的佳餚,人類的邏輯就是這麼獨特扭曲。在巴斯克地區,玻璃鰻會用上等的橄欖油油炸,灑上些許蒜末與微辣的辣椒提味。人們會把熱騰騰的鰻魚放進一只小瓷盤;饕客用一根特殊的木叉吃牠,免得被燙到嘴唇。在旺季,一小撮重約250克的玻璃鰻,在聖・塞瓦斯蒂安的精品餐廳甚至要價6、70美元。
但是阿吉納加與奧里亞河沿岸的捕鰻人,仍有繼續這一行的其他理由。他們不想喊停。因為他們認為這是他們的權利,也因為這正是他們的祖先賴以維生的工作,除了捕鰻的特殊方式,它更定義了他們的存在。該地區也是巴斯克分離主義組織「埃塔」的重要據點。這裏的人們習慣自力更生。長達40年的時間,他們在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的統治下被邊緣化,飽受迫害,因此他們對馬德里或布魯塞爾的官僚爭權奪利的醜陋角力充滿警覺。在這裡,捕鰻人才不管政客或科學家怎麼說,他們仍會帶著漁網與燈籠回到自己的大河。直到最後一位捕鰻人消失。或最後一條鰻魚死去。
在北愛爾蘭的內伊湖,當地人已經捕撈鰻魚至少兩千年了;那裡的鰻魚品質經常被譽為歐洲頂尖美味。內伊湖位於愛爾蘭的東北角,是不列顛列島最大的湖泊,位於莫恩山脈以西,地貌極度貧瘠;一年中大部分地區的氣候都非常惡劣,飽受劇烈風暴的襲擊。但即便如此,捕鰻業卻從未歇息,畢竟這是代代相傳的行業,也因為無論是地點或鰻魚,都不允許出現任何變動。
傳統上,漁獲都被運到倫敦。長期以來,鰻魚都是這座首都的熱門食品,小店與市場攤位到處可見。油炸之後佐以馬鈴薯泥,或者做成鰻魚凍──鰻魚切片放入高湯熬煮,放置成凍。它被視為是物超所值的平凡美食,與東區的勞工階級也有密切的關係。鰻魚富含脂肪,蛋白質含量高,比肉便宜得多,所以成為窮人的熱門食品,可以想見,也因此被富人鄙視瞧不起。
但倫敦人對鰻魚的喜愛並不是這些內伊湖鰻魚被運來倫敦的唯一原因。其中也有政治因素。當英國人在16世紀與17世紀殖民愛爾蘭的大部分地區時,他們不僅奪走最肥沃的土地,也獨占了最寶貴的自然資源。1605年,在內伊湖周圍的愛爾蘭人被迫放棄捕魚權,接下來長達350多年的時間,當地漁業都受控於英國殖民者。有錢有權的清教徒可以決定要捕獲多少條鰻魚,該如何處理牠們,捕鰻人又將支付多少費用。於是這群貧窮又沒權勢的捕鰻人──大部分為天主教徒──被迫離開故土,尋找其他謀生方式。鰻魚是維生的要素。
幾百年來,所有捕魚權都由歷代沙夫茨伯里伯爵擁有,但在20世紀中葉,它們被賣給了一個名為「環」的財團,組織成員為倫敦少數的富裕鰻魚商。1965年,一群天主教捕鰻人聯合組成內伊湖捕鰻人合作社時,「環」仍然掌控內伊湖所有的鰻魚捕撈活動,後來,合作社員募資買下20%的捕魚權。在隨後的幾年間,他們也預備了更多資金好買下剩餘的8成權利。這一切發生時,北愛爾蘭問題隨之爆發,這當然都不會是巧合。「環」的成員作證表示,他們被迫在暴力威脅下出售自己的股票;甚至指證歷歷,表示財團的船隻遭受襲擊。據說捕鰻人之一甚至是愛爾蘭共和軍的成員。
於是,鰻魚捲入了暴力血腥的北愛衝突,它與階級、權勢、擁有權、財富、貧窮及宗教,完全脫不了關係。今天,內伊湖的漁業活動百分之百由內伊湖捕鰻人合作社持有,那些仍然在捕鰻的人們不會忘記自己奮力爭取的過程。頑強桀傲驅使他們繼續為魚鉤上餌,拉出長釣線,因為他們先祖就是這麼做的,未來也應該要如此延續。

現在這一切都即將消失。文化遺產與傳統、地方美食與地標、鰻魚棚、小船與捕鰻工具、代代相傳的知識。最終則是所有的回憶。至少這是內伊湖岸、巴斯克地區的阿吉納加小鎮及瑞典鰻魚海岸的隱憂。因為隨著鰻魚數量減少,保護鰻魚聲浪愈來愈大。歐陸許多地區已經嚴禁捕撈玻璃鰻。科學家及政客正努力將禁令推行到整個歐洲。
那就這樣吧,捕鰻人們說,但請記住,你們不只是在掠奪我們的生計!傳統、知識,以及這寶貴古老的文化遺產也勢必流失。更重要的是,他們聲稱,人類與鰻魚的關係即將岌岌可危。如果人們不再捕鰻──抓牠、殺牠、吃牠──他們就會對牠失去興趣。萬一人們對鰻魚不感興趣,這一切無論如何,都會散佚。
因此,內伊湖捕鰻人合作社目前正努力拯救鰻魚,不再積極捕撈。它正進行一個大規模的昂貴計畫,意圖購買釋放玻璃鰻到湖中。瑞典鰻魚海岸的捕鰻人也聯合起來,努力提高人們對鰻魚困境的認識。他們創立的鰻魚基金會也很類似內伊湖捕鰻人合作社,正致力於野放鰻魚,增加牠們的數量。2012年,鰻魚海岸文化遺產協會成立,主旨是要讓瑞典的捕鰻傳統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該協會的網站寫著:
「全面禁止捕鰻會讓一種活生生的文化、地方技藝與獨特的料理遺產走進歷史。沿岸的鰻魚棚會成為財富階級的避暑別墅。我們的故事會沒了聲音,人們對鰻魚的興趣,甚至鰻魚族群,也會就此散佚。」
這是最大的矛盾點,也是當代鰻之謎最中心的疑惑:為了瞭解鰻魚,我們必須對鰻魚感興趣,因此,我們也必須繼續捕撈、捕殺,把牠放上餐盤(至少根據一些人的說法是如此,畢竟他們比我們更親近鰻魚)。鰻魚,不能只當一條單純的鰻魚。向來不容許如此,因此,牠就也這麼成為我們與這星球上所有其他生命形式複雜關係的象徵了。
為什麼鰻魚特別無法生存?是否有什麼特殊的情境,讓這種看來彷彿可以長生不死的物種無法延續?首先,此問題伴隨一個理論破綻。我們知道,問「為什麼?」絕非解決科學問題的第一步。一切要從源頭開始。我們必須先確認一件事:鰻魚真的瀕危垂死嗎?接著我們再加以觀察,進而解釋事件發生的過程:鰻魚如何死亡的?唯有這麼做,我們才能開始處理「為什麼」。
但每次一提到鰻魚滅絕,上述的做法卻又開始變得複雜。
協調全球環境保護與生物多樣性大部分工作的,是一個名叫「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的組織。IUCN同時編製了所謂的紅皮書,定期更新全球瀕危動植物清單。此紅皮書的明確目標是,建立一個「全球普遍接受的瀕危物種滅絕分類系統」。換言之,IUCN設定的是國際標準,各物種經過科學檢驗評估後,確定目前存在的狀態。
在紅皮書裡,每一物種都被依照既定的標準進行評估,其評等範圍從最令人振奮的「無危」,到「近危」、「易危」、「瀕危」、「極危」以及「野外滅絕」,再到最終難以挽回的「滅絕」。由於它是客觀有條理彙編地球所有已知生命的一份清單,因此可提供從藻類、蠕蟲到人類如何存續的完整資訊。
人類表現得很好。2008年IUCN對智人進行的最新評估報告如下:「無危:物種分布極其廣泛,適應性強,目前數量穩定增加。」報告同時指出,「人類是所有陸地哺乳動物中分布最廣泛的物種,他們棲息在地球的每一片大陸(儘管在南極洲並沒有永久的定居點)。另有一小群人進入太空,居住在國際太空站。」目前,根據IUCN的評估,「不需要採取任何保育措施。」智人數量穩健成長。
相反地,鰻魚則麻煩大了。或者至少我們有充分的理由這麼想。因為種種的證據向來讓我們如此相信。不用說,既然我們對付的是鰻魚,一切都是未定之天。畢竟正如往例,我們取得了知識,卻也伴隨著警訊。因為事實證明,鰻魚不太符合IUCN的評估標準。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根本無法全盤掌握物種的總數量。物種規模原本就是確認它是否受到威脅的首要條件。但根據IUCN的報告,物種規模應由「可繁殖個體」的數量決定,亦即完全性成熟的個體樣本。這代表,IUCN如是說,在理想情況下,此標準適用於「在繁殖地的成熟鰻魚」。換言之,我們得搞懂馬尾藻海的銀鰻總數。但由於人類即使過了100多年的尋覓過程,還是沒在當地找到一條銀鰻,這條件顯然就是做不到。鰻魚不會甘願讓自己浮出檯面。就連想幫助牠們的人,也令牠們避之唯恐不及。
比較有可能做到的是,計算多少條成熟銀鰻從歐洲海岸出發前往產卵地。但這方面的資料也少之又少;鰻魚向來習慣迅速消失在黑暗浩瀚的大海深處,目前有的觀察也顯示過去45年來,遷徙的銀鰻數量至少下降了50%。
第三個較好的選項,也是IUCN目前根據的評估資料,就是從大海的另一端著手,評估鰻魚在馬尾藻海神祕會合後的結果──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稱之為「鰻魚父母存在的唯一例證」,也就是春天在歐洲出現的玻璃鰻數量。這方面目前瞭解甚多,正是這些數據顯示鰻魚現狀正步步走向災難。一切可靠的數字顯示,現今歐洲新近出現的玻璃鰻數量,僅是1970年代末期的5%。當我還是小男孩時,每年若有100條奮力往上游的玻璃鰻,如今的數量約莫只有一個巴掌大。
因此,IUCN決議將歐洲鰻歸為「極危」。根據官方定義,這表示牠正「面臨在野外滅絕的高度風險」。情況不僅致命而且緊迫。在可預見的未來,鰻魚或許真的就要消失了,不僅從我們的視線與知識領域消失,更直接在現實中消失無蹤。
因此,最終的問題是:鰻魚的數量為何凋零?答案並不令人震撼,畢竟這是我們一直在討論的鰻魚:一切都很難說。任何想瞭解鰻魚的研究者早就面臨同樣的問題:答案一直令人猜不透。我們什麼都不確定。我們只知道部分,但看不清全貌。在這方面,我們只能被迫依賴信仰。
目前有幾種鰻魚岌岌可危的合理解釋,科學可以一一證實,但沒有人敢說它們是不是唯一或最關鍵的因素。只要鰻魚的生命週期仍存在著未解的疑問,我們就不能確定鰻魚為何死亡。只要我們不知道鰻魚如何繁衍或導航歸鄉,我們就無法解釋牠為什麼不出現這些行為。為了拯救牠,我們又必須更理解牠。這就是多數鰻魚研究者目前最重視的:為了幫助鰻魚,我們需要更認識牠。我們需要更多的知識與研究,而且愈來愈急迫了。
這就是經典的左右兩難:我們想保護鰻魚,保存某些真正神祕的謎團,因為在這凡事講求啟蒙的世界,一旦謎底揭曉,萬物就會成空。任何認為鰻魚應該繼續當鰻魚的人,卻再也承擔不起讓鰻魚持續當個奢侈的謎團。

但鰻魚之所以滅亡,有一點我們是清楚的:是人類的錯。迄今為止,科學提出的所有解釋都與人類活動有關。人類離鰻魚愈近,牠愈暴露在人類現代生活的衝擊下,滅亡速度更快。國際海洋勘探理事會(ICES)在2017年總結人類該如何拯救鰻魚時,沒有定論卻又明確傳達:人類的活動對鰻魚的衝擊應當「盡可能接近於零」。我們仍然不太清楚鰻魚面臨的威脅,但我們卻又知道拯救牠的唯一方法:必須任牠自在生活。
例如:我們現在知道鰻魚正與疾病搏鬥,狀況更甚以往。牠很容易感染鰻魚皰疹病毒,這是日本人圈養鰻魚時發現的疾病,後來也因為進出口而在歐洲野生鰻魚間傳播開來。1996年荷蘭出現第一個病例;在德國南部的檢驗證實,幾乎一半的鰻魚都感染了病毒。
不知為何,這病毒似乎只影響鰻魚──因此才被稱為「鰻魚皰疹病毒」──這是一種很不舒服的疾病。病毒可以長期寄宿在宿主體內,一旦爆發,卻蔓延快速,極具侵略性。鰻魚在鰓和鰭周圍流膿出血。鰓細胞一一死亡,充滿血絲黏成一團。牠的器官也會感染,讓鰻魚昏昏欲睡,最終只能緩慢移動,在水面活動,直到牠放棄奮鬥,就此死亡。
鰻魚也會得寄生蟲病。例如,寄生性線蟲(Anguillicoloides crassus)。牠最早也是在日本鰻中被發現,於1980年代傳入歐洲,或許來自從台灣進口的活鰻。僅僅幾十年間,牠就傳遍了歐洲與美國。2013年美國南卡羅來納的一項研究顯示,有30%的鰻魚,早在玻璃鰻時期就已經攜帶這種寄生蟲。此外報告中還指出,將捕獲的玻璃鰻放入全新水域,反倒加速了這種寄生蟲的傳播,但人類此舉原本是刻意要拯救鰻魚群的。
這種線蟲專門攻擊鰻魚泳囊,引起出血、發炎和瘢痕。被感染的鰻魚生長速度慢,更容易染病。牠會移入淺水區,只能游短距離。它不見得致命,但一旦鰻魚感染了,就可能無法順利抵達馬尾藻海。
我們還知道鰻魚對汙染特別敏感。由於牠壽命很長,又處在食物鏈的上層,因此特別飽受工業與農業毒素的衝擊。和寄生蟲一樣,毒素似乎會阻礙鰻魚回到馬尾藻海的能力。例如,接觸多氯聯苯的鰻魚出現心臟缺陷與水腫問題,也無法貯存脂肪及能量,使長時間的遷移旅程幾乎無法成行。接觸各種殺蟲劑的鰻魚已經被證明無法承受自淡水過渡到鹹水水域的過程,假使我們單從表面看來,當前只有少數的銀鰻順利抵達繁殖地,汙染是一大可能因素。
有些理論確實很難證明。例如跡象顯示,鰻魚更常成為掠食者的戰利品,這或許不能直接歸咎人類;但可以想像的是,鰻魚因為毒素與寄生蟲而體弱不堪,移動更加緩慢,更接近水面,於是容易成為掠食者的目標,例如:鸕鶿,牠們最熱愛的佳餚之一,就是鰻魚了。
研究人員還認為目前人類造成的最嚴重的威脅,就是鰻魚遷徙時遭遇的各種實體障礙。水閘、洩洪道與其他人工水利設施,都可能阻止幼鰻游上水道,或讓成鰻無法進入大海。儘管水力發電廠對大環境有益,但對鰻魚而言是死路一條。大壩渦輪會讓前往大西洋的銀鰻送命,有些報導宣稱一座發電廠可以殺死近7成路過的鰻魚。為了繞過水壩建造的魚梯,多半都是為數量穩定的鮭魚客製訂做的。
當然,鰻魚生存的古老威脅就是人類的漁業活動,儘管其影響的嚴重程度,長期以來一直讓人爭議不休。鰻魚在歐洲許多地區原本就是很受歡迎的魚類;捕鰻人有自己的傳統、工具與方法,鰻魚產業更是特色獨具,也是某些地區的重要經濟支柱。過去幾十年來,歐洲對日本的出口更是急遽增加──日本人的鰻魚消費量佔全球的7成,但是跟歐洲與美國一樣,也嚴重感受到鰻魚的數量減少了。
對鰻魚繁複的生命週期最具毀滅性的行為,就是捕撈玻璃鰻。此漁業活動主要見於西班牙及法國──在巴斯克地區,蒜炒玻璃鰻近來搖身成為昂貴佳餚──由於牠們在生命如此初期的階段就被大量捕撈,當然會對總體鰻魚數量產生巨大的影響。
另一個難以指證,卻也是最嚴重的威脅就是氣候變遷。一旦氣候產生變化,大海洋流的強度方向也會有所改變,這一點毋庸置疑,所以嚴重阻礙了鰻魚的遷徙。海流變化會使銀鰻更難橫渡大西洋,找到合適的產卵地,讓新近孵化的鰻魚幼體,只能無助地沿著海流漂往歐洲。
一旦洋流力道減弱,更改路線方向,馬尾藻海的鰻魚產卵地點勢必受到影響,這表示幾乎沒有重量的透明鰻魚幼體,可能無法找到該帶著牠們前往歐洲的正確洋流,或是牠們有可能被帶往錯誤的方向。此外,氣候變遷也會改變洋流的溫度與鹽度,影響幼體在旅行途中所吃的浮游生物的數量。
幾項研究指出,氣候變遷是造成近年來抵達海岸的玻璃鰻數量減少的主要因素。這是最不妙的警訊。畢竟這表示鰻魚的遷移與繁殖──數百萬年以來一直都很複雜敏感的過程──僅在幾十年間,就變得踉蹌蹣跚,不堪一擊。
那麼,假使鰻魚真的滅絕,牠又將何去何從?當然,牠會存於圖畫、回憶,與故事。一個從未完全揭露的謎團。
也許鰻魚會成為新的多多鳥。也許牠會愈來愈不像一個真實的生物,而成為悲劇的象徵,提醒人類在自己渾然不覺時,足以造成什麼後果。
多多鳥是一種笨拙的大嘴鳥,人類在16世紀末第一次遇到這種鳥,不到一百年後牠就被全數獵殺滅絕了。牠們最早由荷蘭船員在印度洋某座島嶼發現,後來這座島嶼被命名為模里西斯,也是目前已知多多鳥唯一曾經居住過的地方。
這種鳥體型龐大,大約1公尺高,體重超過13公斤。牠的翅膀很小,灰褐色的羽毛,禿頭,黑綠相間的彎曲嘴喙。牠的黃色雙腳粗壯有力,臀部渾圓寬大。牠不會飛,動作很慢,在人類登島前沒有天敵。當時的畫作常常嘲笑牠的外觀,語帶諷刺;牠無表情的雙眼看起來就像是巨大無毛頭部的兩顆小鈕扣,神情看來總是一臉詫異,顯得不太聰明。
多多鳥最早的文字紀錄出現在1598年一支荷蘭探險隊的報告,內容描述牠比天鵝大上一倍,但雙翅卻僅與鴿子差不多大小。也有人說牠的味道不特別好,肉質不管煮多久都過硬,但至少胸腹肉是可以吃的。
當然荷蘭船員就是這麼對待多多鳥的:他們吃了牠。畢竟很容易就能抓住牠。據說在船員接近牠們時,鳥兒們甚至沒有試圖逃跑。牠們體型笨重,渾身是肉;只需要3、4隻就可以餵飽一整艘船。多多鳥被描述為漠然無感,不受干擾,似乎完全無法想像另一種生物可能對自己構成威脅。1648年的一幅畫顯示,船員們興高采烈地用大棍子將笨手笨腳的鳥兒打死。牠們不僅成為飢餓荷蘭船員的晚餐,人類更將其他侵略物種帶到島上:狗、豬與老鼠,牠們與多多鳥爭奪空間和食物,襲擊牠們的鳥巢,吃了牠們的蛋與雛鳥。
1681年夏天,一名船員班傑明・哈利在日記中寫道,他在模里西斯見到一隻多多鳥。這是最後一份人類記載親眼看見活多多鳥的紀錄。假如紀錄屬實,這有可能是世上最後一隻多多鳥。然後,牠死了,滅絕了,留下的記憶全都褪色了。
有一段時間,多多鳥被人類遺忘,或經過描繪,成為一隻半神話的生物,不是真實世界曾經出現的鳥類。有些人甚至懷疑牠確實存在過。亞歷山大・梅爾維爾與休・史特蘭於1848年出版兩人合著的《多多鳥與牠的莫逆之交》,為當代對多多鳥最詳盡的描述,但同年兩人被迫承認這種已滅絕160多年的鳥類資訊極少。「我們擁有的僅是不科學的水手的粗略敘述,3、4幅油畫以及散落的骨片,這些碎片近兩百年來因為被人忽視,於是保存了下來。相較之下古生物學家的資訊更豐富充足,他們才能夠判斷這種數百年前早已不見蹤影的物種特性,比起查理一世時期的鳥兒們更有其獨特性。」
不過,這兩個人至少確定多多鳥的近親是鴿子;現代DNA測試也證實了他們的發現。但除此之外,梅爾維爾與斯里克蘭並沒有為人類之於多多鳥做出太大的貢獻。他們認為這種特立獨行的鳥類居住於當時的棲息地,一點也不意外。物種的時間與地理分布跟環境氣候沒有關係,當然也無關進化。「造物主」藉此保存「大自然亙古不定的均衡」。多多鳥滅絕也不奇怪了。「死亡,」他們寫道,「是物種,也是個體生存的自然法則。」
不過,我們遲早都會認識許多關於多多鳥的知識。1865年,牠的第一塊化石被人發現,科學家對牠獨特的命運產生了興趣,因為這種鳥不只長相獨特怪異,更象徵了人類對地球萬物窮盡氣力造成的各種衝擊,成為最血淋淋的例證。19世紀末期起,多多鳥成為許多作品的主要角色,路易斯・卡洛爾(Lewis Carroll)的《愛麗絲夢遊仙境》最具代表性;毫無疑問,牠是當今最廣為人知的滅絕物種。多多鳥儼然成為象徵代表,不僅是人類魯莽媚俗的警惕,也拿來隱喻過時或過氣的人事物。「多多鳥」意指愚蠢笨拙的傢伙,無法適應新時代,被遺忘拒絕,最終成為無名小卒,默默無聞。
英文裡有種說法,「跟多多鳥一樣沒救了。」或許總有一天,我們也會說,「跟鰻魚一樣沒救了。」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