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製作團隊

二二八與白色恐怖,曾是台灣社會不可言說的禁忌,也是幾代人少有認知的土地記憶。隨著解嚴,許多藝文創作者嘗試透過作品呼喚那些被封印的歷史幽靈,電視戲劇正是其中之一。而以威權統治時期為背景的影劇作品,在歷史事實的框架下,不僅在製作上須嚴謹,還得經歷投資考驗、評估市場考量,能否受到平台喜好而多接觸到觀眾,也是難關。而觀眾的檢視,更是重要。
2025年3月底播出的客語影集《星空下的黑潮島嶼》,是台灣第一部聚焦於綠島新生訓導處政治犯的電視影集。其創作過程歷經多年打磨,卻在尚未完成後製、無人看過成品的階段,成為立委凍結預算的理由,引發藝文界強烈反彈。這起事件讓本劇所描述的歷史現場──1950年代一群因思想、政治信仰、人際往來或各種理由受當局質疑,而被囚禁於綠島的知識菁英──重新映照出離台灣創作者並不遙遠的政治審查陰影。
2025年1月16日下午,正為公視台語台拍攝新劇的王傳宗,看到製作人傳來的客家委員會預算提案表時,心裡比當時覆蓋台灣的大陸冷氣團還要凍寒。
這份由國民黨立委徐欣瑩提案的表單寫著:「強調具有白色恐怖背景的政治犯生活《星空下的黑潮島嶼》或中壢事件為時空的《1977年的那張照片》(現改名為《那張照片裡的我們》)兩部影視作品,內容雖有客家語言,然除了客語外,對客家文化著墨甚少。」因而要凍結客委會客家傳播行銷藝文傳播推展計畫預算4億元。
而王傳宗,正是《星空下的黑潮島嶼》的導演。

隔(17)日,王傳宗在Facebook發表2,500字的長文以示抗議:「一部客語比例那麼高,費盡心思置入客家元素,在年代服裝與歷史細節製作注入大量心力的作品,竟然被立委以『對客家文化著墨甚少』的寥寥字句來凍結客委會預算?」
王傳宗認為,預算遭到凍結原因,表面理由是「客家文化少」,實際上立法委員介意的是「白色恐怖」,否則,劇還未播出,如何確定劇裡客家文化的占比有多少?況且,「客家語言難道不就是客家文化最重要的一部分。到底立委諸公們還想看到什麼刻板印象的客家文化?」他在抗議文中如此質疑。
「顯然,國民黨立委諸公們是沒有看劇的,只是隨好事者起舞,像跳梁小丑般對一個戲劇節目指手畫腳。」《聽海湧》的導演孫介珩早王傳宗兩天發文回應:「其目的除了顯示自己才是這個國家的老大以外,也是跟包括我在內的所有影像創作者們說:『以後要拍什麼,自己要想清楚喔!拍的不對,後果自負囉。』」
因拍攝公視「人生劇展」單元劇方能踏上導演之路的王傳宗,也有類似的想法。他不僅在文中衷心感謝公廣集團給予創作者空間和機會,也自陳面對這波從公視延燒到《星空上的黑潮島嶼》的「無理摧殘之火」,讓他不得不發聲。王傳宗說,自己之所以能夠拍攝《星空下的黑潮島嶼》,就是這些爭取言論自由、失去自己的生命,或是身陷囹圄長達半輩子的前輩們所換來的,「我不願意看到台灣變成像對岸中國一樣,(成為一個)創作者看到敏感題材會自我審查的國家,會害怕拍完後被秋後算帳、被踩到痛腳的立委諸公們凍結款項,完成不了作品家破人亡。」
一個多月後,在接受《報導者》採訪時,原本談笑風生暢聊拍攝過程趣事的王傳宗,被問及客台與公視等單位預算凍刪問題時,突然語氣高揚且激動了起來:「我覺得這是一個警訊,或是給創作者一個教訓,像是要告訴之後的創作者『如果要做這種題材,你會拿不到錢,因為你的預算會被凍結』。這是一種寒蟬效應嘛。」
「台灣是一個自由的國度,我們做什麼題材都不會被審查,能夠監督我們的就只有觀眾跟市場──但至少我在創作時,是自由的,」王傳宗感嘆,如果因為題材而被凍結預算的情況早一點發生,《綠島先生》或許根本無法完成。而這種透過凍刪預算做的「警告」,無疑是一種「審查」,也會在台灣創作者心中埋下一個自我疑懼的種子,「我對這種舉動非常反感。」

事實上,1978年出生的王傳宗,和許多在戒嚴時期出生、成長的台灣人一樣,對於白色恐怖談不上有什麼清楚認識,只是隨著台灣民主化步伐長大的過程中,逐一撿取過往被遮掩的記憶碎片,卻始終模模糊糊、一知半解,無法看到歷史的全貌。
2018年,王傳宗在網路上讀到作家米果的專欄文章〈曾經,火燒島有最強的醫務室〉,才驚覺自己對這段歷史竟然如此陌生:「這是我第一次知道在1951年,國民黨政府曾抓了1,000多名政治犯去綠島進行『思想改造』。這群知識分子被送到了綠島後,不但沒有自生自滅,還在資源匱乏的蠻荒之地,種出一朵希望的花。」
米果在文章裡,提及1950年代關押在綠島新生訓導處之醫生政治犯們的專科與背景:「初期開刀及牙科器材都沒有,以後才漸漸有規模,開過好幾例手術,連軍官眷屬跟綠島的婦女生產,也由新生訓導處醫務室負責手術。包括藥物以及簡易的醫療設備,都是由這些醫師的家屬從台灣本島寄送過去,兩三年之後,已經有醫務室跟開刀房。過去綠島病患要送到台東開刀,有了新生訓導處的這群醫師,就不必再等船過海了。」
而米果之所以寫下這篇專欄,是因為得知政治案件當事人蘇友鵬去世的消息,蘇友鵬正是這群醫生政治犯之一。他在1926年出生,日治時期考上台北帝國大學醫科,二戰期間被日本政府徵調為學徒兵,直到終戰後才繼續學業並留在台大醫院服務。但1950年5月13日上午,蘇友鵬的命運再次轉變――台大醫院開例行會議時,第三內科主任許強、眼科主任胡鑫麟、皮膚科醫師胡寶珍、和當時任職耳鼻喉科的蘇友鵬等醫師,遭情治人員逮捕。其中,許強和台大醫院外科兼防疫科主任郭琇琮等14人,於1950年11月28日在馬場町被槍決,其他人則被送到綠島監禁。
1951年,隸屬台灣省保安司令部管轄的「新生訓導處」於綠島成立,是白色恐怖時期政治案件當事人被發監執行的主要監獄。高峰時期,曾有2,000多名政治犯被關押在綠島。
蘇友鵬在其口述傳記《Todes Märsche死亡行軍:從神童到火燒島叛亂犯》中,回憶他們這批送往綠島的千名政治犯,搭著美軍遺留給國民黨政府的兩棲登陸艦(LST),在陰暗、充斥柴機油惡臭味和骯髒油漬的船艙地板上,倆倆銬在一起,經過兩天兩夜搖晃顛簸的折騰,才於1951年5月17日停靠在一座島嶼近海──在漁船薄暮歸航、被夕陽染紅時,遠望這座島,會見到猶如熊熊野火簇燒一般的景象,因而有「火燒島」之稱。儘管火燒島距離台東很近,但因黑潮經過、海流甚快,即使到今日,台灣綠島之間往來仍舊無法直線航行,只能順著海潮繞道而走。

這個於1949年被改名為「綠島」的小島,當時居民有2,000人。當這些從台灣來的「比殺人犯還兇惡的犯人」上陸時,在地人不免感到驚恐又好奇,但見這些外地人犯上岸後還得走上好幾公里的路,仍善意地打水給他們喝。而這段從搖晃陰暗的登陸艦,到前往新生訓導處的泥沙路,正是《星空下的黑潮島嶼》一開始引領觀眾踏上這歷史之岸的時空再現。
「很多人說『台灣缺題材』,把自己只能拍小清新跟偶像劇(的結果),歸咎於台灣沒有好題材,但這(綠島的政治犯生活)不就是個好題材嗎?這題材根本超讚的!」王傳宗暗下決心,想要透過戲劇形式來說這段故事。
在投入《星空下的黑潮島嶼》的劇本寫作和田野調查前,王傳宗曾因一場大病停工治療、休養了幾年,而這部以綠島新生訓導處為背景的創作故事,便成為他復工後的第一個案子。他找來幾個編劇一起閱讀口述資料與文獻史料,並訪談了胡子丹、蔡焜霖、張常美、蘇玉鑑等政治案件當事人,以重構綠島新生訓導處的生活細節及前輩們的故事。
儘管花上一年的時間做田野調查與劇本編寫,也成功入選了公視戲劇孵育計畫,但王傳宗卻未想到:就算劇本完成,這個綠島政治犯的故事,別說登陸了,連「船」都差點搭不上──儘管公視為這份劇本辦了創投會議,廣邀投資人聆聽簡報並且媒合拍攝的可能性,但這個原名為《綠島先生》的拍攝計畫,卻因題材與執行難度讓出資方有所疑慮。最後在歷經疫情、金主撤資等波折後,終於由客家電視台接下這個拍攝計畫,出資製作,並以《星空下的黑潮島嶼》之名重新出發。

「這種題材不會有商業電視台願意做,如果公廣集團不做,就沒有人會做了。」客家電視台節目部經理羅亦娌回憶在影集《茶金》的製作後期,聽到知名製作人湯昇榮提起導演王傳宗以及那部「有一群醫生的劇本」,立刻產生高度興趣。後來,羅亦娌又聽聞《綠島先生》在籌備過程中屢遭挫折,便主動向客家電視台台長爭取製作這部作品,這才讓這部戲重遇轉機。
羅亦娌和王傳宗都是後戒嚴世代,也都是長大後才逐漸明白灣近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因此,在看到《綠島先生》劇本前,羅亦娌同樣對1950年代的歷史和新生訓導處的生活一無所知,「但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故事,就像一部斷代史,我們必須很認真看待這樣的題材、把每個斷代史都接合起來,才能呈現出完整的歷史。」
2022年決定接手製作這部作品後,羅亦娌將重組編劇團隊視作啟動此案的第一步。幾乎整整一年期間,羅亦娌、導演和編劇團隊每天早上9點開始就待在會議室討論一整天,有時甚至還晚上11點才喊停,「編劇通常是單打獨鬥的工作,但我想建立一種不同的創作模式:一個能打群架、共同努力的團隊,」羅亦娌強調。
在2024年金馬國際影展試映時,《星空下的黑潮島嶼》被觀眾形容為「台灣版的《機智醫生生活》(슬기로운 의사생활)」,編導也自認這部作品的調性讓人想到美國經典影集《百戰天龍》(MacGyver)──每一集幾乎都有清楚的手術畫面,更不乏科學知識與實作。而這些劇情設計,多半都曾在新生訓導處出現過。這些被關押到綠島的台灣菁英,透過自己的知識與專業,一步步改善當地生活、甚至救助居民。例如,綠島因土地貧瘠和鹽化,只能種出地瓜、落花生,但在具備農業專長知識的政治犯嘗試下,終於有了菜園。
「新生被移送至綠島後,加上管理的官兵與眷屬,人數最多時約有3,000人,(生活)需求量相當龐大⋯⋯。最先發出抱怨的,不是新生們,反而是管理新生的官兵,他們無法忍受如此艱困貧乏的生活。」
政治案件當事人蘇友鵬醫師曾口述當時的情況:新生們為克服綠島自然環境的限制,研究出以茅秆草和稻草製作的防風籬笆,隔絕綠島冬季的薄霧,農作物才能正常生長。此後,每個中隊開闢大約一甲左右的土地作為菜園,同時開始養殖豬、羊、雞等家禽家畜,「不僅供應自己食用,甚至還可以販賣自己生產的農產品及家畜給綠島當地居民。」
養豬知識和種菜的研究過程,在《星空下的黑潮島嶼》中,是透過勤懇、擅於廚藝的19歲客家青年邱永貴(吳念軒飾演)視角,所帶到觀眾眼前。

除了農業知識的實作運用,這部作品最重要的核心「醫療」,也透過鏡頭敘事具體呈現。《星空下的黑潮島嶼》第一集開始不久,邱永貴就因士兵開槍,小腿遭子彈貫穿,陷入斷腿的險境;此時出於醫者本能的主角群,不顧自己未被授權、也不管環境簡陋,想方設法避開眾人視線,替這位剛認識不久的青年開刀急救。而這只是開頭的「小試」,隨著劇情推進,難產、嚴重外傷、傳染病,都成為主角們必須逐一克服的挑戰與課題。這些大大小小的病症與傷難,也都曾在1950年代的綠島真實發生。
當時替難產孕婦剖腹接生的「新生」,是涉入基隆工委會案、曾任省立基隆醫院婦產科醫師的王荊樹,以及涉入學生工委會案的旗山醫院外科醫師林恩魁。兩位醫師憑著高超醫術保住孕婦一命,消息傳遍全島,當地居民甚至稱他們為「綠島守護神」。這段真實故事,在《星空下的黑潮島嶼》則被改編成處長夫人難產,由外科醫師羅有德(黃河飾演)與婦產科醫師李木雄(夏騰宏飾演)一起急救,從而成為醫務室成立的關鍵契機。
蘇友鵬就曾在口述中提到:
「有人戲稱,在新生訓導處唯一缺少的,就是精神科權威林宗義博士(二二八受難者林茂生博士次子,開創台灣精神醫學先鋒者)。如果再增加精神科,新生訓導處醫療所堪稱是完整的教學醫院。」
他進一步強調:事實上,新生訓導處這一群台灣頂尖醫師,原本應是帶領台灣醫學界發展的先行者,卻遭國民黨政府以「匪諜」、「叛亂」、「顛覆政府」等莫須有的罪名禁錮在火燒島,所以才有人以白色恐怖式的黑色幽默笑稱這座醫療所是「台灣大學醫學院綠島分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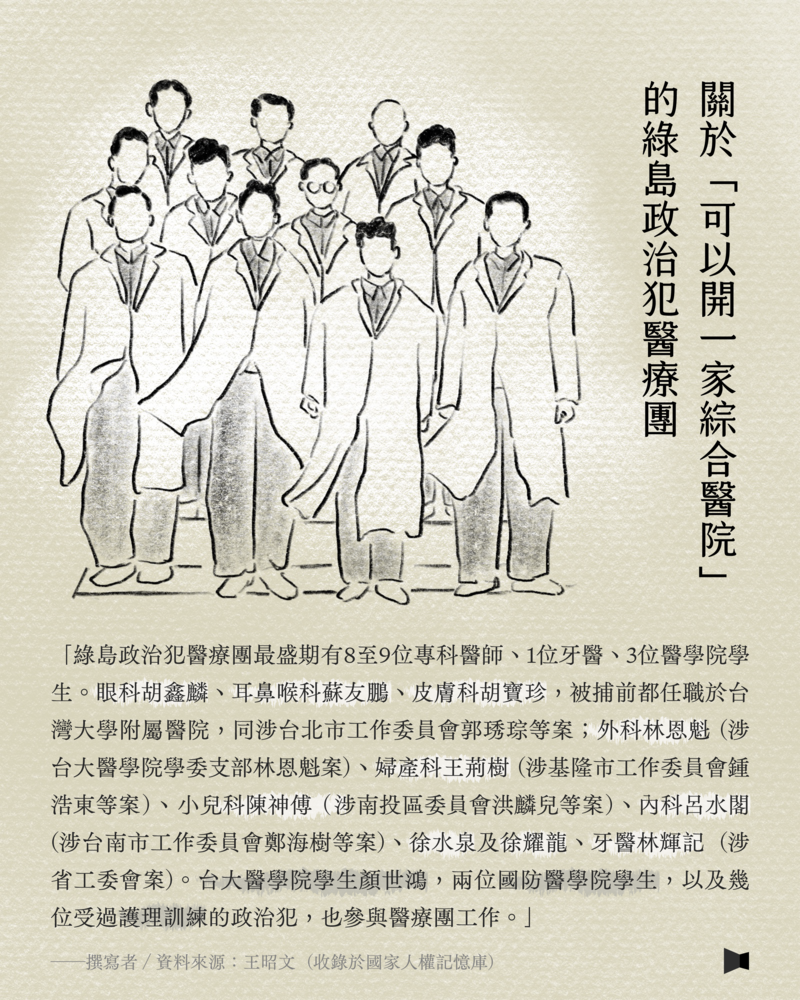
然而,喜歡《急診室的春天》(ER)的王傳宗,儘管以「一群醫生的故事」為創作主軸,最初劇本卻像是編年史一般厚重的歷史劇。這讓羅亦娌看完直搖頭,認為必須要大改,才能讓故事「影像化」。
羅亦娌表示,劇本之所以需要大刀動斧,並在概念上重新包裝,都是為了吸引觀眾──尤其是那些原本不認識白色恐怖,或從本能上就排拒白色恐怖題材的觀眾──因此才花了一整年時間,在編劇團隊共同合作下,讓這部「歷史劇」轉變成一部「複合式醫療劇」。

她進一步補充,公廣集團如同英國《BBC》、日本《NHK》一般,不僅有培養下一代影劇人才的社會責任,也要發展出更多元、不受限制的特色題材。此外,儘管《星空下的黑潮島嶼》是由客家電視台出資製作,將主要角色設計為客家人、並以客語對話,但為了符合當時時代的特性,醫生角色之間的溝通,多是日語為主,偶而夾雜台語和客語。新生訓導處的國民黨軍官和軍醫,也都帶著中國各省的多元腔調。
「這是一個掙扎,你知道嗎?」羅亦娌坦言,以科學和醫療來包裝這麼一個政治嚴肅的題材,他們也會擔心被外界質疑「太輕鬆」、「踩著別人的血前進」,甚至害怕被指控是在「幫國民黨政府洗白」。
為此,羅亦娌時常拿著劇本到處問工作人員:這樣的安排妥當嗎?例如,「我們都是時代的人質」這句由國民黨軍官說出的台詞,既是羅亦娌想出來的,但也令她十分焦慮,不斷向劇組人員確認團隊:這樣寫真的可以嗎?別人會不會覺得我們在淡化加害者的責任?
根據白恐研究和政治案件當事人的口述:新生訓導處的管理者,多是不適任現代化戰爭的老兵,被貶謫左遷、不獲重用的軍吏更占了多數。例如第一任處長姚盛齋,原是基隆要塞司令,因失去蔣介石恩寵才被派至綠島。而《星空下的黑潮島嶼》也花了不少篇幅描寫這些軍官的樣貌、心境與行為動機,例如一位「無能」的軍醫其實是受戰爭所迫、無法完成學業的醫學生,這些背景呈現,都是編導試圖傳達:他們可以被簡化成加害者,但從某些面向看,也有受害者的遭遇。
但無論劇組人員如何向她保證這些台詞不是在替誰「洗白」,羅亦娌還是非常擔心──畢竟不管怎麼寫、怎麼做,對有既定意識形態的人來說,都沒有影響,因為只要觸及白色恐怖、轉型正義題材,本身就是一種控訴。

為此,羅亦娌在通告單上留下這樣的句子:
「我們沒有要對立,沒有要講對錯,只是延續一個時代的記憶──在這個時代底下,每個人都有自己時代的長相。」
這段話,是負責製作通告單的副導,頗具巧思地向劇組廣邀的「是日金句」之一──拍攝期間,無論是對故事的心得感慨,或只是純粹發洩的喃喃自語,只要能發人省思,就會被列在通告單的「頭條」。例如:「死亡是一個數字,還是一段歷史?」又或者是「在那個時代,多少母親,為他們囚禁在那個島上的孩子,長夜哭泣。」
而羅亦娌提醒團隊的句子,就印在2023年9月25日,開拍第一天的通告單上。
2023年9月24日,《星空下的黑潮島嶼》開拍前一天,王傳宗、羅亦娌等人前往蔡焜霖的告別式,向他報告這部戲劇將在隔天開拍──93歲辭世的蔡焜霖,是少年刊物《王子》雜誌的創辦人,就讀台中一中時,他受邀參加老師所組的讀書會,之後被軍警當街抓捕,並成為綠島新生訓導處的第一批「新生」。
多年來,蔡焜霖以見證者的身分,不斷向各界訴說難友的故事與新生訓導處的一切。而他不僅為台灣社會留下諸多口述資料和歷史見證,也是王傳宗最初的田野訪談對象。
「站在他的靈前拈香之際,胸口升起一股時不我予的遺憾。」王傳宗在告別式當天於社群網站感傷寫道:「套句『新生訓導處』裡的順口溜,『你不殺時間,時間就會殺了你。』時間無情地帶走了蔡前輩,誰都逃不了這生老病死的宿命。但藝術與作品會留下,影像見證每個時代的榮華滄桑。」
畢業於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的王傳宗,第一份工作是在新聞台擔任編輯,負責黃金時段前幾個新聞節目的rundown編排。雖說「今日的新聞今日畢,明天的新聞明天來」,但王傳宗心中始終牽掛著「後來」:「台灣的新聞只會提到最驚悚的那一塊,很少有後續報導。可我總會好奇,昨天報導的那對母女,之後怎麼了?但我永遠不會知道,因為新聞已經過去了。」做了一年,他自認再無法繼續做這份工作,因為他沒有辦法不去在意、但也始終無法得知:那些新聞裡的人,後來怎麼了?
「戲劇不一樣,新聞給的議題,可以透過戲劇呈現,而且我可以給它一個結局,讓自己跟觀眾都知道這些人物最後怎麼了,我甚至可以給它一個好的結局,就算現實生活沒有這麼美滿。」辭掉新聞台工作後,王傳宗自行摸索著如何創作劇本;後來因為同學向公視「人生劇展」投案入選,找他當導演,王傳宗才自此走向影劇之路。
然而,自2006年開始拍戲至今約20年,王傳宗導過許多種類的戲劇,且幾乎年年拍一部以社會議題為背景的戲劇,嘗試挖掘一般觀眾不可能在主流媒體裡看到的底層角落,但卻未曾接觸過歷史劇。當以白色恐怖為背景的《星空下的黑潮島嶼》成為他的第一步嘗試時,不免緊張。所以開拍前一天、在蔡焜霖前輩的告別式上,他如此感嘆:
「站在歷史前,每個人都微不足道。更怕的是辜負了前輩們給我們這可貴的言論自由。期許自己能用更謙卑的態度來看待這段歷史。」
「但故事就是故事。」在完成作品的前夕,王傳宗對《報導者》表示,自己沒有被白色恐怖或轉型正義的概念綁住,他認為,白恐只是定義那個時代的名詞,轉型正義則是論述,而他只要把田野調查中觸動人的故事用一種更立體的方式傳達出去就夠了,「我的初衷很單純,我就是要拍戲,剛好這個故事又沒有人看過,我想把它拍出來。」
《星空下的黑潮島嶼》這個片名,除了透過流經綠島的黑潮,傳達政治壓力與束縛,也藉著「星空」這個詞,指向希望。羅亦娌笑說,儘管很多人都覺得片名太長、乍看也不知道什麼意思,但星空這個意象對於整個故事甚至那段歷史,都有其意義。
「綠島生活這麼黑暗,但星空這麼美這麼亮。仰望星空,對這世界才有盼望。」
羅亦娌表示,星空隱含的期待,是當時領導新生訓導處醫務室的胡鑫麟醫師說過的話。
胡鑫麟是台灣眼科醫學權威,曾替台大校長傅斯年看診,傅斯年對其醫術與人格也相當感佩。當胡鑫麟於1951年至1960年間被關押在綠島期間,他時常望著星空,甚至親手繪製出精密的星空圖。之後,他將星空圖送給兒子胡乃元時,半開玩笑說道:
「做這張星空圖,是為了萬一有機會划船逃離綠島,就不會在太平洋上迷失方向──因為有了星空圖,就能從天空中找到回來台灣的方向。」
胡乃元長大後,成為國際知名的小提琴家。而他擁有的第一把小提琴,便是綠島的政治犯們製作的──會拉小提琴的蘇友鵬醫師,以自己的琴作為範本;專攻美術的陳孟和,則以廢棄漁船的甲板、或鋤頭的硬木等材料,製作出許多把小提琴。
不只小提琴,相機架、暗房、底片印相機,甚至醫療器具,都是綠島政治犯們親手所做。因此,除了醫師,《星空下的黑潮島嶼》也帶入了廚師、擅長攝影的美術系學生等角色,以拓展故事的豐富度。而主角們在劇中製作的暗房、星空圖或其他現代社會所需的物件,也都曾是前輩們親手做過的,劇組更是設法還原其真實感。
作為製作人,羅亦娌不斷強調拍攝製作過程的嚴謹,及劇組為了製作品質所付出的成本──尤其攸關科學,更是得「斤斤計較」,只因「科學是不容挑戰的」。因此他們邀請了各領域的專家學者擔任顧問,且凡劇情中會出現的道具或畫面,都得反覆與顧問商榷,包含:綠島有沒有石英砂?當時發生的是鼠疫還是瘟疫?腹部開刀要切幾層?子宮是什麼顏色?連拍攝星空時,都得確認那個年代星星的相對位置、甚至是亮度。
「我只要拍得出星星就好,什麼星座?I don't care。」談及此,王傳宗忍不住崩潰,羅亦娌笑說導演終於說了真話,但也反覆強調,即使是顧問要求他們閱讀伽利略(Galileo Galilei)的理論,他們也得照做,「因為科學是不容挑戰的。」
相較科學的絕對性,時代下的人物故事就有重新塑造的空間。儘管《星空下的黑潮島嶼》的角色與部分情節都有可參照的人物、事件,但編導還是將這些人物混合、改造,「因為,這不是人物自傳,也不是歷史故事,而是一個時間的集合、人物的集合,」王傳宗強調,重點是這麼一群醫生到荒島之上,靠自己的方式生存下來。
王傳宗提起自己喜歡的電影《辛德勒的名單》(Schindler's List),他說,導演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曾將辛德勒(Oskar Schindler)這位視錢如命的納粹商人,打造成拯救無數猶太人的英雄,因而受到批評,「但100個人會有100個觀點,我們很難掌握觀眾的想法,只能盡可能把故事說好。」
「可能大家看了這部戲,也只能感受到這跟白恐有關,而無法拼出全貌。但對我來說,(這個故事)可以在觀眾心裡留下一個種子──就算這個種子很微小,總有一天也會在他們的生命中發芽。」
王傳宗說,就像他在大學、研究所時經歷的民主事件,雖沒有對當時的他造成衝擊或改變,但在他心裡留下種子,讓20年後的他拍了這部作品,也對國會凍刪預算的事,發出聲音。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