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匡噹,匡噹⋯⋯」台南鐵路地下化工程如火如荼地進行,從台南市開元陸橋旁的黃春香家頂樓往北望去,鐵路東側已清出一片施工區域;幾年前,這裡滿佈綠蔭和住家,因為地下化工程由「原軌案」改「東移案」,沿線土地將被永久徵收、居民也得迫遷。8年前,拒遷的住戶組成自救會跟政府抗爭、打行政訴訟,但節節退敗。
今年6月,僅剩最後4戶拒遷。7月21、23日,在鐵道局採取強拆行動下,剩自救會會長陳致曉仍然拒絕拆遷,黃春香等3戶簽下了自拆同意書。照顧99歲老母的黃春香雖在各方壓力下簽字,仍希望有轉圜餘地,日前發出律師信要求鐵道局「撤回自拆切結書」。今(9月20日)是黃春香自拆期限最後一天,9月23日陳致曉家也將面臨拆遷期限,陳致曉放話,政府若強拆、他將發動擋拆。因東移案被影響的迫遷戶總數共340戶,有高達9成5的323戶居民組成自救會,時至今日,只最後剩下2戶堅持。
《報導者》記者深入抗爭現場及抗爭者家中,目睹並記錄拒遷戶如何在各方壓力下崩解;同時分析這場大規模的反迫遷運動中,官方策略與拒遷者內部的矛盾,讓抗爭力量逐漸消散的過程。
時間拉回今年7月21日凌晨,黃春香已與鐵道局人員對峙18小時,上百名警力圍著陸橋旁的黃宅,警力人牆隔開聲援民眾與黃春香,鐵圍欄的影子映在黃春香的臉上,像是一名被囚禁的人。 近百名聲援者高喊:「護家園、反徵收!」聲音一落定,便沒入寂靜漆黑的夜,這句拒遷戶的抗爭口號,是他們8年來的訴求之一,只是聲量日益微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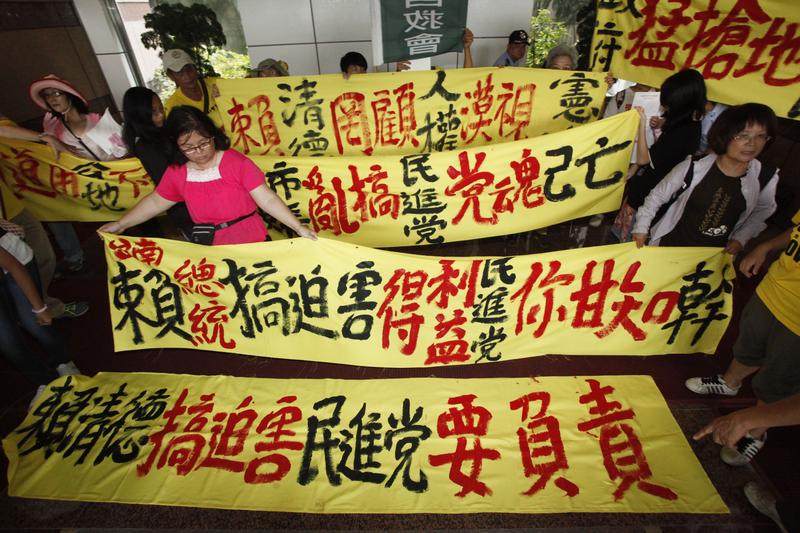
預算高達近300億的台南鐵路地下化重大公共建設,從規畫到動工,走了25年,這條長約8公里的地下化工程,從「原軌案」轉彎到「東移案」,也從租用民地到強制徵收,影響340戶家庭。
「反南鐵東移」不僅沒有民意作為後盾,隨著徵收程序不停進展,只能透過行政訴訟,控訴官方政策轉彎、剝奪人民「居住正義」,但今年4月行政訴訟一審敗訴後,公部門軟硬兼施的策略下,拒遷戶的內、外壓力遽增,抗爭者從8年前的3百多戶,到今年7月時只剩最後4戶拒遷戶:反南鐵東移全線自救聯合會會長陳致曉、黃春香、曾肇陽和呂瑞成。
7月下旬的一波拒拆遷抗爭後,4戶中有3戶簽下了「自拆同意書」,曾肇陽家日前已拆除,呂瑞成因行動不便拆除期限寬延至9月30日,但精疲力竭的他,已決定日後搬至妹妹家住,無力抗爭。剩陳致曉拒遷和半拆戶黃春香2戶在做最後奮戰,抗爭的防線面臨全面瓦解。

反對迫遷的居民大量退場,最主要的關鍵是台南市政府2013年規劃推出「鐵路地下化專案照顧住宅」(又稱安置宅),讓抗爭者內部開始產生變化。「這是製造拒遷戶之間的內部矛盾、削弱抗爭正當性最關鍵的因素,」陳致曉無奈地說。 他進一步解釋,當初台南市政府為了先消除反對意見,不斷放寬拒遷戶的申購安置宅的條件,從一開始必須簽署「搬遷同意書」與「原屋拆除」的雙條件,到最後只要先繳交保證金,保證金也從10萬降至2萬、甚至免費。擔心未來沒地方可住、接受「新家」換「舊家」的拒遷戶都去登記了安置宅。讓自救會的會員一下子減去一半,僅剩100多戶。 陳致曉說,當時許多抗爭戶先登記安置宅,只是想先「卡個位」擔心拆除房子後會無家可歸,並不等於同意被徵收。但時任台南市長賴清德卻對外宣稱「已經有200多戶同意(徵收)」,讓自救會失去抗爭正當性。
2017年安置宅正式完工後,建設公司和台南市府同時寄存證信函給登記住戶,要求在期限內繳交幾百萬的購屋費用,否則就喪失購買資格,「老百姓錢從哪來?只好搬遷同意書簽下去,先領錢(徵收補償費)再自己貼錢買安置宅,搬進去,」陳致曉說。
曾是拒遷戶、最後也妥協搬進安置宅的陳秌沛受訪時即指出,本以為原來50坪大的土地被徵收後剩25坪,仍抱持著一絲希望,盼重新蓋回自己的家,沒想到找建築師討論,調出地籍圖後才發現只剩15坪,而且只有9.8坪可重建房屋,其餘是道路用地。土地加上房屋,連同拆遷補償等,一共只有390萬元,若搬去巿府規畫的安置宅則要550萬。考量年逾八旬、中風的母親,身心俱疲的陳秌沛瞞著老婆,最後一刻還是去登記了安置宅,也在5月簽下自拆同意書,一家6人現在住在30坪大的安置宅裡。
2020年4月,高雄高等行政法院認定南鐵東移都市計畫符合公益性、必要性,判居民敗訴,是拒遷力量第二次挫敗。
原本自救會還有40戶,認為大勢已去連行政訴訟都無法保障他們居住權益,最後31戶簽下拆遷同意書,僅剩下黃春香、陳秌沛、張文耀、呂瑞成等9戶散落在不同行政區的鐵路沿線,抗爭力量變得更薄弱。
同是最後拒遷戶的呂瑞成與陳致曉等3家,距離黃春香家便有2公里遠,開車要8分鐘。拒遷戶彼此之間不認識,甚至有拒遷戶是在黃春香家強拆前一天,才第一次來到黃家聲援。

在人情壓力下,呂瑞成雖不情願,也只能接受區長的提議,最後開協調會,在自拆同意書上蓋印章。區長為了表現誠意,還特別要求顧及呂瑞成身體不便、搬遷困難,多給10天的緩拆期限。
不同常理的是,這場會議一開始,呂瑞成就在一張「空白會議記錄」上,先蓋上了印章和手印,才開始後續一個多小時的談判。《報導者》記者也在現場全程記錄,最後,區長後來才裁示,會議紀錄重新製作,與會代表重新簽名蓋章。
拒遷戶彼此的資訊交換不夠即時和順暢,因耳聞「別人也同意了」,讓拆遷戶被影響,也成了公部門各個突破的策略。

最後4戶拒遷戶,承擔的不只是自己家園存續的壓力,甚至肩負反南鐵東移運動最後守衛的期待,更是官方使盡一切力量要「遊說」的重點,內外壓力下,進退皆難。
以黃春香為例,她的4層樓住家屬於半拆戶,有三分之二被徵收,剩餘三分之一仍可使用。就在預告7月21日強制拆除前一星期,黃春香住家外的橋墩就被裝上2支監視器,強拆前一天,出入口又新增2支監視器。4支監視器的鏡頭全部朝向黃春香家。
黃春香當面質問台南市北區區長李皇興、警察與施工人員,甚至要報案指控裝設監視器侵犯她的隱私,最後鐵道局只承認安裝了其中兩支監視器,理由是「工區內有貴重機具,怕被偷走」,但所謂的工區還沒有機具進駐,只有一般常見的鐵圍籬。
巧合的是,就在黃春香簽下同意自拆後,就有人來拆走監視器,隔天,這些一模一樣的監視器,又莫名出現在另一拒拆戶的陳致曉家門外欄杆上,監控著抗爭者的一舉一動。
反南鐵自救會律師簡凱倫則認為,政府逼迫手法是遊走法律邊緣,除非證明監視器鏡頭是針對民宅內拍攝,才會構成侵犯隱私權。但難以證明違法不代表沒問題,就像過去白色恐怖時代,「警總站在你家門口也不違法,但明顯就是要緊迫盯人、掌握行蹤。」

除了監視器,公部門人員更進行一連串的遊說過程。黃春香家門前是開元陸橋橋下,可遮風避雨,平常擺著一張桌子,幾張椅子、沙發,就是附近居民休息、聚會的地方。預計拆遷日前一天(7月20日)上午9點,身穿白襯衫的李皇興率領鐵道局、轄區副分局長、估價公司大批人馬來到黃春香家,展開一整天的談判攻勢。
不動產估價公司經理拿出一疊厚厚的資料給黃,指稱查估後的自拆補償費,比原本還多出100多萬,希望黃能簽字同意自拆,鐵道局承辦人員林偉玲私下再跟黃春香遊說:「二姊(黃春香在家中姊妹裡排行第二),如果妳同意的話,12點前跟我講,就是這個價格(拆遷補償費)給妳。」
「連辦個信用卡都有好幾天可以決定,要拆的家卻只給我3小時考慮!」黃春香仍未簽字。鐵道局開始增加施壓強度。中午過後,區長、副分局長、鐵道局人員輪流上陣,直至深夜,不停歇地在黃家出沒,如果黃春香不願意談話,就轉而和黃家人閒話家常,包括黃春香高齡99歲的媽媽。
黃春香還未下決定的時候,鐵道局已派貨車載來圍欄,把黃家後方圍住,在中午二度協商不成後,工程圍籬則悄悄地運到黃家附近,沒想到卻是要提早封路,宣稱施工時間由原本公告的晚上8點已改成中午12點開始,等於是提早8小時封路,而且還是先封路、再公告。 突襲封路除了擋住後來趕赴現場的聲援者外,也包括採訪的媒體記者。架起圍籬後,鐵道局人員隨即以「工程區域危險,即將有機具進駐,媒體畫面拍攝已足夠」為由,多次要求早已在現場的《報導者》和《公共電視》4名記者離開,同時拒絕後到的記者進入。

7月間,《報導者》採訪團隊進入黃春香的家,記錄下黃春香家外被安裝監視器及提早封路等過程。不過,鐵道局副局長伍勝園受訪時則強調,監視器和封路都是為了工區出入口管制,「一切都是為了安全。」
7月21日強拆行動當天凌晨2點多,黃春香已體力不支在陸橋下的沙發上短暫休息,李皇興突然出現,急忙地把黃春香帶離開現場,並要求媒體不能跟隨。凌晨3點半,黃春香跟鐵道局人員陪同下再度現身,並在自拆同意書上簽名。上百名配帶警棍的警力隨即整隊撤離,鐵道局更立即展開拆除圍籬作業。
據了解,黃春香在親近者的建議下,希望先取得2個月的緩拆期,這段時間內再和鐵道局協商,看是否有更好的安置方案、確保能有部分重建的底線。
我們目睹,歷經18小時疲勞轟炸的黃春香,無力思考各種方案,而聲援擋拆的力量,成了黃春香良心上的負擔。

「你到底是同意(自拆)戶,還是不同意戶?」《報導者》記者在9月緩拆期限屆臨前一週詢問黃春香,她在陸橋下邊煎著荷包蛋,爽快地回一句:「我是不同意戶啊!」
雖然在7月的凌晨簽了切結書,但黃春香的家是半拆戶,徵收線從房屋中間攔腰切過,剛好位在通往2樓的樓梯邊。她內心從頭到尾似乎都沒有「自拆」的打算,但又怕突來的強拆,已把家中的家當往外搬。7月時,房間裡的冷氣已經被搬走,她家外的陸橋下多了沙發和桌椅;9月時,屋內的馬桶、蓮蓬頭也被拆光,衣櫃、鍋爐、洗衣機全都搬到了陸橋下,一部分的生活機能被迫從屋裡移出,屋內像是被轟炸過般地凌亂,家已不成家。
「我給他們(鐵道局)一個樓梯下(指7月21日簽字同意自拆,讓鐵道局、警察撤退),他們卻不給我留這個樓梯⋯⋯。」
黃春香坐在陸橋下吹著晚風時,邊抬頭看著這住了幾10年的家,感嘆地說。
不過,他也承認,在南鐵的土地徵收手段上,「需要更多的溝通讓事情更平順。」

台灣人權促進會居住權專員余宜家表示,台灣早已簽署聯合國人權兩公約,而在《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CESCR)第7號一般性意見裡寫得很清楚,強制拆遷不但要有合理的通知期,也不可在夜間進行強制驅離,像鐵道局在凌晨3點多跟黃春香進行協商、甚至簽字同意自拆,明顯不符合公約精神。
余宜家表示,很多強拆爭議都只剩下工程問題,「工程是兩面刃,政府最後都跟你說不可行,但其實一定有可行方案。」對黃春香來說,樓梯就是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定會有在拆除和維持生活居住的平衡點,只是政府願不願意。
除了南鐵東移案,台灣各地有許多區段徵收案在進行,如台北社子島、桃園航空城、桃園捷運綠線、新竹台知園區、竹東二三浦,市地重劃如台中黎明幼兒園、高雄鳳山車站等,全台灣總徵收面積超過4,000多公頃,影響人數超過10幾萬人。
台灣土地迫遷案很多,但能給予協助者很有限。以反南鐵運動末期為例,除了在擋拆前一天集結聲援者外,拒遷戶幾乎沒有任何組織性的外援,也沒什麼人能夠討論對策,頂多是聲援者情感上的陪伴。
「我每個月都一定會接到幾通電話求助,打來說他們家要被徵收了,」余宜家無奈地說。
余宜家指出,政府和人民之間「拳頭不一樣大」,多半怕跟政府對抗,即便簽字同意拆遷,不盡然是出於心甘情願,「(走到強拆這一步)只能跟他們(政府)吵,你(拒遷戶)只剩下肉身進行抵抗,但擋不住的。」 此外,律師簡凱倫也點出,法院長期忽略「家」所代表的居住權和人格尊嚴,將民宅視為能以金錢計價衡量的財產,「就算最後徵收處分被認定違法,大不了我(行政部門)賠你錢。」於是,徵收和強拆就更加浮濫。
政大地政系助理教授戴秀雄指出,台灣土地政策的迷思必須釐清:土地徵收就是違逆當事人意願的方式去取得私人財產,本來就是合法暴力,遭到陳抗不但正常也很自然,只要有徵收案,社會就一定要付出抗爭成本;民間常和政府爭論徵收案的「公益性、必要性」的有無,但其實很少有案例是完全沒有公益性的,只是程度跟面向上的不同。
戴秀雄指出,政府進行土地徵收不是不行,而是回到根本的「尺度」問題,台灣土地徵收法律規範地相當籠統,《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非常粗略地列舉了10項可因公益而徵收的事業,「只要為了公益性蓋腳踏車道,台灣幾乎沒有地方不能徵收,」他說,法律規範極度模糊,像給了行政部門開了一扇「魔鬼大門」。 「國外徵收要經過議會,透過民意基礎,出事是大家來扛,我們(台灣)任何徵收都是行政機關決定,若不給他具體限制,誰來煞車?」戴秀雄點出問題的核心。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