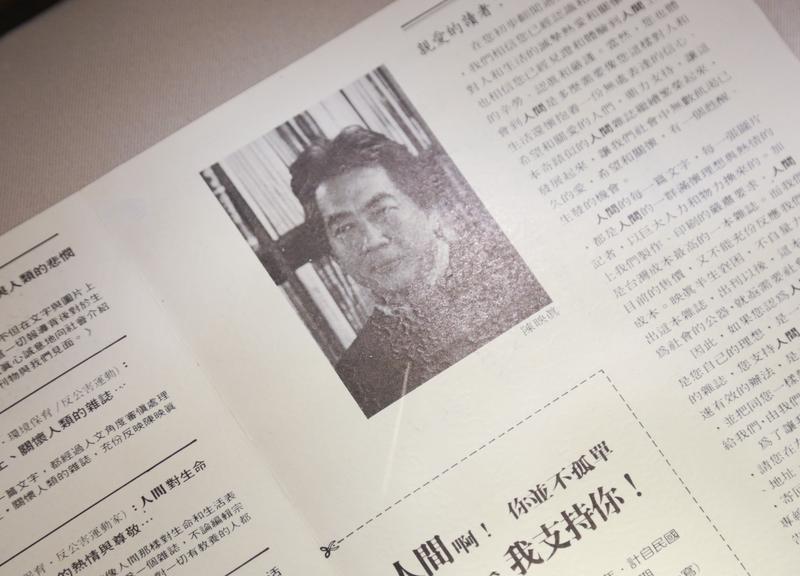週六現場【哲學蟲洞】

作者是活生生的血肉之軀,但有一種作者無影無形、無色無味,藏身在每一部作品之後。怎麼會有這樣的作者存在呢?底下讓我們來抽絲剝繭。
先從小說談起。讀小說有樂趣,一個很重要的樂趣來源是故事中角色的表現。透過作者的生花妙筆,我們能體會到書中人物在不同情境下的作為或反應,進而獲得樂趣。不同的故事角色會顯露出不同的態度、情感或人格特質。我們會對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筆下的福爾摩斯印象那麼深刻,很大程度上不就是因為這位名偵探古怪的個性?若作者無法掌握不同角色的特色,我們就會認為作者刻劃的角色功力不夠好。
然而,當我們跳離微觀的角色層次,進入到巨觀的故事層次時,我們也能在後者中感受到態度、情感或人格特質。例如,讀完《戰爭與和平》,我們可以在故事中感受到一股悲天憫人的情懷;《一九八四》嚴厲地批評了極權主義;《西遊記》則充滿了戲謔的口吻。這些態度、情感或人格特質(底下簡稱心理特質)並不是屬於任何一個特定的故事人物,而是故事整體呈現出來給讀者的。同樣的現象也可見於小說之外的藝術創作,例如電影、音樂或繪畫。高畑勳導演的《螢火蟲之墓》流露出濃濃的反戰主義之態度;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表現了悲壯的情緒;波蘭畫家貝克辛斯基(Zdzislaw Beksinski)的許多畫作表達出深深的陰鬱。
然而,說作品具有心理特質似乎有些奇怪,心理特質是人才會具備的,而作品不是人。那麼,讀者所覺察到的那些心理特質究竟是誰的呢?
一個立即的答案是,這些心理特質是屬於作者。作品是作者創作的,那麼作品所呈現出來的心理特質當然是屬於作者。更精確地說,作者透過作品表現了他的情感與態度,進而讓讀者在作品中感受到。這樣的想法在西方的浪漫主義時期(19世紀)相當盛行,當時的哲學家與創作者認為,作品是作者內心世界的展現,而這也是作品的價值之所在。這種看法一直延續到了20世紀初期仍有許多重要支持者。
然而,上述說法的疑慮在於,我們是否能從作品中呈現的結果反推回作者的狀態。一部作品表現了憂鬱的情緒,是否代表作者在創作該作品時也陷於深深的憂鬱呢?當然未必。上面提到的畫家貝克辛斯基曾說過,他許多表達憂鬱情感的畫作都被誤解了,他實際上想傳達的是樂觀且幽默的情感。高畑勳也在訪談中提過,他並未意圖透過《螢火蟲之墓》傳達反戰情感。
除了這些例子之外,在文學的傳統上更是有「作者被允許戴著面具創作」的說法。這意思是說,在創作小說或詩(主要是抒情詩)時,作者可以光明正大地偽裝自己真正的心理特質。例如,中國古代許多男詩人創作了很多閨怨詩,但這不代表這些詩人都心懷閨怨。仔細想想,對擅長創作虛構故事的小說家而言,他為何一定要在故事中如實地反映自己的內心世界?一名樂觀開朗的小說家,難道就不能出於自我挑戰的動機去創作一部充滿憂鬱情感的故事?

上述討論所導出的結論並不是說作品中的心理特質一定不會跟作者吻合,而是說這兩者之間沒有必然關係。因此我們並不能將前者無條件地歸屬在後者身上。若此,我們要怎麼看待作品中心理特質的歸屬?有比作者更好的候選者嗎?一個思路是,既然心理特質是作品所呈現的,我們應該朝作品中找答案。那麼作品中有什麼呢?
小說的例子也許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發。在一則小說中,呈現出心理特質的人是誰?前面提過,這些心理特質是故事整體透顯出來的,在小說中誰是講述事件的人呢?當然是所謂的敘事者(narrator)。例如,福爾摩斯探案的敘事者是華生醫生;《魯賓遜漂流記》的敘事者就是魯賓遜。把小說所呈現出的心理特質歸屬到敘事者身上,似乎是非常合理的,畢竟讀者就是從敘事者的敘述中感受到這些心理特質。如果作品中傳達了反戰態度,那是因為這種態度正是敘事者對戰爭的態度;如果作品表達了陰鬱的情感,那是因為敘事者在述說中表露了這樣的情緒。
有些人可能會質疑,似乎不是每則小說中都有敘事者,畢竟所謂的敘事者其實就是故事中的第一人稱角色,也就是「我」。但有大量的小說都是用第三人稱寫成,而且有極少數的小說是用第二人稱寫成。這的確是個棘手的問題,但並非無法解決。
讓我們先討論第三人稱的狀況。第三人稱的敘事觀點又可分為兩種:全知觀點與有限觀點。在全知觀點的小說中,讀者能夠洞悉所有角色的內心,《三國演義》就是以全知觀點寫成的。在有限觀點的小說中,讀者所知局限在某個角色的所知,《一九八四》就是局限在主角溫斯頓的所見所聞。然而,不管是全知觀點還是有限觀點,都預設了某個人的視角(否則何來「觀點」?);也就是說,必定存在某個人在告訴我們所發生的事,這個人就是敘事者。
這意味著,故事中的確還是存在一名敘事者,只不過這名敘事者從頭到尾都沒有在故事中現身,而是隱身幕後告訴我們故事中發生的事。如果接受這種說法,我們仍然可以說第三人稱的小說具備敘事者,因此可以將作品呈現出的心理特質歸屬到他身上。
第二人稱的作品狀況單純一些。在這類作品中,敘事的主詞都是「你」。但這樣的用法在暗地裡已經預設了有「我」,否則對「你」的敘說不會有意義。與第三人稱的狀況相似,這裡的敘事者沒有直接露面,但不代表不存在。
把作品呈現的心理特質歸屬到敘事者身上,這樣的做法在很多時候是沒有問題的,但在某些狀況卻不適用。例如,有很多小說存在「不可靠的敘事者」(unreliable narrator)。在這類作品中,敘事者之所以不可靠,正是因為敘事者所表露出來的與故事最終所呈現的存在落差。想像一個敘事者告訴我們下面的事:他被人陷害,成為全民公敵,沒有人相信他的話,但他試著要證明自己的清白以及幕後黑手的罪。故事最後才揭露,主角事實上患了被害妄想症。如果只看表面的敘事,我們大概能感覺到主角陷入絕境中卻又不屈不撓的生存意志,但在發現他的敘事不可靠後,整個故事所傳達出來的情緒可能反而變成同情與悲憫。

另外一點是,文學作品之外的藝術類型有沒有「敘事者」似乎不是那麼清楚。在電影中的確可以區分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的敘事觀點,但在繪畫作品中似乎缺乏這樣的內在觀點。若此,將心理特質歸屬到敘事者身上的作法並無法全面性地解釋所有類型的藝術。
如果把作者與敘事者都排除了,那我們還剩下什麼呢?也許答案就在這兩者之間的某種可能性。我們可以透過檢討作者與敘事者的優缺點來知道我們需要的心理主體必須具備哪些條件。首先,承擔心理狀態的主體必須外在於(external to)作品,而非內在於(internal to)作品。這意思是說,這個主體不是像故事角色那樣存在於故事的世界裡面。這是因為,如果這個主體內在於作品,就會像敘事者那樣,在某些情況(如不可靠的敘事)無法承擔故事所顯露的心理特質;更別提某些藝術類型不具備「內在的」敘事者。另一方面,這個主體必須由作品所提供的細節所構成。這是因為,我們之所以能辨識出作品呈現的心理特質,所根據的就是作品之內的細節,而非超出作品之外的其他事物,例如作者。
如果我們在一本小說中感受到憂鬱的情緒,那麼這是假想作者的情緒。這樣的心理歸屬可以避免歸屬給真實作者或敘事者會碰到的困難。同樣地,《螢火蟲之墓》中的反戰態度不是高畑勳的態度,而是假想作者的態度;貝克辛斯基繪畫作品中的陰鬱情感不是作者本人的情感,而是假想作者的情感。音樂作品中的情感,我們一樣可以歸屬給假想作者;一首表達出輕快情緒的音樂,我們就說是假想作者在旋律中傳達了愉快的情緒。簡而言之,假想作者就是我們想像出來的作者,因而不等同於真實作者,但假想作者是由作品的細節所構成,是作品反映出來的作者。
假想作者理論的核心精神就是,評論家評論的對象應該是「作品反映出來的作者形象」,而不是實際上的作者形象。這樣的區分有兩個好處。首先,我們可以有一個心理主體來承擔作品呈現出的心理特質。這意味著我們仍舊可以談論「作者」,也可以對他進行評價。另一方面,這個心理主體確保我們不會做出無效推論。
我們不能從「《螢火蟲之墓》表達了反戰態度」推出「高畑勳在這部作品中持反戰態度」;同樣地,我們也不能從「貝克辛斯基意圖透過畫作傳達樂觀態度」推出「貝克辛斯基的畫作傳達了樂觀態度」。既然作品呈現的心理特質是屬於假想作者,我們就沒有必要去進行上述這兩種推論。假想作者的理論顧及了作者與作品間的平衡,既不讓(真正的)作者喧賓奪主(畢竟我們在欣賞的是作品),也不讓我們所談論的事物(心理特質)成為無主之魂。
如果我們從一部作品中感受到了抱持某種情感或態度的作者,那麼無論真實的作者如何否認這件事,都改變不了作品既有的呈現,因為那就是我們在作品中看見的「他」。假想作者的理論就是希望可以把我們在作品中遇見的作者從真實作者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哲學蟲洞」是一個通俗哲學的專欄。《報導者》輪流邀請任教於大學的哲學教授們,擇定一個文化、藝術與流行的議題,以哲學之眼,帶著讀者一起跨越不同的視域,挖掘現象背後的深層意義。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