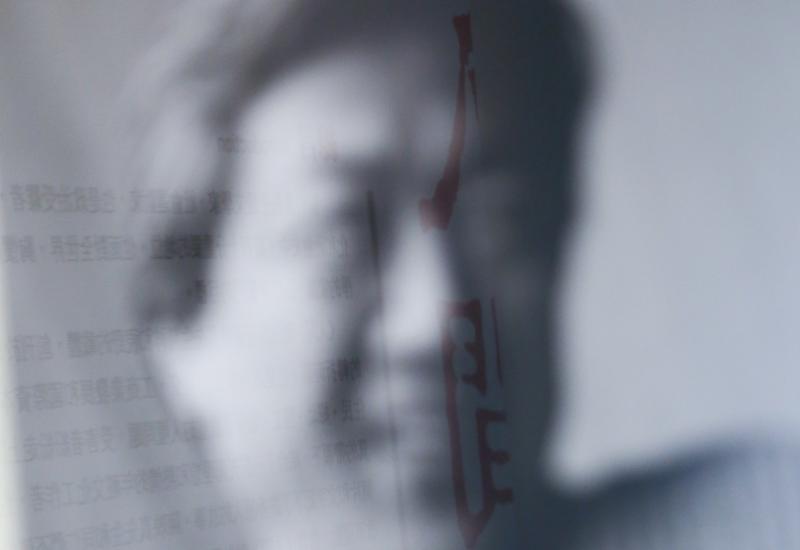評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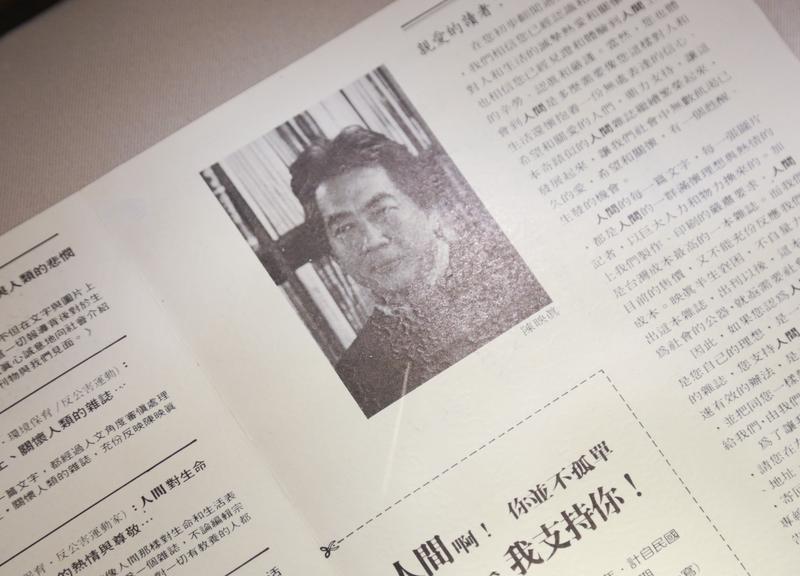
今年10月,在美國哈佛的一場學術活動中,一位台灣留學生突然公開問我:「為什麼是馬共小說該向陳映真學習,而不是反過來,台灣文學(陳映真)該向馬共小說――譬如金枝芒的《饑餓》、賀巾的《流亡》學習?」他針對的,當然是我2013年在《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的自序裡談到我那篇借用陳映真小說篇名的〈悽慘的無言的嘴〉的最初發想是,「既然陳的早期小說是中國以外左翼文學的標竿,馬共小說也該有篇陳映真式的,可惜馬共陣營普遍欠缺真正的文學感覺。」我這兩句話,其實已預先回答了那位台文所出身的青年的提問。
身為寫作這一行的晚輩,我不過是陳映真眾多讀者之一。我從來沒見過陳映真,沒聽過陳映真的演講,不曾參與有陳映真出席的任何活動,不曾動念找陳映真簽書或寫序,甚至連以陳映真為主題的研討會都不曾被邀請。雖然我在台灣居留的這30年,其中的20年是「陳映真在場的台灣」。
對那些甚至可能並不知道自己是在中國革命文學教條的死灰裡寫作的馬華左翼寫手而言,即便他們稍微認真的讀了陳映真,也會認為那不是同道──看起來太過現代主義了。他們頂多只聽說陳映真是「台灣作家」,台灣=民國=蔣幫,大概也就不屑一顧了。
「真正的文學感覺」,談何容易。
即便是陳映真本人,「真正的文學感覺」也一度被他自己 的「意念先行」摧毀──如〈夜行貨車〉、〈萬商帝君〉──那些年,或許可以說是陳映真的馬華文學瞬間。出獄後的陳映真,確實經常否認自己的現代主義血緣,好像那是什麼原罪似的。但陳映真對我而言,最有意義的首先就是他30歲前寫的那些陰鬱幽暗慘綠的現代主義小說,而不是別的什麼。那是不可替代的。
陳映真的過世,說真的,我沒什麼感覺。畢竟他已癱瘓在北京多年,文學生命早就結束了。對我而言,他也不是什麼思想導師。他的大一統論、第三世界文學論都太過常識;和陳芳明那場文學史論戰的學術水平太低,雙方都了無新意;晚年「回歸祖國」更是個人悲劇,也沒什麼好說的。

我讀大學的那幾年,正是《人間》雜誌的盛世,但我也不是訂戶,每每只是到學校對面的書店去看免費的新刊。我手上的第一本陳映真小說,是遠景版的,第9版的《第一件差事》(1985),薄薄的,不足200頁,大二寒假時購於台北某舊書攤。書櫃裡還有遠景版的《山路》(初版,1984)和包含諸多早年作品的《夜行貨車》(5版,1987),大概均購於台大對面巷弄裡的遠景門市,那裡常有遠景自家的特價書在拋售。扉頁沒有註記,可能那時的自己不是那麼重視;沒寄回馬餵白蟻,留著待讀或待重讀。
大學那幾年,讀了可能也沒什麼感覺,大概感受不到箇中寓言的共振,還欠缺充份的在地知識。我畢竟是台灣歷史的局外人,無法像那些與他共同經歷過白色恐怖年代的讀者那樣,對作品有深刻的心靈共鳴,因而對陳映真身上累積的巨大社會聲望,也幾乎無感。
其時較有感覺的文學作品應是現代詩,詩比較沒有背景負擔。
哪時讀了有感覺,其實我也不記得了。也許在淡江唸研究所,在那落雨的小鎮,系統的讀了日據時代的小說,從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呂赫若〈牛車〉、楊逵〈送報伕〉,一直到皇民文學;讀了施淑先生的〈台灣的憂鬱──論陳映真的早期小說及其藝術〉及藍博洲《幌馬車之歌》,及各式各樣的50年代白色恐怖口述或報導;甚至是郭松棻那些彼時還在校對中,還未以書的型態出版的、迷人卻相當深邃難解的小說──再往回重讀,方能比較準確的掌握那些作品的文學的感覺。
似乎可以這麼說,陳映真的小說既是台灣文學史的縮影,也是心靈史的縮微,日據時代以來被殖民者受創的心靈,亞細亞的孤兒的徬徨感;被殖民情境下的無根與絕望──那沿續的歷史創傷,青年陳映真直觀的把握了,表徵為作品裡色調瑰麗、耽美厭郁的藝術感性。那種集體的精神狀態被施淑教授概念化為「台灣的憂鬱」時,台灣戒嚴的歷史已然終結;但那被壓抑的複返、左派的憂鬱的具體化,卻終將成為台灣文學史的紀念碑,也可說是台灣這文學的加拉巴哥島文學演化的有趣案例。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