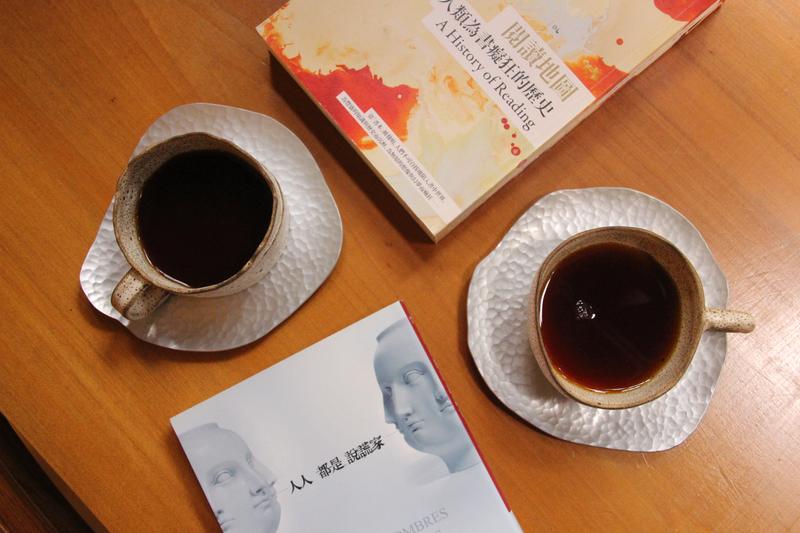楊凱麟 X 童偉格 X 胡淑雯

談及當前台灣文學的熱門關鍵詞,「字母會」必定名列於眾前。這個奇特的組織,由6位小說家組成的團體,似乎引誘著文學的讀者與寫作者們,一步步踏入他們所設下的詭異狀態:以法國哲學中的字母/關鍵字為創作題旨,交互以小說敘事與虛構情節連結、對話乃至於競技的小說家們,彷彿集體浸泡於狂熱的福馬林中,要以小說故事讓現實時間永凍於虛造的冰雪宮殿的神壇之上。冷冽與狂熱,陌異與似曾相識(Deja Vu),而文學是如此冰清晶瑩,如冬之女王以她魔異的美貌,在寒冷季節裡全面地征服我們的心。
於當代文學場域中橫空現身的字母會,帶有獨特的悖反性格。一方面,字母會的策劃(及每個字母來源)既出自法國的文學脈絡,導致一種濃厚的法國哲學式的文學沙龍氛圍;另一方面,字母會群體中的每一位小說家,都是出身於台灣文學,從第一代的陳雪、駱以軍、顏忠賢,稍後加入的童偉格、胡淑雯,以及最新進的成員黃崇凱,使策劃者楊凱麟的法國哲思,透過作家群的實踐,而開拓了在地化的對話空間。
然而,每個個體都是獨特的,這樣的差異性,就個體性鮮明的文學家而言尤其明顯,置身於字母會這樣的文學團塊之中,對於小說家自身的寫作狀態、精神內容與實際生活,產生了甚麼樣的化學反應?
「字母會對我的影響不僅僅是知識面的,對我來說,更屬於友情的豐收。」童偉格一語指出「寫作的勞動是孤獨的」:「字母會讓我認知到──寫作是可以討論的,這樣的認識,奇異地讓我感到溫暖。」
楊凱麟則舉童偉格的《童話故事》,為字母會的性格鑄作事例:「這本書展示了人與書的友誼、閱讀的共同體感,用來解釋字母會也可行──我們對文學有一份溫暖的共感,過去也許每個人都在自己習慣的書房、咖啡廳,獨自孤單地與經典交朋友,但字母會在這五、六年間,共同建立起一種珍貴的、哲學意義上的友誼。」
但寫作的孤獨,是無法被友誼所化解的。胡淑雯說,其實一開始時,她並未決定要太深地涉入字母會,「像陳雪、駱以軍、顏忠賢,在字母會成立之前,已經有他們之間無法容外人插足的友誼了,那形成一股氣壓,我覺得這股氣壓──至少在字母會之中──必須被改變,我才能夠基於對文學的信任,而把自己交付出去。」

回到寫作之孤獨本質,胡淑雯說,閱讀及電影,是她最重要的孤獨的養分:「看電影時,即使有旁人,因為被完全的黑暗所籠罩,每個觀影的個體依舊是孤獨狀態。」而閱讀於她,亦如同在漆黑中摸尋光的體驗。
「透過與作品接觸、交換、甚至交易了些甚麼,取得某種豐饒的陌生感,時而產生與人交談的渴望,希望與共振的同頻心靈說說話,字母會對我來說,就是滿足這渴望的環境,我們幾個人,好像帶著各自的孤獨,一齊來到這個地方,共享我們的孤獨,這不能夠消除寫作的孤獨,但是卻改變了孤獨的性質,變得溫暖、明亮。每次聚會,我都是非常不願意缺席的。」
字母會所帶給小說家們的友誼不同尋常,彷彿是一團冰凍的火焰,散發光亮,也餵養孤獨,對於一開始似乎以指導者身分進場的楊凱麟而言,初始欲改造這批小說家的企圖,最後卻反而在他身上產生反作用力,「其實,被改變的人是我。」他說。
「字母會就像我妊娠出的一個怪異的孩子,充滿誘惑,面目、長相古今未有。當這些小說家聚集起來,鑄造了一個文學的、誘惑的場所,本來我希望自己能以純粹的、不妥協的哲學姿態,與小說家們進行某種抗爭,透過我的哲學養成,激起他們的小說潛能,但最後我反而是我被誘惑了!見證到他們對於文學創作的大無畏的勇敢,因而深受感動故被誘惑了的我,也有了一個生自字母會的副產品,新近完成的小說哲學實驗──《虛構集:哲學工作筆記》。」
如果將字母會比喻為大聯盟的球隊,每名成員都是百萬身價、頭角崢嶸的明星球員(房慧真語),彷彿扮演著教練角色的楊凱麟,對於團隊的調和、組織的目標以及每個個體之間的最大共同價值,是如何決心去挽袖下海、著手煨燉這一大鍋雜燴字母湯?
「我覺得我們這批人,即使沒辦法進國家代表隊,也至少是個小鎮野球隊代表。」楊凱麟笑道。「我所受的哲學訓練,常被認為能鼓舞人們敢於承認自己會思考,不因為自己會思考而感到羞愧。換句話說,這其實是我的本行。」

楊凱麟說,哲學發展的最早期,哲學家便不停問著同一件事:思想到底能不能被教授?
「如果思想或德性是一項知識,那麼答案絕對是肯定的──但如果不行呢?我們該怎麼辦?直到70年代,還有德希達發動的組織在討論這個命題,如果哲學不能被教授,那雅典學院在做什麼?大學又在幹嘛?而我拚命去做的、抖著雙手鋪展出來的,是希望我引誘、召喚來的人們能組裝成一台戰爭機器,透過聚會、善意的理解,用無政府式的方法來動員他們的威力、展現創造性的行動,這本身便是一種差異化的行動──當每個人都發揮出最高創造性的潛能,字母會就是一個以差異為名的、安那其式的動員。 這與我們對於固定的團體想像落差非常之大──我們聚集在一起,是為了以最大的亂度與差異值,來崇顯文學的眾聲喧嘩。而我的角色是去打開一個空間,允許所有創造性的行動在此誕生。每一回,在寫下一個字母前,我給出1千字的暗示,聚會之中,就像風暴即將開啟前一刻,空氣中飽漲著低氣壓的嗡鳴,即將結晶的水氣呈現出最飽和狀態──這在化學上稱作『超穩定狀態』,聚會在這種狀態下解散,各人回去發展對自己而言最強大的、最個人本格風格的方式,去回應、逃離、顛覆字母設計的機關或陷阱。」
楊凱麟指指自己,「而我的角色呢?可能不是在於解釋、定義每個字母的意義,而是讓這樣的小說暴風結晶成為可能、變成所謂『前事件』的狀態,因此,出於個體的殊異性,使每個字母都得以獲取不同的晶體樣貌。」
除了哲學家提供出如此巨大的勞動,對於小說家而言,如童偉格、駱以軍、陳雪、顏忠賢,都是從事「長跑」的跑者,而字母會將這些跑將們一個個放到新的起跑點上,鳴槍後便是一場場短跑競賽(房慧真語),一邊得留意對手腳步,一邊得獨自吃下每次跑程,小說家們是否有時會腹痛如絞、消化不良?
「其實,我沒有那麼大的寫作狂熱。」童偉格帶著幾分靦腆說道。
「我反而花比較多時間讀書,對我來講,去理解每個字母的意思,比陳述它們更有趣,所以字母會的提案並不是幫助我定期產出作品,我純粹是覺得非常有意思,例如宏觀說來,我們並不是當代文學史上第一個文學團體,六年級有過『小說家讀者』(8P), 他們的起步狀態非常接近字母會;七年級又有『祕密讀者』,比較之下,字母會更有意思的是,凱麟的提案非常超現實,他不是將我們這批人定義成超越世代框架,或要給予一個新的陳述,在凱麟的想像中看不到這個東西,他所給予我們的知識上的慷慨,不太可能在眼前的當下發生,所以我會指稱字母會有種超現實因素存在,我會加入是因為這實在太有意思了!」
每當為期兩個月的截稿期一到,眾人作品揭曉如揭開華麗天鵝絨布幕般,舞台上展現的是專業小說家的技藝對決,如駱以軍所言的「武士之間的競技場」(引房慧真語),那景象既使字母會的眾人互相震懾,殘酷又美麗。
「駱以軍比較希望強調出寫作之中殘酷的一面──職人與職人之間的對決。這樣的對決使這個空間存在著強大的聚合力,無論聚會多開心,或者聚會後的時間多逼人,最後還是要回到作品本身,就像凱麟說的──把個體的獨特性催逼出來,展現出你在知識或小說競技上的能耐,回到作品去檢驗你自身──這是非常嚴格的,而字母會的獨特之處便在於,首先不以世代侷限為考量,再來則是純粹的小說創作的場所。」童偉格說。
胡淑雯聽了,俏皮地搖搖頭:「我每次都只覺得自己寫得好爛喔。(笑)」她莞爾一笑,隨即正色起來。
「其實現實生活讓我大多時候都身處文學之外,反而只有字母會這個空間能結構性地去產生某種時間的暴力,那是截稿線對創作者的暴力,通過這份暴力,才能把我拉回文學,否則我會被現實及生命的困頓一直拖走──但陳雪跟駱以軍更辛苦吧!他們好像在長跑之餘還要來跟我們短跑,但我似乎是在泥淖中滾一滾就滾到這兒,來靠近、從事我喜歡的事物,寫自己的小說。」
從2012年至今,字母會已迄五年並將邁入第6年了,新成員不斷加入,編制不斷(緩慢地)擴張,組織本身的晃動(擴大或縮編),又如何隨機或出其意料地影響了字母會未來的圖樣?這樣的不確定性,是否悖離了身在其中的小說家與哲學家們原始的想像?
先身為策畫者,後成為「被誘者」,楊凱麟說,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怎麼去形容字母會後來的樣態:
「剛開始跟駱以軍討論字母會的想法時,設定了一項對小說職人的嚴格要求,聚會可以輕鬆,但小說家必須去展現以小說為志業者,究竟意味著身具什麼樣的職能。當我們談論台灣文學或回顧文學史時,我會傾向於用每個時代具獨特的影響力的思想來界定,比如說,舊時期西方對於《馬可福音》與《約翰福音》的競技;俄國文學在杜斯妥也夫斯基與托爾斯泰之間的爭論;垮派(Beat Generation)展現出毒品與性解放的景象;海明威所展現的19世紀末的美國、那種大無畏的巨大海洋生物影像⋯⋯ 如果整個台灣文藝的狀態,每個階段都存在著一種『蛙跳』式的躍進,例如風車詩社繞過東京,展現與巴黎接軌的『蛙跳』,在他們之前,30年代的台灣根本就還是農村社會!又例如在白先勇作為台大外文系的學生,引進現代主義小說之前,整個台灣依舊是非常封閉的戰後挫敗景象。從這樣的觀點,字母會希望所呈顯的,或從小說的情節或既有語彙難以去定義的,是字母會或許能允許某種非常不同的思想影像,與白先勇、風車詩社有一致的樣態,企圖『蛙跳』到當代人所思索的最前衛、最有趣的概念,而這是需要練習的,如當年風車詩社對達達主義的練習,白先勇對現代主義文學的練習,我們則透過對26個字母的小說練習,來展現當代台灣人的思想影像。」 「順著凱麟剛剛說的,如果從作者角度來看,我自己希望字母會可以對於駱以軍或陳雪這類職人作家造成一些問號,一些震盪,但從讀者角度來說,我們是否還需要更多關於駱以軍或陳雪的陳述、解釋與論述?奇怪地是,其實我們是需要的!像我們這樣身體已泰半被文學擄獲的人,在未來總是透過一種通識性的方式被介紹給讀者,整體而言,這是一種接近失憶症的理解。藉由偏移,產生更嶄新的駱以軍和陳雪,也為這樣的小說家過往的作品證成更有力的說明,例如陳雪一系列的作品已告訴我們,在《摩天大樓》之後的陳雪,應該是什麼樣的陳雪?她的可能潛力是什麼?」
楊凱麟亦稱是,字母會新推出的《字母LETTER:陳雪專輯》,有如與字母會拚場,亦如童偉格所言,字母會似乎使得有一種「後設式陳雪」即將現身:「她透過小說拚命思考:『我如何成為這樣的一個小說家』,這是《戀愛課》結合『小說課』,變身成新的陳雪。駱以軍也一樣,讀字母會時看起來是老樣子的駱以軍,在每個字母的篇章中展現他的新樣態。」對於小說家之間的惺惺相惜,胡淑雯笑著說,駱以軍是格外珍惜童偉格的:「這兩個人,根本就是兩座星球的作家啊!」
楊凱麟說,他們遇到非常年輕的小說家表示想重寫字母會的欲望:
「『重寫』或者『重複』字母會這件事,會產生某個弔詭的處境:因為你不可能重蹈這些小說家的覆轍,因此你必然將要自我差異化,亦即將自己推到安那其的動員狀態。你要創造出全新的中文對中文的翻譯,而且是小說版本的──我覺得這是何等的氣魄與勇氣啊!這些已經成名的小說家,無一不陷入字母會的泥沼或困境,而字母會的精神恐怕就在這裡──它是一個誘惑的場所,傅柯去談福樓拜的長篇小說《聖安東尼的誘惑》,聖安東尼所度過的那一晚裡,每個夢幻孽生的場景個別轉變成誘惑的場所。或許字母會確實有一個目的:透過字母會自身,讓更多人動念開始寫自己的小說。」
不僅僅是小說創作,更像是一場科幻冒險,或者關於時代反應的實驗。字母會像一顆怪石,自身發動能量,如賽亞人自體聚集光束後,將自身投入台灣當代文學的死湖之中,激起巨大的震盪,而周遭的觀者目睹這群怪物自殺式地衝入水面,全都驚呆了。而字母會也讓位居其中的小說家們,彷彿自身突變般,技藝越趨強大,感官無限擴張敏銳如宇宙顯微鏡,就像胡淑雯說的,「字母會讓我多生出一種感官。」
「不管閱讀或寫作,我好像另外多生出了一雙眼睛,去在各種作品之中搜尋線索,搜索作品裡有沒有寫出我們自己不斷重複經驗著、卻從來不認識的事物。真正厲害的作品,可以讓尋常的事物、那些不斷被經驗而已然磨損的事物展現全新的、尚未被人們辨讀的面貌,字母會讓我向來仰仗的直覺歧生出第二隻胳臂。」

由於字母會,哲學家楊凱麟也發生了親身的異變:
「我從未想過我會寫下任何非哲學的文類,過去20年裡,我的大腦養成是非常辯證的,每一句話存在的目的,都是為了在知性或語言意義上去反對、辯駁前一句,這是哲學式的自我要求, 但跟這些小說家混久了,就像之前說的──我確實被引誘了,這種感覺就像打籃球打得無聊了,想打打看棒球。」
楊凱麟雙手交握、告解似地笑說,「跟字母會的這些超人作家在一起,使我開始相信自己好像也可以寫一點很小的東西,重新回想過去幾年,其實我好幾回強烈地被勾引,導致差點辭職轉行,我的能力無法駕馭長篇,但一個小的破片或零件,或許我也可以嘗試練習看看。尼采曾說過寫作的啟動其實可以非常容易,例如一次寫兩三百篇、每一篇只寫兩、三頁,就可以培養出書寫的模式與慣性。我也在他們的鼓舞下誤打誤撞地做了一件小事,對我來說這是一次偏航,表面上,對於這群人我好像是導師的角色,最後這些人全部變成我的老師──這段過程形諸文字,就是《虛構集:哲學工作筆記》。」
「不不不,凱麟還是我們的老師啦!」童偉格接著說道。
「《虛構集:哲學工作筆記》中呈現了完全嶄新的觀看方法,那是足以『讓眼球骨折』的,例如裡面有篇〈白的純粹形式〉,這篇講不小心看到女生的白色內褲,從女孩子的白色內褲講到宇宙星辰的推進,對我來講,這樣的事件具有某種象徵性,參加字母會、定期聚會、長期讀凱麟的書,我自己思維中某個部分已經無可挽回的『楊凱麟化』了。(笑)所以我認為「哲學工作筆記」同時也是小說家的「工作哲學筆記」。」
除了哲學家與小說家自身的質變,字母會是否也讓當代文學這灘沉靜靜的死水?如聞一多的詩句:「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清風吹不起半點漪淪。/不如多扔些破銅爛鐵,/爽性潑你的剩菜殘羹」般,使文學場的水質變擬出時代性的化學反應──「也許銅的要綠成翡翠,/鐵罐上鏽出幾瓣桃花。」
「身在字母會的過程之中,讓我恍然領悟到一件事:即便我們聚合了這麼多條件──我們有最好的哲學家,有這麼多優異的小說家,而衛城出版和小瑞(莊瑞琳)給了我們兼具創見與宏觀與全面的出版設想,但當它(字母會)將自己押在了讀者面前,其實是沒有辦法造成一起真正的文學事件的。」
童偉格說,「字母會所引起最大的事件,就是放在大眾面前時造成的反應。這種反應是非常當代的,或許最後我們也該想想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後記)小說的巡禮之年與朝聖之途
訪談之餘,這三個擁有絕頂聰明腦袋與極細膩思維的、台灣當代最傑出的思想者與創作者,在報導者的陽台上呼呼地迎著風,其中兩人抽著菸,楊凱麟一貫地溫溫地笑著,像摀著一杯很甜很美的茶;胡淑雯紅唇絕豔,長髮及肩;童偉格一身黑衣素衫,眾人都說他瘦了一大圈,怎麼辦到的?他說自己最近勤練瑜珈:「整堂課都是女生喔,只有我一個男生,超尷尬的。」
除了正經談文學,三人也樂津津地聊著「不在場」的其他人,形成某種彷彿隱形氣流似的結界,即使不在身邊,亦如在目前。他們侃談即將推出的《字母LETTER:陳雪專輯》將如何精彩、駱以軍如何在每次聚會中展現無敵嘴砲功力,以及,他們最新進的年輕小說家黃崇凱,如何替字母會往未來更跨進了一步。
「找到黃崇凱,等於幫字母會更恰當地展示了一種未來圖樣。」童偉格說。
「有一天我想到:啊,字母會裡年紀最小的竟然是我啊!頓時有一種鐵門拉下來一樣的感受──因為我的個性和小說美學都是壓縮性很強的,全然被鎖在象徵性裡面。所以我覺得字母會需要透透氣,而在我看來,七年級小說家中,黃崇凱對小說的投入度與成就是第一流的!崇凱對小說的投入是古典意義的投入,他是非常虔敬的作者,不會刻意去展演花俏的技法;另外,他每一部作品之間的跳躍性非常強,不由得讓我去想像──那樣的小說未來到底是什麼?我覺得這就是字母會的命題所在。」
身為專職作家,胡淑雯、駱以軍和陳雪,走的路比其他人更曲折一些,「當我對別人說自己的工作是寫作的時候,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解釋,有種奇怪的羞愧感,一種寄生在謊言中的感覺。」胡淑雯說,幸運的是,她早年失學的父母對於文字反而有種奇異的崇敬,「我的生存之道,就是讓爸媽覺得我一直有賺到錢(笑)。」
然而,巨大的現實之輪仍然無差別地輾壓過每個人,相對於在學院安身的楊凱麟、顏忠賢,以及較晚開始教書生涯的童偉格,其他三個人的生命狀態是相對困頓,但也因而更逼近小說創作的純粹剔透。
「我覺得,小說創作若要達到一個純粹狀態,如果要挑戰的是一個不斷越界、不斷探索小說邊界的人的狀態,似乎必須要求一種生命的純粹,所以這樣的人大多處於失業、無業狀態。除了淑雯,也包括駱以軍,他在乎的除了家庭,就是一天可以有兩個小時無旁騖地寫作,其他的時間裡他可以照顧小孩、可以養狗、可以跟朋友搏暖,但他不能沒有那兩個小時來專注面對他這一生中最重要的挑戰──但前提是你得是駱以軍,能在兩小時內把整個宇宙的能力動員起來、拋擲到字面上。」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