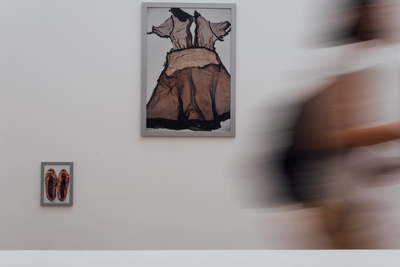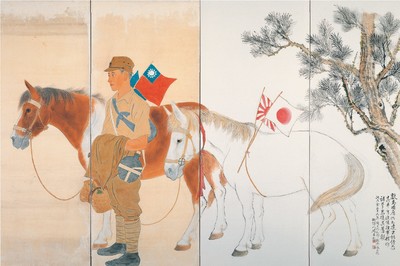攝影評論

托瑪斯.德曼(Thomas Demand)是當代最具代表性的攝影與裝置藝術家之一,他以「紙模型」為核心創作媒材,將媒體影像轉化為1:1的手工紙雕塑,並透過攝影定格後,再摧毀原作,讓「永恆」與「毀滅」的張力交織在他的作品中。他的創作常常圍繞著歷史事件、權力領域、媒體影像與現實之間的張力。此次於北美館的展覽《歷史的結舌》展出多件經典作品,從檔案、建築到圖像技術,探討我們如何觀看、理解與詮釋現實。
德曼究竟如何透過「紙」的脆弱與可塑性,重新檢視我們對影像、權力與歷史的理解?在北美館一間封閉的房間,我與托瑪斯.德曼透過譯者進行訪談。我意識到,不只是討論概念本身令人著迷,更是我們身體如何共處於一個「封閉且人造的空間」,以及翻譯如何成為「溝通的中介」。德曼在訪談中表示,他更像是一名「譯者」,致力於轉譯現代的圖像生活。
現代系統對控制的執念、人類文明的災難陰影、歷史創傷的集體記憶、創作者工作室的氛圍,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幽微細節,這些場景無不環繞在德曼的作品周圍,構築出一種冷靜疏離又鬼魅的空間氛圍。這些場景既令人不安,卻又因鮮豔的色彩充滿吸引力,彷彿存在於一種「既是又不是」的模糊狀態。
用脆弱的紙搭建的場景,抹去了現實的細節,只留下幾何形狀與顏色的平滑感。然而,抽象化的結構卻帶給人似曾相識的熟悉感。由於在轉譯過程「選擇性遺忘」細節與具體內容,以及採取巨大尺幅的照片輸出,使得觀眾在觀看照片時,必須更主動地投入自己的想像,停下腳步沉思;這與我們日常快速消耗媒體生成的訊息刺激形成了對比。 他作品費時勞動的製作過程以及大尺幅,暗示觀眾必須靜下來好好「閱讀圖像」,彷彿抵抗數位媒體讓人接受喧囂訊息的過載感(資訊錯失焦慮)。微妙的是,這份靜謐中,我們更深刻地體會歷史的創傷、暴力以及處於夾縫中的狀態。
德曼不止於「藝術攝影」的脈絡;而是遊走於檔案、雕塑、建築之間「持續轉譯」的過程。他放大了系統結構中的細節與裂縫,並以「圖像的中介性」(翻譯)為核心,探討圖像如何塑造我們對現實的認知。對他而言,「圖像世界」與「現實」之間始終存在著張力。我們往往透過媒體的「可控框架」來理解「不可控的現實」──如同許多人在親臨石窟之前,早已透過媒體影像建立了先入為主的認知。
這種對框架的思考,延伸到「模型」以及「景框」的探討,也回應現代管理系統至關重要的三個要素──「檔案」承載記錄、「建築」塑造空間與「攝影」平面傳播。

德曼的作品弔詭地融合了精密與脆弱──他以高度精確的建模方式,卻選擇極易損壞的紙材作為媒介,從而營造出一種充滿張力的視覺體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莫過於《森中空地》,一片乍看之下彷彿被綠葉與光影包圍的寧靜森林。然而,這片「森林」並非來自自然,而是由270,000片手工剪製的紙葉構成。這種對「自然」場景的人工再造,不僅凸顯我們如何透過媒體來認識與感知現實,更進一步揭示我們所身處的「第二自然」──一個由語言、圖像與媒體建構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我們的記憶與感受往往先於經驗被塑造,比如在親身造訪一個地方之前,我們早已透過網路上的風景圖像形成了既定印象。
經過德曼作品的洗禮,我們會發現自身對現實的感知已悄然改變。那個原本堅固、厚實、看似無法撼動的物理世界──實則從未脫離媒體符號的編織──宛如權力的象徵般屹立不搖,卻在德曼的作品中顯現出紙一般的脆弱與可塑。這種轉化不僅讓我們重新意識到現實的無常與易碎性,更進一步突顯了「紙的可塑性」,它既是承載,也是一種對權力結構的重塑。
我們可以將這種可塑性視為契機。權力的「操控」(manipulation)雖然無所不在,但德曼的作品卻暗示,儘管撼動現實的權力結構或許困難,我們卻能選擇重新塑造想像現實的框架。透過放大其中的裂縫與開放性,我們得以重新審視這個世界,甚至重新編寫我們的感知方式。
在談及藝術的政治性時,德曼強烈指出:
「藝術不應該只是政治宣傳,但它可以成為一面鏡子,讓我們重新審視已知的圖像。」
相較於現實政治的對立與預設引導方向,藝術的映射打開更多彈性空間。也可以說,藝術並非是政治宣傳的工具,也不是抽象的浪漫化,而是宛如平滑的鏡面反射現實權力,同時以安靜且不直接對抗的方式,解構權力引導中的操控性,為個人的詮釋與感受保留更多可能性。
這在他的《控制室》中尤為明顯──他並未直接再現福島核災的混亂現場,而是選擇重現福島核能控制室的「秩序」,讓人們在觀看時發現,那種「井然有序」本身正是問題的一部分。這種方法不僅是一種去脈絡化,更讓觀看者意識到,「我們如何觀看」,其實也受到權力機制的影響。
在我看來,「鏡像權力」在於透過藝術對原本政治脈絡的「去脈絡化」,重新激發出一種新的政治視野──這並非僅僅是將去脈絡化的內容轉化為消費物件,而是通過大費心力的重構,將媒體大事件傳播中被忽略的「場景小細節」帶回視野。這些微不足道的模型細節,正是對權力操控的一種抵抗──它們要求我們放慢節奏,重新審視那些看似不重要的事物,並從中發現潛藏的信號。

高度控制的「封閉空間」與保持開放的「細節韻律」,成為一組進入德曼作品的路徑。他不同於表現主義的強調個人感知的極端,而是以宛如新即物主義(New Objectivity)的視角,平靜地重構並拍攝媒體場景。他既不悲觀地批判封閉的系統性暴力,也不懷有對現實的浪漫寄望,而是游走於兩者之間,擺盪出一種既冷靜又如實的觀看方式,瀰漫場景中的細節,引導觀者感受系統控制背後的脆弱與無常。

德曼平靜地呈現場景,並非追求「客觀系統的真實」(如歷史學家或新聞媒體的標準),也並非僅僅是藝術中的個人情感表現。而是更接近文學家追求的「如實」(truthfully)──混雜著記憶、虛構、操控與重構於一塊的敘事鋪展過程。換句話說,他不是單方面告知我們事實到底為何;而更多是搭建起場景,邀請我們去編織、重組與想像。儘管看似以靜態攝影呈現,但更多是邀請觀眾一起參與某種心智遊戲的解謎運動,不只沈浸於事件,而是探索圖像本身的秘密(比如類似觀念藝術抹除訊息的手法,只留下宛如犯案的痕跡,讓觀眾猜想)。
但無論是客觀系統的「真實」(truth),或小說家的「如實」(truthfully),這兩套系統都繞不開「紙」作為關鍵媒介。紙是這些系統得以運作的根本條件,既是現代性官僚運作的基礎(大量繁瑣的檔案文件核銷);「紙的空白」也是讓想像力得以流淌的基礎,是創造力的起點。紙的觸感與手感,讓我們得以用雙手重新觸碰世界,而不僅僅依賴眼睛或耳朵接受數位媒體的感官刺激。渺小的紙不僅是構建現代性管理系統的工具,更是突破這些宏大抽象系統、重構想像與感知現實的載體。

面對演算法與AI系統全面來襲的時代,強調「紙」如何不只是浪漫化的懷舊或單純的戀物?我向策展人道格拉斯.佛格(Douglas Fogle)提出這個問題。他在手邊擺了一張A4白紙,潦草地繪製著展覽的平面圖,邊隨手塗鴉邊說:
「空白的紙作為一種文化技術,它是一個充滿潛力的場所,讓世界再次自由地做夢。」
灰色的小柱子以一種幽默的方式嵌入場景中,既凸顯又打破了這種不適。如果說德曼的作品透過攝影建構幻覺,引導我們深刻反思現代文明的封閉系統,那麼這根擠在角落的柱子則重新拉回我們對現實肌理的感知。它讓觀眾不僅僅沉浸於圖像世界的思辨,還與北美館的在地場域交互對話,用身體跟柱子產生觸摸跟摩擦,同時消解典型「大師巡迴展」的距離感。
紙,不正是支撐起現代文明(北美館建築)的隱形支柱嗎?紙,可以傳播謊言;紙,可以止住快速瀏覽的習慣;紙,可以柔軟地重塑現實;紙,也可以銳利地割破手指;紙,更可以像突兀的柱子,戳破媒體營造的圖像裂縫。紙,讓細節得以棲居,並在我們的閱讀過程中持續翻譯、重組、發酵、蔓延。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