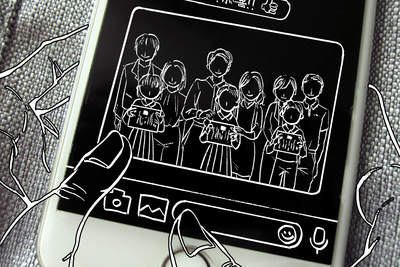年輕人的情緒困擾已是跨越國界的共同現象。美國2019年報告顯示,在美求學的大學生,無論心理諮商、藥物治療或住院比例,相較9年前皆顯著增加,接受諮商的大學生成長了10%,有自傷行為和強烈自殺意念的學生也明顯上升。心理健康的惡化,已讓英國、澳洲等國積極投入資源應對。
盤點台灣的心理支持資源,大專院校的心輔能量能回應學生們的諮商需求嗎?離校後,近用心理扶助資源的機會如何?而在專業支持之外,一般人如何能成為這些情緒受苦者的「撐傘者」、陪伴他們一同面對苦難?
4月的夜晚,夢生(化名)爬到住家外的遮雨棚,8樓的高度可以抵換23歲的生命長度,幸虧親友及時趕到,讓她走回圍牆內。大學開始接受心理諮商和藥物治療的夢生,幾度動了自殺的念頭,她說自己好想消失。
然而,是否通報卻成為部分陪伴者心中難解的道德難題:一邊是當事人的生命安全,一邊則是人身自由和個人意願。
俗稱「強制就醫條款」的《精神衛生法》第41條,是為了避免當事人傷人或自傷,條文寫明:若嚴重病人有傷害他人或自傷之虞,經專科醫師診斷有全日住院治療之必要者,保護人應協助病人前往醫療機構辦理住院;若拒絕住院治療,地方主管機關可指定機構緊急安置。
對此,有長期實務經驗的黃揚文則表示,法律雖如此訂定,執行面通常仍會徵詢當事人的意見,「原則上只要我(指當事人)還是意識清醒的狀況,不願意去就醫,那種就沒辦法。」他舉實例說明,假若當事人站在圍牆上、或拿刀割腕,只要他不願意就醫,未必能夠強制就醫。

那次行動後,夢生在台大醫院的急性精神病房住了一個多星期──她衡量現實後自願就醫,為了不讓自己真的去死。精神病房位在舊大樓,門禁本就森嚴,因著COVID-19疫情關係,更只剩下家人有探病和陪病資格。她的智慧型手機被院方替換成只能撥電話和傳簡訊的「軍人機」,夢生與朋友的聯絡開始有了時差。
凱妮(化名)曾陪著夢生進出幾回急診室,但長時間不能見面卻是第一次,連想捎去一封手寫信,也得透過她的家人轉交。凱妮看著夢生反覆地服藥過量和自傷,幾度想開口問她為什麼,「但我沒有真的開口問過,我不想她像每次在診間面對精神科醫師、護理師的詢問一樣,說出那些話,但我更怕她向我道歉,努力地活在這世界上有什麼好道歉的。」
但凱妮很害怕,如果下一次不是在急診室,而是夢生真的離開了呢?不是每次都有僥倖,於是她對夢生說希望她住院,凱妮一方面希望精神病房是個好的選擇,另一方面又希望它不是,「我不知道她在裡面過得好不好,我只知道她在那裡不會死。」
寂寞和更漫長的寂寞,凱妮好像只能選擇前者。她知道醫療只能讓夢生活著,暫時「奪去」她死亡的選擇,卻不能完全消除她的痛苦。

夢生說,OD(overdose,藥物過量)是她遠離清醒的方法,在失去意識的時空裡才能躲避所有負面情緒。藥是矛盾的產物,渴望自己消失時,過量的藥效是引渡的橋梁;渴望好好活著時,它則幫助弭平過激的情緒波動,適度使用藥物能在生理上支撐基本日常運作。
看似已跟藥物成為緊密的夥伴,夢生也走過排斥的歷程,「我其實之前有一段時間會很焦慮,很緊張說自己是不是要吃藥吃一輩子,」但當她看見因其他疾病必須長期服藥的患者時,又轉變了想法,「明明就有些人比我更慘,可能有慢性病、或是糖尿病之類的,就是每天都要打針那更慘。」夢生認為若不將藥物視為控制,而是輔助的力量,似乎也非壞事。
藥物的汙名和其危及自我掌握感的焦慮,同樣也困擾著小嵐(化名)。在台大四年級時,她經歷嚴重的情緒困擾,經心理師介紹到身心科看診,領回的藥原封不動,「我沒有吃下那一顆藥,因為我真的很怕吃了有副作用,我回家會被發現。」小嵐擔心父母察覺異狀,研讀社會科學的她,理性上知道用藥恐懼來自社會建構的汙名,感性上還是無法克服。
根據衛福部2019年的最新統計,全台有139萬人在服用抗憂鬱藥物,其中30歲以下人口佔16萬人,較5年前增加5萬人,5年間的成長率(43.3%)也是所有年齡組中最高的。
用藥的原因眾多,並不能直接等同於臨床身心疾患診斷,卻意味著有更多人尋求醫療手段來處理情緒困擾的議題。就讀國立大學研究所的洋子(化名),因憂鬱和焦慮的情緒,已經很久沒去上課。她聽從學校諮商中心建議,打算尋求藥物治療、循校方提供的名單到校外診所;進入診所後,櫃臺服務人員遞給洋子一份5頁的量表,問題涵蓋諸多領域,從食慾、睡眠一路問到性慾,讓初診的洋子大開眼界。
「我對醫療很有信任感,開始填表之後我就還滿冷靜的,覺得我今天就是要來解決問題的,很理智地跑過來,我過來是要把我自己治好,」洋子說她自小體弱多病,對醫院再熟悉不過,所有問題好像踏進醫院就有了解方。醫師向她詳細說明可能引起負面情緒的生理原因,以及種種藥物如何改善現狀的機制。
藥物治療確實給洋子帶來安定感,且掛號費和藥物費加起來大約300元,不會造成過大的經濟負擔。但診所能給的也僅止於生理作用,後來回診,大多只是衡量身體情況和副作用,調整藥的種類和用量,醫師問診時間往往不超過10分鐘。
除了生物層面,心理和社會因素也是影響身心疾病是否發作和能否順利復原的關鍵,這是由美國精神科醫師恩格爾(George L. Engel)提出的「生物-心理-社會」模式(Biopsychosocial Model),對後續身心醫學的發展影響甚鉅。在台灣的實務分工裡,精神科醫師著重在藥物或其他生理療法,心理和社會的部分則落到心理師或社工身上。
已經服藥將近兩年的Joyce(化名)便感覺,用藥多寡和身心狀況是否好轉並不能劃上等號,「不會像什麼感冒,每吃一包你就會好轉一點。」藥物只是讓她不致於陷落情緒的谷底,連帶效果是被挖空的感受能力,「滿多時候很沮喪,怎麼吃了那麼久,我就是無法再跳回一個正常的狀態。」
Joyce說,她也明白自己的情緒困擾不純然是生理因素,只靠藥物當然無法完全「痊癒」,但其他資源卻未必如此容易接近。

幸運的是,如果這群年輕人尚未離開學校進入職場,在台灣各大專院校都設有學生輔導單位,名稱從「輔導中心」到「諮商中心」不一而足,但都可以提供在校生免費的個別心理諮商服務。2014年,為促進學生身心健康及全人發展,立法院通過《學生輔導法》,規定各級學校應設置專責單位辦理學生輔導工作,並設下專業輔導人員與學生人數的生師比,例如專科以上學校,每1,200名學生就要配置一名專業輔導人員。
設下限制除了讓案主和專業工作者協商出短期可執行的目標,也是為了更有效率地使用有限資源,「我們希望可以幫助更多學生,如果有一個學生一整年都在這邊,等於是把一個老師的時間都占住了,可以提供其他同學服務的可能性就減少了。」基於行政管理,校方必須考量資源分配和近用性,但次數限制對部分學生則製造新的焦慮,擔心「額度」用完之後,問題還沒解決。
需要心理服務的學生增加,是許多大學都感受到的趨勢。值得一提的是,台大已在學生保險中提供身心科的醫療給付,接受自費治療也可申請補貼,每月最高額度是1,450元,黃揚文舉例,「他吃的藥可能是一些自費的藥,短期如果吃一週可能沒什麼感覺,但當要吃到一個月的時候,加起來的錢就滿多的。」然而,目前此做法僅有台大推行,其他學校尚未實施類似的方案。
問起在學校諮商將近2年的夢生,她說畢業後大概沒辦法繼續諮商,私人院所諮商的費用一次動輒上千元,嚴重排擠社會新鮮人其他的支出。休學的洋子搬回台北後,則尋求住家附近費用較低廉的社區諮商服務,但可適配的心理師較少,晤談時間也比在學時短上一半。
一旦有情緒困擾的學生畢業或休學,離開校園,就像雨天收傘,得獨立面對沒有什麼支持和資源的未來。

前年(2018)9月,Joyce終於申請上準備已久的建築聯盟學院,展開第二次赴英留學,但在一個月後,她的負面情緒和自殺想法逐漸變得不可控制,即便勉強去了學校,也只是躲在廁所裡嚎啕大哭。Joyce找學校合作的家庭醫師(General Practitioner)看診服藥,也尋求心理諮商協助,情況仍未見好,只得在11月時返台休養。
失去學生身分後,社會現實和情緒困擾會如何彼此扞格,Joyce可說是深刻體會了。
回國後,Joyce已經在私人機構接受超過50次的心理諮商,跟心理師卻一直沒辦法深入核心,她苦笑自嘲,總不會在結案前都算是磨合。諮商遲無進展讓她無比焦慮,尤其當心理師不斷提醒「無用的」諮商等同在浪費錢,「我當場就被她重擊,她也知道金錢對我來說是一件很焦慮的事情。」
每次1個半小時的諮商,都得掏出3,000塊,至今花費已經超過15萬元,都是父親在支付。情緒困擾讓她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難以持續,雖然老闆願意讓她休養後回歸,沒工作的期間就是沒有收入。全心想著要怎麼讓自己快點「好起來」的Joyce如同碰壁一般,「我在諮商這個過程投注了很多努力,我也很誠實地面對我自己了,為什麼問題都沒有明顯的改善?對自己還有對諮商心理師都感到很抱歉。」
高額費用是讓許多個案中斷諮商的主要原因,特別是社會新鮮人,即便有高學歷,菜鳥的薪水也通常沒有餘裕負擔頻繁的諮商,更遑論因為身心狀態不佳而無法工作的案例。在這種情境下,平價的心理健康資源便扮演重要的角色。Joyce曾經待過的英國,便已推行超過10年。
此業務由台北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統籌,執行祕書李琬渝說明,市府和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合作,透過北市心理師公會招募諮商專業人力,希望讓有需求的民眾就近諮商,近年服務量大約都在每年8,000人次。李琬渝坦言服務推行的難處,在不容易主動接觸目標使用者。
儘管社區諮商服務比起私人院所平價,但並非廣為大眾所知。此外,晤談時間較一般諮商短,而各區每週僅有2~3個可預約的時段,平日晚上少有心理師提供服務,假日更沒有服務。換句話說,假如剛開始工作的年輕人有意使用費用低廉的社區心理諮商,也難以配合看診時段,在實務上不容易近用。
私人諮商的費用不堪負荷,公共資源又缺乏彈性,對於這群離開學校後仍持有情緒困擾的青年們,還有什麼機會接住他們?

情緒困擾和身心疾患的距離是精神醫學的一紙診斷,對陷在心理痛苦的人來說,「病」有兩面性──它既附帶著強大的汙名,也給當事人一個理解和安放自己的空間。小嵐便認為,「生病」可以切出正常和例外的自己,「它可以把我沒做好事情的那段時間切割,告訴自己說好了、我要重新開始了,之前做不好,不是我在正常狀態下做不好,自己安慰自己。」
病的本質是正常和異常的區分,病態的彼岸是健康,讓人感覺有地方可以復歸。然而,當愈來愈多青年感覺到自己被負面情緒圍困,到底是集體的異常、還是社會文化所給予的新常態?
英國流行病學教授威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皮凱特(Kate Pickett)則透過數據分析發現,在貧富差距愈大的社會愈容易出現心理健康問題,人們更傾向用階級高低來評斷他人,激烈競爭和個人主義促成嚴重的地位焦慮,即便是高社經地位者也無法免於這種情緒困擾。
當外在文化沒有改變,精神醫療和心理諮商就只是後端補救,像拔河般試圖拉住一個個被製造出來的痛苦個體。弱肉強食的邏輯如此穩固,青年只能把自己塞進競爭的框架裡,無論社經條件再好、學歷再漂亮,都沒辦法拯救他們,反倒使其更難從主流路徑逃跑。
在台大社會工作學系任教的陳毓文,觀察到學生近年頻繁地出現情緒困擾,一開始她也不太明白台大學生為何還悶悶不樂,後來才懂得這群年輕人是有苦難言。社會普遍認為「優秀」的人不該有這些問題,歸因於杞人憂天或抗壓性差,陳毓文分析,這合理化大眾用外在條件來衡量他人的憂苦,「當這個社會這樣看定他的時候,他的苦是更不能被同理跟理解的,更不用講擁抱跟安慰了。」
在心理學領域有一概念稱作「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它是降低壓力對人們產生負面影響的保護機制,正向的情緒支持、適度肯定當事人感受、提供資訊和建議或物質協助,都是社會支持的一環。
長年研究青少年的陳毓文指出,來自家人、朋友、同儕等非專業者的情緒支持,對於當事人的保護和復原有關鍵作用,「專業關係當然OK,但是專業關係可遇不可求,比例還是很低,」陳毓文解釋,很多人認為自己沒有專業訓練,無法成為支持者,但這並不是陪伴的必要條件。她進一步說明,基於人際關係的支持,會讓受苦者感覺被有脈絡地理解,「至少他的議題是有人看到且關心跟回應的,而不是指責的。」

在台大心輔中心協助過許多個案的黃揚文也認為,除專業者外,更多人的參與能撐開更大的網,「我如果注意到你怪怪的,我就讓旁邊的人也知道,大家一起來關心你,1個人不行10個人、10個人不行100個人,總會有人本來的那個樣子,是適合你當下掉下去、可以接住你的那個樣子,就把你接住了。」陪伴者需要互助,合作能減輕個人負擔,讓支持的體系走得更長久。
有時候,正是受情緒困擾所苦的同類拯救了彼此。政治大學畢業的詩恩(化名)回憶,在她最苦難的一段人生風景裡,自殺離開的大學學姊貞璇(化名)是手牽著手、拉著她走過的人。
去年4月,詩恩失眠整整一週,萌生強烈自殺意圖。她和母親起了激烈爭執,當時詩恩已和出版集團簽約,準備實踐自小以來的作家夢,媽媽卻決意要她赴英留學,「所以妳念到這麼高學歷,只是為了想做這個嗎?」言語彷彿利刃,詩恩形容,母親用「為她爭一口氣」抵住她的脖子,「原來我23歲這麼努力,不是為了我自己而活,居然是為了妳嗎?那我幹嘛不死掉?」最絕望的時候,是貞璇給她活下去的理由,「她跟我說,『妳不可以走,因為我還在這裡。』」
詩恩將貞璇看作姊姊,儘管沒有血緣關係,成長過程卻像同個模子印製。「我們是被想像成大家閨秀那樣長大的,天生就應該要肩負很多責任,應該要有知識,要有主見,說話條理行為舉止都是被設計過的。」
彷彿同為長女的宿命,從小便被教育要表現端莊得體,喜怒不形於色,「我們血液裡面就是流著一樣的靈魂。」在貞璇身邊,她可以安心撒嬌,許多經歷不必多言就能互相理解。她清楚知道貞璇也在接受治療,拼盡力氣活著。
貞璇曾提起和心理師連玉如之間的約定,「我們約好等我50歲時要見面。」每一次見面諮商都是對未來的預約,許諾路途有人同行。日本神道教信仰裡有所謂言靈,言語一旦出口則生力量,貞璇對詩恩的喊話,或許也是說給自己聽;她既是被陪伴者、也是陪伴者,從專業者身上得到的溫暖魔法,她試著施加在所愛之人身上,一人拉著一人傳遞善意,向生命拔河多要一些時間和可能性。
詩恩永遠記得,貞璇曾對她說過,「不管妳病有沒有好,妳都是我愛的詩恩。」那是她的幸福,也是她的遺憾,「後來在回想這句話的時候,我相信她一定也希望有個人可以跟她講這麼一句話。」雖然貞璇最終還是選擇離開,但她曾為另一個人撐起傘,抵擋烈日和暴雨,供她一處靈魂的遮蔭。
也許世界軌道如常,一個在1990年代出生的年輕人,一樣會被擠壓進逼仄的升學管道,一樣會被認為好學歷等同於就業保證,一樣得練就十八般武藝,一樣背負著家族的期望,一樣不能說「我做不到」。但只要他們相遇,只要他們看見彼此標籤下忍得發疼的傷口,那一瞬間找到同伴的連結,就帶來一點癒合的可能。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