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選書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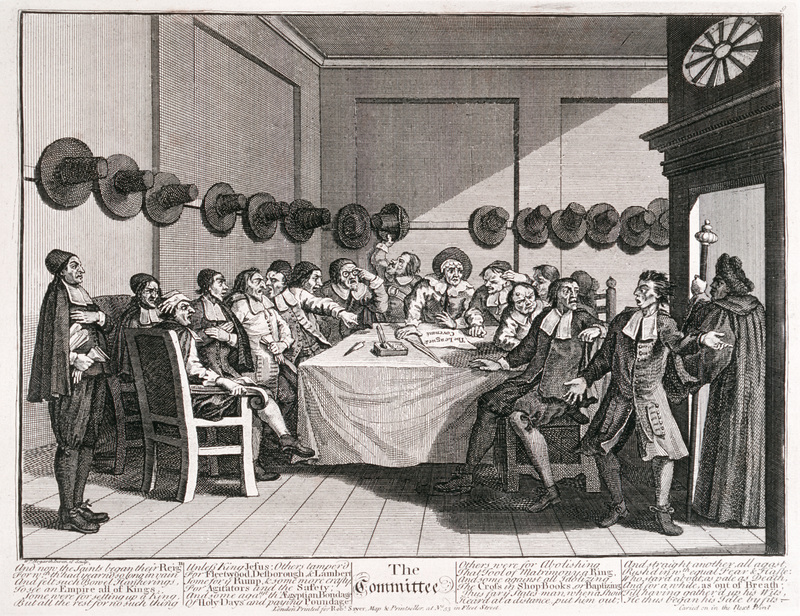
本文為《革命前的寧靜:激進想法的起源,往往在意料之外》部分章節書摘,經黑體文化授權刊登,文章標題與文內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所改寫。
改變人們思想意識的革命,究竟是轟轟烈烈的,還是緩慢孕育的?美國資深媒體編輯蓋爾.貝克曼(Gal Beckerman)試圖在本書指出,推動革命的想法,其實更常是在安靜私密的空間中交流成形的。革命先驅們在狹小隱蔽的角落竊竊私語、構築理想,並慎重討論如何實現他們的目標。而人們為求變革所運用的媒介科技,往往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本書帶領讀者穿越時空,描繪11個歷史現場,考察人們如何用各種不同的媒介交流互動、一點一滴地醞釀革命。從17世紀推動科學革命的信件往返,到1830年代的英國工人爭取投票權的請願書,再到百年後非洲的黃金海岸反抗殖民者的報紙、1990年代讓女性發出憤怒之聲的小誌,乃至COVID-19大流行時,流行病學家和醫師在無能政府的陰影下,利用通訊軟體來自救。
然而,貝克曼也敲醒警鐘:當下由社群媒體主導的世界,正令這樣私密的人際空間加速消逝,也導致阿拉伯之春、占領華爾街和「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等運動未能發揮其潛力而功虧一簣。
在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1958年出版的哲學專著《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中,她擔憂自己口中所謂的「共同世界」(common world)最終會消失。「共同世界」的確切含義一直有點模糊,但對她來說,這個詞似乎意味著構成我們共同現實的所有具體而穩定的元素──從學校到街道標誌等各種機構及人工製品。此書是鄂蘭對於當時加速的太空競賽以及推動自動化的回應,她懷有先見之明地認為,這些行動將導致人們與這個共同世界脫鉤(名副其實地脫離地球界限),轉向合成與虛擬版本的現實,而在這樣的現實中,身為人類的定義將徹底改變。
我們所有人之所以能不孤立、不四處漂流,是因為有一組將大家團結在一起的要素,我深受這樣的想法吸引。對於鄂蘭來說,這些要素不僅是實踐政治、維持社會與文化的先決條件,也是過上有意義生活的先決條件。在書中某段,她以一延伸隱喻描述如果我們失去這些要素會是什麼樣子:
「這種情況就如某種通靈降神會一樣怪誕:圍著某張桌子坐的一群人,在某種魔術把戲的作用下,會看到桌子從他們中間消失了,於是原本面對面坐著的兩人不再被隔開,但同時也完全沒有任何有形的東西將他們彼此連結在一起了。」
你們都在一起,共用一張桌子,在這張桌子上吃著午飯、生氣、用拳頭敲桌,或者看著你的口水飛過這張桌子,或者在有木紋的木頭桌面上握手。然後這張桌子消失了,你們彼此便什麼都不是,只是尷尬地坐著的人。鄂蘭所言之意為,桌子的存在本身將我們聯繫在一起,形成了一個群體、一個社群。且我認為她使用桌子作為隱喻是刻意的:使這些人聚在一起的環境,是某個人造的物體,用思想鋸切和雕刻的物體,這個物體主要目的是讓人們進行討論,讓他們的臉轉向彼此。
當網際網路開始在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殖民時,它承諾了一個無限廣闊的房間,裡面擺滿了這樣的交流之桌。但是在2010年代中期我開始搜尋這些交流之桌時,我並沒有找到很多。只找得到我們都稱之為「社交」的目的地。我意識到,問題主要在語義上。「社交」的意義變成了什麼?我們可以加入Facebook或Twitter,進入老鼠的獎懲迷宮,讓這些網站的商業模式運轉起來,而自己最終只是感到非常孤獨、心煩意亂且困惑。我們已經看到,社群媒體對阿拉伯之春及「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社運人士做了什麼,他們懷著極好的意圖來到這裡,拉把椅子坐下,卻發現自己被打得趴倒在地上。
不過,到了2010年代末期,這種對「社交」含義的誤判已經幾乎完全消除,很少有人對於在Facebook上互動的意義抱有任何幻想──包括馬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本人。祖克柏在2019年3月發布一篇非同尋常的貼文,宣布了公司的新方向,並承認Facebook在分類上的混亂。他寫道,「在過去的15年裡,」他創建的平台幫助人們「在一座數位城鎮廣場上與朋友、社群及喜好興趣建立連結。」然而結果證明,Facebook的用戶開始意識到平台上的路邊小販、街頭公告員以及永無止境的八卦所造成的嘈雜喧囂,他們想要一個不一樣的社交領域。「人們也愈來愈希望在數位客廳裡私密地建立關係。」
這個「客廳」聽起來很像我們的交流之桌。正如祖克柏所描述的,「人們應該擁有單純、私密的場所,讓他們可以明確地掌控誰能與他們交流,並相信沒有其他人能讀取他們共享的內容。」這樣的客廳,隱密而焦點集中,將不再符合祖克柏所說的:他的網站一直以來的目標都是「積累朋友或追蹤者」。不用說,鄂蘭會對積累作為任何社交環境存在理由的這一概念感到震驚。這當然不是培養激進思想的方式。
近年來,道德墮落者和異議人士都自行得出了這個結論,他們想方設法重新利用Discord等新平台或電子郵件鏈等舊科技提供他們所需的東西。對交流之桌的渴望屬於人性,並且從未消失過,當你覺醒並意識到自身利益與關注的事可能偏離初衷時,這種渴望尤其強烈。對於那些早期的數位先驅者來說,這就是網際網路的全部意義所在。他們想像自己正在建立脫離社會、自己的公社,一個重建的像素化部落。我們已經偏離了最初的願景,事實上,它本質上始終是一種幻想,是沙漠中的麥司卡林(mescaline)幻覺之旅。但是,如果說,我們現在了解了交流之桌的必要性,那麼如今我們可以在哪裡找到它們,以及它們將來可能位於何方?徹底的變革可無法等到祖克柏開始建造客廳。
如果我們將社群媒體更概括地看成任何使人們能相互交流的數位平台,會如何呢?2020年,伊桑.扎克曼(Ethan Zuckerman)到騎士第一修正案研究所(Knight First Amendment Institute)擔任客座研究學者時,開始了一項繪製社群媒體全範圍地圖的計畫,而他當時便是這樣看待社群媒體。扎克曼的意圖不僅是要描繪像Facebook這樣的大片陸地,還有從大陸伸出的各小島及半島。
身為麻省理工學院公民媒體中心(MIT Center for Civic Media)的前任負責人,扎克曼已成為數位行動主義的佛陀,他在職業生涯的早期負責創造彈出式廣告,造成我們上網時的麻煩,他似乎自從那時起一直在為此贖罪。他在思想上傾向不必跳出現有框架,反而是在框架中翻找,確保沒有工具未使用過。這就是這個計畫的推動力。與其幻想可能瓦解Facebook的種種規則,批評者需要放眼更遠的地方,「找出打破現狀的平台」。正如他所言,「在主要平台的陰影之外,還有一個多元化的社群媒體空間,我們相信它就在那裡,是開啟不同未來的關鍵所在。」
為了開始這次的搜索,他明確地指出了構成任何社群網路(social network)特質的要素,其中包括它的治理模式(可以接受什麼言論以及由誰決定這件事)、它作為一個平台的思想體系(他說,Facebook的意識形態是「連結每個人並最大化股東價值」),以及最有趣的,是他稱之為「功能」的要素,也就是它讓用戶能夠做什麼(分享貼文、「按讚」評論、炫耀「讚」數)。他相信這些是形塑一場對話的特點,並開始使用它們來構建他的地圖。首先,他將全範圍的社群媒體分為廣闊的區域、分開的大陸,各自以不同的「邏輯」驅動。
例如,他發現有一組平台的取向是「在地的」,這代表在這些平台上的聊天內容會圍繞附近的活動,例如尋找丟失的貓,或指出樹上發現的老鷹,或幫辦在自家車庫的二手拍賣打廣告。即使在這些平台之中,扎克曼也以他的測量儀表發現了一些區別。
例如,像Nextdoor這樣的網站在預設用途(affordances)的運作上,便與Facebook非常相似。任何人都可以發布任何內容,發表的內容會立即出現在網站上,然後其他人能發表評論。而且,就像在Facebook上一樣,人們對一些事的發言有時會演變成沒完沒了的怒罵,像是:預設四處遊蕩的是某個黑人是否構成種族歧視,或者是否應該通過新的分區條例。
也有其他一些網站採用這種在地性的邏輯思維,但治理和預設用途不同,例如一對佛蒙特州夫妻在兒子患腦性麻痺後為尋求鄰居的支援,創辦了Front Porch Forum。此網站現在提供服務於佛蒙特州的每個城鎮以及紐約、麻薩諸塞州及新罕布什爾州的一些城鎮。與Nextdoor不同,Front Porch論壇設有一個版主團隊負責檢查每則發文,以確保發文符合網站的「社區營造使命」。此外,貼文和評論不會立即浮出,而是每天發出一批,就像當地報紙一樣,這種內建的緩慢機制往往能帶來較多的體貼和較少的爭吵。
我喜歡扎克曼思考社群網路架構的方式,即社群網路的架構是如何鼓勵某些類型的談話,並阻斷其他類型的談話。不過,當我請他指出地圖中的祕密發言群島給我看時,扎克曼的態度更加謹慎了。他說,大多數情況下,當人們被迫離開更大的平台時,就會發生這種私密、激烈、親密的群體對話。「這些團體本質上是在表達:我們在這些環境中無法擁有足夠的言論自由,因此我們將開闢自己的空間,」扎克曼說。

他舉出了此類社群的例子,相當令人驚駭。他提到了Mastodon,一個Twitter的翻版,但它有一個關鍵的不同之處:它是去中心化的,這意味著任何人都可以在此網路中支援自己的伺服器節點(Mastodon用戶將這些節點稱為「實例」[Instance]),從而使得各團體能創建他們自己較小規模、自我監管版本的Twitter。
我告訴扎克曼,我需要一些更利社會的例子,比如,在這張地圖上的某個地方,「黑人的命也是命」組織者們可以一起制定影響地方市議會的最佳策略。「台灣,」他說,「看看台灣。」
台灣最初使用Pol.is的其中一次是在2015年,當時台灣政府面臨著如何監管優步(Uber)的問題。年輕人喜歡這項服務,而當地的計程車司機卻厭惡這種競爭。任何關心這個問題並想參與其中的人都受邀加入在Pol.is平台上的辯論。在平台上,他們會看到一系列意見不一的聲明,有的建議完全禁止優步,有的堅持由市場決定,還有一些介於兩者之間(「我認為優步是一種商業模式,可創造彈性的工作」)。參與者也可以添加自己的聲明,但他們不能回覆其他人的聲明。對於其他人的聲明,他們只能表示「同意」、「不同意」或「略過」。
Pol.is接著便使用積累的數據來構建實時的意見分布圖。起初,這只是分成支持優步、反對優步的兩大派別,但隨著每個團體都希望拉攏其他派別,人們開始發表不那麼兩極分化的言論,例如「政府應該建立一個公平的監管制度」或「應允許代僱駕駛加入多個車隊和平台」。然後這張分布圖開始分解,從兩大區塊變為七個集群,每個集群都代表了大多數人認為合理的觀點,並成為實際監管的起點。
儘管Pol.is幾乎只用於此類大規模的民主辯論,但實際上是一場社會運動促發了此平台的誕生。
Pol.is的構想來自於一小群西雅圖的政治宅,他們的領導人是柯林.梅吉爾(Colin Megill),他之所以制定出此平台計畫,不是因為他有電腦工程師的技能,而是他有國際關係的學位。
在看到發生在社運人士身上的事情後,梅吉爾有了開發這個平台的動力:「我看到一大群占領華爾街運動的人都試圖同時說話,沒有人知道他們是否在為每個人說話,但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是在為所有人講話。而那個運動確實徹底自我分裂了。」他的下一個數據點是埃及的解放廣場。他說,Twitter和Facebook基本上是「枕頭大戰」的場所,「但是當談到『讓我們寫一部憲法』時,就會覺得,這並不是這個工具的真正用途。這個工具是為了枕頭大戰。」
因此,梅吉爾和他的朋友們仔細地思考,要如何設計出一個平台,讓人們能夠直觀地看到他們的分歧點和共識領域。不允許用戶回覆彼此的意見聲明的決定是有目的的,並且達到了預期的效果。「把社群媒體想像成一座足球場。如果每個人在場內都只是與對面的其他人交談,那就會有肢體衝突,」梅吉爾說,「但如果現在有一則評論來到場上,然後大家都必須排成一排走過它,並打一個勾,那麼就會有一些秩序。」互動仍然存在,「但這樣的互動產生了很多有用的數據。」他說,測試Pol.is的最大團體是德國左派政治運動「起來運動」(Aufstehen),30,000人在上面制定出他們的綱領。
梅吉爾認為社會運動──變革的驅動力──在行動上以及進化和適應能力上受到限制,因為它們依賴只涉及二元論的工具。當你能辨別出各種分歧間的細微差異,就有機會獲取新的策略和盟友。「我們生活在單向的政治維度上,因為我們自我表達的分類法與思考自己和他人的工具是單一軸向的,」他說。
Pol.is肯定是一種社群媒體,埃及革命者或「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人士本來能充分運用它;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它甚至能幫助那些急診室醫生努力協調出指導方針,以提供給困惑、恐懼的公眾。但它本質上也是一個意見調查應用程式,具備某種有用的資料視覺化功能。而人們需要的就是能夠表達意見。

我在札克曼地圖中另一個廣闊領域看到了更多希望:WhatsApp、Discord、iMessage、Snapchat、Slack、Telegram和Signal等聊天應用程式。札克曼將它們的定義特徵歸類為「隱私、短暫性和社群治理」,正是因這幾個特徵,互動式媒體的前數位交流形式才會如此有益。到2010年代末,排名前四的傳訊應用程式的月活躍用戶數量已經超過了排名前四的社群網路應用程式。這可能是馬克.祖克柏想要將Facebook轉向這個方向的原因(以及他在2014年收購WhatsApp現在看來如此明智的原因)。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這些聊天應用程式可說是非常有助於以數位形式複製出那種由書信、薩祕茲達或小誌撰寫者所創建的小型社群,這一點經常被遺忘,因為我們往往專注在這些應用程式的陰暗面──它們如何逃避監視或提供戀童癖者或仇恨團體的家園。而它們也能帶來一定的生產強度和創造力。
Signal的創建者是一位難以捉摸的無政府主義者,名叫馬克西.馬林史派克(Moxie Marlinspike),他在2020年的《紐約客》(The New Yorker)個人簡介專文中描述了他創造的平台所扮演的角色。像Signal這樣的應用程式因其密閉的端到端加密而臭名昭著,所以很容易忘記這一切的保密性是為了什麼,並想像最糟糕的情況。但是,馬林史派克認為隱私是使社會變革成為可能的實驗必要成分。他表示:
「如果說我對這世界不滿意──我想我可能會不滿意──有個問題是,你的渴望只能根據你的所知。你在這個世界上有一定的經驗,它們會促發一定的慾望,這些慾望會再造這個世界。我們今天的現實只是不斷地自我複製。如果你能創造出顯現不同慾望的不同經驗,那麼這些經驗就有可能創造出不同的世界。」
馬林史派克的Signal使人們能控制房間的大小以及能進入的對象。這個應用程式能確保牆壁的隔音性。對於一群異議人士來說,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此外,若有任何一群人需要釐清自己要如何挑戰現狀,甚至只需說服自己可以做到,它也能派上用場。
我最近讀到,艾莉莎.納肯(Alyssa Nakken)成為美國職棒大聯盟歷史上第一位在球場上執教的女性。結果發現,她是某個WhatsApp半祕密群組的成員,這個群組由職業棒球界的女性所組成,成員從一開始的10名,在一年之內增加至49名,並已成為一個相互共情、分享故事和提供支持的地方。要在男性占主導地位的文化中生存,甚至可能得志,這是她們採用的方式(在大型聯盟中,女性總裁的存在要比女性投手更容易想像得到)。此群組由克里夫蘭印地安人隊(Cleveland Indians)的生活技能協調員發起,建立了女性之間的團結,並充當了滲透這個封閉世界的跳板。「這就像另一種類型的家庭,」納肯說,「如果發生了什麼事,我可以與她們分享,她們會懂的。她們就是會懂。」
像Facebook這樣更大的平台能否創造這樣的機會?有些人向我指出,能夠以中國及其廣受歡迎的微信一瞥未來。
微信於2011年推出,一開始是一個傳訊應用程式,最終承攬了一系列其他功能,包括提供該國幾乎每個人都會使用的電子商務平台。它的成功在某個程度上與它定義社群網路的方式有關:上面刻意維持小規模的社群網路,反映出一個人在現實世界中的實際社交關係。若在微信上未加好友的兩個人對同一則貼文發表評論,他們永遠都看不到對方寫的內容。
由於微信的大部分收入並非來自廣告,因此它從未有過最大化參與度的動力。換句話說,它的目的並不是將人們相互介紹給彼此(儘管有超過10億人使用)。這對中國人來說很有吸引力,他們現在似乎比起微博──中國對Twitter的回應──更喜歡微信。研究過中國互聯網的作家安曉(An Xiao Mina)向我解釋說,在微博出現各種酸民行徑、錯誤資訊和爭執(聽起來很熟悉?)之後,「大家開始往私人的地方轉向,就像,好吧,至少我有自己的小小綠洲。」
微信當然是個令人擔憂的例子,因為其用戶體驗的隱私是一種錯覺。微信用戶一直受到監視,這得歸功於一個叫「天網」(Skynet)的監控系統,此系統能審查政治敏感詞、鏈結、圖像,精細到連揶揄領導人習近平的玩笑都會被搜出。在COVID-19病毒爆發的最初幾個月,一個名為「公民實驗室」(Citizen Lab)的監察組織發現,微信上有2,000多個與COVID-19大流行相關的關鍵詞被屏蔽。其中包括武漢市一位醫生的名字李文亮,他像赤色黎明一樣,試圖警告同事潛在的新型傳染病出現了,卻遭到官方訓斥,幾週後死於COVID-19。
我可以花上很長的時間,在札克曼的社群媒體地圖上漫遊。有些平台,或是有些平台的角落,前景一片光明,不過整體而言,社群媒體似乎愈來愈依賴資本主義及其熟悉的辯證推論:當某種萬無一失的盈利方式與人們真正想要及需要的東西發生衝突時,就會進行一些調整,如此一來,資金才能繼續流動。
Facebook真的會將自己改造成一系列的「客廳」嗎?不會,除非它想出一種商業模式,讓這種交流空間變得像它的「城鎮廣場」一樣有利可圖。那麼,像Signal這種用於私密聊天的應用程式可以保有非營利性質嗎?也許吧,但如果它不擴大規模──這需要資金──又如何能觸及那些也許可以使用它提供之「小島」的人們呢?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