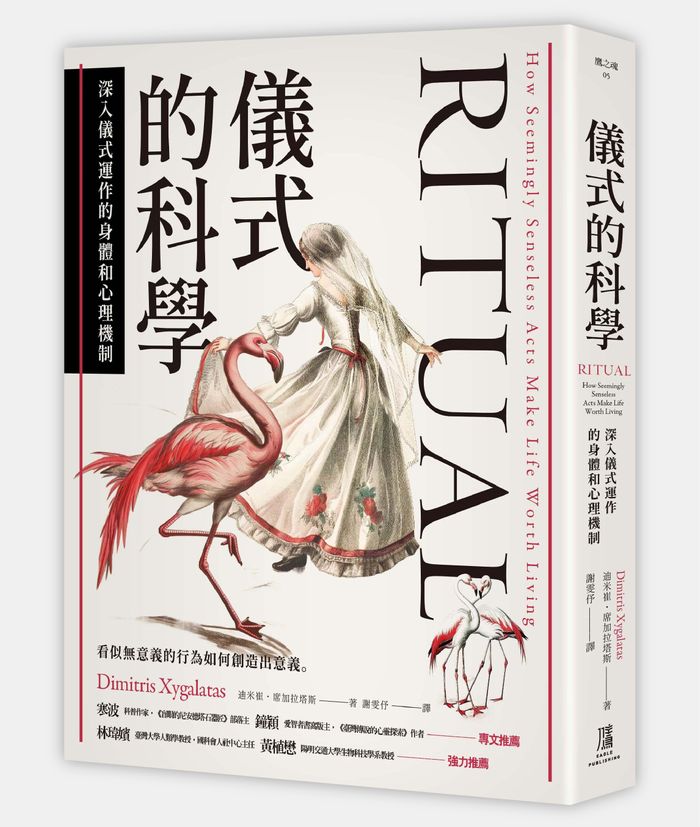精選書摘

本文節選自《儀式的科學:深入儀式運作的身體和心理機制》第6章,由鷹出版授權刊登,文章標題經《報導者》編輯改動。
儀式是人類文化史上最古老也最神祕的泉源,幾乎在每個人類文化中都存在。而儀式的存在,滿足了基本人類需求,也幫助我們解決問題。但我們仰賴這些禁得起時間考驗的傳統,並不是因為它們具有邏輯,而是因為它們對我們來說很有用──即使這些儀式行為對於物質世界沒有直接影響,卻改變了我們的內在世界,透過身體實踐過程中,產生秩序、歡愉、黏著、幸福感等心理機制,形塑了我們的社會角色,以深刻又微妙的機制將所有人連結在一起。
《儀式的科學》作者、人類學家暨科學家迪米崔.席加拉塔斯(Dimitris Xygalatas)在超過20年的旅程中,研究並見證了各種極端儀式和生活中常見的儀式,包括生日派對、加冕典禮、默默祈禱、踏火、爬刀梯、種種可怕的成年儀式,以及本文收錄的祭典。他親歷現場、參與在當地人群當中,把一系列在實驗室中做的實驗帶入田野,以此瞭解人們追求儀式的驅力。本書帶我們一覽這些科學發現,揭露儀式的內在運作,以及它們對我們及社群帶來的重要功能。
模里西斯,馬達加斯加東岸外800公里的一個熱帶小島,只比美國最小的州羅德島一半大一些,位在廣大的印度洋中間,在世界地圖上很容易就被忽略。有些人知道它是度度鳥的故鄉,那是一種體型很大的、不會飛的鳥類,在人類活動出現後很快就在島上滅絕了。還有許多人從未聽過這地方。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小而獨特的地方。在其簡短的歷史裡,它陸續成為荷蘭、法國和英國的殖民地,直到1968年才獨立。獨立之前的行政單位起初引入數以千計來自馬達加斯加、莫三比克和非洲其他不同地區的奴隸,以耕作甘蔗田。在奴隸制廢除後,有甚至更大量的契約勞工從印度、中國和亞洲其他地區遷徙至此。所有那些種族團體的後裔組成了一個真正的彩虹國家,居民說著多重語言,進行多種宗教傳統。這種多元性讓模里西斯成為一個研究儀式的理想地點,你可以在幾公里內找到所有主要宗教的廟宇,各自舉行著不同的儀式慶典。
模里西斯最迷人的儀式是由坦米爾印度教徒於19世紀傳入。坦米爾人是原生於印度南部和斯里蘭卡北部的種族,已有數千年歷史。除了他們的起源地之外,有超過數百萬人居住於全球各地的移民社群中。這些社群使用全世界最古老的語言坦米爾語,並維持著各式各樣的古老傳統,包括那些真正令人感到興奮的習俗,像是踏火、爬劍山和身體穿刺。
這些儀式中最壯觀的,便屬於大寶森節卡瓦帝遊行(Thaipusam Kavadi)。這是一個漫長且痛苦的朝聖旅程,用於敬拜印度神祇穆魯干(Murugan),他是濕婆和雪山神女的兒子,雪山神女是母親女神的轉世,迦梨女神也是。這項儀式在坦米爾曆10月「泰月」(Thai)的滿月時分舉行,是大寶森節的高潮,也是坦米爾社群最重要活動。
大寶森節卡瓦帝遊行由數以百萬計坦米爾印度教徒在世界各地舉行,從南非到澳洲,從部分歐洲和北美地區到印度洋、太平洋和加勒比海的各個島嶼上,是世界上最古老、分布也最廣的極端儀式。這個節慶時長數日,包括一系列的活動。當中最特別便是卡瓦帝祭舞(kavadi attam),舉行時信徒會以尖銳物品穿刺他們的身體,肩上揹著沉重的卡瓦帝(kavadi)加入長長的隊伍,走到穆魯干神廟。人們經常是因為向穆魯干許下了誓願而參與這項儀式。信徒可能會請求穆魯干滿足其特定願望,像是從疾病中痊癒、升職或是讓他們的孩子考試順利。其他人則是因為已達成願望而來還願,感謝神祇保佑他們獲得祝福。但也有許多人是基於社會因素而進行這項承諾。
當我向他們問起為什麼要參加卡瓦帝祭舞時,人們通常會以傳統和團體感作為他們參與背後的原因。「我們是坦米爾人,這是坦米爾人要做的,」他們會說,「這是我們的傳統。」坦米爾人解釋說,他們從小就看別人參加,所以他們就想著有天他們也要參加。其他人則歸因於他們的祖先:「我們的父輩這樣做,他們的父輩也這樣做,所以我們接著他們的腳步。」
大寶森節在模里西斯是公定假日。那天,島上各個角落,大大小小超過100個神廟都會開始組織遊行。這些遊行中最小型的可能只吸引到數百名朝聖者,但較大型的甚至會吸引到數千人,每場遊行都是真正的盛會。其中有個地方特別突出。那是一座名為Kovil Montagne的神廟,位於卡特勒博爾納鎮(Quatre Bornes)前衛峰(Corps de Garde)山腳下的一座山峰,俯瞰著整座島嶼,西邊是印度洋,東邊是中央平原。這裡是模里西斯最早開始籌辦大寶森節慶典的神廟,距今已有一個世紀的歷史。今日,這裡成了大寶森節的主要朝聖地,吸引來自全國甚至海外的崇拜者前來朝聖。
大寶森節慶典在神廟升起那面象徵準備活動開始的旗子後正式展開。旗上描繪著穆魯干的象徵物:長矛和孔雀。隨著大寶森節逼近,信徒會花好幾天搭建他們的卡瓦帝:那是一個由木頭或金屬為框架的可攜式祭壇,精心地以聖像、鮮花、椰樹葉和孔雀羽毛裝飾。他們會在遊行中把卡瓦帝揹在肩上,在數小時的路程結束後將其獻給神明。
大寶森節當天,黎明時分,穿著紫紅色或暗黃色傳統長袍的朝聖者聚集在附近河邊。在親友的陪伴下,朝聖者揹著卡瓦帝,沿著河濱有秩序地列隊行進,驕傲地向每個人展示自己的卡瓦帝。朝聖者的遊行從在河流淺水區進行淨化儀式開始。他們使用薑黃沐浴,接著換上腰布,用聖灰塗抹身體。在印度教信仰中,每條河流都是神聖的,因為它們在象徵層面上都與恆河有關,所以沐浴可以同時潔淨身體和靈魂。他們向穆魯干和他的母親雪山神女祈求保佑,祈禱他們有力量和勇氣面對接下來要發生的事。
很快地,這片寧靜被淒厲的哭喊聲給打破了。在信徒進行朝聖之前,必須承受痛苦的身體穿刺。穿過舌頭的針象徵了──也強加了──沉默的誓戒,這樣的限制會持續直到他們抵達神廟為止。部分女性會出於同樣目的用圍巾把嘴綁住。然而,大多數男性會承受多個部位的穿刺,包括將數根針刺在臉頰和額頭上,或將數百根針穿過整個身體,或者在身上穿過鉤子,掛上鈴鐺或檸檬。針是銀製的,並且有著葉片狀的頂端,就像穆魯干的長矛。即使身上扎滿了針,他們也會將這些針以整齊有序的方式排列,在背上、胸前、手臂和腿部形成美麗的對稱圖案。
我曾問一名剛從神廟下來的青少年穿刺了幾根針。他年約15歲,看起來筋疲力盡,但一直帶著驕傲的微笑。「500,」他以不流利的英語說道。我看著他,不敢相信我聽到的答案。我可以看到他的兩頰上有兩個巨大的疤痕,而他的胸前和手臂上也有好幾十個刺傷的傷痕,但沒有他說的那麼多。「你是說50根嗎?」我問。「不是,」男孩堅持,「500!」我想著這一定是語言不通的問題,所以我用破爛的法語再問了一次,「50?5、0?」「不,」他回答,清楚地說出每個字。「500。5──0──0。」說完他接著轉過身來,讓我看他的背部──像篩子一樣,每一寸都被刺穿了。
在進行穿刺的過程,哭喊聲在人群中此起彼落。那些經歷身體折磨的人肯定處在痛苦中,然而那些看著兒子、丈夫或兄弟遭受折磨的女性才是尖叫得最大聲的。這種同理反應也是疼痛儀式很重要的部分。如同我們在西班牙踏火儀式中所看到的,社會連結強化了情緒感染。當朝聖者經歷疼痛時,他們所愛之人也會間接感受到他們的痛苦,當他們共享彼此的感受時,整個社群彼此的連結就變得更加緊密。
許多參與者甚至更進一步,用與掃帚柄一樣粗、長達幾公尺的巨大金屬棒刺穿臉頰。這些金屬棒的長度和重量需要兩手才握得住,它們的承載者必須要咬住金屬棒,以免棒子撕裂臉部。好像做到這樣還不夠似的,有些信徒會在穿過背部皮膚的鉤子上綁上鎖鏈來拖拉馬車。這些馬車是卡瓦帝的超大型版本,看來就像是有輪子的神廟,上面帶有豪華裝飾,載著等比例尺寸的雕像或呈現神話場景。有些馬車有多層結構,高到必須用竹桿把空中的電線抬起來才能讓馬車穿過。我曾看過一名男子用他皮膚上的鉤子拉著一台18個輪子相連的馬車,而他就像拉動火車的火車頭一樣。
當所有人的穿刺都完成了,信徒們便會集結,往穆魯干的神廟沿路進行遊行。他們如穿牛軛般,將他們的卡瓦帝放在肩上,直到抵達目的地前都不會將其放下。「kavadi」這個字在坦米爾語中的意思是「負擔」,似乎相當切合其義。這些卡瓦帝的結構可能有3公尺高,重量可能超過50公斤。每個卡瓦帝上都有一尊穆魯干像,載著食物貢品和裝滿牛奶的銅罐,待他們抵達神廟後,就會用來供奉神明。據說穆魯干會保佑牛奶不變餿。整場遊行的路徑6公里,朝聖者一路赤腳前進。有些人會為自己增加額外的困難,像是穿著以尖釘製成的鞋子來走這段路。就算不穿鞋,這也不是件輕鬆的事,瀝青在熱帶正午陽光的炙烤下熱得灼人。對像我這樣不習慣赤腳行走的人來說,光是走一步都痛苦萬分。

遊行隊伍移動得很緩慢,卡瓦帝神轎總是在隊伍的最前方:抬這座神轎被視為極大的榮耀和祝福,這項任務每年都由不同的人進行。神轎後面的人們分別扛著一尊孔雀、一尊穆魯干雕像、一把金矛、一根木頭權杖和一根林伽──濕婆神的陰莖狀象徵物。一組樂手為控制遊行行進的節奏,演奏著長型管樂器吶音管(nadhaswaram)和桶狀的桶鼓(thavil)。
每當群眾經過十字路口,便會停下來進行驅逐惡靈的儀式──如同在許多文化中那樣,交叉路口被視為兩界交界的空間,經常有靈魂和其他黑暗力量造訪。每一次他們停下,樂聲就會加快,朝聖者隨之起舞,跟著旋律搖擺依然揹負重荷的身體。隨著音樂的節奏漸快、音量漸強,許多人似乎進入了恍惚狀態,雙眼翻白,兀自旋轉著。有人喊叫出聲,引發一鼓席捲群眾的情緒感染,讓人們一個接著一個開始顫抖、打轉,彷彿對身邊發生的一切失去知覺。當他們快要失去控制時,陪伴他們的家人會輕柔地觸碰他們,幫助他們重拾對周遭的感知。不久之後,音樂慢了下來,遊行繼續進行,直到下一個十字路口。
遊行持續以這個步調前進,花上好幾個小時才會抵達終點。然而,就在朝聖者疲憊又脫水地到達目的地時,最吃力的部分才剛要開始。要進入神廟,他們必須揹著他們沉重的負擔走上山。這表示爬上242階由黑色火山岩製成的階梯,而階梯在太陽整日的曝曬下變得灼熱。到了此時,許多人已瀕臨崩潰邊緣,但每個人仍努力撐到最後──幾乎每個人。
大寶森節卡瓦帝活動為我提供了設置自然實驗環境的理想條件。在這個節慶的脈絡下,同一社群的成員進行一系列儀式,在儀式中扮演不同角色,參與程度也各不相同。這表示我們有可能比較這些因素在自然脈絡下如何影響人們的態度和行為。
每天晚上在神廟都會舉辦集體祈禱,參與者會坐下來進行幾小時的唱誦。這項活動沒有任何激烈的身體或情緒張力,與卡瓦帝所需的最高喚醒有著尖銳對比。根據人類學家對於儀式社會角色的理論,問題浮現了:參加高強度儀式,會讓人們變得更親社會嗎?
話說回來,不是每個人都暴露在等量的痛苦中。有些卡瓦帝很小,有些很巨大;有些信徒只有單一穿刺,而有些人穿了數百回;雖然那些針和鉤每一個都很疼,但在臉上穿一根棍子又是另一回事。因此我的另一個問題是:那些經歷更多疼痛的人,會比那些經歷較少的人更為親社會嗎?
最後,在朝聖者揹著他們的重擔時,他們的家庭成員也會在整趟路程中走在他們身邊,卻沒有進行那些痛苦活動中的任一項。如果這些儀式真會產生親社會的效應,這種影響也會延伸到他們身上嗎?
在行為科學中,一項最常用來測量親社會行為的方式稱為「經濟遊戲」。經濟遊戲是牽涉到參與者(在這種脈絡下通常稱他們「玩家」)之間金錢交易的實驗,這些交易會受到實驗者所制訂的特定規則所約束。在這些任務中最常見的就是所謂的獨裁者遊戲:玩家會獲得預先給定數量的金錢,然後被告知他們可以選擇按自己的意願保留部分金錢,然後把剩下的錢交給另一名玩家。這讓研究者得以衡量每個人對他人的慷慨程度。
經濟遊戲的主要優勢在於風險是真實的。實驗參與者可以給出實際的金錢,也可以把錢留在自己口袋裡。這相當關鍵,因為當研究者要求人們回報他們的態度和行為時,他們的答案並不總是與他們實際上想做的一致,特別是回報那些在所屬社群中會視為正向、在特定社會中會得到讚美的特質時。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人們往往會誇大在社交上具吸引力的特質。因此,經濟遊戲透過要求人們進行會造成重大損失的交換來解決這個問題。與其檢視人們宣稱他們願意給出多少錢,不如檢視他們實際上會給出多少錢呢?
在最近幾十年,透過這類遊戲,我們已經瞭解到許多與人類本質有關的事物。舉例來說,長久以來,許多經濟理論盛行一種觀點,即人們受到將效用最大化的純粹欲望所驅使,會根據理性以及狹隘而自私的成本效益計算來進行決策──這樣的決策模型被稱為理性經濟人(Homo economicus)。然而,當研究者開始使用行為實驗來檢視人們如何做決定時,他們發現理性經濟人只存在理論架構中;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的本能、情緒、無意識偏見和社會預期,經常以各種方式影響我們的行為。
在大寶森節當天,我們早早抵達神廟。寺廟委員提供一間位於山腳的接待室,讓我們在那裡把設備準備好,靜待活動開始。我們知道當群眾到達後,一切都會變得混亂。直到最後一批信徒離開神廟前,我們只有幾小時的空檔來招募參與者。
沿著階梯爬上山丘頂端後,朝聖者排成一列,將他們的卡瓦帝放下,一個個進入神廟向穆魯干獻上貢品,並由祭司幫他們取下身上穿刺的針。許多人在踏進神廟時突然淚流滿面,被歡欣和寬慰所淹沒。在完成試煉後,他們便從另一頭走下山丘,往出口行去。我們的研究助理就駐紮在出口這一側,邀請他們參與研究。我們會領那些同意者進入接待室,給他們一份簡單問卷,讓他們評量朝聖經驗的痛苦程度。完成調查後,我們會感謝他們的參與並給他們補償。然而在他們離開建築時,研究團隊聘請的一名演員會上前詢問,他們是否願意將剛賺得的錢捐一些給當地一個慈善團體。他們會拿到一個信封並被帶進一個亭子裡,讓他們在全然隱私的狀況下將他們的捐款放進募款箱中。每一個信封上都標有我們隱藏的密碼,好讓我們在不影響匿名性的前提下與每名受試者的問卷進行配對。
為了與其他情況下進行的捐款進行比較,我們在不同脈絡下進行了同樣的程序。稍早幾日,我們在同一間神廟,為同樣節慶舉辦的集體祈禱活動後招募受試者,而在大寶森節過後幾週,我們在另一個非宗教地點、離開任何儀式脈絡的情況下,收集控制組的數據。所有的受試者都住在同一個小鎮上,都參與了大寶森節的慶典。由於他們是隨機招募的,因而他們在行為上的差異,理論上會與他們參加的特定活動有關,並排除了任何個性特點或是人口分布特性的影響。
分析數據,我們發現控制組的受試者(沒參加任何儀式的人)會將他們賺得金錢的平均26%捐給慈善團體。這樣的數字相當可觀,考慮到他們本來可以將整筆錢都留給自己時更是如此,不過這與人們在實驗室中進行獨裁者遊戲時的典型分配比例接近。相比之下,那些參與集體祈禱(低強度儀式)的人明顯捐出更多:平均約為40%。更甚者,參加卡瓦帝儀式的受試者捐的金額幾乎是前者的兩倍,平均捐款比例達到他們賺得的75%。在進行痛苦儀式後,人們將他們賺到的四分之三捐給了慈善團體。
事實上,當我們檢視疼痛和捐款的關係時,發現一個明顯的正相關性:信徒在儀式中經歷的疼痛愈多,捐給慈善團體的錢就愈多。但這項儀式的親社會效應並不僅限於那些第一手經歷到疼痛的人。那些在遊行中陪同儀式參與者的人也給出了相當的捐款。他們在自己的親友身旁,看著他們接受穿刺,在他們揹負卡瓦帝時走在他們身旁支持他們、為他們哭。這麼做的同時,他們也間接經驗到他們的犧牲。他們不僅與直接參與者產生了同樣的感受,也表現出與直接參與者類似的行為。在卡瓦帝祭舞當日,整個社群都變得更慷慨了。
在研究中,我們僅專注於我們能夠在這場儀式中測量的面向。不過我們也可以直接親眼觀察到其他親社會性的表現。
大寶森節當天,整個當地社群彼此連結。當遊行通過鎮上時,人們經常打開家門,不僅為了觀賞遊行,也是為了提供幫助。他們會拿出水管和水壺,將卡瓦帝揹負者的腳弄濕,以減緩他們光腳走在炙熱柏油路上的劇痛,並用毛巾為揹負者擦去額上的汗水。他們也會照顧陪伴著揹負者遊行的數千人,設置桌子和臨時篷頂,為他們提供茶點、水果和一小段遮陰。在神廟裡,志願者花上整天時間打掃、跑腿、煮飯並在遊行結束當晚免費供應給每一個人,所用的材料也來自數以百計的捐贈。那晚每個家庭都會精心製作一種稱為七道宴(Sept Cari)的傳統餐點,包括七種不同的蔬菜咖哩,與米飯、木薯製成的甜點和其他數種點心及飲料一起放在香蕉葉上。當地人會驕傲地邀請親友和陌生人一同享用這些餐點,社群中最富有的成員甚至可能一次宴請數百人。每次我參加卡瓦帝活動時,我都受邀參加數個這樣的盛宴。他們的邀請是如此真誠而堅持,以至於我最後經常享用不只一次晚餐。

對外來者而言,像是大寶森節卡瓦帝遊行這樣的極端儀式可能令人費解。然而,正是這種磨難的強度,造就了他們親社會效應的基礎。共享痛苦所鍛造出的強烈連結,或許是幫助早期人類社群在面對戰爭、掠食者或自然災難等生存威脅時齊力合作、克服分歧的一個革命性適應手段。這也是何以我們總在生存威脅中發現人類最非凡的合作案例。
人類學家麥昆(Brian McQuinn) 加入了一群對抗利比亞獨裁政權格達費(Muammar Gaddafi)的反抗軍。麥昆在田野工作中理解到,這些男人彼此間形成的關係,與他們和親近家人之間的關係一樣緊密,甚至更加強烈。他收集來自整個軍營的數據後發現,那些和敵軍進行直接武裝衝突的前線戰士,與其他沒直接暴露於戰場中的後勤支援如技術和醫護人員相比,鍛造出更強烈的連結。這些連結如此深刻,以至於這些戰士往往願意為保護同袍而犧牲生命。雖然他們之間並沒有血緣關係,但這些軍人會以兄弟情誼來表達對彼此的情感,且經常回報他們和同袍之間的連結,比他們和自己親人的關係來得更深。在描述那些情緒時,他們會解釋這種上戰場的經驗存在著某些外來者不能瞭解的感受。他們知道自己和同袍共享了這種私密經驗,正是讓他們彼此間擁有獨特關係的原因。
以越戰老兵萊利(Robert J. Reilly)少校的話來說:
承受戰鬥最強的動力⋯⋯是同一隊或同一排成員間形成的連結。這種凝聚力是士兵唯一最重要的支柱和激勵。簡單來說,士兵會戰鬥是為了他們小單位的其他成員而戰。⋯⋯大多數人不會為了崇高理想冒生命危險⋯⋯但他們會為了他們有凝聚力團體的成員這麼做。
與此相似的,在二戰期間曾任中尉的哲學教授葛雷(Jesse G. Gray)這麼說道:
無數士兵或多或少心甘情願地死亡,不是為了國家、榮譽、宗教信仰或其他抽象的高尚目的,而是因為他們理解到如果為了挽救自己的性命逃離職守,會讓他們的同伴陷入更大的危險當中⋯⋯不是為了什麼主義,不是國家主義,甚至也不是愛國主義,不是這些人類透過被規訓操控而生的情緒,而僅僅是為了袍澤情誼。對團體的忠誠是戰鬥士氣的本質。⋯⋯能夠保持並強化這點的指揮官,知道所有其他心理或身體的因素都遠遠難以比得上這點。
本質上,極端儀式似乎模擬了這些情況,使之獲得親社會性的好處。與其等到戰爭或其他災難發生,許多社群會透過主動提供強大的儀式經驗來激勵社群成員。而效果確如預期──那些經歷強烈集體儀式的人所表達的情緒,經常與那些軍隊士兵表達的情緒相似。如同一名參與這類儀式的年輕男子告訴我的:
「第二天,你在街上看到另一個人,你知道你們一起參與了這項儀式,你們之間有了連繫,現在你和他之間有了一種不同的關係。就算那人是你的敵人,當他與你同在時,他就成為了你的同志,你的兄弟。」
這種與其他成員深刻、無條件的認同,形成了一種特殊的連結。
在大多數案例中,要成為一個社會團體的成員,需要在個人認同(作為個人,我們對於我們是誰的感覺)以及社會認同(我們與其他團體成員間共享的東西)之間進行某種交換。我們屬於個人認同的自我以獨特的生命經驗構成,在我們生命中的那些關鍵時刻形塑了我們的個性。相對地,集體認同一般基於更抽象的概念、理想和信條──舉例來說,關於一個人的國家或宗教──以及關於其他團體成員的普遍化論述。因此,在這兩種自我之間可能存在一種液壓般的關係:要啟動一個人的集體認同,需要對他個人認同的自我進行抑制,反之亦然。當我認為自己是個希臘人時,我不會去想到我的個人經驗或特點。更準確地說,我喚醒的是那些在我腦海中意圖代表希臘性的典型特徵:它可能是國旗、地圖上國土的輪廓、歷史文化的面向,或是其他各種經年累月形成或學習的種種關於希臘精神的事物。在這種認同中,我不會去想我與特定幾個人的特殊關係紐帶,我的父母、我的姊姊和我的友人。這些關係更可能在我想到我的個人認同自我時啟動──他們對我來說很重要,但不是對所有希臘人來說都很重要。
社會認同的抽象形式是社會化的結果。透過定期參與團體活動,暴露於其信條、習俗、象徵和傳統之中,我們開始將自己感知為社會的有機成員,與其他成員分享一系列基因的相似性和興趣。透過鼓勵個人接納、效忠於一個抽象社會秩序,可使複雜且通常還有異質混雜的成員團結在一起。白宮稱之為教義的那種高頻率低喚醒儀式,已經足以鞏固他們的團結。宗教團體的規律集會、軍隊每日的升旗典禮,以及公司的每週快樂時光(weeklyhappy hour),全都是為了讓團體成員在貶低個人自我的同時,強化這種集體自我。
意象式儀式與前述那些活動不同。透過讓參與者經歷與團體成員共享的特別經驗,它們同時啟動了個人認同與集體自我。對於一群一起經歷儀式的人來說,它形成的記憶既標誌了他們個人的敘事自我,也在他們腦海中代表了這個團體。讓一群參加成年禮的新成員產生連結感,不在於他們學到的教義:真正首要的,是他們在儀式中體驗到的共同經驗。與其壓制他們的個人感知,意象式儀式讓他們的個人自我更為突出,同時也讓這種個人自我與他們的社會自我顯得更加難以區別。
心理學家稱這種個人與團體的整合感稱為認同融合,這個詞彙反映了人們的個人認同與集體認同混合在一起的感覺。研究者設計了不少方式來測量它。舉例來說,透過口語調查的形式進行,要求回應者表達他們對於諸如「我是我團體的一分子」、「我的團體讓我變得強大」以及「我就是我的團體」等陳述的同意程度。另外也有一個方式,以兩個圓圈形成的圖解作為視覺幫助,其中一個圓圈代表個人,另一個圓圈代表個人所屬的團體。研究者會要求回應者透過擺弄兩個圓圈間的距離遠近,來描述他們如何看待自己與他們所屬團體間的關係。某些感覺與他們所屬團體完全融合的人,甚至會將兩個圓圈完全重疊在一起,讓自己與同儕間沒有區別。
當人們與團體高度融合時,他們不僅會將自己和團體抽象地等同起來,甚至會開始將自己與團體中的個別成員等同,他們彼此之間建立了個人性的聯繫──無論是想像的或是實質的,團體中的其他人彷彿也成了自己的骨肉一般。他們不再是非個人團體中的其他成員,而是成了共赴戰場的弟兄姊妹。研究顯示,在高度融合的認同狀態下,個人會將他們所屬團體面臨的威脅視為對他們自己的個人冒犯。當一名團體成員的夥伴遭到威脅,他們展現出的情緒反應和家庭成員面臨威脅時會產生的反應相似。與非認同融合的個人相比,他們更願意幫助他們的同志,為團體價值戰鬥,就算這代表了代價高昂的犧牲也是一樣。他們也表達了更多為所屬團體戰鬥、赴死的意願。意象式儀式可以形塑這種強力膠般的效果。
儀式作為強力膠的暗示和它們的表面意義一樣廣泛:意象式儀式能幫助打造具有高度有凝聚力的團體,無論好壞。在強調包容性的脈絡下,它們可以成為形塑一致性的重要媒介。舉例來說,我們在模里西斯調查參加大寶森節卡瓦帝活動的人們時,發現這項儀式是全國共同慶祝的節日,經常會有其他宗教社群的人參加,並以相對平和的方式共存。在這樣的場景中,我們發現參與儀式也增加了人們對於國家的團結感:在進行疼痛的儀式後,參與者對於自己國家的驕傲感有所提升──他們更加認同自己是模里西斯人。然而,於此同時,他們也更加傾向於把其他的當地團體視為模里西斯人。有趣的是,這項判斷根據那些團體在大寶森節卡瓦帝活動的參與程度而有所不同。不意外地,他們視他們自己的團體,印度教徒,為最具有模里西斯國族性的人,接下來是經常參與慶祝活動的基督徒,最後則是較少參與的穆斯林。
相比之下,在面對外在團體威脅(無論是實際的還是想像的)的社群中,這些儀式也能刺激敵意以及對暴力的支持。舉例來說,一項在巴西進行的研究發現,那些和他們支持隊伍認同融合程度更高的足球球迷,更有可能對敵對隊伍的球迷施加身體暴力。而在一項針對西班牙囚犯進行的研究中,研究者也發現那些與他們宗教團體更有融合感的囚犯,更有可能進行恐怖主義行為。
至此,我們對極端儀式的心理機制和連結效應進行了部分的檢驗。不過,透過西班牙和模里西斯的發現可以顯示一個補充面向,而這對儀式的社會效果來說至關重要:極端儀式的連結效應不僅作用在群體和第一手經驗創傷性磨難的個人之間,在正確的情況下,這種連結甚至能延伸到整個社群上。
儀式是人類天性的原始部分,幫助我們彼此連結、尋找意義並探索我們是誰:我們是儀式的物種。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