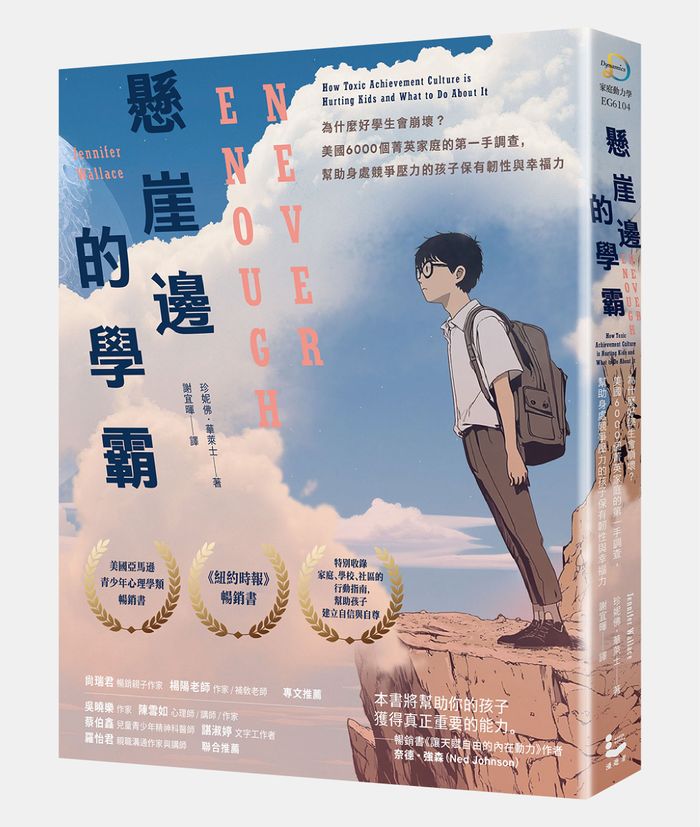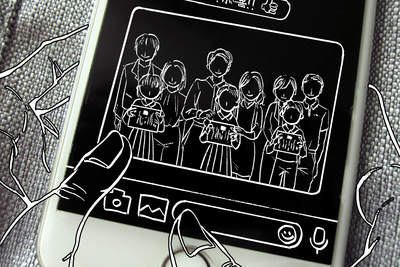精選書摘

本文為《懸崖邊的學霸:為什麼好學生會崩壞?美國6000個菁英家庭的第一手調查,幫助身處競爭壓力的孩子保有韌性與幸福力》第五章部分書摘,經由漫遊者文化授權刊登,文章標題經《報導者》編輯所改寫。
《懸崖邊的學霸》作者珍妮佛.華萊士(Jennifer Wallace)是美國獲獎記者和社會評論員,報導主題涵蓋教養和生活風格趨勢。在本書中,她揭露美國社經地位前20%家庭的孩子,如何在競爭中成了以出類拔萃為目標的奴隸;也引用心理學、教育學與經濟學等各領域研究,幫助父母辨認教養焦慮的深層因素。華萊士特別提出「重視感」,而非用狹隘的優秀標準來看待孩子,鼓勵大人從成就中鬆綁,幫助孩子從小奠定自我價值感,以此培養韌性、同理心、為他人付出的意識,我們的下一代也才能獲得心理健康與社群生活的意義。
當我問心理學家和研究學者,是什麼讓現在的年輕人比過去幾代人更脆弱時,他們都指出了一個因素:對「成功」的定義愈來愈狹隘。問題不在於想要成功,而在於整個社會怎麼定義成功,以及我們為實現成功所制定的路徑有多嚴格。「在富裕的社區,你可以列出一張什麼是『最好』的清單,這給同儕和家庭帶來了巨大壓力和競爭。」專門跟紐約市區明星學校和家庭合作的顧問及親職教練瑞秋.何內斯(Rachel Henes)說:「我跟學齡前孩子的家長一起工作,他們已經開始擔心自己的孩子走上這條路。」
在表面上,這意味著孩子開始相信,他們的價值取決於達成社區所設定的外在標籤:他們上哪所大學、他們找到什麼樣的工作、他們住在哪裡、他們買了什麼。在更深的層次上,他們則可能會相信一些更有傷害性的事情:他們是可以被犧牲的。他們的健康、興趣、需要,都沒有被標記成重要。相反的,「努力工作,盡情玩耍」被視為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出類拔萃的預期成本。
而且任何成本都不算太高。西雅圖地區一名高中應屆畢業生在當地廣播節目中說:「如果在我14歲的時候,你問我願不願意砍掉自己的腿,換來去史丹佛大學讀書的機會,我會毫不猶豫地答應。」她從12歲開始,就「成了以出類拔萃為目標的奴隸」,想要在史丹佛大學等頂尖大學獲得一席之地。來自於父母、學校、同儕、電影、書籍和雜誌中的訊息,不斷在她身上累積壓力;直到她高一那年,她的心理健康狀況開始惡化。當她的體重下滑,而且開始吐血時,她的父母把她送進醫院接受治療。那一年的大部分時間裡,她都在住院。
「我在病床上會哭,不是因為想著『我要死了嗎?』而是因為我的成績在下滑。我正在失去我上史丹佛大學的夢想。」
身為父母,我們有時候會認為,要幫忙激起和支持孩子的雄心壯志。但在競爭激烈的文化中,孩子需要的有時候剛好相反。他們需要生活中的大人偶爾制止他們,防止他們把自己的身心都犧牲在成就的祭壇上,並教他們建立一種不需要借助物質來逃避現實的生活。
從孩子的角度來看,受到重視,意味著一個人身心的極限是值得尊重的。這個領域的專家一次又一次地告訴我:
我們的孩子需要有人能運用智慧來維護平衡,積極地幫忙保護他們的時間、精力、健康和品格。
換句話說,我們的角色不是支持每項努力,而是明智地挑戰這樣的文化、撐出空間,告訴孩子:他們不是機器中的齒輪,而是值得休息和保護的人,幫助他們在這個不斷要追求和保有更多成就的環境中,重新構想自己的抱負。我們傳遞與齒輪式奮鬥背道而馳的明確訊息──他們值得被保護,來向孩子展示我們對他們的重視。
我們需要明確地教孩子,真正的成功,來自於找到(無論是身體上還是心理上)健康的方式來追求卓越。兒童心理學家麗莎.達摩爾(Lisa Damour)說:「我是那種在成長過程中認真負責的學生,花上好一段時間才到達這個境界;基本上,我要求孩子做得更少,並教他們做事要有策略。」在她執業生涯裡,來諮詢的高中生都是被自己的低效率方法壓垮,讓她確信一定有更好的做法。隨著學業負擔逐年增加,如果學生唯一的策略是在每件事情上都付出百分百的努力,就會心力交瘁。我們的孩子需要重新思考什麼是好學生,放棄不健康的責任心,她告訴我:
「我們必須幫助孩子稍微退一步。」
當她的大女兒艾倫在一門課穩定取得優異成績時,達摩爾會建議她也許應該稍微放鬆一下,將這份動力轉移到生活的其他領域,例如跟朋友一起玩,或者花更多時間在其他科目上。達摩爾告訴她:「在需要完成的時候,妳知道怎麼樣把事情做好。」現在,她希望艾倫學會如何在課業中事半功倍。她解釋,在上學期間,都要想像自己一週的精力是一個油箱的汽油。如果你在所有事情上都加足馬力,那麼到了星期四你就會耗光汽油,透支到冒煙。
她向女兒解釋,「好學生」的任務就是要弄清楚什麼時候應該全力以赴,什麼時候應該摸魚,甚至搭個順風車。父母可以給孩子自信,讓他們不必過度努力。「我告訴艾倫,妳有本領,這些內容妳都懂了,妳還有其他事情要做。」她說:「妳不需要考100分來向誰證明什麼。」達摩爾告訴我,這種策略性的方法,對緩解學生的壓力和焦慮非常有用。就像達摩爾的一位同事指出的基本概念:91分和99分之間的差別,是一輩子。
我在默瑟島遇到的父母都富有同情心、為人著想,也願意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每年,學生們都會接受健康調查,來評估他們的心理健康狀況。桑妮雅.盧塔(Suniya Luthar)受邀過兩次,來此對孩子進行更深入的調查,第一次是在2009年,第二次則是在10年後。在2019年疫情爆發前夕,盧塔的調查發現,默瑟島中學生最擔心的問題是「學業成就」。跟全國其他明星學校一樣,孩子的成績紀錄讓他們處於焦慮、憂鬱以及濫用藥物的「高風險」範圍之中。盧塔將默瑟島和她造訪過的其他富裕社區,描述為「我能,所以我必須做到」的文化;她的研究將這種文化認定為青少年的一項重要風險因素。
英國研究學者安德魯.希爾向我解釋,有些老師、教練和父母都過度簡化了杜維克的見解。孩子可能會誤以為如果他們沒有成功,是因為自己不夠努力。「這些學生能力充足,能夠非常非常努力地嘗試,」他解釋:「他們缺乏的,是知道什麼時候應該放棄、什麼時候應該離開的自我調節能力。」在一篇2018年發表的論文中,桑妮雅.盧塔和妮娜.庫馬爾(Nina Kumar)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主要問題不在於缺乏動機和毅力,」他們寫道,而是在於「應該放手時卻無法放手。」
盧塔和庫馬爾指出,成長性思維確實可以幫助在競爭環境中表現不如預期的學生。然而,對於已經過度努力、追求完美的學生來說,他們面臨的風險,在於為了脫穎而出所付出的努力可能會變得病態:他們開始相信,為了在某科獲得A或擠出時間來多參加一項活動所做的犧牲和努力,是他們能力所及、而且能讓他們進入夢想大學的敲門磚。
他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應該對自己說:夠了,今天就先到這裡吧。而這會把他們累垮。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