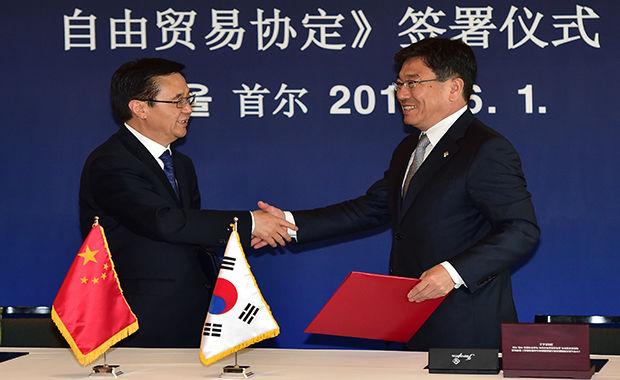閱讀現場

(編按:本文為《我相信世界可以改變──韓國MBC記者提供的鏡子》書摘,經大塊文化出版社授權刊登。)
2001年7月我轉調文化部。我做夢都沒想過會前往文化部,因為自認文化素養不足。我外向好動,喜歡有音樂和故事的音樂劇,對於古典樂或芭蕾幾乎等同門外漢,美術或陶藝這些領域,更是距離遙遠。因此我主要負責宗教和媒體。
文化部要供應新聞給《新聞平台》相當困難。一天頂多只會穿插一篇報導,並且大部分製作成晨間新聞。其他電視台也大同小異。在文化界,電視台記者的影響力比報紙來得低落。因為播出不太順利,因此連要掏名片給人家都不容易。我認為,大家應該重新思考如何對待文化新聞,最好是在晨間時段另闢文化單元,這是轉調到文化部,我跑文化新聞之後的心得。然而當時的社會氛圍,還沒法讓人持續想這麼多。
被《朝鮮日報》視為紅鬼子攻擊的金大中,於1997年當選總統的執政初期,並沒有對這些保守派報紙有積極的對應。當時為了克服外匯危機,需要和保守勢力攜手同行。《朝鮮日報》在金大中執政初期姿態也擺得很低,這是大韓民國政府第一次政權交替,他們這段時間做了不少壞事,生怕有一天會被反攻,因此小心翼翼。
反《朝鮮日報》和報社稅務調查的新聞同時接軌,一路擴大。當時我正好負責媒體,這件事就成了我的主要業務。一位從俄羅斯當特派員歸國的尹次長和我組成搭檔。我負責採訪每天發生的反朝鮮運動報導,尹前輩則進一步做深度分析。
當時的MBC社長金重培希望我們積極報導反《朝鮮日報》運動,工會也是同樣的立場。然而公司裡保守傾向的長官都反對,報導局長不希望太過積極,只選擇某些條目。即使有反《朝鮮日報》運動的報導,也都放在後段。《新聞平台》後半段是所謂的地方台新聞時間。全部45鐘的新聞中,從25分鐘起,首爾總台以外的地方台可以隨時切斷,只播放他們自己在當地製作的地方新聞。反《朝鮮日報》運動的新聞就配置在這個時段,如此一來,他們向社長和工會可以說已經報導了反《朝鮮日報》運動,對反對報導這些的保守派人士,則說是已經冷卻為首都圈新聞。
反《朝鮮日報》運動持續了一個月,我因而認識了民主媒體市民聯盟(民媒聯),從此成了會員。而我在MBC內卻是傷痕累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我們做了報導卻被安排到新聞後半時段,保守傾向的長官更將我視為敵人。
我只是根據理念報導反《朝鮮日報》運動,尹前輩對於把我拖下水不斷表示歉意。當時還不太懂的我,並不了解他為什麼要抱歉。在保守傾向長官占多數的組織裡,積極報導反《朝鮮日報》運動的我,臉上被刻下永遠都洗不掉的紅字。
我和尹前輩從那時開始就情同手足。尹前輩是MBC最會寫報導的人之一,也有優秀的新聞嗅覺,而且有人情味、不貪圖名位、尊重晚輩。他唯一的缺點就是喝太多酒,還有對其他人無法殘酷。我們社會應該讓這種人得以有所發揮才對,但事實並非如此。
媒體是觀看社會的窗口。每個人從裡面可以看到外面,都是因為有窗。如果這扇窗是黃色的,外面的世界看起來就是黃色的;如果這扇窗是紅色的,外面的世界看起來就是紅色的;如果這扇窗很小,我們就只能看到很小的空間;如果窗很大的話,那麼就能看到寬廣的世界;如果不把頭伸出窗外,那麼就看不到窗底下;沒有窗,我們就會與世隔絕。
沒有人能得知外界發生的所有事。可以告訴我們這些事的就是媒體。我們透過媒體間接了解世界發生的情況。近來影像文化發達,可以栩栩如生地重現現場,然而許多內幕則必須透過媒體說明。舉例來說, 畫面上雖然看到失火,但為什麼會失火,造成多少傷害等,就需要由媒體轉達。
然而,萬一說明中帶有偏見該怎麼辦呢?失火死了3個人,有些媒體報導人命死傷嚴重,其他媒體卻說幸好只有3個人死亡,那麼誰說得正確呢?
媒體常說要有客觀性,不能有任何偏見,要有平衡的觀點。然而究竟什麼是客觀呢?每個人觀看的角度不同,客觀這句話能成立嗎?有把世界看成紅色的人,還有把世界看成藍色的人,那麼紫色就客觀嗎?執政黨和在野黨在政治上相互攻擊的時候,什麼是客觀?是把雙方都各打五十大板嗎?還是機械化地把兩種立場都一起報導呢?勞工發動罷工的時候,又該如何報導呢?
世上最常被濫用的詞彙,就是客觀或中立。嚴格來說,媒體的客觀性是假的。《朝鮮日報》和《韓民族新聞》的論調完全不同,但他們都認為自己客觀,那麼誰說的才對呢?
或者根本沒有客觀這回事?不是這樣的,我們至少有辨別客觀與否的基準。那就是以社會多數和社會弱者為中心,看待世界的角度。首先,我們看待少數掌握權力的人的角度應該是嚴格的。總統或政府、國會、財閥、法院等,對我們社會有極大影響,他們若是錯誤使用權力,遭受損害的人將超越想像。這些握有權力的人雖是少數,但是受他們影響的人是多數。媒體的第一作用,就是監督和批判這些掌握權力的人,是多數弱者對少數強者的牽制。媒體應該牽制的少數強者,也不只政府和執政黨,還包含了在野黨和其他媒體,因為他們也是重要的權力機關。同時,媒體也要關懷社會弱勢。
方濟各教宗在世越號慘案當時造訪韓國,朴槿惠政府和執政的新國家黨不希望教宗和世越號遺族見面,即使見面,也不要在胸口別上象徵世越號的黃絲帶。一名地位崇高的神父,以政治中立的名義,向教宗傳達這份要求。教宗的回答是:「在人類的痛苦前,沒有中立。」
媒體,以及我們所有人,基本上都代表社會多數,要具備關懷社會弱勢的視角。這樣,社會才得以維持下去。這就是可以拿來判斷客觀與否的指標。媒體為了讓自己的看法合理化,會不斷找出一些事實(fact)來牽強附會。然而如果真正想讓這些看法具備客觀性,那就必須代表社會多數,或是讓社會多數有同感,或是照顧到社會弱勢。

如果媒體是我們觀望世界之窗,那回顧我們的媒體歷史,不免感到悲哀。解放之後,從軍政時期開始,媒體便已經受到控制。李承晚政府就把《首爾新聞》收歸政府所有,又關閉《京鄉新聞》,做出種種壓制媒體的事。然而,壓軸的還是朴正熙政權。
朴正熙政權通過維新憲法,建立絕對權力後,企圖掌握輿論。他用緊急處制權,讓媒體無法批判政府。甚至威脅廣告主不得提供廣告給當時批判政府的《東亞日報》,引發廣告開天窗的事態。之後《東亞日報》 和《朝鮮日報》大量解雇記者,改以政府機構自居,換取政府給予各種利益,在商業上急速成長。這就是所謂的鞭子和紅蘿蔔,懷柔與威逼的兩手策略。
全斗煥政權繼承了朴正熙政權的輿論掌控政策。雙十二政變後,透過媒體整合,大幅減少報社數量,順應政府政策的報社就提供各種好處,反之就被視為紅鬼子,加以打壓。透過「報導方針」(設限的規範),連報導的單字都要逐一審核。
存活下來的媒體,就和政府一個鼻孔出氣,維持極右的保守論調。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朝鮮日報》、《中央日報》和《東亞日報》這三家報紙。他們被扶持為媒體界的強者,但是他們對人民隱藏真相,政府要他們寫什麼就寫什麼。
問題是,除了這些媒體外,當時沒有足以代替的媒體。人民可以取得資訊的窗口,只有這些極右的保守媒體罷了。這種情況持續了數十年之後,人民已經習慣他們的論調。就像每個人都有自己熟悉的衣服或髮型。突然改變服裝或髮型會怎樣呢?會不舒服、陌生,難以適應。由於人民的這種慣性,加上朝、中、東這三家媒體從獨裁政府時期累積的財力,所以在民主化之後,他們仍然在媒體市場占了最大分量。對那些保守報紙而言,這是幸運;對我們國民而言,這是嚴重的不幸。
1987年民主化之後,媒體發生重大變化。軍事政府時期被政府收編,擔任政府馬前卒,也得到政府優待的那些媒體,本身變成了巨大的權力象徵。
民主化最重要的是輿論,而輿論可能被那些壟斷資訊的媒體所影響。所以像朝、中、東這樣的報紙既然擁有這麼大的市場占有率,當然也就對輿論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尤其在民主化之後,因為政府已經逐漸沒法再對媒體伸手,所以那些勢力已經龐大的保守派報紙,也就變成媒體市場誰都動不了的恐龍。
韓國的媒體要走上正途,還有段險峻的路程。今天雖然資訊科技發達,打破了少數媒體的壟斷,也使得他們沒法像過去那樣隻手操弄輿論,然而只要那些既得利益的勢力還盤據在那裡,我們要走的路就依然很漫長。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