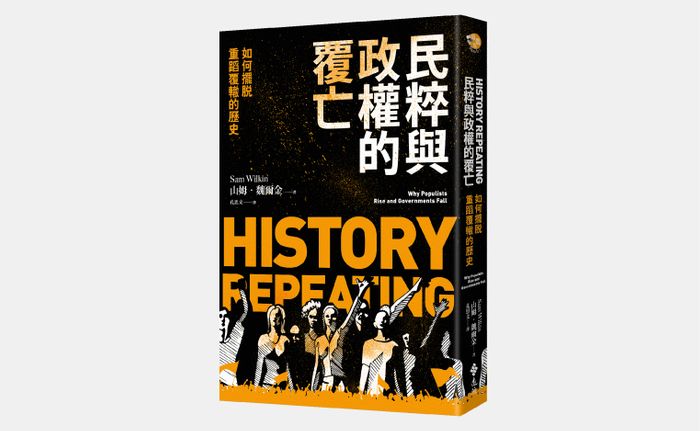閱讀現場

本文為《民粹與政權的覆亡:如何擺脫重蹈覆轍的歷史》部分書摘,經遠流出版授權刊登,文章標題與文內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所改寫。
作者山姆・魏爾金(Sam Wilkin)畢業於芝加哥大學,獲得國際關係、經濟學學位。曾任教布朗大學華森國際與公共事務研究中心。
本書以歷史觀點,敘述民粹主義的興起,如何招來動盪、導致穩定政局崩解。作者以泰國、希臘、美國、伊朗、法國、帝俄為例,分析民粹的興起、造神運動捧紅的政治人物,怎麼影響國家。他詳細解釋民粹主義者的個人特質 、政治動員趨勢、議題極化之後的難題,並指出今日許多國家的現狀,或許正在重蹈覆轍。如何避免民粹「滅國」?在本章節中,作者提供了面對政局動盪、感受到強烈亡國感之際,可以注意的幾件事。
在這本書中,我們提到了許多政局不穩的因素與相關的研究。所以,未來我們是否註定會重蹈這些歷史的覆轍?又或者,自二戰以來政治治理上的進步,代表著當今的民粹主義分子無法像過去一樣,掀起政治滔天巨浪?
先前提到,全球金融危機和隨之發生的撙節措施,都給主流政黨帶來極大的打擊,而且在2016年給民粹主義者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讓他們興起。當然,金融危機帶來的驚嚇退去後,民粹主義潮流也會消失。我不認為未來會有國家步上阿根廷衰敗的後塵,我也相信希臘能快速復原。
話雖這麼說,我覺得未來要面臨的挑戰,遠大於一些出人意外的選舉結果。有些國家正在一步一步地落入難以脫身的圈套。因此我也提出幾個建議,避免不愉快的歷史重新上演。
大多數的人談到政治,尤其是拯救國家的議題時,幾乎馬上就討論到如何讓對手陣營下架。美國的政治非常兩極化,到了極端對立的程度。我有不少朋友和點頭之交都已經無法通過「螢幕測試」,也就是如果總統出現在電視螢幕上或是網路,這些人的厭惡之情馬上溢於言表,馬上轉台。歐巴馬執政的那幾年,我有幾個從年輕時就認識的朋友,也同樣無法通過「螢幕測試」。(我成長於南達科他州和印第安那州,2016年的總統大選,川普在這兩州贏得多數選票。)而我那些比較左翼的朋友,對川普政府的反應也是很激烈。
不過,請再思考一下泰國與阿根廷的歷史。就算是推翻裴隆和塔克辛,甚至讓他們流亡海外,國家並沒有因此得救。這種勝利也可算是代價慘重。大家只要談到自己國家的政治,通常都是以所擁護的政黨、而非政治風險的角度去考慮。但總體來說,若要思考國家完不完蛋這個問題,誰執政其實所只佔了這個議題的一小部分而已。當大家都只顧著討論讓誰下台的問題時,這可能象徵著:事情基本上已經出了很大的問題。
希拉蕊在她的自傳中提到,她和柯林頓重新閱讀了艾瑞克.霍夫(Eric Hoffer)的經典之作《狂熱分子:群眾運動聖經》,並且在2016年的總統競選過程中,分送幾本給在她手下工作的資深員工。我可以理解希拉蕊的用意。本書第二章提過,《狂熱分子》宣稱大型群眾運動通常會吸引到那些絕望又憤怒的魯蛇。假如我們是以這個角度看待川普的支持者,那麼柯林頓夫婦肯定覺得非常滿意。
但是,就像我們在前面幾個章節所讀到的,把所發生的政治事件歸咎是群眾情緒集體失控,這樣的說法是不正確的。革命之所以會發生,並不是由於群眾情緒集體失控,也不是極端困頓的個人生活導致暴力出現。《狂熱分子》一書中所提到的論述,正好和會形成有效率大規模群眾運動的原因完全背道而馳。霍夫指出,發動俄國革命群眾運動的,是那些人生失敗的魯蛇,這群人在崩潰的社會底層苟延殘喘,極度想逃脫因為自己錯誤的選擇而造成的後果,這些人正好成為列寧教義眼中的獵物。
可是我們也看到,俄國大革命發生的原因,完全不是霍夫所說的。事實上是那群在社會中有機會往上爬的俄國工人,這群人所凝聚的群眾力量之所以所以變得強大,並不是因為社會結構的崩解,而是因為他們本身不斷提升的社區組織效率,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幫助他們克服群眾弱點的工會。
當然,任何人都有權利稱呼對手是瘋子,這是民主自由中最值得珍惜的部分。但是一直計算這個國家有多少人瘋了,絕不是評估國家風險的好方法。
與其擔心那些孤僻又憤怒的個人,不如把重點放在義憤填膺的團體,因為政治是群體運動。人們透過選票讓政府下台的主因,並不只是自己的荷包縮水,而是因為不滿政府在治理國家經濟上的無能。我們會起身參與政治,跟我們個人所受的痛苦沒什麼關係,而是當我們覺得「自己所屬的群體正在受苦」,於是挺身而出。
2016年,美國和英國那些感到委屈的社會群體,在大選中投下支持川普和脫歐的一票。這些選票中也許有參雜著部分選民的種族歧視和排他的心態。不過最近的研究顯示,這些社會群體本身也有滿腹的牢騷:全球化衝擊著他們、職場就業不順利、自己有過親友因濫用藥物而死亡的切身經驗。在這些社會群體中,有些人還是過得不錯,有的就過得很慘。無論個人處境是什麼,處於這種社會群體的人,容易把票投給民粹主義者。
有人說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其實見證了一場階級的戰爭。如同《紐約時報》記者奈特.柯恩(Nate Cohn)在他的一則現在已經出名的推特上所言:
「如何解讀這場選舉?就是白人勞工階級選民,想以弱勢族群之姿投票,而他們所佔的比例就超過總選民人數的40%。」
我並不完全同意階級之戰的這個說法。我所認識把票投給川普的友人,都有受過大學教育,他們剛好處在一個正在苦苦掙扎的群體中。事實上,那些勞工階層中相對處境比較好的成員,比較容易把票投給川普。這也不難理解,如同我們在稍早的章節所看到的,在一個滿肚子怨氣的社會群體中,通常是境遇比較優渥的成員,例如俄羅斯的工人,首先發起動員之戰。
2016年令人驚訝的選舉結果,起因是突發的。例如聯邦調查局局長詹姆士.柯米(James Comey)在不對的時機點上,決定宣布有關希拉蕊郵件門的新證據;而英國的強森(Boris Johnson)決定加入脫歐的陣營。我認為滿腔怒火的社會群體所發起的動員運動早已行之有年,歐洲的社會群體為2014年的歐洲議會選舉帶來重大的紛擾,讓英國和法國的右派民粹主義政黨在歐洲議會中成為最大的陣營。投票率低的地區容易成為發起動員的領頭羊(就像歐洲議會選舉中,英國的合格選民只有不到37%的人投票),因為規模不大,但意志堅定的族群就可以帶來改變。
同樣的道理,美國的右派民粹主義茶黨運動,多年來都不斷發揮其影響力,尤其是在投票率不高的議會初選。
動員政治並不是在2016年造成民粹主義紛擾現象的唯一力量。許多會針對議題投票的慣性選民,也把票投給民粹主義者,例如恪守宗教教條的美國白人也容易投給川普。但是,當今政治的兩極化態勢是否會繼續升高,主要還是取決於動員政治。社會特定族群為生活載浮載沉的掙扎故事──特別是當那個族群式微且受到不平等待遇時,會激發出群體認同感與影響政治的機會,讓上百萬非慣性選民投下支持英國脫歐的一票。如果這些社會群體依舊對政治不滿,他們就會將想法轉化成政治行動,也有可能會繼續發起動員。
動員政治當然也有優點。當政治出現新的聲音時,常能為社會公正帶來進步的動力。2017年,眾議院議員在全美各地的市議廳為大眾所舉辦的公民會議,平均出席率從原本不到50人增加至280多人。看到美國民眾參與自己國家民主的熱情,的確很振奮人心。
川普總統大選勝選後,是女性發起引人注目、大規模動員的活動。這可能是美國有史以來,女性遊行活動單日人數最多的示威抗議;而參與群眾較為多元的反性騷擾抗議活動,人數也不遑多讓。
許多人讚揚這種類型的動員,因為這樣才能帶來實質的政治改革。回顧歷史,歐洲的民主曾是富人的專享權利。更早之前,統治階層則由世襲貴族所掌控。當然,動員中產階級參與歐洲民主運動的人士,可算得上是英雄而非壞蛋;歐洲政治能不斷進步,與法國大革命脫不了關係。
不過,動員政治所帶來最大的危險是分裂社會。稍早的章節中提到,當人們認定自己所屬的社會群體出現了政治問題,他們就會決定採取政治行動,因此一個社會族群所發起的群眾動員,會引發其他社會族群的政治動員。動員會導致動員,展開循環,使對立情勢升高。在塔克辛讓鄉村選民成為泰國選舉政治的一股勢力後,黃衫軍搶先一步走上街頭,接著大批紅衫軍也湧入曼谷市中心,而事情的演變就是從此開始每況愈下。
不穩定的政治,也成為民粹主義者大展身手的表演舞台。民粹主義分子常是成功動員了對政治不滿的非慣性選民。民粹主義分子也能在經濟動盪的時局中,藉著打擊執政的政黨而獲得利益。民粹主義者在兩極化的環境中壯大,因為他們發現,可以輕而易舉地獲得不同政治立場選民的支持。希臘的主權違約讓左派民粹主義者贏得勝利,之後又與右派民粹主義者共同組成聯合政府。這種做法著實跌破評論家的眼鏡,但是裴隆肯定能夠理解的。
從更廣義的面向看來,如同我們在前面的章節所讀到的,民粹主義者喜歡鼓吹大家起來反對「危害人民的這個國家」。而民粹主義者在這種情況下的宣傳,如果摻雜著些許事實的話,那就更容易贏得選票,在「封建路易斯安那州」的脩義龍(Huey Long)就是最好的例子。
今日的民粹主義者,更容易做出類似的宣傳。在美國政治中,金錢可以買到很大的影響力,而左派民粹主義者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選戰中特別呼籲大家提防這件事。在英國及其他歐洲國家的人民,普遍認為歐盟的治理方式走菁英路線,一般大眾無法影響歐盟政府。這種「民主上的不足」,會導致一般人對政治領導人逐漸失去信任感,這也反映在選民用選票支持民粹主義者的投票行為上。美國和英國如果不進行政治改革,則民粹主義者用「政治體制真糟糕」作為藉口,很可能會繼續贏得選票,為自己增加政治勢力。
一般來說,有錢人是平淡政治最好的密友。保守派慣於拘泥守舊,偶爾也會打打馬球、獵獵狐狸打發時間。不過如同稍早所提,自從1980年以來,學術界對民主失靈做了詳盡的研究,結果發現有錢人的干政與貧窮人所發起的暴動相較下,前者更容易讓民主失效。
大多數人認為,在阿根廷式的恐怖平衡中,必須要有像脩義龍這樣的人物──巧取豪奪的駭人野獸,也是富人們的惡夢,脩義龍積極發動階級之戰。但是到了今天,像脩義龍的這種行徑,只有外表可怕,卻無法發揮太大效果。1980年之後研究民主失靈的統計數字顯示,這種造勢行為很少真的會威脅到民主。有關財富分配的研究也指出,這種挑起階級戰爭的行為,幾乎從未真正造成財富的重新分配。
已有證明顯示,近年來的恐怖平衡更加常見。有錢人不滿長期受到課稅,也不爽平民百姓一天到晚覬覦富人財富,想分一杯羹,於是把他們的怨氣轉化,變成對抗民主制度的行動。這是恐怖平衡原本就帶有的一種反差。「民主」與「財富不均」這兩者處不來,因為在某些情況下,最好的辦法就是吸乾有錢人。
換句話說,在貧富高度不均的國家,「重新分配財富」的想法對普通的投票者是有號召力的。而會製造這種恐怖平衡的政治人物,通常是思路細膩、溫文儒雅甚至是專業的政治家,簡言之就是像歐巴馬那樣。歐巴馬的「平價醫療法」(Affordable Care Act),或是俗稱的「歐巴馬健保」,就是最近30年來美國最具有財富分配性質的立法內容。歐巴馬把從有錢人那課徵來的稅,用來擔負窮人的健康保險費用;內容包括對那些高額的醫療保健計畫課稅、對醫療保健公司課稅、從薪資裡扣繳額外的0.9%聯邦醫療保險稅,以及外加3.8%的投資收益稅。
許多持右派民粹立場的人們並不喜歡「歐巴馬健保」,因為他們擔心自己的健康保險會受到牽連。而美國有錢人對財富重新分配的激烈反應,更是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記者珍.梅爾(Jane Mayer)曾報導,美國共和黨大金主、石油大亨柯氏兄弟(Koch brothers)組成了反歐巴馬政府論壇,並且募得將近十億美元的政治獻金。我知道不應該將恐怖平衡套用在美國身上,因為在希臘的案例中,是沒辦法對有錢人課稅的。不過柯氏兄弟的資產,多半是與美國本土息息相關的重工業,因此不像希臘船舶業者的財富具有流動性而可以免於課稅。
理性的人可能認為,柯氏兄弟的反政府計畫,其本質並非是「反民主」的。基本上來說,這只是柯氏兄弟先想出來的聰明政治策略罷了(現在民主黨也急起直追採取行動好加以反制)。歷史上看來,有錢人熱衷投入政治,通常只會讓事情往壞的方向演變。
如果有人撒下大把銀子想贏得選舉(像柯氏兄弟還有泰國塔克辛那樣),那麼社會大眾不會把這種行為解讀為「有錢人有錢有閒的嗜好」;相反地,這一定是追求更大政治影響力的行為。如果柯氏兄弟和其他富豪能有其他的嗜好,我大概會睡得比較安心。過去數十年來,富裕國家都不會遇到阿根廷式恐怖平衡這個問題,財富不均的情況在富裕國家也不嚴重。然而現在,財富不均的情況愈來愈嚴重,我們還真是「幸運」。
「牛津分析」年度會議閉幕晚宴,於金碧輝煌的布倫亨宮殿(Blenheim Palace)舉辦,所有與會者都盛裝出席。台上講者演講完畢後,一位與會女性(有支持民粹主義的傾向)說:「這聽起來簡直就像是法國大革命前夕,在凡爾賽宮所發表的演說。」我語帶風趣的回說:「而且我們還吃著山珍海味。」她又說:「我們在這會場中支持全球化,外面則有90%的人想終結全球化。」
她說的沒錯。在布倫亨宮裡出席會議閉幕晚宴的人,都想改善世界,這群人絕大多數是地緣政治專家,大家集思廣益計畫著如何拯救全球化和自由民主。但是這群專家並沒有考慮其他人是否也認同他們的觀點。政治科學家卡斯.穆德(Cas Mudde)也提出類似的觀察,他注意到歐洲政治科學領域的學者,非常有興趣研究極右派民粹主義的崛起,可是沒有一個學者認同民粹主義。所有的學者,都是把民粹當成一個「該被根除的社會問題」來研究。
進步主義者在這樣的形勢下,免不了受到牽連。有抱負、高成就且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總是持續拼命提升自我,而他們也希望全世界跟他們一樣努力。但歷史上進步主義者拯救世界的計畫也是一波三折。在脩義龍時代,進步主義者就曾走偏,帶著錯誤的科學認知投入一些領域,其中最糟的負面案例就是優生學:以優生學為題材的書籍曾是排行榜暢銷書,農業博覽會中也舉辦「美滿家庭」和「健康寶寶」比賽。進步主義者對提升人類基因品質的信念,到了走火入魔的境界,還鼓吹立法強制絕育精神病患者,美國也竟然有30多州實施強制絕育。進步主義者的這種想法的確是走在科學的尖端。後來希特勒將此思想「發揚光大」,把社會帶往一個進步主義者不想要的境界。
如同歷史學家薛爾頓.史托若姆奇斯(Shelton Stromquist)所指出,進步主義者不喜歡玩階級戰,但是到頭來,他們打的正是一場代表自己的階級戰。「牛津分析」年度會議閉幕晚宴的與會者也差不多一個樣:想運用專業拯救這個世界,但我們真正想的是拯救我們自己的世界。這可能就是進步主義的原罪。
當社會變得兩極化,或是民主受到威脅時,挽救政治穩定的責任,往往落在中產階級的社會進步者身上。但是,他們的努力有可能會出錯。最糟糕的情況是,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最後可能會動員起來,對抗傳統的中產階級或是窮人。伊朗革命結束後的混亂時期就曾發生這種事,阿里.沙里亞蒂(Ali Shariati)夢想中的理想伊斯蘭革命,後來演變成獨裁。而1980年代,希臘和阿根廷的中產階級起身對抗貧民。最戲劇化的例子莫過是當今的泰國。這些都是不利於政局穩定的情況。
進步主義者也常稱呼投票給川普及贊成英國脫歐的選民是瘋子,會被民粹主義利用。這種想法對任何跨階級結盟的動作來說,都沒有幫助。這種想法同時也忽視了大多數研究的重點,也就是造成政局不穩的成因到底是什麼。當一個社會群體對政治不滿而被動員起來,此時的他們絕不是一群待宰的羔羊。他們會積極參與傳講自己的苦難故事,形成更多群體認同,讓他們能夠動員。他們之所以會站出來,是因為他們相信自己能夠改變局勢,而2016年證明這種想法的確是正確的。
這也帶我們進入最後一點:當心兩難抉擇,而且如果你看到它迎面而來,感到恐慌之餘趕快逃得愈遠愈好。我最近收聽波士頓公立廣播電台所播放的節目,內容是一名記者的訪談,她出版的書獲得國家好書獎(National Book Award),主題是有關俄羅斯總統普丁執政下的俄國。她說當川普當選總統時,歐巴馬和希拉蕊應該要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並宣布選舉無效。
這聽起來的確是兩難的抉擇。
當社會變得兩極化,兩難的抉擇很容易成為政治議題。最常發生的是,在民粹主義者取得勝利後,下一場選戰反而是民粹主義者彼此之間的對抗,而非民粹主義者與中間路線者的競爭。人民可能會被迫在「犧牲經濟發展」或「犧牲民主」這兩者間做出選擇。當阿根廷的經濟長期陷入衰退,阿根廷的民眾就得不斷在一籃爛蘋果中做出選擇。這樣的兩難抉擇,容易造成政局不穩。有時候,受到動員的團體之間會仇恨彼此,他們在爭執之於就會開始搞破壞;或是當情勢失控後,乾脆一把火同歸於盡。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