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現場

本文為《民主國家如何死亡:歷史所揭示的我們的未來》部分章節書摘,經時報文化出版授權刊登,文章標題與內文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所改寫。
川普(Donald Trump)的當選,加上川普政府的許多作為,不少人擔心美國正遭遇民主危機。本書作者史帝芬.李維茲基(Steven Levitsky)和丹尼爾.齊布拉特(Daniel Ziblatt) 皆為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他們指出,隨著專制領袖當選、濫用政府權力與完全壓制反對黨,民主制度以十分欺瞞大眾的方式,逐步零散地消亡,而這三個步驟正被全世界引用,川普的當選也不例外。我們必須了解有什麼方法可以阻止這些情形發生。
作者主張民主國家並不是因為一個人的衝動而毀滅,而是在黨派惡鬥的過程中,長期忽略規範慢慢被削弱;從媒體、法院、情報單位與倫理機構,這些民主的制度性緩衝不斷被弱化。當恐懼、投機或失算,導致主流政權把極端派帶進主流,就會危害民主。本書不只是歐美眾多國家的歷史血淚經驗談,也不只是美國當代獨有的危機,眾多現象、警示和提點,更值得台灣政黨和所有人民借鏡。
思考如何反抗川普(Donald Trump)政府的濫權顯然很重要。然而,美國民主面對的基本問題仍是極度黨派分裂──不僅由政策差異還有深層憎惡來源,包括種族與宗教差異所造成。美國的重大兩極化早在川普當總統之前發生,而且很可能延續到他下台後。
政治領袖面對極端兩極化有兩個選項。第一,他們可以把社會分裂當成常態但是藉著菁英階層的合作與妥協設法抑制。智利政治人物就是這麼做的。
如我們在第五章所見,1973年社會黨與基督民主黨之間的激烈衝突摧毀了智利民主。兩黨間深刻的猜忌持續了許多年,壓倒了他們對皮諾契特獨裁體制的共同反感。流亡的社會黨領袖里卡度.拉戈斯(Ricardo Lagos)在北卡州立大學演講,回顧基督民主黨前總統蒙塔瓦(Eduardo Frei Montalva)在1975年造訪該大學時,他決定不願跟他說話──所以他請病假。
但是政治人物終究開始對話了。1978年,拉戈斯回到智利,受前基民黨參議員雷耶斯(Toma s Reyes)之邀吃晚餐。他們開始定期會面。
大約在同時間,基民黨黨魁艾爾文出席多元黨派背景的律師與學者集會,許多人為政治犯辯護時在法院認識過的。這些「24人小組」集會只是在會員家裡輕鬆地吃晚餐,但是據艾爾文說,集會「在曾經是敵人的我們之間建立了互信」。最後,對話有了成果。1985年8月,基督民主黨、社會黨和19個其他政黨在首都聖地牙哥高雅的西班牙圈俱樂部聚會,簽署《向全面民主過渡的全國協議》(National Accord for a Transition to a Full Democracy)。
這份公約形成了民主協商大聯盟的基礎。
大聯盟發展出一套「共識政治」做法,關鍵決策要由社會黨與基民黨領袖們協商。結果很成功。民主協商大聯盟不只在1988年全民公投中推翻皮諾契特,還在1989年贏得總統大位,掌握了20年。
協商聯盟研發出的統治風格跟1970年代的政局大相逕庭。領袖們害怕不斷的衝突會威脅智利的新民主,發展出非正式合作的做法──智利人稱之為「協議的民主」──總統向國會提出法案之前要諮詢所有政黨領袖。皮諾契特的1980年憲法造成了獨大的行政權有權多多少少片面地制定預算,但是基民黨的艾爾文總統密集諮詢社會黨等政黨,才送出他提案的預算。而且他不只徵詢盟友。艾爾文也跟支持獨裁維護皮諾契特的右翼政黨協商立法。
據政治學者西亞維里斯(Peter Siavelis)說,新規範「有助避免大聯盟內部與朝野之間潛在導致動盪的衝突」。近30年來智利成了拉丁美洲最穩定又成功的民主國家之一。
民主黨與共和黨能否遵循智利的經驗令人懷疑。政客很容易哀嘆文明與合作精神淪喪,或緬懷過去兩黨合作的時代。但是創造規範是集體作業──夠多領袖接受與遵守新的不成文規則才可能成功。這通常發生在來自整個光譜的政治領袖們望著深淵,發現如果他們不設法解決兩極化,民主就會衰亡時。通常只有政客們遭受像智利那樣暴力獨裁體制的創傷,甚至像西班牙的內戰,利害關係才會真正變得清楚。
即使有潛在兩極化也要學習合作的另一個方法是克服兩極化。在美國,政治學家們提出過許多種選舉改革──僅舉幾例,終結重劃選區不公、開放初選、強制投票、選舉國會議員的替代規則──這可能緩和美國的黨派敵意。然而其效力的證據仍很隱晦。
我們認為專注在驅動美國兩極化的兩個潛在力量會比較有價值:種族宗教重組和惡化的經濟不平等。我們認為,處理這些社會基礎必須要重新洗牌美國政黨所代表的東西。
共和黨向來是兩黨裂痕的主要驅動者。2008年起,共和黨有時在掣肘、黨派敵意與極端政策立場方面表現得像個反體制政黨。它的25年右傾過程是組織核心空洞化造成的。過去25年來,共和黨的領導架構被掏空了精華──先是因為資金充裕的外圍團體興起(像是Americans for Tax Freedom、Americans for Prosperity 和其他許多),他們的募款能力讓他們多多少少能主導許多共和黨民選官員的政策議題,接著還有福斯新聞等右翼媒體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像柯赫兄弟等富裕的外部金主與有影響力的媒體名人,比共和黨自己的領袖更能夠影響民選的共和黨官員。共和黨仍在全國各地勝選,但是以前所謂的共和黨「建制派」如今變成了幽靈。如此空洞化讓黨很容易被極端派掌控。
減少兩極化必須靠共和黨改革,甚至直接解散重組。首先,共和黨必須重建自己的體制。意思是在4個關鍵領域奪回領導階層控制權:財務、草根性組織、宣傳和提名候選人。唯有黨內領袖擺脫外部金主與右翼媒體的掌控才能進行自我改造。這需要重大的改變:共和黨人必須排除極端元素;他們必須建立更多元的選民結構,讓黨不再重度依賴萎縮中的白人基督徒鐵票;他們也必須設法不靠白人民族主義,或亞利桑那州共和黨參議員弗雷克所謂的「民粹、排外和煽動的食糖亢奮」訴求贏得選舉。
重新建立美國主要的中間偏右政黨是個苦差事,但是這種轉變是有歷史先例的──而且在更艱難的情境中成功。只要成功,保守政黨改革會觸發民主的重生。特別戲劇性的例子是西德在二次大戰後的民主化。這項成就的核心是個被低估的發展:德國的中間偏右基督教民主聯盟(CDU)從喪失信用的保守與右翼傳統的廢墟中組成。
1940年代之前,德國從未有過組織良好、能勝選的保守派政黨,而同時是既溫和且民主。德國的保守主義長期被內部分化與組織缺陷摧殘。尤其是保守新教徒與天主教徒的激烈分化製造了極端派與專制勢力可利用的中間偏右政治真空。這個趨勢在希特勒掌權時達到最低潮。
1945年之後,德國的中間偏右在不同的基礎上重建。基民盟遠離極端派與專制派──主要由具備「無懈可擊的」反納粹資格的保守派人物( 像是康拉德.艾德諾(Konrad Adenauer))創立。該黨的成立宣言表明它直接反對舊政權與其代表的意義。基民盟黨魁赫密斯(Andreas Hermes)曾形容斷層規模之大,在1945年評論說:「舊世界沉沒了,我們想要建立一個新的⋯⋯」基民盟提供了德國民主未來的清晰願景:拒絕獨裁體制、擁抱自由與包容的「基督徒」社會。
基民盟也把基本盤拓展與多元化,招募天主教徒與新教徒。這是個挑戰。但是納粹與二次大戰的創傷說服了保守天主教與新教徒領袖們克服曾經分裂德國社會的長久歧異。如同某基民盟地方領袖所說,「天主教與新教徒的密切合作,以前只發生在監獄、地牢與集中營,終結了舊衝突並開始建造橋梁。」當天主教與新教的基民盟新領袖們在1945~1946年創立期挨家挨戶到信徒家,他們實現了即將重塑德國社會的中間偏右新政黨。基民盟變成了德國戰後民主的支柱。
美國在鼓勵基民盟成立扮演了重要角色。所以,美國今天要從這些成功案例學習,幫助搶救自己的民主,真是歷史的一大諷刺。言明在先:我們無意把川普或其他任何共和黨人跟德國納粹畫上等號。但德國中間偏右的成功重建提供了共和黨一些有用的教訓。就像德國經驗,現在的共和黨人必須從陣容裡排除極端派,與川普政府的專制與民族主義傾向劃清界線,在白人基督徒之外設法拓展黨的基本盤。基民盟或許提供了一個模型:如果共和黨放棄白人民族主義並軟化其極端自由市場意識型態,廣泛的宗教保守訴求能讓它建立可以長久的基本盤,例如新教徒與天主教徒,同時也潛在吸引相當數量的少數民族選民。
當然,德國保守主義的重建是在重大災難之後。基民盟別無選擇只能自我翻新。現在共和黨面對的疑問是這種翻新能否在我們掉入更深刻的危機之前發生。領袖們能鼓起遠見與政治勇氣在造成進一步傷害之前重新調整越來越失能的政黨嗎,或是我們需要一場災難才能引發改變?
雖然民主黨不是美國加深兩極化的主要動力,還是可以扮演角色去減輕它。有些民主黨人提議過讓黨專注在重新吸引所謂白人勞工階級,或沒受大學教育的白人選民。這是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在2016年慘遭敗選創傷之後的顯著議題。桑德斯(Bernard "Bernie" Sanders)和一些溫和派強烈主張民主黨必須贏回在鏽帶、阿帕拉契山脈等地失去的藍領選民。許多意見領袖認為,要做到這點,民主黨必須從擁抱移民與所謂「認同政治」的立場退讓──這個定義含糊的詞彙通常包括促進種族多元性,還有最近的反警察暴力倡議,像是Black Lives Matter運動。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的特約社論中,潘恩(Mark Penn)和史坦(Andrew Stein)敦促民主黨人放棄「認同政治」並軟化對移民的立場以贏回白人勞工的選票。
雖然很少明講,核心訊息是:民主黨必須抑制少數民族影響力才能贏回白人勞工階級。
這種策略或許能減少黨派兩極化。如果民主黨要放棄少數民族的要求或把他們放到議題的底層,幾乎確定會贏回某些中低收入白人選民。實質上,黨會回到1980~1990年代的樣子──公共面貌是壓倒性白人而少數民族選民頂多只是次要夥伴。民主黨會名符其實地開始顯得像共和黨對手。而且當他們在移民與種族平等方面靠向川普的立場(意思是,兩者都要削減),他們會顯得對共和黨鐵票比較沒有威脅性。
我們認為這是個餿主意。我們必須極力強調,尋求削減少數民族團體在黨內的影響力不是減少兩極化的正途。這會重演我們國家最恥辱的一些錯誤。美國開國先賢們讓種族宰制保留,最後導致了南北戰爭。當民主黨與共和黨終於在重建失敗之後妥協,他們的和解方式再度以種族排斥為基礎。1960年代的改革給了美國人第三次機會建立一個真正多種族的民主國家。雖然這個任務格外困難,我們非成功不可。如同我們的政治學者同僚丹妮爾.艾倫(Danielle Allen)寫的:
此事的簡單真相就是世界上從未建立一個多種族民主國家,達成沒有特定種族團體占多數、政治平等、社會平等與經濟全民共享。
這是美國的大挑戰。我們不能逃避。
但是民主黨還有其他辦法幫助重新建構政治環境。現今美國黨派敵對的強度反映出不只種族日益多元化還有經濟成長趨緩、所得分配階層下半部的工資停滯、貧富越來越不平等的綜合效應。現今種族色彩的黨派兩極化反映了種族多元性在一段經濟成長趨緩的期間急升(1975年至今),尤其對低收入底層者而言的事實。對許多美國人而言,近幾十年來的經濟變化讓工作越來越沒保障,工時加長,升遷機會減少,帶來社會仇恨升高的結果。憎惡推動了兩極化。所以,克服我們深化中的黨派分裂的辦法之一就是,真正去處理長期被忽視的部分人口的生計顧慮──無論他們是什麼種族。
以解決經濟不平等為目標的政策可能加劇也可能紓緩兩極化,看怎麼安排而定。不像其他許多先進民主國家,美國的社會政策一向很依賴資產審查──只把利益分配給落在某收入門檻以下或符合其他資格的人。資產審查計畫製造出許多中產階級公民認為只有窮人從社會政策獲利。又因為種族與貧窮在美國歷史上有重疊性,這些政策可能帶來種族污名化。反對社會政策者通常用種族指控的措辭反對資產審查計畫──雷根說到用食物券買牛排的「福利女王」或「小富翁」就是個主要例子。 因為覺得受惠者沒資格的認知,福利在美國變成了貶義詞。
相對的,北歐國家拋開僵化的資產審查而採取比較廣泛的社會政策目標模式可能對我們的政局有和緩效果。造福每個人的社會政策──主要例子是社會安全系統與聯邦醫療保險──可能幫助減少憎惡,在美國選民的裂痕間建立橋梁,確保社會支持更長期的收入不平等政策,而又不會帶來種族反彈的話柄。全面的健保就是個明顯例子。其他例子包括更激進的提高基本工資,或普遍性發放基本收入──曾經被認真考慮過,甚至被尼克森政府送交國會的政策。另一個例子是「家庭政策」,這個計畫提供父母有薪假期,補貼雙薪家庭的子女托育,讓幾乎所有人享有學齡前教育。美國政府在家庭的支出目前是先進國家平均的三分之一,跟墨西哥與土耳其差不多。最後,民主黨可以考慮更全面的勞動市場政策,像是加強職業訓練,補貼工資給受訓與升等訓練的員工,高中與社區大學畢業生的在職進修計畫,還有外地員工的交通津貼。這類政策不只可能降低促成憎惡與兩極化的經濟不平等,還可能有助形成一個廣泛、長久的大聯盟,把美國政局重組。
當然,採用政策解決社會與經濟不平等在政治上很困難──部分是因為政策企圖解決的兩極化(造成制度性僵局)。我們對建立多種族大聯盟──包括少數民族與藍領白人的障礙──沒有任何幻想。
我們無法確定普遍性政策會提供這種大聯盟的基礎──只知道這代表比現行的資產審查計畫更有機會成功。不過,雖然艱難,民主黨還是必須解決不平等的問題。畢竟這不只是社會正義問題而已。我們民主制度的健全就靠它了。
比較我們目前的困境與其他國家或歷史上的民主危機,美國很明顯跟其他國家沒有什麼不同。我們的憲政體制,雖然比歷史上其他國家古老又茁壯,仍然可能被其他地方扼殺民主的同樣病徵侵襲。所以到頭來,美國民主要靠我們美國公民。沒有任何政治領袖能終結民主;也沒有任何領袖能一手拯救它。民主是個共有企業。它的命運要靠我們所有人。
在二戰中最黑暗的時代,美國的未來岌岌可危,作家E.B.懷特(Elwyn Brooks White)受美國聯邦政府作家戰時委員會(Writers' War Board)請託撰寫對「什麼是民主?」的簡短解答。他的答案很謙遜但是啟發人心。他寫道:
委員會當然知道民主是什麼。就是走路靠右邊。就是不要推擠的「不要」。就是拆穿繡花枕頭的漏洞;就是高帽子上面的凹陷。民主就是不斷懷疑過半數的民意有過半數的機率正確。就是在圈票亭裡的隱私感,在圖書館裡的共同參與感,到處都有的活力感。民主是報紙的讀者投書。民主是九局上半的比數。是尚未被證明錯誤的點子,歌詞還沒寫壞的一首歌。是熱狗上的芥末與配給咖啡裡的奶油。民主是戰時委員會的要求,在戰爭中某天的早上,想要知道什麼是民主。
E.B.懷特所描繪的平等主義、文明、自由理性與共同目標,是20世紀中葉美國民主的精華。如今不只在美國還有整個工業化西方,這個願景正遭受攻擊。光是恢復逝去年代的自由派民主理想不足以復興現今的西方民主國家。我們不僅必須恢復民主規範,還要把它延伸到整體越來越多元的社會上。這是個嚇人的挑戰:歷史上很少社會能夠種族多元化又真正民主。但是有個先例與希望。100年前在英國與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勞工階級曾被成功整合進入自由民主的制度──幾十年前這種事還被許多人視為不可能呢。在美國,儘管有許多相反的負面預測,早期的幾波移民──義大利和愛爾蘭天主教徒、東歐猶太人──也被成功吸收到民主生活中。歷史教導我們民主與多元化是有可能協調的。這是我們面對的挑戰。歐洲與美國的前幾個世代作出了非凡的犧牲,捍衛我們的民主制度,對抗強大的外部威脅。我們這個把民主視為理所當然長大的世代,現在面臨著不同的使命:我們必須防止它從內部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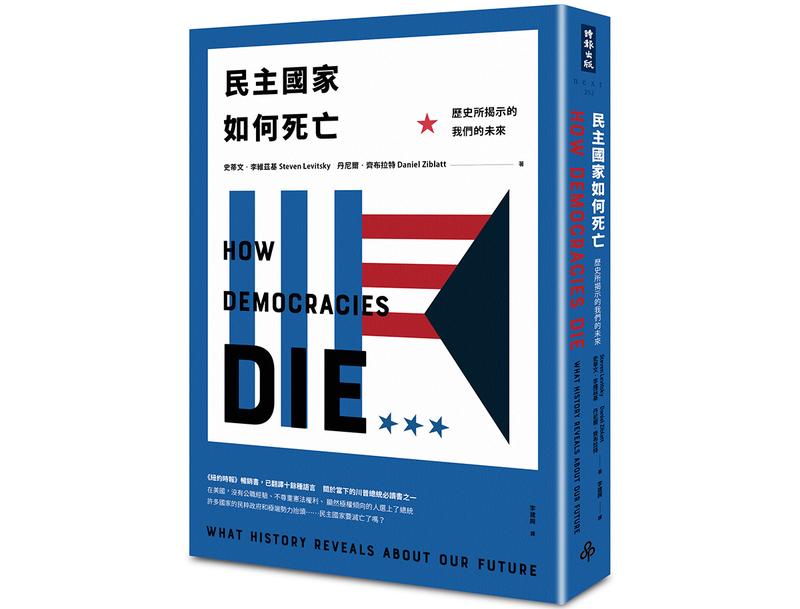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