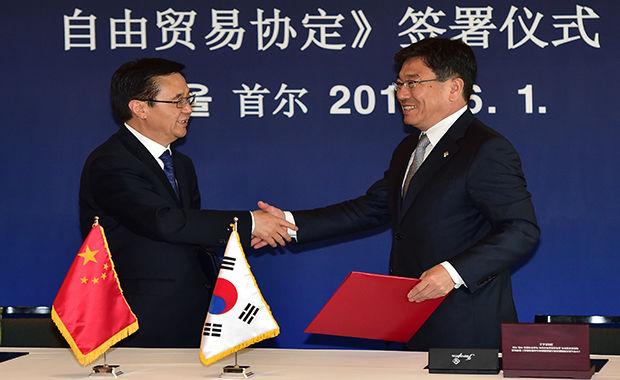台灣是熱衷選舉的國度,1977年的一場桃園縣長選舉,群眾包圍警局、翻覆警車,最後把警察局都燒掉,史稱「中壢事件」。40年前台灣仍處於戒嚴的肅殺氛圍,桃園縣民風保守,脫黨參選的許信良,用短短幾個月就炒熱原本冷感的民氣,也衝破戒嚴的圍籬。40年後許信良重回現場,細說分明。
1977年11月19日投票前兩天,桃園縣長候選人許信良辦完政見發表會後,被群眾簇擁著遊街,鞭炮聲震耳欲聾。
桃園縣救國團在同一條街上,選舉期間國民黨中央黨部整個搬到中壢,駐紮於此。黨政軍聯手大軍壓境,要將脫黨參選的「叛臣」許信良輾成粉碎。指揮作戰的是最了解許信良的人,曾一手提拔他的前長官李煥,每晚開會,傳回來的都是捷報,李煥勝券在握,深信孽徒終將落敗。
這晚,孽徒在街上造勢,李煥領著工作人員下樓吃消夜,空氣中滿是煙硝味,越走心越慌,眾人的腳脛皆被淹沒在鞭炮屑裡,低頭不見鞋子,放眼望去,街道彷彿一片紅海,李煥神情凝重,不發一語。
大勢已去,但不用怕,黨還有最後一招必殺絕技。1975年,宜蘭黨外陣營領導人郭雨新競選增額立委,選前聲勢浩大,卻不敵選舉當天的作票,投給郭雨新的「廢票」高達8萬張,有著鋼鐵意志的郭雨新也不敵作弊,心灰意冷下遠走海外,客死異鄉。
2年後桃園縣長選舉,黨故技重施,卻有截然不同的結果,作票者被民眾活逮,扭送警局,卻被縱放,民眾不服,聚眾包圍,翻警車燒警局,史稱「中壢事件」。桃園多眷村軍營,是黨的鐵票區,鐵票加作票,許信良還是贏了,大勝國民黨提名的歐憲瑜近10萬票。
「即使作票,我都有辦法贏他啦,我信心滿滿。」76歲的許信良重返「中壢事件」現場,和我們講起40年前的往事,他急促激昂的語氣,躍動的手勢,彷彿是昨天才剛當選的新科縣長。他頂著招牌大光頭,臉上皮膚光滑如剛剝殼的水煮蛋,沒有一絲皺紋,不老的祕方,其實也不用多問,談政治,談選舉,談理想,就能讓許信良瞬間回春。
脫黨之前,許信良一路根正苗紅,就讀黨校政大政治系,大一就入黨。26歲時拿中山獎學金到英國讀碩士,兩年後回國在中央黨部工作,和同在黨部上班的張俊宏喝咖啡聊出一篇〈台灣社會力分析〉,登在《大學雜誌》,引起廣大迴響,蔣經國要求黨團詳加研讀。32歲,許信良經由李煥薦舉,披上黨之戰袍,當選省議員。
在省議會,黨籍省議員發言前都須先報備,1968年在歐洲經過學潮洗禮的許信良根本不甩,為了隨賦徵購稻穀政策(國家強制以低價徵購農民的稻穀),出身農家的許信良和黨徹底鬧翻,「我發了瘋似地反對,在省議會一個人杯葛,國民黨說我比黨外更黨外。」
省議員的任期原本是4年,為了配合縣市長選舉,那一屆延長成5年,第5年正是1977,「最後一年是多出來的,我就拿來寫《風雨之聲》,回顧我4年的問政。」忠貞黨員皮囊下的壞孩子至此原形畢露,不但搞破壞,還要留下紀錄。此書讓國民黨省議員群起圍剿,罵許信良「流鶯」(「留英」諧音),卻因此博得媒體版面,《風雨之聲》一炮而紅,盜版達十幾萬本。

1977年底的桃園縣長選舉,按桃園政壇往常兩大慣例,南北區輪替及省議員出征,這屆輪到南區當縣長,本該由國民黨的中壢省議員披掛上陣,許信良如果乖乖聽話,提名早是囊中物。無奈壞孩子已破繭而出,「國民黨當然不會提名我,他們提不提名都一樣,我很早就說我一定要選。」
1977年,當年25歲的張富忠是國立藝專美工科大專畢業生,也是中壢人。2年前的立委選舉,為了向朋友證明選舉的荒謬,「我拿妹妹的身分證去投票,居然也可以!」張富忠因為認識許信良的侄兒而參加選戰,負責海報設計。當時像他這樣的年輕人還有林正杰、賀端藩、范巽綠等人,他們大多在1975年曾替郭雨新助選,雖不敵作票,但餘燼中仍有星星火苗閃爍,春風吹又生,延燒到2年後的桃園選戰。
20來歲的都市年輕人來到中壢,搭帳篷埋鍋造飯,彷彿大學迎新宿營。年輕人和當時也不過36歲的候選人,主張將選戰定調為輕鬆愉快的嘉年華,一拍即合。空地上的競選總部,由許信良的農家親戚徒手搭棚,花費低廉,又有新意。氣球飄起來了,和平鴿飛向天際,台灣選舉史上第一首競選歌曲也誕生了。
許信良說:「我是學政治的,研究國外選舉的戰術,決定要用競選歌曲,有位助選員對音樂有興趣,建議不用額外作曲,而用人人琅琅上口的〈四季紅〉做曲調,再填上詞。」
十一月,時正當;大家來選咱的人。 咱的幸福久久長,心情真輕鬆! 許信良,做人不相同,敢擔當,肯幫忙; 縣長選伊有希望。
1977年代久遠,讓我們來到1994,陳水扁擊敗勁敵趙少康的首次台北市長直選,陳水扁的競選歌曲是街頭巷尾傳唱的〈春天的花蕊〉,完美複製許信良經驗。不僅於此,「快樂・希望・陳水扁」的文宣主標語,與1977年許信良海報上的「新精神・新人物・新桃園」,都是10字以內的「一句話」文宣,也有似曾相識之感。
簡潔有力的口號,勝過長篇大論的政論。許信良引入美國總統選舉中的「一句話」文宣,而對手歐憲瑜的文宣重達1公斤,每一種都寫滿十幾二十項政見,塞滿密密麻麻的蠅頭小字。
後來也選過國大代表的張富忠說:「1977年許信良選舉的造勢晚會、宣傳車、競選歌曲等競選手法,影響深遠,今後台灣的選舉模式雛型,在此建立。」
選戰剛開始,並非那麼順利。黨的輔選鋪天蓋地,甚至動了後備軍人的主意,主導軍中政戰系統的王昇,大規模教召桃園的後備軍人,每次都是上千人,來聽罵許信良的演講。年輕助選員很沮喪,林正杰、張富忠頻頻問許信良,該如何是好?
許信良要大家別慌,說起《三國演義》的故事。西涼馬超起兵造反,聲勢驚人,曹操變裝逃亡後,決定堅守陣地,不出寨迎戰。不斷有情報來說馬超增兵,曹操樂得喝酒,士兵都很納悶。最後一役讓馬家軍潰敗,事後曹操才說,如果馬超一開始打敗跑回西涼,反而很麻煩,因為回到邊疆地盤,就很難消滅他,終成大患。反而讓他打勝仗,不斷從西涼增兵過來,就可以一舉殲滅。
「國民黨就像幫我們增兵一樣,把後備軍人找來,罵我給他們聽,也是幫我宣傳嘛!他不教召的話,靠我們宣傳,要影響這麼多人是很難的。這些人已經對你產生好奇,準備聽你怎麼反擊。我們最後一戰一次宣傳,就可以改變他們。」
童年時許信良就將一本《三國演義》翻得滾瓜爛熟,日後讀政治系,出國留學,左手援引西方政治理論,右手使出三國兵法,西洋劍與偃月刀他同樣能耍。他是帶兵的將軍,也是制定謀略的策士,選舉初期,他還要身兼開車的司機,他花了半年時間,載著張富忠、林正杰這些年輕小老弟,到鄉下發書。
「鄉下人聚集的雜貨店,我一次放10本《風雨之聲》在那裏,《風雨之聲》談的就是農民的問題。看到有人在種田,我走進田中央給他一本。後來鄉村人都開始討論,許信良居然自己來送書。」
以鄉村包圍城市,是許信良的策略之一,在戒嚴的肅殺氣氛下選舉,許信良一方面完全不強調「黨外」的悲情,將選舉定調為:「輕鬆、愉快」而非「恐怖」的事。另一方面,城市人做生意怕得罪人,較不願意表態支持,而鄉下人個性直爽,一認定就相挺到底,許信良需要以鄉下人的熱情,來融化戒嚴的冰封壓抑。
在中壢市中心的競選總部成立後,11月正是二期稻作收割時期,農人卻放下鐮刀,天天都來,本來較為畏縮的城裡人,看到空地上每天有人聚集,一傳十十傳百,於是也以一種看熱鬧的心情,通通圍上來了。
1977年王派然剛滿20歲,等當兵的空檔,他在市場幫忙父母賣菜。有一天他看到許信良的宣傳車經過,攤販們紛紛把豬肉、魚、青菜往車上丟以示支持,「車子經過一趟,就全部載滿了。我太好奇了,就跑去競選總部看熱鬧,居然還煮飯給人吃耶。」
張富忠說:「有天晚上許信良在桃園市演講,講完下一場在中壢,桃園市的群眾居然全部跟過來聽。宣傳車在街上,民眾蜂擁過來,丟錢丟水果,很瘋狂。」
投票前三天,許信良集中火力在「防止作票」。張富忠用美術字體寫下大字報:「只有共產黨才作票!」「作票是匪諜,發現作票立刻喊打!」以許信良的縝密布局,不能只有口號而已,早在幾個月前,他已讓遠房親戚許應深訓練一批監票部隊。桃園共369個開票所,每個開票所需要3個人監票,總共需要1千多名監票員。

2年前的郭雨新選舉,同樣有監票的規劃,但當時就發生監票員邱義仁被毆打的事件,即使這次配置3個人,要如何以寡敵眾?
40年後,許信良說出他的錦囊妙計:「最初群眾會說,支持你有什麼用,國民黨作票你就輸了。我跟群眾說我一定會贏,怎麼贏先不能說,嘿嘿嘿,選前最後三天,我才跟他們說,投完票你們不要走,留在投票所等開票,幫助我們的監票員。」
勝選的關鍵是更多「監看的眼睛」。其中一雙是牙醫邱奕彬,11月19日他在中壢國小排隊等投票,看到選務人員也是中壢國小校長范姜新林,走進圈票處,將兩位老人家已圈好的選票塗毀。范姜新林被群眾扭送到國小正對面的中壢分局,邱奕彬也跟著去作證,然而檢察官沒有偵訊范姜新林,反而讓他離開,回投票所繼續工作。
這一天的作票當然不只這樁,到處都傳來,和以往不同的是民眾敢於挺身而出的態度。上午檢查官將范姜新林縱放的消息,已經傳得沸沸揚揚,到了下午2點,范姜故技重施,又被民眾逮到,趕來的警察圍起人牆保護范姜躲進警局,徹底激怒民眾。
沒多久,中壢分局外面已經萬頭鑽動。儘管競選幹部如林正杰都被找來現場勸離群眾,是巧合也是歷史的機遇,中壢分局的幾支擴音器均壞掉不堪使用。
張富忠趕到中壢分局時,群眾正開始丟石頭,像下石頭雨一樣,把警察局的玻璃窗砸得一片不剩:「我到分局裡,看到警察有如喪家之犬,已經在收拾東西要從後門溜走。」張富忠回到競選總部後,被告誡不准再去現場,以免節外生枝,但他忍不住又捉著相機回去拍照,在警察局對面的樓房上,為中壢事件留下唯一的影像紀錄。
鏡頭下,人群密密麻麻彷彿螞蟻雄兵,一輛輛警車被翻得底盤朝天,彷彿黑色甲蟲難得露出脆弱的肚腹。
更晚一點,警察投擲催淚彈驅散民眾,民眾散去又聚集,聽聞有大學生傷亡,便開始點火燒警車,到了午夜,把中壢分局都燒掉了。
王派然說:「我傍晚才知道中壢分局前發生事情,想去看熱鬧,但已經擠不進去。那天中壢像是無政府狀態,街上人非常多,因為人多,所以不會感到害怕。」
當中壢鬧翻天,下午4點,許信良搭朋友的車北上,「擒賊先擒王,當時中壢有很多特務,我不離開的話,一定馬上被控制住。」在縱貫線上,許信良看見從台北下來的鎮暴警備車,與之錯身而過。
螞蟻雄兵翻警車、燒警局的那個晚上,沒有人知道蟻王許信良在哪裡。遠離騷亂現場,許信良在台北找了一家三溫暖,人們都關心選舉去了,裏頭空蕩冷清,他睡了久違的一場好覺。「醒來到朋友家,電視上播報都跳過桃園縣,印象中到了凌晨1點,才宣佈我當選。」
隔天一早,上班時間準時9點,許信良主動出現在台北市警務處(警政署前身),說要找警務處長,「我整個晚上不見蹤影,突然出現,把他們都嚇壞了,我跟處長說,群眾心理學有個說法,群眾只有13歲,13歲的人沒有行為責任,希望不要擴大鎮壓、秋後算帳。」
事件當天晚上,往中壢的道路都封鎖,軍隊也進駐,據說當時的行政院長蔣經國搭著直升機,在上空盤旋巡視。年紀比較長的人,還記得30年前的228發生什麼事,早早就熄燈拉下鐵門。清晨,除了被燒毀的警車與警局,以及傳說有2個大學生傷亡,徹夜瘋狂的群眾回到被窩裡補眠,原本預期中的鎮壓,並沒有發生。
秋後算帳在一個月後,但不算太厲害,檢察官起訴見義勇為的證人邱奕彬「偽證罪」,疑似作票的范姜新林則是不起訴處分。隔年1月,邱奕彬被判處有期徒刑1年半,緩刑3年,邱奕彬不服提起上訴。
許信良在中壢事件隔天才來到事發分局,「我去跟警察握手,他們看到我都頭一歪,還有人吐口水。但他們不能拿我怎麼樣,我已經選上縣長了。」
真正的天羅地網,稍慢,還在後頭。
受到桃園縣長選舉大勝的鼓舞,1978年的國大代表以及立委選舉,更多有志之士投入,黃信介等人組成「黨外助選團」全省助選,氣勢如虹,然而在投票前一個禮拜的12月16日凌晨,台美斷交,選舉被迫中止。
真正的秋後算帳在1979,蔣經國接任總統這一年。年初由余登發父子被捕揭開序幕,許信良主張前往聲援,因為參與「橋頭事件」遊行,許信良被省政府以「擅離職守」罪名移送監察院,6月底,就職縣長1年半的同時,公懲會宣布許信良「休職2年」。只因曠職1天,辛苦拚來的桃園縣長,被迫提早謝幕。
1979年底發生美麗島事件,許信良說:「美麗島被捕的人,幾乎都是第2年(1978)參選或助選的人。」美麗島的鎮壓風暴,早在1977年的中壢事件,蝴蝶就先搧動了翅膀。而被判「偽證罪」的邱奕彬,2年前的帳還沒算完,美麗島事件當天,邱奕彬並沒有去高雄遊行,但美麗島大逮捕有他,關押後對他的刑求也特別慘烈,一度咬舌自盡。
「2年的時間,鎮壓的工具,國民黨都準備好了。」許信良說。
1977年選後由林正杰、張富忠合寫的《選舉萬歲》,紀錄中壢事件的完整過程,其中有一段:
「群眾的拳頭,像雨點一般地落在警察的小圈子上,警棍和拳頭互有斬獲。然而雙方的眼神顯得有些恍惚,動作都非常生硬,非常彆扭。拳頭沒有握緊,警棍也打不結實,好像雙方都是從來沒打過架的人似的。群眾似乎還在猶豫,像警察這樣之威權,真的是打得的嗎?而平時不把老百姓放在眼裡的警察,在初次面對團結而憤怒的群眾時,也有了一份不可克服的畏懼。」
群眾的拳頭從遲疑到堅定,警察的表情由肅殺到畏懼,這段生動的現場描寫,正是從戒嚴到民主,那條隱微的分界線。
20歲的菜販王派然,在中壢事件中受到民主啟蒙,80年代的黨外運動,他不是捐錢就是送便當,無役不與。如今來到耳順之年,菜販變成營造公司總經理。他回想年輕時的第一場「運動」,直呼好幸運,遭遇了不得了的一件大事:「居然可以這樣!台灣原來也可以這樣喔!」
(閱讀英文版,請點: Prelude To A Storm: The Zhongli Incident, 40 Years Later。)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