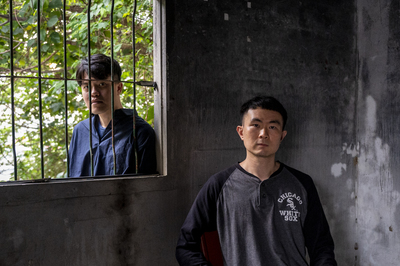十年磨一劍,戲情長片《大佛普拉斯》及《同學麥娜絲》,分別在2017年及2020年獲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最佳新導演,及觀眾票選獎的導演黃信堯,早年以紀錄片導演身分聞名影壇。2002年《多格威斯麵》跟拍爭議人物柯賜海,探索媒體現象;2005年《唬爛三小》記錄老同學生活逸事,背後埋藏一段傷心轉折,亦是《同學麥娜絲》的創作原形。
前期從人物故事反思創作意義,創作中期往地景之間漫遊,雲林口湖鄉《帶水雲》(2009)、日本與那國島《雲之国》(2015)、台中新社《印樣白冷圳》(2018),已不再聚焦特定人物,轉而關心土地本身的聲音。今年他以跨越12年拍攝的紀錄片《北將七》,入圍第13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台灣競賽片。這部紀錄片中,黃信堯記錄台南「北門、將軍、七股」三地的影像故事──綠電開發計畫即將永久改變當地人文地貌,身為台南人的他,用鏡頭帶著觀眾走進時間封存的家鄉。
2008年,黃信堯到雲林口湖鄉拍《帶水雲》,以流動的影像風景畫,帶入地層下陷議題。拍攝紀錄片的日子,從台南七股開車,走台61線(西部濱海快速公路),路途經過將軍、北門、布袋、東石,最後才會到口湖。從七股到口湖之間來來往往,黃信堯起心動念,拍攝自己的居住地。隔年 8月,《帶水雲》拍攝結束之後,黃信堯便開始籌備拍攝《北將七》,以「北門、將軍、七股」三地為題,展開對家鄉的拍攝計畫。

什麼是家鄉?「當我開始拍攝《北將七》的時候,我其實才在七股住了4年,」黃信堯回憶,自己直到2005年拍完《唬爛三小》,才舉家搬到七股定居。「我從小到大,搬過20幾次家。小時候在台南市區來來去去,之後來台北念大學,也搬了好幾次。直到搬到七股,住了17年。」在他小時候的記憶,搬家是生活常態,直到在七股買地、蓋房子,才對七股有感情──這裡或許是自己會長期居住的地方。
「我的家鄉在哪裡?」年輕時,黃信堯常在想,自己是台南人,但對不斷搬家的自己來說,家鄉具體上是在哪裡呢?從對城市的概略想像聚焦,在七股生根落地之後,他萌生想法,可以用攝影機關注「家鄉」的生活樣貌。
「早期概念非常抽象,我中間拍其他片子,過程不斷被影響、也常停下來思考,該怎麼繼續拍,」黃信堯自承,自己不是計畫縝密的創作者,常常需要靠直覺判斷。在2015年,黃信堯走訪日本與那國島拍紀錄片《雲之国》,他形容,自己當時對於拍攝一籌莫展,直到打開心靈的雷達,聽見與那國島與他對話,才順利完成作品,「島嶼有很多委屈,想要訴說,卻沒有人聽見。對我來說,當時是那座島在告訴我,該怎麼拍電影。」
這樣的創作想法,在《北將七》依然成立。「電影一路拍了12年,我感覺『它』會告訴我怎麼拍,但我很難講『它』是誰,可能就是北門、將軍、七股這片土地。」黃信堯相信,萬物皆有靈,只要將自己的身體投入當地,頻率契合,就能聽見土地的聲音。

「你在幹嘛?」 「沒啊,看人家收牛蒡。」
180分鐘的《北將七》,是台南一幅悠長平和的活動風景畫,黃信堯記錄時光緩慢流動的日常,還有在地人的生活步調,理所當然,也有他觀察當地人文活動的個人趣味。電影中的片段組織,多半來自隨興所至的有感而發。
「有天,我開車經過台17線省道,看到有7、8個人在某地聚集。第二天,我又開車經過,發現同一個地方,人數變成幾十人,我當下就感覺很有趣,想知道他們在幹嘛,開車折回去,原來是一群賞鳥人,他們發現稀有的蜂鷹在當地出沒⋯⋯。」
之後,這群賞鳥人的閒話家常,就被剪進作品當中。黃信堯說,自己與拍攝對象大多是萍水相逢,也有些人看到他在當地拍攝,就主動跑來與他搭訕。
電影開場,有顆兩分鐘的長鏡頭。一個人從遠處慢慢走來,快要抵達攝影機所在位置,卻又原地折返,走回漫漫長路的另一端。談到這顆鏡頭,黃信堯笑說,他當初也是一頭霧水,只是遠遠看到一個男子在荒涼處走動,讓他產生好奇心,至於為什麼那人最後調頭折返?「因為我的攝影機在拍,看到攝影機,他就往回走了。」
在創作早期,他會將這些「攝影機與拍攝對象發生互動」的鏡頭剪去,直到後來,他慢慢覺得,就算自己是在地人,但當他以拍攝者身分來到現場,就永遠是外來者。於是,他不再避諱攝影機存在,保留互動瞬間,還有被攝對象跟攝影機的關係。
「直到現在,我其實也不知道那個散步者是誰,」黃信堯笑說。
以幽默趣味與荒謬人生、環境相對,一直是黃信堯電影裡鮮明的風格。《北將七》一景,是路邊的芝麻田,上面插了數支候選人的競選旗幟,黃信堯解釋,這些旗幟是用來趕鳥,類似稻草人,風一吹動,旗幟隨風飄揚,鳥就不敢下來吃農田裡的芝麻。他自承,這就像《大佛普拉斯》片段,副議長的帆布海報,最後蓋在菜脯家漏水的屋頂。選舉結束之後,道具被拿來廢物利用,也成為窺看台灣政治文化的一扇小窗。
拍劇情片跟拍紀錄片,有什麼不同?黃信堯談到,自己如果是學劇情電影出身,可能就不會拍出《大佛普拉斯》,自己在電影中使用旁白的方式,也不是來自「正統的」電影想像,「創作會互相影響,譬如布紐爾(Luis Buñuel Portolés)早期的《安達魯之犬》(Un Chien Andalou,1929),比較像實驗電影,非常先鋒,可以影響未來更多電影創作。」美學很重要,黃信堯認為,創作不能只談議題不談美學,他用紀錄片創作經驗,影響自己對劇情片的拍攝,但談到個人美學的最大期許,他希望能夠永遠「保持不同」。
黃信堯提到,他與每一個領域都有距離感,很難用任何一種身分來界定自己。「拍劇情片其實滿辛苦,因為我沒有真的學過,我的個性又比較奇怪⋯⋯,」他笑談,拍攝劇情片,許多事是由監製鍾孟宏在張羅;而現在的自己,雖然也還在進行紀錄片創作,但與「紀錄片圈」似乎也有點疏離。
談創作理想,黃信堯更希望自己能成為跨越不同媒材的藝術家。他提起台灣行為藝術家謝德慶的行為藝術作品《打卡》(1980-1981),以一年為期,每小時打卡一次,一天打卡24次,微小的行為,極端實踐之後可能自成意義。黃信堯說,自己不想只停留在劇情片與紀錄片的世界,他近年開始嘗試表演,未來若有機會,也希望去拍VR、XR,甚至挑戰行為藝術、裝置藝術。「我希望,創作本身能先於媒介,」黃信堯表示,希望自己突破框架,不受限於電影導演身分。
黃信堯也朝這個方向開始嘗試各種可能,正與製片人蔡之今合作,製作《北將七(三頻道)》版本,用三面銀幕同步放映,預計在美術館展出。「我希望三頻道版本,跟單頻道版本能夠互相對話,三面銀幕同時播放,對我來說,像是一個對夢境的想像,跟單頻道效果不同,」黃信堯提到,單銀幕的播放像是眼睛所見所聞,但三頻道放映,可以更實現自己心中對創作的感受。
將《北將七》帶進美術館,對黃信堯而言,是希望讓電影像是一個時間切片,觀眾進來、觀眾離開,可以看30秒就走,也可以看完3個小時。「就像是你今天去宜蘭玩,看到一位農夫,你跟他聊聊天、看他種菜,之後你會離開,但那個時間點,你就在那裡,」黃信堯認為,這個過程是自由的,就像旅行、像是生活的片刻。
旅行不只局限在北將七,電影最後,黃信堯在片尾字卡放上2012年5月拍攝的超級月亮,問起原因,他說:
「你不覺得很漂亮嗎?如果有機會,我也想去月亮上面旅行。」
12年的拍攝跨度,《北將七》最後收束於光電板的開發計畫。黃信堯提到,不同於北部建設快速、地景變化樣貌大,台南生活步調轉變比較慢,拍攝的過程也較少感受時間流動。最後決定結束《北將七》拍攝的轉捩點,來自近年太陽能光電板進駐台南的開發計畫。
「發展太陽能,大家會說比較環保,但它與當地農業發展其實是衝突的,太陽能板需要清潔,清潔劑會影響農田往後的使用。」談到綠能議題,黃信堯心情複雜,太陽能發電是對環境傷害較小的發電方式,但到頭來,它對台南的地貌影響仍然是難以回溯的。
地景地貌開始有明顯轉變,政府推動荒廢農地裝置太陽能板之外,很多民間人士,也開始自發在農田裝置太陽能板,「廠商紛紛進來遊說,現在也可以看到光電公司的人,在那裡跑來跑去,」對於當地人士的反彈聲浪,黃信堯的態度也比較無奈,「這件事的發展方向不太可能扭轉,很難有社會輿論支持他們。」話鋒一轉,他認為,對於台灣優惠工業發展的能源政策,若沒有從源頭檢討,在當下只能看到狹隘面向。
電影最後,也有一段空拍鏡頭,記錄下台南景色,還有太陽能板進駐之後的農地樣貌。黃信堯在本片與《捕鰻的人》聲音設計師澎葉生(Yannick Dauby)合作,用空拍機飛行時自然發出的機具聲音,設計電影尾段的空拍鏡頭,保持電影中不採用配樂的想法。「一般空拍畫面都會用配樂,我原本想過用其他現場音效代替,但是Yannick認為直接採用機器本身的聲音即可,我就放手交給他去做。」因此創造出電影尾段在聲音呈現方面的特殊設計。
除了綠電影響之外,黃信堯談到在2021年去世的父親,還有失蹤的愛貓「喵b」,表露出多幾分感性,「貓失蹤之後,我找了很久,甚至還有媒體朋友幫我轉發,但都沒有結果。」訪談過程始終語氣輕鬆的黃信堯,在談到愛貓的時候,流露不加掩飾的別離傷感,「很難過,沒辦法再帶他出去玩。片子裡也有喵b的畫面。」
父親離世,愛貓失蹤,黃信堯提到,時間點剛好吻合,確實帶有一點感傷。人事已非,北門、將軍、七股三地也因開發進程,地景變化不同以往,但黃信堯強調,《北將七》終究只是他自己的主觀採集,他的走訪、他的選擇,沒辦法做為保留生活樣貌的完整呈現,「它不能完全吻合一個印象,思考這件事情也是沒有意義的。這就是作品,它只能是這個樣貌。」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