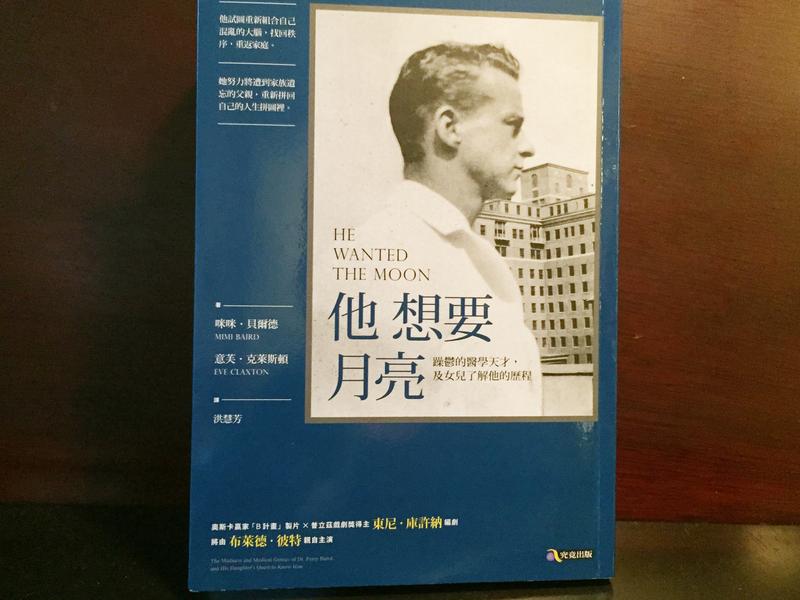評論

剛好是十年前的9月,蔡明亮攜《郊遊》(2013)於威尼斯影展向媒體宣布,這是他首部數位影片,更公開表示這應為其創作的最後一部劇情長片,未來將專注於更具藝術性的創作成品。過了十年,這位縱橫影壇卅年的電影巨匠不啻馬不停蹄地上街賣票宣傳長片《日子》(2020),還有他第3度在北師美術館舉辦的個展「蔡明亮的日子」(2023)。十年期間,蔡明亮的創作能量絲毫未因停拍劇情長片而減少,反而更多面地由短片、劇場、繪畫至展覽拓展開來,甚至意外催生了第11部實則從紀錄素材逐步轉化而出的劇情長片。
對《郊遊》之後的蔡明亮而言,影像創作再也無關編劇,而是和生活緊密相連,讓尋常成為影像。當初聲稱再也不拍劇情長片的他,由於遭逢李康生於歐洲巡演《玄奘》(2013)前竟忽然血栓導致小中風,導演一邊陪伴在側照料演員,一邊開始用照相機與攝影機記錄小康長期接受治療的過程。一年多後,東京的冬季又讓赤腳行走拍攝《無無眠》(2015)的小康歪脖舊疾再犯,讓他不得不再次接受漫長的中西醫療程。2015~2016年間,蔡明亮有次去曼谷旅行,在美食街偶遇亞儂(Anong Houngheuangsy)。年輕的亞儂是一位從寮國到泰國打工的非法勞工,蔡導跟他要了「微信」,回台後經常與他視訊聯繫,尤其被他記錄燒飯煮菜與朋友聚會等生活影像吸引,故決定到曼谷拍攝這位寮國移工。
值得強調的是,不管是生病與治療中的李康生,還是在異鄉打工的亞儂,蔡明亮對他們的拍攝,一開始即設定於影像紀錄。這批小康在新店山上養病的日常畫面,最早被香港音樂家梁基爵投映在結合音樂與影像表演《一零》(2016)的巨大銀幕上。而這些由蔡明亮手持攝影機拍攝的影像素材,得等到導演深感小康與亞儂兩位處於不同時空的人,無不分別被身體與生活給牢牢地困住時,才有進一步發展為劇情影片《日子》的想法。因此,片中關乎兩人在曼谷旅館中,亞儂為小康按摩與愛撫的性愛段落;兩人於粥店餐廳的晚餐;亞儂夜市的擺攤、離別後各自的生活段落(包括片末亞儂在公車站的等待等場景),皆屬為了順應紀實影像素材的邏輯而展開虛構情節的結果。

《日子》先「捨虛求實」,花了數年記錄亞儂與小康異地生活記事,後「以實為虛」,虛造他們之間短暫的邂逅之緣與生活片段,就影史發展脈絡而言,一方面與戰後胡許式(Rouchian)的民族誌虛構影片(ethnofiction film)互通聲氣;另一方面,又進一步對於鮑德威爾式(Bordwellian)的亞洲極簡主義(Asian Minimalism)電影之說進行擴寫。
《日子》虛實交錯的敘事,簡直和胡許(Jean Rouch)的《我是黑人》(Moi, un noir,1958)此類糅雜虛實之傑作使了個眼色,尤其是蔡明亮將小康與亞儂兩人同時無事發生(nothing happens)又永不落空(much more than nothing)的生命情狀,在奠立於長時間記錄的前提下,因勢利導,從中擬構劇情走向,又將長達數年之多、為數可觀的影像素材進行裁剪與配置,達至巧妙匯融段落鏡頭與蒙太奇的雙重美學。
蔡氏第11部劇情長片絕不可忽略的另個關鍵,與其當屬手工業的電影製作模式息息相關。如今,蔡明亮捨棄大規模劇組的拍攝型態,《日子》到香港與曼谷拍攝只由製片、攝影師、收音師及演員等區區幾位成員組成;相比當前台灣影片動輒數千萬新台幣的製作規模,本片預算甚至低於千萬。然而,劇組與預算規模僅為蔡明亮與當前台灣電影產業格格不入原因之一,其奠基於數位成像的獨立製片如何將即興與再現、紀實與虛構組裝為另類敘事,恐怕才是造成他致命不適感的主因。
如果蔡明亮的電影素來因側重角色的日常和私密活動、被抑制而非表達的感情、鬆散的情節結構,及要求觀眾關注細節的長拍鏡頭等特定風格,而被冠上亞洲極簡主義電影,《日子》則分別在拍攝上採取減化(數人的劇組編製);故事上著重儉樸(以形式簡單與透明的紀實推展劇情),風格上選擇剪法(在海量影像素材上展開蒙太奇同時裝配段落鏡頭),藉此蘊含出一種能在論題、敘事和體制上展開差異認同且開創新猷的新極簡主義影片(neo-minimalist film)。
耗時多年的《日子》完成並發表於新冠肺炎侵襲全球之前;至於歷經3年的疫情,才再度進入美術館的影片展覽「蔡明亮的日子」,嚴格而言,不該將其定位於如同先前的「來美術館郊遊」(2014)或「無無眠」(2016)兩檔展覽,為蔡明亮單一影片或系列作品展陳的補充,而應進一步視之為《日子》作為美學表述、乃至電影藝術系統的擴充,「日子」的多變意義為箇中通關密語。
展場共3個樓層,每層的展件與題旨之間的關係各有不同,彼此相互對話。地下展間與影片《日子》緊密相連:白牆上輪播投映著5組影像,部分是小康於歐洲病倒,導演為他按摩、小康接受煙灸、打針、養病、逗貓、散步、睡覺與亞儂講手機等紀錄,有的則是新店住家廢墟景象,也包含拍攝於疫情期間,且發表於巴黎「取經」個展的短片《身在何處》(2022)。投映影像的珍貴之處,在於有一部分為最後未被剪入《日子》的素材,這些日後構成劇情的日常生活,既為兩位角色的真實生命,亦作為毛片。
二樓可看作《日子》的延續:靠白牆的一側布滿一張張藝術家高俊宏表演《玄奘》時用炭筆畫上高僧之夢、蜘蛛與大自然景物的大白紙,連綿不斷,形成曲線高低起伏之形,連帶地亦有揉成一團團、但未上牆的紙張散落幾處,極富雕塑感。而靠玻璃帷幕的另一側,《玄奘》炭筆紙鋪滿地上,正對面的白色高牆上正好高懸掛著畫有126張影院座椅的巨大圖像。這兩側的炭筆紙上,蔡明亮不是擺放了各種各樣的物件(小音樂盒、皮箱、金童玉女頭像、微型雕像、小玩意兒、容器、獎座、檯燈、屏風等),就是在其周邊錯落著曾於「河上的月色」(2010)裝置概念展展出的多幅椅形畫作和收藏的老椅子,還有在疫情期間因思念小康與亞儂而作的畫像、小康多年前的油畫習作、時鐘及盆栽植物等。不時,亞儂唱著泰語及寮語的歌聲隱隱約約傳出,迴盪在寂靜且透光的展廳。
登上三樓,映入眼簾的是前述曾展示於威尼斯藝術館劇院的一大張白紙,上頭畫有各種電影角色;牆上則一一掛著蔡明亮署名「電影記憶系列」的作品,畫著《不散》(2003)戲院與放映師的海報、小時候住的七層樓、外公與5歲的自己,及兒時常去的鵝殿(Odeon)大戲院等。走到三樓盡頭,兩面牆垂落黑鴉鴉的紙,上面塗滿各種無以名狀的圖像,還密密麻麻寫著華語老歌的歌詞。這是2019年蔡明亮到香港舉辦「良夜:蔡明亮的電影、音樂交流與即興創作」時導演與亞儂一起創製的產物,而當年恰逢「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導演臨時起意拍攝的短片《良夜不能留》(2021)即以液晶螢幕輪播。展場中,這兩張偌大紙張,一邊擺著一個玻璃外型的銅櫻花獎與古董真空管收音機,另一邊則是好幾個《臉》(2009)的電影箱子與好幾個膠卷拷貝。鄰接的牆面,則貼上《你的臉》(2018)的劇照彩繪。走到三樓向外延伸的平台上,蔡明亮擺設了一幅多年前向畫家奚淞習畫的作品、顏料與畫具。駐足之際,除了佩妮演唱的老歌〈良夜不能留〉(1948)時而響起,還會聽到蔡明亮布展期間為每幅作品在牆上寫下文字時哼唱老歌的歌聲,忽遠忽近,忽隱忽現。
基本上,由地下室至三樓,在這些形態不一且樣態多變的展件,藉由「日子」和「電影記憶」彰顯出展覽命題。關於前者,當屬蔡明亮對於《日子》由一開始記錄小康與亞儂的影像至歷經疫情結束為止的圖文書寫。至於後者,即主要由《臉》的檜木箱子以降,歷經「河上的月色」裝置概念展、《玄奘》炭筆圖像、《你的臉》肖像彩繪、圍繞《不散》4K修復版首映於威尼斯影展而發展出的各類大小畫作,及拍攝於香港「反送中」期間的《良夜不能留》。
若將這兩者統合起來思辨「蔡明亮的日子」,一方面而言,意外的長片固然說明了這位在《郊遊》之後或許再也無心投注劇情影片的導演,既以實探虛又以虛襯實的手工業技藝,徹底地透過與生活水乳交融的電影,成就藝術無所不在且無時不在的理念,為其所處的電影時代展現一種截然不同的開放性;另一方面,由《不散》至《日子》,小至一個早已不合時宜的可觸膠卷,大至張貼於白色高牆上一張繪著紅通通百張影院座椅的畫作,蔡明亮意欲藉此體現過去十餘年以來其影像藝術與跨界實踐的追求,不言自明:當電影繁華落盡之際,美術館成為錯身而處的導演最好的藝術庇護所。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