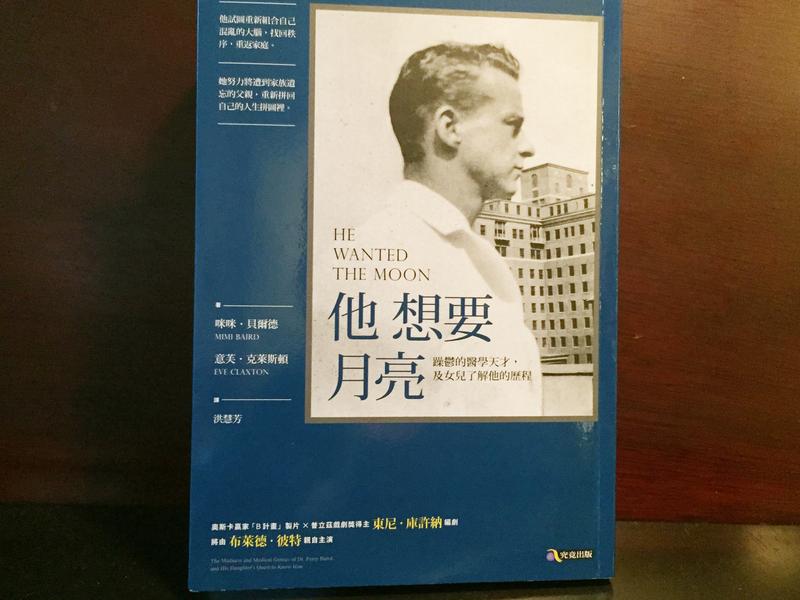13張臉在大銀幕逐一浮現,那是一段平靜卻讓觀者從腦中不斷撈取記憶的78分鐘。總是突破大眾對電影想像界線的蔡明亮,究竟期待你、我、他看見什麼?
2018金馬影展閉幕片,獲得2019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從電影走入劇場,走進VR的虛擬實境,電影大師蔡明亮繼《家在蘭若寺》之後,凝視純粹,一張張臉的紀錄,訴說著歲月,訴說著愛情,訴說著明亮。
蔡明亮
1957年生於馬來西亞,台灣新電影運動之後最具代表性的導演之一。1994 年以《愛情萬歲》奪下威尼斯金獅獎,2013年以《郊遊》獲威尼斯評審團大獎、金馬獎最佳導演獎。近年來亦積極參與藝術與跨界創作,並推出舞台劇《玄奘》及VR作品《家在蘭若寺》。
曾經從電影逃離的蔡明亮,現在回來了。
這一次,他的新作《你的臉》78分鐘的電影,只有14個鏡頭,對準13張臉,每一道皺紋、每一個毛孔,在不同的光線下,隱隱細訴愛的綿長與人生的推移。
《你的臉》走過威尼斯影展、紐約影展、釜山影展之後,回到台灣,於2018金馬影展閉幕放映。2019年5月,終於在台灣正式上映。
那是一段平靜卻讓觀者從腦中不斷撈取記憶的78分鐘。一張張面部特寫,對著影廳的人訴說自己微小平淡的過往,還在期待下張臉將說些什麼時,迎面而來卻是一段長長的對望、無語。在說與不說之間,凝視已成為充滿力道的說詞。
這樣的觀看,是蔡明亮在他的作品中從未停止提供給觀眾的:《愛情萬歲》坐在公園長椅上的楊貴媚,《郊遊》對著殘破壁畫凝視的陸弈靜、《不散》跛腳遊走在戲院裡的陳湘琪、《河流》扭著脖子望向天空的李康生⋯⋯像一雙帶著反射鏡的窺視之眼,蔡明亮將難以察覺的時間流逝,釘進銀幕。
蔡明亮說自己從來都不願被界定,然而在面對難以定義劇情片還是紀錄片的《你的臉》,除去情節與敘事之後,他究竟期待觀眾看見什麼?或許早在2013年金馬影展《郊遊》映後座談上,蔡明亮所說的這段談話,已是創作者面對觀眾的真誠告白:
「我覺得我電影最大的功能是變成天上的月亮、地上的一朵花。你看月亮、花朵,不會想看懂,不會想得到什麼啟示、知識,你有你自己的月亮跟理解,但最起碼你要懂得抬頭看。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月亮,這句話是李安說的。
所有藝術創作都像一朵花,長在那邊,讓你有所啟發、感受,不是讓你獲得什麽,你獲得的是你早就已經有的,所以我想把『看』這件事帶回電影的思考。我花了20年都在做一樣的事,我相信有很多觀眾因此知道怎麽看電影、享受電影,我想我已經足夠了,你們也應該謝謝我了。也謝謝你們。 」
對藝術,蔡明亮是出了名的任性。「創作就是回到自己人生本身,沒有更多,沒有更少。我拍了10部電影,都是人家找我做的。老闆和我是平等的,我不太care老闆的感覺,」他在一場企業內部演講裡笑著說。
由於不滿電影現在被塞入太多的視覺、敘事、情節,曾拿下威尼斯和柏林影展大獎的蔡明亮,這一次,只想好好凝視一張臉。
「現在看電影就是去shopping mall嘛,我想要回到電影,喚醒我們所失去的。為什麼電影一定要有劇本?一定要有表演?一定要有對白?我們能不能只是凝視生命最細微的變化?」蔡明亮說。
對藝術如此,對愛情,更是如此。自從1991認識李康生之後,蔡明亮11部電影的男主角,全是他。
「生命真的很有限,我只夠看一個人。我的變化就是跟著李康生的變化。我跟他說,就算小中風,就算你脖子歪,就算你殘廢了,你都是我的男主角,」蔡明亮這樣公開說。
對愛、對電影那份自由的渴望,在馬來西亞砂勞越的小鎮童年就生了根。
蔡明亮3歲以前,跟著阿公阿嬤賣乾撈麵。有時候,他會一個人拿著外公煮麵的長筷子,扮演武俠片裡的金燕子。外婆常常牽著小小蔡明亮的手,走路去鎮上的電影院看電影。30分鐘從麵攤到電影院的路上,會經過跑馬場,塞滿武俠小說的書店,一個小鐵鋪,一個飄著麵包香的麵包店。這些氣味和畫面一直徘徊在他的記憶裡。到了晚上阿公推賣麵的推車回來,阿公也會握著小小蔡明亮的手,聽著廣播機的廣州大戲和潮州戲入睡。
「童年跟著阿公阿嬤,我是很快樂的。在那個沒有手機、沒有電腦、沒有電視的時代,我就已經擁有了自己一個小世界,」蔡明亮回憶。
等到4歲被爸爸接走,他向快樂的童年告別。2個哥哥、2個弟弟、2個妹妹都睡在一起,只有4歲的蔡明亮自己睡在一個小鐵床,躺在小蚊帳下。睡前的一個小時,小小蔡明亮認真地在腦海裡重溫和阿公種田、捕魚、賣麵,和阿嬤看電影的每一幅畫面。「我很小就知道要怎麼逃離這個世界,」他說。
到了小學,即使有同學叫全班同學都不要跟蔡明亮說話,他也不會覺得受傷,因為他把圖書館的書都借來看完了,有自己的世界。
「我不太care別人不理我,也不太有分別心,《古蘭經》我也看,經過印度廟也會鞠躬,住在廢墟也很好,這是我的個性,」他自剖。
透過這雙自由的眼睛,很多人重新找回觀看的可能。
「我近10年來看電影,老覺得有一隻手在幫我翻頁。所有的一切變得規格化,你的鏡頭很長,讓我看到了、聽到了、思考了,」有位50多歲法國女人看完他的電影這樣告訴他。
每個人透過蔡明亮電影尋回的事物,不太一樣。或許是一顆慢下來的心,或許是抵抗遺忘的力量。或許,只是一種對生命本質的敏感度,願意抬頭看天邊的一朵雲,願意問候朋友一聲,你那邊幾點。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是李康生?拍到最後就知道,無情才是永恆的自然狀態。我是從35釐米膠捲開始拍的,我就是想要拍出他臉上的光,」蔡明亮任性地很驕傲。
對蔡明亮而言,電影已經分成工業和手工業。而78分鐘、14個長鏡頭的手工業作品,希望讓電影觀眾在一張張時間雕琢過的臉孔上,找回那表面又內在,既遙遠又迫近的真實。
為了瞭解蔡明亮拍攝《你的臉》思考與過程,《報導者》與孫松榮教授來到蔡明亮的工作室,進行這場訪談。訪談開始前,蔡明亮談起自己從1999年拍完《洞》之後,拍片的方式越來越沒有「計畫」,甚至連劇本也逐漸精簡。他當時曾問法國製片人,能不能幫他找到一筆錢,讓他慢慢地拍一部電影。「不要問我拍什麼,也不要問我什麼時候拍完。我猜他們當時一定聽不懂我在說什麼。現在的我,就是這樣,其實也不需要很多錢,有多少拍多少,拍完就是一個作品,這樣我就很快樂了。」
緩慢而行的蔡明亮,仍然一直走在最前面。

以下為台南藝術大學動畫藝術與影像美學研究所教授孫松榮、《報導者》與導演蔡明亮進行的專訪內容。
孫松榮(以下簡稱孫):《你的臉》裡你一共拍了13張臉,其中8位男性,5位女性,請你談談選擇拍攝這些人的原因與拍攝的過程。
蔡明亮(以下簡稱蔡):我跟攝影師小古上街,一直走一直找,就是單純地找一張「好看的臉」。有些人的臉看起來就是不同,比較有生命力。後來小古跟我說:「喔,原來你喜歡的是那種『還在活著』的感覺。」找到的大部分是老人,就想怎麼樣說服他們讓我拍。
第一個想法是「不想把它拍成紀錄片」。紀錄片可能比較簡單,就到這些人生活的地方拍就好,但我想,再純粹一點,沒有那些生活背景,就是安安靜靜地拍那些臉,所以最初想到攝影棚拍,可是攝影棚又太空,沒感覺;突然想到中山堂的光復廳,那裡很安靜,幾乎聽不到外面的雜音,而且是一個有時間意義的空間。
所以我們安排了每個人來光復廳,因為大部分都70、80歲,不好讓他們等太久,差不多每個人一到,半小時內就要拍到他們,每個人都要在位置上坐上最少一個小時,主要是每張臉的光都不太一樣,要慢慢地、很仔細地打。我也給每個人選了不同的位置,每張臉都有應該有一個自己的背景。照這計畫,一天也只能拍3、4個人,拍了4天。
孫:每個人講話的內容是怎麼討論出來的?
蔡:每個人都各拍兩次,一次25分鐘,是一次跟他們聊天,一次要他們不講話,沒有NG。大部分的人我都不熟,除了那個吐舌頭、做臉部運動的,她是小康的媽,她本人就非常愛講話,拍她不講話的那個鏡頭,她的臉就開始動起來,還自言自語,我在機器旁邊笑到不能控制;其他的人我就隨便問,隨便他們講,我覺得這樣他們會比較放鬆,接著我再拍一個不講話的。我都跟他們說,就像在相館拍照那樣,靜靜地坐著就好,他們也沒想到會坐多久,一直到我喊卡為止,有人在我開機不到一分鐘睡著了。
孫:你覺得在剪接時想把「很紀錄」的東西剪掉,當時怎麼跟剪接師討論?
蔡:我不喜歡電影被界定,什麼叫劇情片?什麼叫紀錄片?《那日下午》是紀錄片嗎?我就故意去報名金馬獎的劇情片,果然沒有人理我。把那些講話的內容剪進去,例如李媽媽說:「人老了就要去醫院,我就是不要他們陪,要排隊,他們陪會累死。我時間很多,反正抽到100號我就晚兩個小時再過去⋯⋯」她講很多,有些非常動人,可是也會跑出老人孤獨的意識出來。另外打瞌睡那位江先生,講起他年輕時混幫派的經歷,完全就是一個西門町的記憶,都很有意思,但馬上就出現了「紀錄」或「口述歷史」的概念。我拍他們,13張臉,並非13個故事,就是想凝視他們的臉,到底可以昇起什麼樣的感受。
孫:最初的版本是不是三個多小時?
蔡:第一個版本超過三個半小時,我很興奮,它絕對是「美術館」的概念。
孫:那是怎麼樣的三個半小時?
蔡:有講話、有安靜,同樣的一張一張臉,只是時間更長,每張臉要看的更久。也許有一種強迫症的概念,我看多久,你就要看多久,你可以不看,但是我就拍了這麼久,甚至更久,我只是決定了這個長度拿出來給你看,你不想看也沒有錯,我也沒有不對,這是我長期想要跟觀者建立的關係,也許非常一廂情願,因為這個版本只有我跟剪接師看過,所以我也不知道,它如果這樣面世,會有什麼效果。
剪接就這樣子,剪完的當下都會很興奮很喜歡,就決定這個長度了;有天晚上我一個人看,自己竟睡著三次,我就傳簡訊給製片,請他安排再剪,就剪成兩個半小時。後來又覺得太多說話的內容,那些內容都帶著情緒,比如說有一位媽媽,說著說著眼淚就滾下來了,我就把它剪掉,最後就變成現在這個版本(78分鐘)。
報導者:剪接的選擇相信是很困難的。以記者的角度,當聽到一則有力量的真實故事時,會希望它可以被記錄下來。但身為導演,你所做選擇卻決定了它是一個「訪問記錄」,還是一個「藝術創作」。
蔡:我覺得大家都太愛講故事了,都在賣故事。那天我聽到有人說,電影就6個字:故事、故事、故事。電影什麼時候變成講故事的工具?觀眾也長期被訓練成聽故事的人,電影不是用看的嗎?我拍《你那邊幾點》,每個都是固定不動的長鏡頭,我的法國攝影師班奈・德洪(Benoît Delhomme)特別費心思打燈,有一天他跟我說,他覺得自己以前都在拍對白,現在在拍電影了。
所以我去西寧First青年電影展訓練營擔任導師時,他們說要先給個拍攝主題,我丟出了「無事」,可是你相信嗎?他們不可能會拍「無事」,沒有人敢拍「沒有事情的事情」給我看,哪怕是一個鏡頭。我真希望有人拍一個杯子拍得很棒,但是沒有,因為整體的影視教育已經非常僵化,所以我思考的是,電影還有沒有更多的可能性。我在豆瓣看到網友留言:「蔡明亮已經沒有以前那麼精采了。」我只想說,你所謂的精采不是我的追求,sorry。
孫:這次配樂是坂本龍一做的,談談你們的合作過程。
蔡:原本《你的臉》沒打算要做配樂,是因為遇到了坂本龍一。去(2017)年《家在蘭若寺》去威尼斯影展,在飯店吃早餐,小康看到坂本龍一在散步,我去跟他打招呼,那天在沙灘上聊得滿開心的。回來沒多久就寫一封信問他:「要不要看我的新片?也許有機會一起合作。」他說好,影片就寄去了。第二天他回信:「我幫你配樂,給我一個月時間。」
接著就寄來12首曲目,他信裡面說:「你可以用,也可以不用;你可以用一秒、一分鐘,我都可以。」我本來還滿擔心,會拿到一個「美美的音樂」,後來聽了非常興奮。
孫松榮:坂本龍一給你12段音樂,但並沒有指定它要配在電影的哪裡?
蔡明亮:他沒告訴我,我也沒問,我怎麼用也沒告訴他,憑著感覺就配上去了,配完我就寄給他,問他有什麼意見,他隔了兩週都沒回我。我請製片再問他有無意見,坂本回了:「我看到了,我非常興奮,忘記回你了。」大概就這樣。後來我們在釜山見面,一起出席映後座談,他跟觀眾說,他做了那麼多的電影配樂,只有兩個導演沒有給他任何指示或要求,一位是大島渚,一位就是蔡明亮。
現在想起來,我在放置坂本的音樂的時候,感覺他就坐在我身邊,在中山堂,看到這些臉的發生,所做的即興演出。
孫:《你的臉》最後一個鏡頭拍了大約8分鐘的中山堂,迷人的地方是與你之前拍《臉》有點像,它忽明忽暗,有光的元素,好像會呼吸。
蔡:這個鏡頭應該是在我們休息的時候拍的。在拍其中一個老人的時候背景也是這樣,有些忽然間暗掉,有些很暗,有些後來慢慢又亮起來。有點像有一個光在操縱,但其實那是自然的光,我滿喜歡。
孫:這你跟當年拍《不散》裡的電影院感覺很像。
蔡:對,我當時很安靜地坐在那邊,看燈光師傅們幫福和戲院打燈,很慢又很仔細;《你的臉》是請了《家在蘭若寺》的燈光師小古,來當我的攝影師。
孫:「特寫」會讓我覺得回到電影一開始的時候,例如默片。你覺得你在拍《你的臉》的時候,有一點想到回到電影最開始的那個感覺嗎?
蔡:就是「凝視」的概念吧。人有什麼機會可以凝視著一個人、一個物件,或著一個風景,心神隨之流動,就是電影嘛,你不能把眼睛移開那個格子,除非你睡著了。就像我的電影,為什麼有人會睡著,他覺得悶,覺得乏味,沒有事情發生,他不習慣看這樣的電影,不是離開就是睡著。如果你是我的影迷,你就會看我的電影,知道在看什麼,不會睡著,或者睡著了,也不會罵我。
特寫,臉的大特寫,就是我對電影最強烈的感受,一直都是;我常常說,人有機會凝視另外一張臉,通常只有三次,一次是小嬰兒出生,一次是親人離世之前,再來就是電影的大特寫。你會忘記電影的故事,但不會忘記特寫,《四百擊》(Les quatre cents coups,1959)的尚皮耶・里奧(Jean-Pierre Léaud)、《恐懼吞蝕心靈》(Ali: Fear Eats the Soul,1974)裡的那個老太太、德萊葉(Carl Theodor Dreyer)的《聖女貞德蒙難記》(La Passion de Jeanne d'Arc,1928)。
特寫,是要讓你在戲院看,你才知道它的力量,所以我拍完VR的《家在蘭若寺》才會那麼渴望拍一部關於特寫的電影。
孫:在《你的臉》中,李康生是你拍的最後一張臉,你把他臉上的燈光打成左邊暗一點、右邊是亮的,我覺得你其實在想辦法把「臉」成為一個影像的過程,而這讓我覺得你是想讓它不是那麼靠近「紀錄片」,是要我們真的去看「一個影像」。所以你說這不是紀錄片的這件事,我覺得它是可以成立的。
蔡:電影的力量不就是源自影像嗎?不管你是記錄還是講一個故事,那些強悍的力量都是來自影像。有的時候,我們以為力量是來自故事或敘事,所以對電影有很多的界定。《行者》是紀錄片嗎?之前《無色》被請去馬賽紀錄片影展(現已更名為馬賽影展)競賽,我還笑說不要吧?去參加競賽不就變成紀錄片了嗎?馬賽影展的主席尚皮耶・雷姆(Jean-Pierre Rehm)回我說,我們對紀錄片的認定沒有那麼狹隘,你來吧,我們幫你找一筆錢,在馬賽拍小康走路,後來就拍了《西遊》。
也有人批評《行者》不是電影,是行為藝術,批評的人只是沒有看到他習慣的元素:故事啊、劇情啊、表演啊⋯⋯《行者》的元素,就是走路;《你的臉》的元素,就是臉。
一個鏡頭,也可以是一部電影,管他多長還是多短。我幾乎都在經營一個鏡頭,勝過經營一個故事,我忍不住還是想問:看李康生的臉,你看到了什麼?

(編按:本文初版日期為2018.11.13,後於2019.5.17更新)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