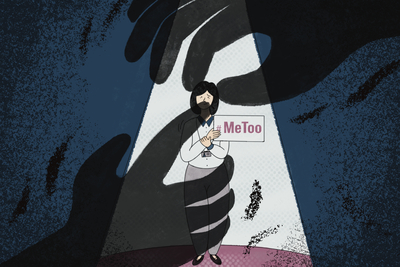評論

2017年#MeToo浪潮席捲全球之時,社群媒體盛行的台灣沒能掀起同樣的浪潮。彼時的東亞鄰國都出現了#MeToo運動,而且此些運動的出現與該國的媒體及政治環境密切相關:民主化時程與台灣相近的韓國出現對抗性很強的#MeToo #WithYou運動;威權的中國有風起雲湧的米兔運動;而即使是被害者雖然現身但鮮少具名指控加害者的日本,街頭也出現溫和的#MeToo集會遊行,女記者伊藤詩織上法院控告男上司性侵害的民事求償案件更獲得勝訴。只有自詡為亞洲性別平等領航者的台灣,在當時的全球浪潮中缺席。
台灣是全亞洲女性國會議員比例最高的國家,不僅有第一個非出身於政治家族的女總統,是亞洲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同婚合法的國家,也有相對進步的性騷擾、性侵害立法。然而,#MeToo當時在台灣的缺席,既不是因為台灣的相關法律已經十分完善,也不是因為台灣社會業已相當平等,而是與另一種缺席有關:欠缺有品質的媒體深度調查受害者的故事並描繪背後的結構圖像,為被害者的可信度提供支撐,因此被害者無法利用輿論法庭(the court of public opinion)來發聲尋求正義。
我們在2021年於英文期刊《Politics and Gender》所發表的短文,為東亞的MeToo運動與台灣的缺席現象提出了上述的分析與觀察。這樣的解釋呼應許多研究對#MeToo運動緣起的看法。受害者的故事通過有公信力的媒體查核(vetting),形同事實獲得某種程序上的調查確認,而不是一般認為的各說各話、未經證實的單方說法。畢竟,2017年秋天#MeToo運動得以成為全球風潮的基礎,是在於國際上具有相當公信力的知名媒體美國《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與《紐約客》雜誌(The New Yorker),對好萊塢名製作人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長期性騷擾的深度調查報導。

經過了5年,台灣的媒體環境並未有大幅的改善。然而,#MeToo運動出現了。不少評論者與國內外媒體將之歸功於Netflix影集《人選之人》。不過,揭發民進黨包庇性騷擾的陳汘瑈受訪表示,她完全不是因為《人選之人》才出面揭發,雖然該影集確實提供她情緒的出口。確實,《人選之人》對性騷擾現象的呈現映照了現實上的案件,「我們不要就這樣算了」這句經典台詞召喚出對騷擾者究責的公眾支持,但真正使得許多被害者現身說故事、催生#MeToo浪潮的關鍵,恐怕是事件的時機形成了民進黨必須處理的政治危機。被害者出面指控性騷擾與包庇行為的時間點,正是民進黨為大選徵召立委候選人組成「民主大聯盟」的時候,被指控的加害包庇者有兩人在「民主大聯盟」的提名徵召名單中,被害者對民進黨婦女部包庇加害者、對被害者造成二度傷害行為的指陳更是嚴重傷害民進黨形象。
在全面執政近8年後,自豪擁抱進步價值、支持性別平等的民進黨形象已然褪色,「討厭民進黨」的氛圍高漲,面臨大選壓力的民進黨已無法承受縱容包庇性騷擾的高聲量指控,必須有力回應以處理此政治窘境。民進黨承認錯誤與願意積極處理的表現,為被害者提供了可信度,而被害者挑戰執政黨的指控獲得支持,更進一步鼓舞其他被害者具名發聲指控加害人,建立了被害者群體的可信度。
在這波#MeToo浪潮中,許多被害者的故事都未經深度調查報導查核就獲得公眾的信任。雖然某些被害者受到攻擊詆毀,但多數被害者得到的是廣泛的支持,多數被指控者則受到嚴厲的譴責。被害者的可信度為何能夠在欠缺深度調查報導的支持下建立?這是值得探討的經驗謎題。我們認為,這可能是一些因素綜合作用產生的結果。
首先,不少案件早已在相關圈內傳聞甚久,原已存在的「耳語網絡」(whisper network)支持了被害者的指控。其次,「顯名性」──被害者具名現身、以具名或半匿名但有高度可辨識性的方式指陳加害者──有助於其指控產生可信度。再者,法律、教育與倡議共同促成台灣社會性別意識的提升,也有助於人們看到被害者故事與加害者言行所反映的性別不平等,並進而支持被害者。於是,輿論法庭成為被害者追求正義的去處。
我們也發現,相較於2017年美國的#MeToo運動源於知名女性對掌握權勢男性的指控,台灣的#MeToo運動當事人與被指控者特性有些許不同。舉例來說,知名女星艾希莉.賈德(Ashley Judd)和葛妮絲.派特洛(Gwyneth Paltrow)指控在好萊塢呼風喚雨的溫斯坦;《福斯新聞》(Fox News)名主播格蕾琴.卡爾森(Gretchen Carlson)指控《福斯新聞》的巨人羅傑.艾爾斯(Roger Ailes)。在這些案例中,被害人的高知名度有助於建立其可信度,知名女性願意冒著被打壓與不被相信的風險具名指控,讓人們傾向於接受其指控的真實性;掌握龐大權力的加害人被公眾認為是濫用權力的性掠奪者,並且進一步被追訴或失去權力職位倒下,則增強了對加害者的究責性。
台灣#MeToo浪潮初始對民進黨提出指控的被害人是不具知名度的黨工或支持者,後續現身的諸多被害人並非名人,即便有些被害者(如作家、記者與議員)相對較有知名度,似乎並沒有如前述女星和主播的極富盛名。換言之,台灣的被害者可信度主要是由諸多不具公眾知名度的被害者勇於發聲所建立,這是彌足珍貴的一點。再者,此波浪潮中的案件中也包括男同志對同志性騷擾/侵害的指控、並且獲得支持,更有助於人們看到男同志所爭取的不只是性自由、也有性平等,男同志之間的性騷擾與侵害不能被合理化為男同志「情慾特色」,更何況同性性騷擾不一定是因為雙方有相同的性傾向才會發生。
就加害者來說,台灣被指控的加害者雖然不乏名人,但是其所掌握的權力似乎也不及溫斯坦與艾爾斯在各自領域呼風喚雨的程度。即便是權力地位或許最接近艾爾斯的被指控者王健壯,對他的指控似乎沒有進一步究責的發展。換言之,至今為止,並沒有「權力的巨人」因這波#MeToo浪潮而倒下。被害者可信度與加害者究責性的提升程度相較起來,似乎不成比例,後者的提升程度明顯較低。
從目前的發展來看,進入正式法律程序提出申訴或告訴的被害者似乎是少數。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機構在未經被害者申訴的情況之下主動進行調查處理,特別是適用《性別平等教育法》,制度建立相對完整(但仍有很大改善空間)的學校。整體而言,被指控者如果否認指控,往往會受到公眾的譴責,這顯示被害者所獲得的可信度。不過,被指控者有各種不同的回應方式,包括委任律師發表否認聲明並揚言提告被害者,否認被指控事實並且繼續在公共領域活動,認錯道歉且暫時淡出、或者宣布永久退出公共領域,以及擔任政府職務者「被請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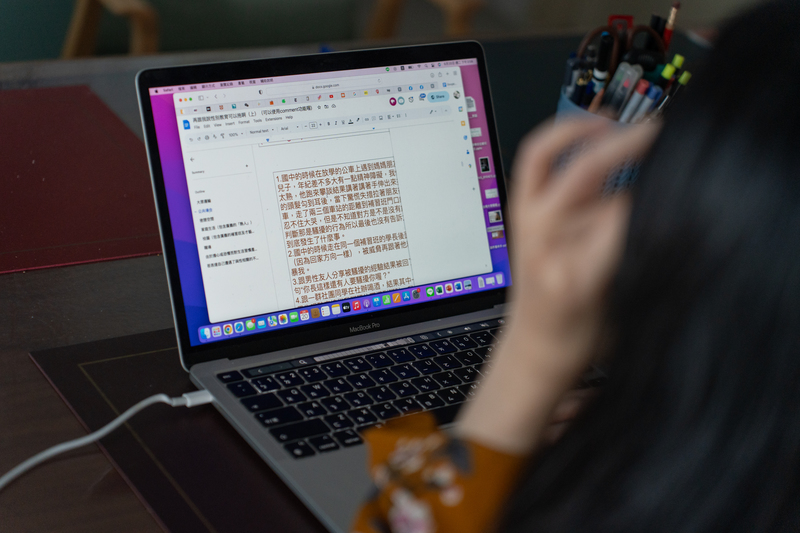
對一些被害者來說,加害者的認錯道歉能夠帶來撫慰,如果該道歉確實承認錯誤,而不是以假設性的語氣所為的條件式道歉。就目前所見,加害者的道歉大都是迫於輿論法庭直接或間接的「強制」。弔詭的是,如果被害者走進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反而無法得到強制加害者道歉的結果。
本波#MeToo修法,行政院提案中的《性別平等教育法》修正案,還特別將學校未能採取確保行為人向被害人道歉的措施排除於處罰範圍之外。這是因為憲法法庭最新的見解(111年憲判字第2號)認為,強制道歉是強迫人民表達不符合其良心價值信念的表意,違反憲法對於言論自由與思想自由的保障,大法官並進一步質疑「心口不一」的道歉能否達到真正填補被害人損害的正面功能,因此禁止以強制道歉作為回復名譽的方式。姑且不論「女人是男人的性物」這類思想信念是否應該受到至高無上的保障,多數意見的大法官們如何幫當事人決定「心口不一」的道歉無法達到填補損害的正面功能呢?對當事人來說,加害者堅持不認錯反而可能進一步深化傷害。
其實,被憲法法庭該判決變更的2009年司法院釋字第656號所提出的看法,可能較為合理。如果強制道歉的方式符合該號解釋的條件「未涉及加害人自我羞辱等損及人性尊嚴之情事」且符合比例,並且也是被害人所接受的損害填補方式,為何不能以判決要求強制道歉?就此來說,輿論法庭或許可以做到法律法庭所無法做到的事。
不過,輿論法庭的某些制裁也造成爭議。例如,這波#MeToo浪潮中「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的實踐,有些被指控者「被取消」,也有些被指控者「自我取消」。雖然,這些「取消」在多大的程度上會導致「社會性死亡」,還有待觀察,但相關爭議確實值得進一步思考。
有一些熱心公民建立案件清單與加害者名單公布在網路上,也引發爭議。私人建立加害者名單的支持者認為,這個做法有助於提升對加害者的究責,並保護潛在的被害者。建立、公布與散布名單的人們可以主張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但也面臨法律風險,這包括遭到被指控者以妨害名譽提起民事或刑事告訴、被依據管制假消息的法律裁罰或遭到起訴等等。這樣的法律風險其實與#MeToo敘事者的法律風險類似。
除了法律風險之外,也十分值得注意的是製作、公布、散布加害者名單背後隱藏的意涵:認為性騷擾者是偏差的惡人,透過公布姓名來對公眾提出警示,並進而將這些人全部或部分隔絕於社會生活之外。這樣的想法並不陌生,人們往往對性侵害犯有這樣的想法,台灣也因此制定了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制度、禁止性侵害前科犯從事特定職業(曾被大法官認定合憲),也曾經出現過社區公告制度的倡議。然而,性騷擾不是社會的異常偏差現象,而是父權社會的「常態」;並非所有的性騷擾者都是所謂的「變態」,許多性騷擾者是「普通人」,有些甚且是公眾形象相當良好的人。正如對性侵害犯的各種社會隔絕封鎖措施,加害者名單若是強化了人們將性騷擾當成「偏差變態現象」的有限想像,而無法真正認識性騷擾發生的關鍵是不平等的性別權力結構,這是令人擔憂的發展方向。

面對#MeToo浪潮,民進黨政府迅速地提出《性別平等工作法》、《性別平等教育法》與《性騷擾防治法》三部法律的修法草案,預定在7月的立法院臨時會中快速通關。這批行政院版的修法草案標榜「有效、友善、可信賴」。確實,相較於現行法,草案確實有不少改善之處,例如強化擴充雇主責任、延長被害者申訴時效、處理三法的管轄競合漏洞等等。然而,目前的修法方向至少有以下三個面向值得深思與進一步考慮。
首先,正如性侵害改革常見的主張是以重罰來遏止並嚴懲性侵害,這波#MeToo的修法也不例外,強調以重罰來「有效打擊加害人」,加重對雇主、學校、行為人等等的行政罰,以及《性騷擾防治法》中乘機觸摸罪(特別《刑法》)的刑罰。我們認為,提高現行法的行政罰固然值得考慮,但是將重罰化作為問題的解方,想以威嚇和嚴懲來遏止性騷擾這種「父權體制的常態現象」,不見得有效。至於對於利用權勢或機會乘機觸摸罪的加重刑罰,不只牽涉到重罰化的問題,還涉及以下第二個問題:這次修法並未包含妨害性自主罪修法的規劃,也沒有處理《性騷擾防治法》的乘機觸摸罪與《刑法》強制猥褻罪的競合問題。
本波#MeToo修法未能納入妨害性自主罪的修訂,是個重大的缺憾。更何況,當初為了處理所謂「襲胸案」問題而制定的《性騷擾防治法》乘機觸摸罪,想以「意圖性騷擾」為主觀構成要件,以「乘人不及抗拒」的概念來填補過於狹隘的強制概念之不足,造成與《刑法》強制猥褻罪的競合爭議,原本就是有問題的設計。性騷擾就是一種性別歧視,而反歧視法的核心議題之一是,證明歧視不應以行為人具備歧視意圖(intent)為要件。一方面,歧視的意圖很難證明;另方面,歧視者往往欠缺主觀歧視的意圖,因為對他們來說,這類言行並不是歧視。再者,如果人們沒有隨時防備抗拒的義務,何需明定「不及抗拒」?這種立法所預設的防衛義務反而變相地讓「抗拒」的幽靈繼續存在,還不如廢除特別《刑法》的乘機觸摸罪,直球對決處理《刑法》中的強制與意願概念。
最後,本次修法對於強化被害者使用制度管道求償的改革,做得太少。不論行政罰的罰鍰有多高、就算增加了行為人本人的罰鍰,所繳交的罰鍰都成為國庫的收入,很少有被害人能走到獲得損害賠償金的階段。雖然這波修法提案中增加了懲罰性賠償金的規定,也增加得委託民間團體提供法律諮詢或扶助等規定,但這能夠多麼有效地改善當事人取得損害賠償金的困境?令人懷疑。
我們認為,相較於我國的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或性別工作平等會無法代表當事人提起訴訟,美國依據1964年《民權法》(Civil Rights Act)第七章所創設的就業機會平等委員會(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EEOC),具有代表就業歧視被害者進行訴訟的獨立當事人資格地位、且可與雇主進行和解的制度設計,值得參考。
EEOC不只制定性騷擾的相關指引(包括禁止報復),有權進行調查、對相關法院訴訟案件提出法庭之友意見書,更可以代表當事人與雇主和解(優先)或提起訴訟控告雇主。雖然人力不足的EEOC處理案件可能耗時數年,但是由EEOC來代表當事人進行訴訟或和解,可以降低當事人求償與改善職場環境的負擔。不只是小企業商家案件,EEOC更針對性騷擾盛行的大企業達成高額和解與改善計畫,曾經為三菱企業的女性員工爭得3,400萬美元(約新台幣10.5億元)的和解與防治計畫,今年1月也與橫跨3州的麥當勞加盟店達成200萬美元(約新台幣6,200萬元)的和解與防治計畫。EEOC代表性騷擾被害者提起訴訟的案件也有獲勝之例,例如曾為佛羅里達州一家餐廳的5位女服務生贏得合計155萬美元(約新台幣4,800萬元)的賠償。從今年1月到7月,EEOC不只達成多起性騷擾案件的和解,也對數個雇主提起性騷擾訴訟。
EEOC的獨立當事人資格設計或許不是唯一值得參考的制度,強化私人直接求償與集體訴訟管道也是應該同時追求的目標。我們想強調的是:行政權的行使不應限於或過度重視裁罰、也應更積極地用於協助被害人求償;反歧視機制應該更強化當事人獲得民事損害賠償與司法的角色,降低人們使用司法尋求正義的門檻。
本次#MeToo風潮中的前懲戒法院院長案,其處理方式令人遺憾,也已為司法所可能扮演的正面角色蒙上陰影。在媒體揭露司法院包庇前懲戒法院院長性騷擾女下屬案後,司法院先是由發言人召開記者會公開對大眾說謊,否認曾收到性騷擾的指控,接著在司法院院長承認安排前懲戒法院院長以健康事由提前退休之後,發出新聞稿指稱當時的否認與處理皆是依據被害者的意願、遵守《性別工作平等法》,要求雇主在知悉性騷擾後採取立即有效糾正改善措施的規定而為,並且在司改與性別團體召開記者會抗議司法院包庇之後,又再次發出新聞稿強調司法院是依法行事。
然而,司法院的數次公開回應皆隻字不提的是:司法院院長及其當時的祕書長(已於處理性騷擾案時轉任懲戒法院院長成為被害者的直屬長官)在處理此事時,違反司法院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處理要點〉第四點中「本院各級主管於知悉有性騷擾情形時,應通報性騷擾申評會,並由該會依相關規定辦理」的規定。司法院可以採取其他的方式來保護當事人,發言人公然說謊絕對不是選項,否則人民要如何相信政府發言人公開的發言?我們更要進一步提醒,司法院院長與前祕書長自己違反司法院的規定,且司法院院長同時也是憲法法庭大法官,該院的處理方式已嚴重傷及司法信任。如果有被害人不滿雇主的類似作為,進行法律救濟最終敗訴後,要思考是否提出裁判憲法審查的聲請,難道不會懷疑司法院對本案的處理態度可能影響到憲法法庭的公正性,從而無法信任憲法法庭是否受理的決定與結果?

最後,我們要指出房間裡的大象:政治體制的性別權力結構。當民進黨主席賴清德在公開宣示民進黨反性騷擾立場的同時,說出「每一位女性都是可愛的玫瑰花,玫瑰花就是要漂漂亮亮的,所有從政人員不管男性、女性,都要讓每位女性幸福、快樂、亮晶晶」這樣的言語,《民視》、《TVBS》、《鏡新聞》等藍綠媒體將之稱為「撩妹」金句,執政黨總統候選人及主流媒體對性別平等的理解令人感慨。
性別平等從來就不只是要讓女性幸福,性別平等是要讓每個人都不因位於性別權力關係的下方而失去自己的自由與尊嚴。權力關係既展現在職位與資源分配上,也展現在文化習俗中,改變資源分配與轉化文化同等重要。
作為台灣第一位女總統,蔡英文總統在性別平權的進展上最令人失望之處,就是在她的領導下,內閣中的女性比例、民進黨中常會的女性比例,以及民進黨智庫新境界文教基金會董事中的女性比例,都創下歷史新低。民主化初期曾經引領台灣進行性別平等改革的民進黨,在全面執政之後,不只明顯輕忽,更惡化黨內及政府的性別權力失衡。最令人覺得反諷的是,行政院性別平等處,長期追蹤管考政府委員會的性別比例是否符合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但是上述最具備決策影響力的幾個場域,明顯違反這個原則,卻既不在性平處的管考範圍內,也很難透過性平會的制度有所改變。性騷擾的根源是性別權力的不平等,不致力改變性別權力結構,性騷擾的防治終究是緣木求魚。
賴主席和主流媒體對「可愛的玫瑰花」用語背後的父權意涵毫無所覺,反映出#MeToo運動想要追求的性別平等多麼不易達成。在這波運動中勇敢發聲的女性及男性被害者,以及所有支持他們的人,無非是希望台灣能成為一個真正自由民主的社會,一個所有人都能平等且自由地發揮其能力才華的社會。政府和媒體的職責是傾力打造這樣的社會,而不是與此願景背道而馳。政府力推的#MeToo修法案或許很快就會通過,但這只是邁向性別平等的新起點。在#MeToo運動建立被害者的可信度之後,隨之而來的正義應該是更根本徹底的法律改革、政治結構的改造,以及文化的變革。
(※本文部分內容於2023年7月19日以英文發表於美國《外交家》雜誌〔The Diplomat〕:"Taiwan’s Belated #MeToo Movement")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