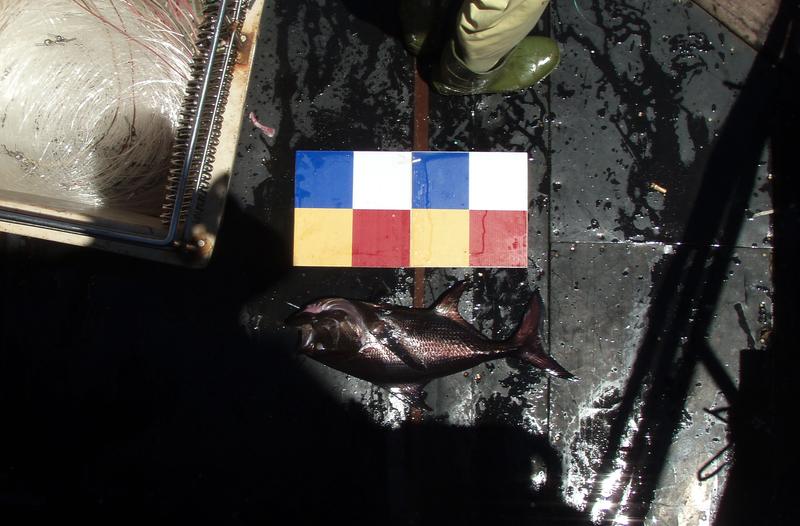讀者投書

我,出生在東港漁村,海洋是我們人生的背景。
從小家人聽聞或交談的話題總環繞著跟漁業有關,家人在高雄前鎮工作,親戚們從事養殖漁業以及在漁業署相關機構擔任職員。過去跟爺奶共住的大家庭中,從早到晚都有穿著雨鞋,剛從魚市場工作完的親朋好友來作客。還沒擔任船東前的父親,凌晨3點多鐘總是需要去市場批價剛上岸的新鮮魚貨,被他起床的窸窣聲吵醒,是兒時回憶。我不懂什麼叫做魚市場的魚腥味,因為這種味道早瀰漫整個家。
幾年後,父親與親友合夥經營船公司,爸媽開始來回東港與前鎮生活。旗津造船廠的漁船下水典禮,我與堂兄弟姐妹們搶著從新船上灑下的糖果和麻糬,那是漁村孩子的獨特童年。東港漁村和前鎮漁港一直是那樣讓我熟悉的地方。
從事漁業的父親一直都是個內斂不太跟孩子互動的人,直到我大學畢業到海外求學,來回紐約台灣次數不多,父親自那之後,才開始會跟我討論他從事的工作,而我也喜歡跟他晚上吃飽飯,沿著東港大鵬灣潟湖的步道上聊目前台灣漁業現狀。而他也會時不時要求我去幫忙處理船工、船長以及靠港補給的庶務。這是我近年對台灣漁業深一層認識的方式。
高中畢業的父親,嚮往的是賺錢給家人好生活。郭台銘、李開復等資本家老闆經營之道的相關書籍,時常會出現在他桌上。保守右派價值逐漸成為他的人生哲學,對世界的理解是《文茜世界周報》。而他的兒子,大學讀的是社會政策,到紐約念碩班,在紐澤西念博班,博班研究社會不均跟貧窮,擁抱的是左派與公平正義。
價值差異極端的兩個人,卻愛聊漁業這產業的現狀,企業的勞資關係、漁業捕撈工法與海洋永續發展等等議題,雖然不會激烈爭執,但言詞犀利的交鋒討論時常出現,但我感謝父親在爭辯不過我或有一絲不悅時,不會回我一句「再吵,你以前讀書錢從哪來?」這種話。他的結語時常是「我要你會思考」來結束每次的討論。
《報導者》深度訪談與研究的調查報導出來,我認真地看完《造假・剝削・血淚漁場》的6篇文章後,感覺沉痛,看著印尼漁工的悲慘故事,獨自在遙遠地球這一端流淚。從批判性、深度報導的文章中反思跟自省,號稱擁抱左派價值的我,當批判來襲,身為一個邊緣既得利益者的自己,我的反省在哪?我的觀察又是什麼?
最讓我掙扎的是漁工「境外聘僱」的制度。文章有一段談及,「漁況好的時候,起鉤或起網作業就要16小時,怎麼算工時?」有些不理解仲介制度如何苛扣外籍漁工薪水的老闆會抗議:「我們給的薪資遠超過當地水平啦!」一開始,我想著這是否可以類比某跨國銀行公司或是某科技公司,把部分團隊搬到台灣,總部還是在美國紐約,但只要在台北信義區租個辦公室,以派遣合約的方式,7到9萬塊台幣月薪聘僱台灣優秀青年,這樣薪資可以聘到台灣優秀大學畢業生,但在美國一個電腦工程師初階薪水,其實是月薪1萬塊美金(約32萬台幣)。在這全球化脈絡底下,到底是要用什麼角度去看,是我一直在反思的境外聘僱制度。
但再進一步思考後,這當中其實是截然不同的脈絡,這群漁工簽下的是不平等的契約,因為普遍教育程度不足,漁工幾乎沒能認真看過契約內容;此外,跟設立當地工廠或辦公室不同的是,這一艘艘海上大船,這群人是一上船就2年,他們是把人生全部交給船東與船長,輪班休息,長期看不到家人。回憶自己也曾當兵失去自由的日子,現在的自己也是流浪在外唸書沒能說回台灣就回去,閱讀文字時,時不時的試著想去同理,但船工的孤獨感受應該早已超乎一般人所能體會的。
看見印尼漁工Supriyanto因為船長不當管教或可能虐待而生命逝去,讓我想起幾次深夜父親接到船長緊急越洋電話打來的交談。
隨著國際競爭的壓力,一艘船管理至少3個以上不同語言和不同國家的船工,我們很難去比較過去跟現在船長虐待船員的狀況,但時常耳聞船東們說的是,哪位某船長又遇到「狀況不好的船工」(狀況不好可能就像Supriyanto這樣,沒受過訓練,拿著假的船員證上船,手腳不俐落,而被用傳統方式「管教」),船長為了建立威信,老一輩船長最常用的方式就是體罰跟軍事化的管理,海上漁工要聽船長的話,他們是賺錢工具,不能有自己。
在台灣深夜聽見我父親接起這些船長來的電話,他始終用很冷靜的語氣告訴年輕一輩的船長,「先讓這些狀況不好的船員休息,千萬別動手,當船靠港之後再把他們送回去。」但父親的作法也許是少數,也許不是。
在海上,放眼望去只有海跟船的環境,這種打罵式的管理,據悉一直是過去老一輩船長的管理方式。當船長離岸,除了全球的GPS定位漁船系統,和每天一通回報船公司老闆電話,基本上船東們只能信任船長,像父親這樣的船東總會說:「漁獲量有到,船有賺錢,船長要什麼我們就儘量滿足他。」那彼此信任的關係如果受到傷害,船長在海上做壞勾當、打船員又或是越界抓魚,那是船東們夢魘的開始。
身為一個漁業產業的旁觀者,我最常聽到船東們說的就是「飯都吃不飽了,你會想到永續跟保育嗎?」漁業人的觀念是有魚就抓,誰抓的到誰厲害。爺爺曾說,「咱討海人的自信是在海上才找到的。」從小聽到長輩們說的故事都是「住在哪裡的哪位阿伯多會抓魚,今年又是豐收」,又或「看看那些伯伯們的人生都在跟大海搏鬥,都60歲了還是出海,海是他們的戰場」。
這些兒時故事就像是小時候要我們閱讀某英勇將軍的事蹟一般,背後所傳達的也就只是,競爭、賺錢是漁業人唯一的信念。
船長們、討海人很難意識世界的變化,對他們唯一有意義的,是與自然搏鬥的能力;他們把學習能力放在困難的水溫圖、雷達圖,告訴國小畢業學歷的船長「這學會可以賺錢」,他們幾乎都認真學習。但要他們改變動機,十分困難,因為長年在海上,很忙很累,他們概念中認為自己抓的是公海資源,而公海是大家的,所以不覺得在掠奪別人。這樣的概念依舊是舊世代的想法和概念。這樣的想法和概念尚未看見被改變的契機。
不論是圍網船或是延繩釣漁船船東與船長,都有 「不能被虧到」的想法。他們擔心「做了保育」,就會搶輸別人,他們擔心別家船公司抓比較好,他們也擔心中國漁業打敗台灣,別國都在捕,台灣怎麼可以少貪一點。
除了文化,人才是更大的挑戰。在全球化脈絡下,新一代船長也多是採用境外聘僱的方式,且薪水相當可觀;在這個產業,年薪百萬甚至數百萬新台幣的船長大有人在,薪資待遇遠超過台灣剛進社會年輕人。我曾和過一位25歲的年輕大車(編按:輪機長)談及他幾歲出海,他答「16歲」,當我們16歲拼著高中升大學的壓力,他出海捕魚,過著9年海上生活,等待爬到船長那位置。
這可以讓我們想想可能的產業轉型,也剛好順勢思考怎樣去培育出好的船長,以及現在是否還有年輕人願意吃這種勞力苦。而實情是,越來越少年輕人願意上船,船上船長和輪機長很多已不是台灣人。
如《報導者》文中所說,日本已經與菲律賓的漁業學校合作訓練漁工。台灣產學合作的成果怎麼打入這封閉的產業與陋習已久的官僚窠臼?在全球化過程中,我們一直在透過尋找低廉人力做為解方,以為這是最好的方案,但與其飲鴆止渴追逐低廉的勞力,是否有可能是自己培育好的漁工或船長,增加台灣漁業界的人才庫,這不也是增加這產業產值的重要方向,而非去剝削他國的低廉勞動力來讓資本家獲取暴利。
在和父親的對話中,我時常想著,這群在漁業界擔任管理階級的老闆們,是真的知法玩法,又或是只是因循傳統?我的親身感受是,在漁業界的老闆們,大腦依舊停留在許久前,他們的思維本來就少有人道、人權這種思考,他們跟著過去20年來的管理方式,照著各種漁業的規則或潛規則走。過程中有人知道變通、改變、改善,也有人跟不上。他們的資訊多半來自漁業署的最新辦法,不一定接軌國際的「進步價值」,當整個利益結構過於綿密,仲介、船公司、漁會、漁業署的關係,就變成剪不清理還亂的狀況,或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心態。
當一個封閉已久的產業,在前現代的思維中被教育著要理解保育跟環境,這系列文章倡議的冷凍技術改變、漁況的永續經營、產品生產鏈的制度等等,都是要進一步被推動、推廣。在產業上,對於人才的培養,我真心認為那是幫助這產業的關鍵,老一代的思維假使難以撼動,不如再培育新一代船東、船長,將這樣概念深植在他們的腦海中。人才培育、人力資源管理、引進大數據分析,漁業署資料的公開透明,都是必須改革的方向。
《報導者》的優質深入報導,就像一個現代文明的視角探視了一個前現代的部落。而這些漁業老部落裡,該面對的或許是個溝通和理解現代文明的過程。過去在我所學社會政策領域討論中,時常被提醒著「我們不要在制度底下責怪個人,但要避免每個人都躲在體制下就可以免責」。因此,身為一個邊緣的漁業產業既得利益者,遠洋漁業二代人,以上文字只是我試著跟著反省著各種改變跟進步的可能。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