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視勞動系列之二

今(2021)年2月,勞動部召開諮詢委員會,討論電影製片業拍攝現場的工作人員是否適用《勞動基準法》第84條之1;9月13日,第二次諮詢委員會中,諮詢委員達成共識,同意電影製片業勞工納入這項俗稱「責任制」的條款。其實早在11年前,燈光組和攝影組就已經被納入「責任制」,歷史重演,是否代表台灣影視勞工的勞動困境始終沒變?當影視人達成共識要改善過勞沉痾,他們得先面對哪些障礙、如何拆解?又有什麼新路可走?
《報導者》採訪不同世代的影視工作者、專家學者與政府主管機關,嘗試從勞動法規、合約範本、補助金政策及產製效率等面向切入,找尋讓政府和民間對話、影視產業和工作者永續共榮的方法。
「那天下大雨,劇組明明有發雨衣,但我看那些實習生小朋友都沒穿雨衣,我問他們為什麼不穿,他們說『只有淋雨感冒,才有辦法休息』⋯⋯。」入行30年的資深電影燈光師屈弘仁(暱稱哈克)坐在氣氛輕鬆的咖啡廳裡,描述著幾年前一部電視劇的拍攝現場。
屈弘仁說,很多學生懷抱夢想而來,沒想到那個劇組拍片每天至少16小時起跳,才拍一週,學生就撐不住。那一年,他和台北市電影戲劇業職業工會總共接到74通申訴電話,幾乎都是投訴劇組超時和苛刻工作人員,例如從沒有吃到過溫熱的便當;拍到中午收工,下午再開工,只因為劇組想省中午飯錢。
拍電視、電影的勞工除了超高工時外,職災更是嚴重。屈弘仁提到曾有個年僅23歲年輕助理想找他拜師,結果某天超時工作後,開車睡著開到對向,人被夾死在卡車裡,「臉拼回來都還是歪的⋯⋯。」且因為保險保的是旅遊團體險,最多只能賠8萬元,最後還是劇組每個人自掏腰包,湊個白包給家屬,助理還是家中的獨子。

目睹這些慘狀,屈弘仁在11年前就嘗試實際做出改變,推動電影製片業中的燈光組、攝影組、場務組、電工技術人員適用《勞動基準法》第84條之1;此案核定通過後,此後他的合約都會寫明工時以12小時為限,需有超班費、保險、標配司機等。
沒想到堅持簽訂相對合理的合約,卻讓屈弘仁成為燙手山芋。業界覺得他規定多、成本又高,且拍電影得各組協力才能完成,如果燈光組12小時就要下班,代表其他組也被迫提早收工,漸漸地就沒人找他合作。
「本來1年滿檔拍8部片,後來變成3年才1部片,」屈弘仁回憶,當時還有幾位朋友認同他的理念,加入簽訂合約範本的行列,只是多數都撐不下去。但他並不後悔,「我知道會有過渡期,所以我很努力去學泡咖啡(因應沒片可拍),」屈弘仁自嘲,這就是主張勞權的「陣痛期」,雖然一痛就超過10年。從外行到行家,他已經協助7、8家咖啡廳開業,熱愛的拍片工作變成副業,誰也沒想到那雙熟練泡著咖啡的手,曾經在片場打著燈。
11年後的今天,台灣電影再度面臨責任制的勞動挑戰。
- 工時:每日最高工作時間12小時(2小時加班含交通時間)或每日最高工作時間11小時不含交通
- 休假:做6天休1天,連續休息時間達11小時;完整休假日為收工起算30小時;移景不算休假日
- 工作中休息時間:工作中休息1小時
- 加班費:11至12小時加成為1.33
- 安全及保險:工作場地需設感電危害預防;劇組需幫工作人員保團保及商業保險;若已經於工會保勞健保者需出具加保證明
*註:《勞基法》原則規定,勞工每日工時不超過8小時,單週不超過40小時;每日最多得加班4小時至12小時,前2小時(第9、10小時)加班費乘以時薪的1.34倍,後2小時(第11、12小時)加班費乘以時薪的1.67倍;每7天休息2天(一例假日、一休假日)。

電影基金會董事長朱延平說,近年來不乏劇組被年輕工作者投訴工時過長,「大家也才意識到,原來我們一直都在違法。」促使基金會和各團體開始討論解決方案。
「希望給我們一個『守法』的機會,」朱延平說,拍電影血汗是事實,但產業性質難以遵守《勞基法》也是事實;不過,工時12小時、做6休1等是業界勞資雙方討論出來的共識,如果能適用責任制,電影產業才能夠合法運作,而不是大家都明知違法,檯面下胡搞一通。過去只有燈光組和攝影組等適用責任制,但實際上根本沒有造成影響,希望這次全部納入,才真的有機會產生改變,「台灣電影好不容易要翻身了,不要再用一個法(《勞基法》)把我們框住!」
電影基金會提案後,勞動部在今年2月召開諮詢委員會討論電影製片業是否適用《勞基法》第84條之1,會議結論卻不是通過或不通過,而是補件再審。
參與會議的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工時科科長李怡萱說明,《勞基法》第84條之1主要是讓經核定的特定勞工,得由勞資雙方另行約定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性夜間工作,適用的大前提是「工作者必須是《勞基法》中的勞工(僱傭)」。但由於電影業工作型態多為甲、乙雙方簽訂承攬契約,諮詢委員認為必須要先釐清電影業勞工的勞動契約型態,才能進到實質討論。
台灣電影發展幾十年來,從來都跟勞動法規絕緣,即便是11年前燈光組等先納入《勞基法》中的責任制也不是通案,最大關鍵就是大部分工作者不屬於「勞工(僱傭)」,因為不是勞工,才難以有約束力。
電影產業每個國家都有,其他國家又如何面對影視工作者的勞動議題?
以電影工業最成熟的美國為例,曾在紐約電影學院洛杉磯分校學電影製作的新銳導演詹家維表示,好萊塢通常拍一部電影就會成立一間公司,所有參與這部電影製作的人都會成為這間公司的員工。工會力量強大,若會員工作遇到超時、受傷等情況,工會能直接介入跟製片方協商或談判。
好萊塢經驗或許離台灣太遠,可以對照同在亞洲的鄰國韓國。韓國近年內影視產業迅速崛起,「韓流」更行銷全世界,但光鮮亮麗的螢光幕後是比台灣更嚴苛的勞動環境。2016年,韓劇《獨酒男女》的副導李韓光自殺,留下遺書控訴血汗的影視製作生態,其遺屬在事發後成立韓光媒體勞動人權中心(簡稱韓光中心),致力於改善韓國影視工作者的勞動條件,電視編劇工會、電視工作人員工會也相繼成立,經過數年努力,已初步在「減少工時」取得重要成果。
李韓率說,韓國政府過去並未統計影視業的工時,但據韓光中心自行調查的結果,在他哥哥李韓光在職時期,電視劇拍攝期的每日平均工時達16至18小時、每週工時約80小時。但在政府承認影視工作者是勞工後,每日工時已降至約10小時、每週工時約50小時,可說是大幅下降實際工時。
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長黃維琛表示,要尊重影視工作者的意願和工作型態,很多人希望保持創意和接案彈性,反而不希望被勞工身分綁住,勞動部不會直接認定這個行業就屬於僱傭。如果工作者自認為是勞工,但資方不願承認,工作者仍可到勞動機關去申訴,或是走司法途徑確認僱傭關係。
「工時過得去(符合前述團體提出的每日12小時限制),僱傭才能光明正大往前走,不然只能回到承攬,」黃維琛說。

「責任制對一般產業來說可能是降低勞動條件,但對於我們來說,是提升勞動條件,一天只拍12小時?太好了!」電影基金會祕書長段存馨說,如果電影製片業能被認定為責任制,工作者才有依據來跟資方要求提升勞動條件。除了本就是僱傭的勞工能受到保障外,其餘承攬工作者也有機會跟進。
由此不難看出政府和業界雙方的認知分歧。勞動部認為,按照《勞基法》邏輯,必須先是僱傭勞工(適用《勞基法》)身分,才能討論放寬限制的《勞基法》第84條之1責任制;但電影基金會、職工會卻認為,認定僱傭比認定責任制更加困難,但如果連責任制都無法認定,更遑論被認定為僱傭。
「燈光、攝影也不全然都是僱傭,但它之前可以適用責任制,為什麼其他組就不行?」廖蕾嘉質疑。
段存馨表示,基金會將儘速補件,說明業界僱傭的型態,仍希望儘早通過。一旦中央認定是責任制後,後續也能夠跟地方政府合作,找劇組來示範如何達到工時等要求,「讓大家知道這是做得到(12小時內收工),就不會再有理由說做不到。」
先做到才能認定,還是先認定才能做到?勞動部、電影業界對於工時12小時的交集點,能否透過責任制來保障,仍有待觀察。
9月13日,勞動部針對「電影業適用勞基法增修提案」第二次召開的諮詢委員會中,諮詢委員便達成共識,同意電影製片業勞工納入勞基法第84之1條(俗稱責任制)人員。最終是否通過,仍有待勞動部決定。
若暫且跳離僱傭關係認定和責任制的無限迴圈,除了在《勞基法》上打轉外,仍有其他解方。
李韓率表示,韓國影視工作者本來和台灣一樣,都只是簽約的乙方,並無合約範本。但自從被認定為勞工,韓國影視主管機關文化體育觀光部(簡稱文體部)針對業內不同職種擬定標準契約書,供勞資雙方沿用簽訂,目前產業中約有半數工作者使用此契約,已經對電視台造成一定的壓力和制衡效果。
台灣亦有民間力量先行。職工會於4年前陸續推出不同組別的合約範本,但廖蕾嘉表示,影視界當前生態無法達到合約範本的基本標準,實際上難以適用,加上沒有強制力,個別勞工又缺乏議價能力,範本普及率不高,且目前工會版本的保障尚不夠嚴謹。她進一步建議,勞動部帶頭訂定合約範本會更有示範效果;再者,若政府願意配套獎勵機制,可提高落實的誘因。
能否由勞動部門主動制定合約範本,官方回應仍相當保守。黃維琛表示,勞動部無法熟知各行各業的實際勞動情形,過去訂定合約範本,多由熟悉該行業的主管機關主導,勞動部則協助檢視涉及勞動法規的條文是否完備,像住院醫師和漁工的合約範本,就分別由衛福部和農委會主導。他建議,由影視主管機關文化部發起,訂定適合從業人員的合約範本,勞動部可以從旁協助。

文化部表示,因應條例公布施行,已啟動訂定契約指導原則的相關工作,由綜合規劃司主責此業務,將諮詢各業別的專家學者及業者。不過,是否能做到如韓國文體部公布的標準契約書之程度,知情官員說明,母法用詞為「契約指導原則」,未必能詳如業內期待的「公版合約」,原則可以走到多細,得待各業別依產業現況和需求討論後才能確定。
至於現階段影視業關注的工時和職安問題,《文獎條例》的修正仍打開了政策的機會之窗。文化部綜合規劃司表示,未來會向電影基金會、導演協會、職工會等團體廣徵意見。假如勞權已是業內凝聚多時的共識,這是民間議程進入公共政策的重要時刻。就算勞動機關的法規問題難解,從文化主管機關切入,有空間藉合約保障使工作者權益邁前一步。
作為發放補助金、和影視產業關係最為密切的對口單位,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簡稱影視局)局長徐宜君表示,樂見法律修正給工作者更多保護,電影製片業也是藝文產業的一環,「等文化部把原則訂出來,影視局會按照部所出的指導原則,去輔導業界來依規定簽約。」
事實上,在今年修法前,考量劇組交通事故頻傳,影視局已修正「電視節目製作補助要點」,要求簽約團隊,預估製作經費時必須規劃車輛租賃(包含聘請司機、加保乘客險)費用,避免工作人員收工後還要自己開車、出車禍卻發現根本沒有保險。徐宜君表示,未來會多與工會合作,望從勞動教育和意識推廣著手,將職業安全內容納入劇組人員培訓課程。
將發給製作公司的核定函攤平在桌上,「我們核定補助案的時候,會跟他說我們核定多少錢,也要求他一定要履行下列義務,其中一條就是要遵守《勞動基準法》跟《職業安全衛生法》,」徐宜君強調,受補助團隊絕對必須守法,「如果不符合、被檢舉,或是真的違法的時候,我們是可以撤銷補助的。」站在文化部依法行政的立場,《勞基法》和《職安法》是退無可退的紅線,自然也不能用額外獎勵來鼓勵「合法」,「你跟它說遵守的話我給你bonus,那代表它可以不遵守,這絕對不可以。」
不過,一位不願具名的製片透露,有些惡名昭彰的製作公司,並未被列入黑名單,因政府是針對內容補助,只要有好的創意和票房,就算血汗也能獲得輔導金。至於過去是否有因違法被撤銷補助的製作公司,「沒有這個案例發生,如果今天真的有職業災害或違法,它怎麼可能不被處分?」徐宜君說,任內沒接到針對工時的檢舉,工作人員可主動投訴,文化部才有依據處理。
明明整個產業長期都和《勞基法》脫節,為什麼沒人去檢舉違法?
段存馨認為,最大原因是說了等同在「為難產業」,「現在這個(《勞基法》)本來就做不到,所以也沒想說要去檢舉,大家都知道實際狀況是這樣,如果去檢舉,人家問你覺得真的做得到嗎?那就沒辦法啊。」她也直指,要讓產業正常化、健康化,就得先擬出一套可行的規則,才有遵守的可能和意義。
廖蕾嘉則坦言,若不能確保真正匿名,個人要在業界生存下去就不敢輕舉妄動。「工會不怕做這件事情,願意代替大家去檢舉,」但她也提到過去的經驗,勞檢處收到投訴後,需要事證等資料來做紀錄和核對,但如果當事人不願具名,勞檢處並不接受以工會的名義檢舉。
回到根本,在設定遊戲規則和管制的戰場,主控權還是握在政府手上。當業界遞出橄欖枝,是吶喊求救也好、是願意協力也罷,都需要主管機關伸手承接。
不過,除了官方的職責,影視圈也有自己就能改革的當務之急。

在台灣,拍片為何總是得拍這麼久?不少導演說,現場因素無法控制只好超時,而演員就是常被提及的不確定因素之一。拍手Clappin平台致力演員培訓和媒合,執行長吳芮甄指出一個常被忽略、卻很重要的存在:臨時演員。
魏德聖感嘆,拍電影這麼辛苦,沒有夢想的話,大可去做更輕鬆的工作。「你要呼應他的熱情,不要讓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魏德聖說,必須讓現場每一個人理解自己的角色和任務,不該只是把他們當工具,「他有參與感,覺得我有在拍戲,不只是被叫去拿東西的人。」
被圈內人戲稱吸走業界半數人力的《台灣三部曲》,作品量體龐大,光前置期就將近2年。舉最繁複的戰鬥戲為例,特效組、動作組、美術組、導演組全都得在前期一塊溝通,甚至得做出模型,模擬不同軍隊的移動方向、士兵種類和武器使用⋯⋯魏德聖說,「大家都清楚這場仗怎麼打,才能夠提意見,你沒有做這個分析,根本判斷不出來要做什麼事情。」構想還要落實到分鏡層次,劇組才會清楚哪裡需要用力、哪裡可以省力。
拍片也彷彿打仗,要有戰略準備。「讓工作人員等導演是不對的事情,拍一堆用不到的鏡頭,就是將帥無能,累死三軍,」魏德聖說。
既然資源有限,節流和開源就同樣重要。有導演決定先捲起袖子,改善產製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嘗試在預算、工時和品質之間尋找三贏的可能。
詹家維在好萊塢實習期間,發現美國電影劇組分工非常明確,「連槌子掉在地上,你也不能去撿,那是道具組管的,如果不見了他們要負責。」好萊塢專業人員在拍片現場各司其職,除了仰賴強大的工會,更重要的是詳盡的前置作業──拍攝預算、行程、佈景陳設圖和每個分鏡,都寫在製作企畫書裡,成員間沒有資訊落差,大家就照計畫執行。
回到台灣,電影產製停留在手工業時代。詹家維表示,美國跟台灣當然有文化差異,不是學美國就一定比較好,但有效率的工具值得借鏡。2020年3月,他開始與交通大學合作開發前期規劃App,取名為Greenlight book,或許也是希望讓台灣劇組的前置工作亮起綠燈,一路順風。
前置期,計畫內容有這些⋯⋯
- 拍攝大表:拍攝期的行政大表,讓劇組人員知道每日預定完成項目、進度和行程。
- 角色資訊:劇本中的角色背景、視覺設定和人物關係圖等。
- 順場表:依劇本分鏡順序排列的場次(Scene)表,包含該場次的劇本頁數、大綱和場景道具需求等。
- 劇本分解表:又稱breakdown,將劇本場次分別對應到成品的確切時間區段。
- 各場次拍攝計畫書:包含該場次拍攝所需的各項資訊(如:劇本、分鏡、場景圖、道具表等),以利工作人員準備和動作。
拍攝期,工作人員會拿到⋯⋯
- 完整的前置計畫書
- 當日拍攝計畫書:從各場次拍攝計畫中取出所需。
- 通告單:發給劇組人員的當日拍攝行程表,包含基本資訊、天氣條件、預定進度、拍攝內容等,詳實的通告單會包含各組人員的通告時間及個別工作項目的起訖時間。
詹家維打開其中一份範本說明,「裡面很多手寫、word的表格,其實一般劇組都會做,只是散落在不同組的腦袋或筆記裡。App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這些筆記集合起來,讓大家可以知道彼此在想什麼,方便隨時溝通、編寫、調整。」相對地,《報導者》亦採訪到前置作業一蹋糊塗的劇組,工作人員別說拿到拍攝計畫書,連拍攝大表都拿不到,只有前一天匆忙趕出來的一日通告單,上頭資訊也是掛一漏萬。

雖然尚不知新工具是否適用於所有類型的劇組,業界還是持樂觀態度。
廖蕾嘉認為,Greenlight book就像是建立一套SOP,若能結合勞動條件的提升,也許能幫助台灣逐步進展到電影工業,「只是大家可能已經習慣之前那一套模式,」她舉工會推動職業安全指引為例,需要一定的時間和精力去教育,「但使用過這個工具、知道它的好的人,慢慢就會去推廣。」廖蕾嘉也建議,從學校的影視科系出發,提供實務面的電影教育,可以培養更多種子。
「Greenlight book也是一個類似的方向,跟推限制工時是相輔相成的路,」段存馨說,當初導演協會願意加入一同提案,也是觀察到現在業界拍片沒效率,「有工時的限制,從管理資金的面向來說,超班要多付錢,製片就會有壓力要去盯場,」她也認為,知道有工時規範,大家會願意撐起來8小時拍完,「所以其實限制工時跟提升效率是一個良性的互相帶動。」
同是美國海歸派的許承傑,記得在紐約大學讀電影研究所時,「老師會要求,拍片一旦滿12小時,製片就要去把東西全部shutdown(關機),只要超過1分鐘,東西就可以丟著不用收,就可以走。」學生期間經常擔任副導和製片的他,覺得這是思維的差異。
開出1.9億票房的《孤味》,預算是4,000萬,以國片平均3,000萬製作經費的標準來說不算特別高。「怎麼在一定的預算下、在合理的工時架構下,把內容做好?」許承傑說,《孤味》40天的拍攝期,沒有超時,有時候還提早收工,一些習慣長工時的前輩反而不適應,甚至抱怨和擔憂,「業界覺得『拍得很開心(勞動條件好)的,成果就會不好』,這已經被虐待到一個等級了,概念是錯的。」
精準的工時掌握,關鍵是前置作業的完成度。許承傑舉例,拍片最怕碰到收音干擾,如果有垃圾車經過,聲音怎樣都遮不掉,只能整組人停下來等,如何減少這種浪費?「可以先去調查附近有幾台垃圾車,是幾點會來,我們可以避開這些時間拍啊,」完整的場勘有助於控制突發狀況。
遇到演員哭不出來,許承傑也說這有三個方案:花時間等他哭、明天再拍,或者拿眼藥水給他,並不是哪個方法一定最好,「只是如果試不下去,應該要有變通方案。」當拍攝時間延誤,有些東西就得取捨,為了讓大家準時收工,他常常都得合併鏡頭數(砍鏡頭),「今天講多久就是多久,這是對於自己職業的要求。」
屈弘仁感嘆,他的合約堅持簽12小時工時,有人說這樣一定做不到,「《失控謊言》本來預計拍攝期要45天,因為我(每日工時上限12小時)的關係拉長到55天,但最後41天就拍完殺青了。」事實證明,有工時和預算壓力要遵守,反而能催出效率。專業技術和工作紀律可以讓拍攝又快又好,未必會增加成本。
韓國經驗同樣可以佐證。李韓率表示,本來劇組工作人員是領月薪的「工時吃到飽」,每日工時16到18小時,但影視業被認定為勞工後開始有了「加班費」,竟然是資方率先喊出要加強前置規劃,提高拍攝現場的效率。
最根本是觀念的革新,許承傑說,「我不相信只有災難的過程才能磨出好的藝術,」大家不只是藝術創作者,還是產業工作者,「電影99%都是失敗的,但如果工作人員有好的效率經驗,才會願意用這樣的方式拍下一部片,」論斷電影的成敗,不單取決於得獎或票房等結果,過程也許更重要。
COVID-19(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台灣各行業都受到衝擊,紛紛伸手向政府要紓困,沒片可拍的電影人也一樣,跑職業工會備妥文件去申請補助。國外電影業雖受疫情影響更深,卻不會只找上政府。詹家維說,美國好萊塢有相當成熟的工會制度,工會不僅有規模也有專人在做資金投資規劃,疫情期間沒片可拍,工會甚至能發給會員維持基本生活的生活費。
當影視產業和勞動市場發展成熟,自然就比較不需要透過勞動法規去硬性制定規則,或是由政府補助金給予限制或獎勵,而是回到勞資雙方的集體協商能力。但問題就出在台灣離成熟的體制太遠,才有許多不同路徑的想像。
確定電影業工作者的僱傭勞工身分、適用現行《勞基法》第84條之1責任制、直接強化合約勞動條件、補助金政策鼓勵等解方如果都效果有限,除了直接提升片場效率、降低製作成本外,慢慢走向完整體制仍會是最終解答。
「最理想情況是工會(勞方)和公會(資方)雙方去簽訂團體協約,保障勞動條件,」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總幹事陳淑綸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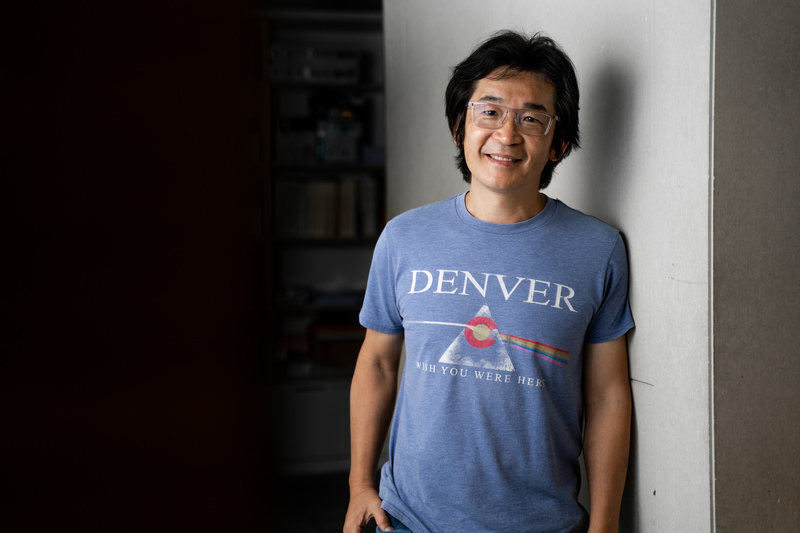
魏德聖認為,強化工會仍是必要的,如果能抽成拍片薪資讓工會運用,工會也強大到能幫電影工作者跟資方談薪資等條件,整體勞動條件才有機會提升。但他也坦言,最大問題仍是勞方自己,「如何說服他把賺來的錢給工會抽?」這仍需要業界有共識,有公信力的人或組織跳出來做才有可能。
「拍片的偉大沒有比你的生活偉大,沒有一個電影的藝術性高到需要犧牲這些東西(指合理的休息時間)。」許承傑嘗試突破台灣業界被「浪漫」綁架的思維,認為唯有每個工作者的意識改造,願意站出來為自己說話,環境才有機會改變。
韓國影視業雖然在降低工時上取得極大改善,但職安和霸凌文化問題仍相當嚴重。不過,環境確實因為韓光中心和工會的存在而有所不同。李韓率說,現在如果揭發特定劇組壓榨勞工,該劇收視率便會因抵制而直線下滑,觀眾對於幕後工作人員的處境比從前有感。
悲劇促使韓國做出改變,面對台灣目前改革的呼聲,李韓率這麼說:「不管電影或連續劇,都是想帶給大家安慰、開心和感動,如果現場情況落差很大,會覺得懷疑挫折,為什麼要面對這麼痛苦的環境。希望這個反差愈小愈好,所以也希望台灣可以改善,不要一個人難受,要團結起來面對!」
勞動部於2021年11月2日公告「電影片製作業拍攝現場工作之人員」適用勞基法第84條之一,影響人數約4,000人。勞動部勞動條件司司長黃維琛指出,電影拍攝作業有賴天時、地利、人和,在現場很難以工時8小時或12小時內完成拍攝工作,讓檯面下超時工作變長常態,這次將其納入責任制,慢慢把工時浮上檯面,讓影視工作人員可以朝向合法運作並落實勞基法。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