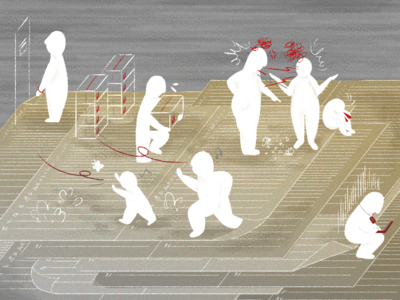2024年4月23日,憲法法庭針對「死刑是否違憲?」進行言詞辯論,該案由王信福等37名死刑犯提出申請,大法官預計7月作出判決。除了言詞辯論成為焦點外,許多死刑犯們過往被法庭宣判的罪行也再次被公開。
關於死刑犯,一般大眾印象只停留在「被捕、受審當下」的媒體照片,接下來就是處決死刑的那一刻。中間長達十數年的關押日子,他們的處境與心理不為人所知。
「廢死爭議」討論的是死刑犯的生命權,但已經定讞的死刑犯是否真的在乎自己的生命權?隨時可能被執行死刑的日子,他們如何度過?如何影響他們對廢死的看法?
一份針對全台死刑犯的研究──「死刑定讞和無期徒刑收容人訪談計畫」,預計今年(2024)9月發布完整報告,《報導者》專訪該團隊計畫主持人及成員,呈現37名死刑犯的生命經驗及反思。
涉及殺人的重大刑案發生之際,加害者嗜血冷酷、泯滅人心的形象,往往成了大眾停格於腦海的模樣。極端犯行過後,「一命抵一命」的呼聲總不免鋪天蓋地,但是否對加害者執行死刑,是司法制度探問生命權的艱難辯論;而另一面,要如何理解這群加害者更立體的面貌,同樣不易。
但要再進一步理解死刑犯,要到2020年11月,經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第40次委員會議通過、法務部矯正署同意協助,才有廢死聯盟針對台灣現存37名定讞死刑犯的全面性調查計畫。該計畫目標搜集死刑犯的生命經驗,並了解受刑人在長期關押下的監所處遇、生活情況。
身為計畫主持人的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Ciwang Teyra,長年關注原住民族、性別等人權議題,受訪時卻坦言,一開始其實並未答應接下計畫,「這是一個離我生命經驗很遠的議題。」
即便她曾在台灣人權促進會工作,早已認識許多關注死刑議題的夥伴,亦約略了解廢死的倡議,但她過往並未有研究監所的直接經驗,擔心因不夠熟悉該領域而在訪談中無意間傷害受訪者。不過,也正是因為她謹慎以待與受訪者的關係,才在廢死聯盟的請託下,加入計畫團隊。
研究計畫主持人為台大社工系副教授Ciwang Teyra,與陽明交通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教授、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召集人黃嵩立。核心團隊成員包含廢死聯盟執行長林欣怡、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執行長黃怡碧等人。
團隊並召集司法、精神、心理、社工等領域之專業人員,在廢死聯盟祕書處的陪同下,針對全台灣各看守所、監獄之死刑定讞收容人及無期徒刑收容人進行訪談。每位受訪者進行二次訪談,全程錄音記錄以便撰寫逐字稿,每次訪談時間大約1.5~2小時;為確保研究參與者的權益以及對訪談保密性的信任,訪談過程裡監所人員皆不在房內進行戒護,保留獨立空間給訪員與受訪者。
研究工具包含一份涵蓋個人基本資料、監所處遇與監禁經驗等面向的45題項問卷;以及一份半結構訪綱,主要詢問題目包含監所生活、成長背景、案件主觀感受以及待死現象等主題;再加上一份關於監所的機構問卷,希望能從監所人員的角度了解收容人日常作息、監所處遇等現況。
計畫從2021年12月開始進行死刑定讞收容人的訪談,2022年5月開始進行無期徒刑收容人的訪談,所有的訪談在2023年11月結束,共歷時2年(中間因受COVID-19疫情影響而中斷數月),總共完成全部37位死刑犯(計畫開始執行時,台灣有38位死刑定讞者,1位基於健康因素拒絕,後來該位死刑犯於2023年病逝)、以及抽樣的40位無期徒刑收容人。預計於2024年9月發布完整報告。
資料來源: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

回想最初進監所訪談死刑犯時,即使有豐富訪談經驗的Ciwang仍不免感到忐忑,畢竟生活周遭很少有死刑犯,身旁的朋友也很少犯下重大刑案。當時Ciwang一直思考要用什麼心態去面對那些受訪者,自己也上網查找資料,預先了解受訪者的案件背景。
實際與死刑犯見面,她的第一個印象就是模樣與媒體照片的樣貌有不少反差,「媒體拍起來都很凶神惡煞,加上聳動的標題,你對一個人的感受就會變那樣。」
哪些人會是進到監所的死囚?她舉訪談計畫的期中報告為例,和背後的社會環境、經濟地位可能有關,「其實你會看到有些狀況,像裡面有65%的學歷是國中以下。」
報告中也提到,死刑犯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在童年階段就因著校園或家庭環境的影響,走入風險因子較高的聲色場所或較複雜的交友圈;過往人生歷程看似完全和犯罪路徑毫無交集,但出於情緒失控、判斷力減弱等當下內外在因素而犯案。」
Ciwang理解社會大眾常會質疑,「這些人殺了人,進去(關)還可以吃免費的飯,多好啊!」但她親身訪談後,才知道原來很多死刑犯都很想要有工作、不想要不勞而獲,甚至還有死刑犯很願意將收入給受害者家屬。
若下工場作業,每個月的勞作金可以稍微多一些,但死刑犯不被允許下工場,僅有少數監所能在舍房內作業,能夠做的就是簡單的摺紙袋、摺蓮花。收入有限外,在不到2坪大的房間內,必須長時間在地上彎腰作業,摺完的蓮花就堆疊在其四周,長期接觸蓮花紙也容易得皮膚病。
關於監所內的環境,Ciwang在訪談前也從未想過如此惡劣,像是水質很髒,出來的水有些是黃的、有味道的,讓皮膚過敏、腹瀉,因此收容人得自己花錢買礦泉水,也是這些死刑犯想要有收入的原因之一。還有飲食品質的問題,像吃到鐵絲、戳到嘴破,「我想說這個是什麼狀況?為什麼可以這麼粗糙對待在監所裡面的人?」
訪談後,Ciwang更認識死囚們立體的生活樣貌,並讓她反思:「當然他犯罪,但不代表犯罪的人不用尊嚴。人會犯錯,誰都會犯錯,只是犯錯的程度輕跟重。那難道犯錯的人,沒有值得被尊嚴的對待嗎?他還是一個人啊。」

雖然外界看待死刑犯,總貼上自私、冷血的標籤,但對彭湘鈞來說,這些死刑犯也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彭湘鈞也提到,在倡議廢死議題時,大部分時候想的是生命權,但訪談之後覺得想淺了。比如說她自己很認同「修復式正義」的精神,覺得不論是加害者、受害者都可以以更立體的面貌相見,但當她問死刑犯有申請嗎?對方的回答是:「那個對受害者家屬是二次傷害,家屬連看到我,不一定要開口講什麼,看到我應該就是二次傷害了吧。」
又或是,當彭湘鈞聽著死刑犯說「不然就執行,不要在這邊折磨我們」,以及受訪者說如果有機會出獄要歸隱山林,因為知道出去之後整個社會還是沒有他們生存的空間時,她想,「也許有些事情比生命權更重要,例如一個人的基本尊嚴。」因此她也思考,沒有尊嚴、沒有希望地活著,真的比死要好嗎?
從死刑定讞那一刻算起,這37位死刑犯平均被關押13年。13年的每一天都可能被執行死刑,他們如何面對可能沒有明天的今天?
Ciwang聽過很多死刑犯對家人的牽掛或遺憾,像有死刑犯因為母親過世,心境便從「還有生活目標」變得「過一天算一天」。死刑犯當時自陳:
「關那麼久都是她來看啊,都是她來關心的,啊突然沒了啊,啊就自己就覺得啊一直想回去,可是現在沒(家人)了,外面已經都沒人了啊,就自己不要那個,就整個心放開了。」
「會怨嘆(uàn-thàn)啦、不甘願(m-guān)啦⋯⋯像我現在我就你如果要來帶(指執行死刑)就帶啊,反正我現在剩一個人啊,我沒差啊,我沒有顧忌啊。」
漫長難熬的監所生活中,不同的死刑犯有不同的生活態度,除了順其自然過生活外,也有死刑犯原本十分絕望、孤獨,但還惦念家人,而努力適應長期監禁的日子。不過,也有一類受訪者認為生活沒有意義,希望自己早點被執行死刑,甚至嘗試自殺。
有死刑犯認為,判死後拖著不執行是一種凌虐,現在的政府把死刑犯擺一邊只是為了人權的表象。這位死刑犯說:
「我就是沒有那種決意,我沒有那個勇氣去死。那怎麼辦?那就等你嘛,強迫我來槍斃嘛,那我問題就解決了啊。不然我很痛苦啊,那你要我怎麼辦?」
也有死刑犯覺得,對於時不時被拿來當政治籌碼感到悲哀,覺得自己的生命無法掌握在自己手上:
「我如果覺得我的人生沒意義了,那為什麼要強迫我活著,應該我們有自己的一個決定,就像放棄醫療一樣,那我們應該有這種權利。」

死刑犯悲觀的態度,也顯現在長期監禁下有數人出現身心狀況。看在彭湘鈞眼裡,她比喻這些死刑犯的生活很像每天都是「臨終」,「誰不會憂鬱?」有幾位死刑犯也表示,在監期間被診斷出精神疾病並有持續服用藥物。
訪談計畫中最優先的一部分是探討「待死現象」──面對死刑的不確定狀態──有些死刑犯疑似出現身心狀況:
「就一直轉不出去啊,就一直轉不出去啊,就是覺得整天都很悶這樣。」
「我在裡面曾有3次要自殺,他(心理師)問我為什麼沒有自殺,我說沒有勇氣啊(笑),事實不是。就很奇怪,這3次就是十幾年來,剛好今天想不開,決定下午要決定自己生命的時候,很奇怪,媽媽以前都不來看,就忽然跑來看,『就早上忽然就很想看你啊』、『不知道你是不是發生什麼事』,(我)心情就好了。」
訪談計畫的期中報告也指出,當死刑犯展現出生存意志低落的狀態,或者有企圖自殺的行為時,反映了監所環境以及司法制度對個人的影響。
「死刑這一塊,對我個人而言,也真的就是一個折磨。因為講白一點,我們進來裡面關,法官也確定,不管你有什麼,說真的我們也坦然接受,就是執行,坦然接受。那你又拖,你看我20歲到現在,三審定讞,到現在已經16年、15年。那說真的,我不曉得我的希望跟未來在哪裡,我不曉得以後我還能再做什麼?就算我在裡面,我說真的,你說學毛筆也好,管樂班也好,什麼也好,我覺得這只是一種,讓自己不去亂想的一個心態下面去做,不會讓自己瘋掉。」

許多人將「殺人償命、一命抵一命」視為理所當然,但Ciwang認為,「有時候我們想的都是自己可能是被害者,誰知道,我們也都有可能會成為加害者。」她舉有些人初犯就是犯重大刑案為例,裡面可能跟親密關係的、情緒的一些議題有關,她認為,如果從小沒有培養如何面對情緒挫折、衝突,那誰都有可能變成加害者,尤其情緒失控的狀態下,當下不知道怎麼處理。
她也探問,如果拉到更大的結構面,誰會有機會變成在這裡面的人?
「通常是那些在社會不利處境的人。所以我覺得難過就在這,就是說我們好像沒有去看到人怎麼今天會變成這樣,我們只是想要就這個事情上,來做很多的指責,那我們自己能不能扮演起一點,讓社會更好的角色?」
執行訪談期間,彭湘鈞也不時感到悲傷,正是因為想著社會大眾對於死刑犯殺人,要他們付出的代價不只是死,還要活得愈痛苦愈好。她舉例,許多死刑犯想自殺,但監所需特別防範,要他們好好活著,「好好活著,就是等我有一天來殺死你,這是不是很荒謬?」
彭湘鈞也坦承,會害怕提出要給死刑犯基本上的尊嚴或人權環境,認為沒多少人會重視,「背後的那種仇恨,希望別人受苦這件事情,這個情緒是讓我覺得很難受的。」
小燈泡事件曾引起各界譁然,加害人王景玉開庭爭論精神鑑定報告時,鑑定人討論王景玉如果住院的話,需要投入很大量的資源,包括醫師、護理師、心理師、社工師。旁聽的彭湘鈞想著:「這不是基本嗎?」
身為心理師的彭湘鈞,她的專業領域總是告訴來看診的個案,他們是無條件值得活著、值得被愛、值得被肯定的;但法庭給她的衝擊是,社會卻在秤斤秤兩、評估人的價值,在討論一個人值不值得活下來。
在倡議的路上,彭湘鈞也曾一度對於自己支持推動廢死有一絲動搖,原因並非覺得他們該死、或者死刑制度有什麼好處,而是她想著,「如果廢死成功,我硬是把他們留下來,我們是要把他們留下來面對怎樣的人生和社會?廢死會不會是我沒有貼近他們真實處境、一廂情願的願望?」
當然,彭湘鈞後來還是沒有轉而支持死刑,是因為她想這些是監所處遇和整個社會需要改變的問題,並不是死刑制度有必要或者比較好。就像在死刑案件辯護的工作中,聽到「因為現有的矯正資源沒有辦法教化他們,所以要判他死刑」時,她總是覺得很荒謬──「我們居然可以那麼大聲地說出國家的能力不夠,並且以一個或多個生命來為這件事承擔,而沒有感到一絲羞愧。」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