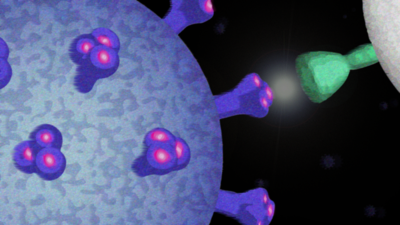以防疫之名,澳洲嚴格的邊境管制一直持續至今。今年9月,雪梨機場一週只允許750人入境,而自印度回國如無履行必要防疫規則,可能會處以5年以下刑期或新台幣130萬元的懲罰。
不少滯留國外的澳洲人得花新台幣20、30萬元,轉機、搶機位、訂防疫旅館,回家之路漫漫,一位滯留在印度的公民甚至向澳洲聯邦法院提起訴訟,認為政府權力「亳無限制」,侵害了人民移動的自由。
公衛政策及人身自由限制的平衡,是當前疫情下全球民主國家皆面臨的難題。回不了家的人付出代價,而7成以上在澳洲境內的公民卻站在政府這一方,等待國內疫苗16歲以上兩劑接種比例達8成再開放邊境。面對國家「清零」的戰術,開展出憲法層次的辯論,澳洲社會出現怎麼樣的思辨?
澳洲與台灣一樣同為島國、人口相近、也曾是防疫模範國之一。然而今年6月底,雪梨一位未施打疫苗的計程車司機,被一位帶有COVID-19 Delta變異株的機組人員感染,病毒進入社區,讓睽違一年沒有封城令的雪梨大都會再次封城。單是新南威爾斯州,自8月底起每天新增確診人數已越過千人大關。根據澳洲衛生署統計,至9月2日止,雪梨所在的新南威爾斯州,已有近3萬人確診;全國統計確診約5萬6,000人,並已有1,019人死亡。

「這感覺就像是你被自己的『家』拒絕!」已在荷蘭住超過20年的澳洲公民凱瑟琳(Katharine)接受《報導者》採訪時表示,「這樣的防疫政策,極其傷人及無情。」
截至今年7月,有高達3萬4,000多位居於境外的澳洲公民及永居者(permanent resident)向澳洲外交貿易部登記回國意願;當中包含在印度的9,000人,而這其中有173位是沒有父母陪同的孩童。在超過18個月的期間,已有一位澳洲公民在印度等待返國期間,因感染COVID-19而不幸去世。
「最傷心的是當你看到某些親朋好友在社群媒體上說,我們這些住在國外,沒有早在18個月前疫情剛爆發時回來的人是『自作自受』,」凱瑟琳說,當時澳洲政府的態度是鼓勵非本國人離境,而要住在國外的澳洲人,如果人身安全,就待在原地。「當時我們乖乖地留下,沒有急著回來,但已經超過18個月了。我也已經打了兩劑疫苗,還刻意選擇打了澳洲政府認可的BNT疫苗。(現在)荷蘭正漸漸解封的同時,另一個封城(意指回澳洲困難重重的狀況)才正要開始,」凱瑟琳哽咽,「因為他們(在澳洲的家人)出不了國,我剛滿2歲的兒子到現在都還沒見過所有我在澳洲的家人,包括他的外婆。」
在地球另一頭的智利,擁有澳洲永居身分的雷奧(René Leal)向《報導者》記者表示,「如果我沒有辦法在今年11月26日入境澳洲的話,我的永居身分將會被取消。」現年61歲的雷奧,當年為逃離智利的獨裁政府(1973~1990),加上當時缺乏技術勞工的澳洲政府向智利打開移民大門,便在1980年初與妻子決定移民,其兄弟姊妹及父母親也緊接其後移居澳洲。在澳洲完成博士學位取得永居身分後的雷奧,因陸續獲得了在美國及智利大學的聘僱,過著一個在澳洲、美國和智利之間不斷移動的生活。在澳洲獲得永居後如要申請成為公民,必須要在本土連續居住達一定年數,雷奧在三國間移動的情況,讓他一直無法獲得申請公民的資格。
雷奧全家在去年疫情剛爆發時,便向澳洲外交貿易部登記回澳意願,盼能買到政府的包機航班,「但因為智利的聖地牙哥是南美洲來往澳洲的主要機場,幾乎所有滯留在南美洲的澳洲人都聚集到這裡,再加上政府的特殊包機的時間非常不固定,從公告到可以訂購的時間可能都不到一週,更不用說幾乎都在短短幾分鐘內就會被搶購一空。」
雷奧現年26歲的小兒子、兒子的妻子和孫子(皆是澳洲公民),在2020年6月時幸運購得機票,在短短不到一週內快速打包所有家當,舉家離開智利。「因為我永居證上所註記之旅行有效期(travel facility)已過期,代表我不能自動入境澳洲,當時只能申請居民返國簽證(Resident Return Visa),無法同我兒子一起離開,」雷奧無奈地表示,他在2020年11月底才獲得效期一年的居民返國簽證許可。

看著限制國人入境人數不斷砍半,雷奧卻因搶不到回澳機票,與家人團圓的希望依舊渺茫。問起他是否有其他抵澳的方法時,他表示,「如果無法從聖地牙哥離開,那就得先到墨西哥,轉機到洛杉磯,然後再從其飛往澳洲的任一城市。但花費相當驚人,且我手上沒有這麼多錢,」雷奧解釋,疫情前聖地牙哥到雪梨單程為2,000澳幣(約新台幣4萬元),但如果要從美國或歐洲轉機的話,當前疫情下單程就要1萬至1.5萬澳幣(約新台幣20至30萬元),「這只是一個人的交通費用,還不含兩週防疫旅館支出(2,800澳幣,約新台幣6萬元),我並沒有這樣的財力(合計約超過新台幣35萬元)。」
今年7月中,澳洲中央政府發布將原先一週全國還有6,000人的入境人數砍半。接著隨著澳洲國內疫情持續升溫,於9月開始決定再砍一半,全國一週的入境上限只剩下3,000人。以雪梨機場為例,一週只允許750人入境,也就是一天只有約100人的入境人數,比一架波音747客機的載客人數還少。
- 國際防疫需要之醫療援助人員
- 無法以遠端進行之工作必要旅行
- 必須至其他國家接受在國內沒有的緊急醫療
- 出於同情或其他令人信服的理由
- 因緊急或不可避免的個人事務
- 國家利益
澳洲邊境部(The Border Force)發言人針對旅行豁免的申請時間表示:
「對於極為緊急的案件,盡量會在申請者提案離境的時間往前推1週內給予結果。而其他非緊急的案件,通常會在收到申請的2週到4週內通知結果。」
然而截至2021年7月,在超過36萬的旅行豁免申請案件,卻只有約17萬人通過,平均通過率不到一半;與2020年底(10月至12月)相比,當時平均70%的通過率,到了2021年上半年,通過率速降至40%。
澳洲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s)表示,此入境人數限制會至少到2022年,且在國內疫苗16歲以上兩劑接種比例達8成以前,沒有人(澳洲公民及永居者)可以自由出境。
依照目前的疫苗接種趨勢,澳洲中央政府預期在11月中會達到全國8成民眾接種兩劑。然而,觀看國際間疫苗接種的經驗,抵達6成後會是接種停滯的門檻。
「澳洲的邊境管制對我和我的家人的確造成了很大的傷害,」擁有台灣及德國血統的澳洲公民阿恩特(Tasch Arndt)向《報導者》表示,她的父母親人現正在台灣,在2020年3月初澳洲邊境還未關閉前先離開澳洲,然而原本以為只是幾個月的時間,似乎卻成了永無止境的等待,「現在覺得好像他們(父母)永遠都回不了澳洲了。」
阿恩特表示,父母親因為工作關係,通常是台灣和澳洲兩地各住一半的時間,「以前我從來不覺得台灣離澳洲很遠,因為只要一個夜晚(8小時)的班機就會到了。但現在出不去的我,加上回不來的他們,讓我現在覺得他們離我好遠,」阿恩特惆悵地說,「只不過是想要見自己的家人,為何如此困難?」

阿恩特的母親對我們表示,「預期是希望在年底前可以回澳洲,但政策朝夕令改,還是沒有辦法確定。之前女兒身體出問題,在澳洲也沒有其他親戚可以照料,真的很不忍心。」
莫里森今年7月時頒布「國家回歸正常之四階段計畫」。此計畫沒有明確給予預計時程,而是依照澳洲國內疫苗施打率來作為啟動下一階段的依據。目前澳洲還處於第一階段,只有在16歲以上兩劑疫苗施打達到7成時,第二階段才會啟動。莫里森表示他相信此目標能在2021年底前達成,然而他也重申:「確切的時程掌握在國家每個人的手中。」截自2021年9月24日,澳洲兩劑施打率為50.2%。
進入第二階段後,還是有可能會封城,但機率會大幅降低,然而國際邊境管制及入境人數限制並不會鬆綁。莫里森公開表示:「已經接受兩劑疫苗施打的澳洲人,可以享有較有彈性的防疫措施。」此特別規則針對已完成兩劑接種等待回澳洲的人,回家的機會將會提高,也會有限度地讓國際學生及獲有工作簽證者入境。
只有在全國達到8成接種,啟動第三階段後,國際邊際管制才會大幅鬆綁。意指已完成兩劑接種無論境內外的澳洲人,將不會受限於當前嚴峻的出入境限制,並逐漸與「疫情安全」的國家,在搭配必要的防疫措施下啟動旅行泡泡。
即便澳洲各大媒體連續有相關討論如「邊境管制如何造成澳洲每天超過3,000萬澳幣的損失」、「旅行禁令的繁文縟節造成的困惑及哀慟」及「澳洲的離境禁令是世界上為防堵COVID-19最嚴厲的公衛措施之一」等,這似乎仍不是境內國民目前特別關注的議題。
在今年5月《澳洲人報》(The Australian)所做的民調指出,73%的澳洲人相信「邊境應保持關閉至2022年中,或一直到全球疫情獲得控制」。9月22日,澳洲的貿易旅遊投資部則釋出消息表示,最晚在今年聖誕節可能就會開放邊境。
麥可拉克蘭(David Mclachlan)向《報導者》表示:「說真的,現實是大部分(境內)的澳洲人並不在意邊境管制的事,因為除了暫時不能像以前以樣出國旅行之外,我們(境內的澳洲人)其實滿無感的。」另一位剛取得澳洲公民的越南裔女性道氏(Khanh Doan)也向《報導者》解釋:「雖然我是個移民,但因為我的父母親和兄弟姊妹都已經住在澳洲了,所以目前的邊境管制其實並不太影響我。」
對於沒有家人旅居國外,或有需要離境的澳洲公民或永居者來說,他們似乎沒有意識到目前的邊境管制所產生的影響。但若有親友在外,或本身仍滯留在國外的人,卻陷入滯留在外而失業、無家可歸、錢財散盡等情況,像是活在另一個慢性焦慮的平行時空,時時緊盯著澳洲政府的防疫政策,及各大航空公司的通知,深怕自己的機票可能又要再次被取消。
由於位處昆士蘭州的布里斯本(Brisbane)將於2032年舉行奧運,昆士蘭州州長帕拉夏(Annastacia Palaszczuk)前陣子獨排眾議,堅持在東奧期間拜訪東京的行程,引發議論。帕拉夏在記者會上表示:「我在東京的出席對於確保布里斯本舉行2032年奧運,及幫助昆士蘭從新冠疫情中恢復至關重要。」但網路上有超過3萬人連署,嘗試阻止昆士蘭總理的東京出訪;連署人認為,在仍有許多澳洲國民因邊境管制回不了家的當前,昆士蘭總理的這趟訪東京行程不僅「非必要」,更彰顯其特權。
公衛政策及人身自由限制的平衡,是當前疫情下全球民主國家皆面臨的難題。在澳洲,實施防疫措施的法律依據來自於《聯邦生物安全法》(The Biosecurity Act)第477節,授權衛生部長在緊急狀況下有權採取必要的措施來預防,或控制疾病進入澳洲,或傳播至其他國家。
因此,當前的邊境管制措施是否滿足此法律條件?還是有過度管制的疑慮?
雪梨大學的憲法教授托美(Anne Twomey)向《澳洲國家廣播電台》表示,「如果有任何人願意提出挑戰,最大的癥結點會在於,根據此法律(聯邦生物安全法),衛生部長的確有權禁止國民出境,但只有在以為『避免疾病傳播至其他國家』為由下才得以成立,」托美解釋,「因此政府是否能夠『有理』地『證明』如此大範圍,且幾乎沒有彈性調整空間的邊境管制,是澳洲為避免將COVID-19病毒傳播至其他國家之必要措施?」
「然這看來並不是衛生部長之目的,其目的似乎是為了減緩國民回澳洲的速度,」托美指出。
新南威爾斯大學另一位專研澳洲憲法的教授威廉(George Williams)向《報導者》表示:「今年的確有人以憲法第92條──國家之間的貿易與流動應『絕對自由』,挑戰政府的邊境管制,但高等法院判定此舉為避免感染風險的適當且合理的措施。」威廉所指案件,為今年4月雪梨的馬克律師團(Marque Lawyers)代表73歲的紐曼(Gary Newman),針對今年4月27日開始禁止從印度返國,違反者將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令,向聯邦法院提出挑戰。
紐曼為澳洲公民,其澳洲護照於去年11月15日到期,當他在2020年3月6日因拜訪朋友而入境印度,因為疫情的爆發而滯留印度至今已超過一年。滯留期間,他所在的邦加羅爾城(Bengaluru),於今年5月3日創下單天超過2萬名確診人數。由於擔心染疫,紐曼足不出戶,但他回國之路持續受阻。
馬克律師團用兩點作為挑戰依據,一為「違反者將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懲處有超過當前防疫情況之必需,這是《聯邦生物安全法》中保障人民的關鍵要件,且衛生部長沒有考慮其他替代方案。他同時也指出,澳洲首席醫療官(Chief Medical Officer)凱利(Paul Kelly)曾公開表示:「我並沒有建議衛生部長用監禁懲處的方式。」
然而聯邦政府的法律顧問,將《聯邦生物安全法》形容為「立法推土機(legislative bulldozer)」,意為此法凌駕在任何可能保護人們擁有基本普通權利的法律保障之上。最後在今年5月法院判決「禁止國民從印度返國」為合理且必要的防疫措施。
澳洲衛生部長亨特(Greg Hunt)拒絕回應此案件,只在記者會上表示:「我相信這項防疫懲處是通過絕對謹慎,且按照適當的程序。」
「我不認為在澳洲現有的法律下,有挑戰邊境管制的法律基礎。聯邦政府在這方面擁有極為廣泛,且基本上不受約束的權力,即便這些權利在國際法上獲得承認,但國際法的承認並不一定約束澳洲國內的法律,」威廉如此認為。他意指,即便澳洲為「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簽署國之一,此公約保障「每個人皆擁有權利離開任何國家,包含所屬公民國,」以及「不得任意剝奪任何人進入其所屬公民國的權利。」
「在防疫需求的基礎之上,的確在某些原先法律保障人民的權利會被限制。然而這不代表政府可以『毫無限制』地做任何事,」代表訴主紐曼先生的其一律師布拉德利(Michael Bradley),在結案之後向《報導者》表示。
一位去年在科威特當英語老師的阿納姬(Fatima Al Anazi),在一場西雪梨大學舉辦的線上研討會裡敘述她波折的回家之路:
「因為COVID-19疫情,科威特關閉了所有學校,我也因而失去的工作,如此失業滯留在科威特超過了一年。我聯絡了在科威特的澳洲大使館,希望能夠尋求某些協助,但什麼都沒有得到。我也聯絡了澳洲外交貿易部,他們給了我非常有限的經濟協助,但現實上就是回澳洲的班機極為有限。」
阿納姬表示在將近一年的折磨後,她終於預訂上了一班原定2021年1月回澳洲的班機。於是她開始處理手上的傢俱及聯絡退租的事宜。然而就在即將上機之前,航空公司緊急通知她,由於澳洲拉緊入境人數的上限,必須取消原訂的航班。她趕緊通知房東,但房東表示已有新住戶要在同一時間搬入。
「我感覺整個人像被毀了一樣,手頭上既沒有住旅館的錢,向許多朋友求助,也沒有一個人可以幫忙,」阿納姬表示之後終於輾轉找到一個前同事的朋友願意讓她借宿,然而,「在等待的期間,我不論是經濟或是心理上都處於極為掙扎的狀態。」
「澳洲政府沒有給我任何的幫助,我覺得澳洲政府認為住在國外的我們不比在國內的人重要。」阿納姬在各種折騰後,於今年3月回到了家。

「澳洲政府的防疫口號『我們都一起在防疫的這條路上』,但我必須要說事實並不是如此。我們(指國外想返家的澳洲人)嘗試想要和政府一起走在防疫的這條路上,但政府根本沒有考慮過我們,」人在荷蘭的凱瑟琳說,最折磨人的是強烈且漫長的壓力,及昂貴的交通開支。凱瑟琳仍在等待能夠回澳洲見家人的那天。「我在國際學校裡教書,我的學生在暑假期間該回英國美國的都走了,當我的同事知道我沒有辦法回澳洲時,都無法理解怎麼會有回不了自己國家這種事。」
「對我來說,這(嚴格的邊境管制)正反映了政府對現行的防疫旅館系統沒有信心,」澳洲流行病學家圖爾(Michael Toole)向《澳洲國家廣播電台》表示,「我認為這是很可恥的。」
相對歐美西方國家的確診數,澳洲在這防疫的一年半中,因採用極為快速及強硬的措施而控制住了去年首波的疫情,並且持續到今年6月底,才又再次爆發當前大規模的社區感染。但隨著世界上對於COVID-19的瞭解已愈來愈多,現今澳洲是否仍要沿用單純將病毒拒國門之外的「防疫鎖國措施」,還是要利用累積至今的科學知識,來增強公衛上應對病毒的能力?
「我們現在其實是脆弱的,且仍用一種非常『不符人性』的方式在保護自己,」迪肯大學的流行病學教授貝內特(Catherine Bennett)在今年5月底於非營利媒體《對話》(The Conversation)上說道,「我想是時候澳洲該退後一步,並權衡是否還要繼續採取『零容忍』的戰術,來對待只是想要回家的人了。」
凱瑟琳說:「我們(滯留國外的澳洲人)感覺是被自己的家拋棄的一群人。」如此的「被拋棄感」在自2020年7月初成立,目前成員超過1.8萬人的Facebook社團「滯留世界各地的澳洲人(Australians Stuck Around the World)」裡比比皆是。社團裡,一篇9月初的貼文裡如此寫著:
「願我們都能找到回家的路,無論是何種形式,願我們都能找到到達彼岸最佳的路途。」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