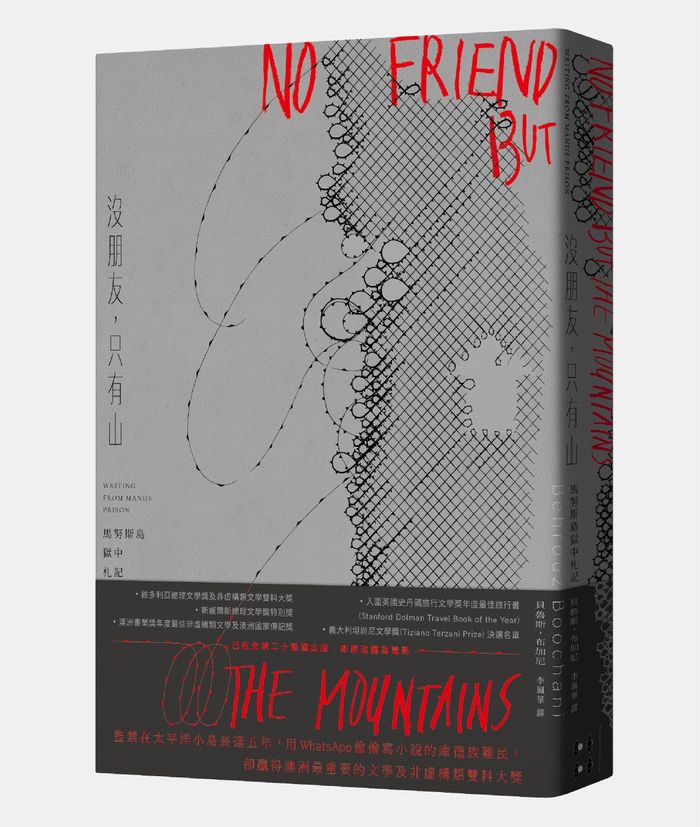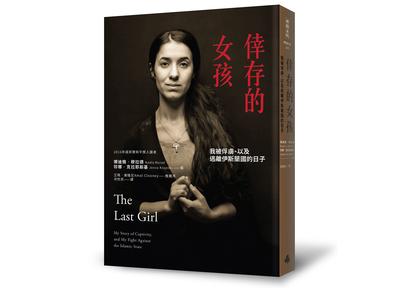精選書摘

本文為《沒朋友,只有山:馬努斯島獄中札記》章節書摘,經南方家園出版社授權刊登,文章標題與文內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所改寫。
除了山,庫德族有其他朋友嗎?
寂靜的汪洋中有一座孤島,島上囚禁著一群人,無法接觸島外的世界。他們在自己的國家遭遇各種苦難、欺壓、消音、欺凌,甚至種族滅絕,於是逃往他國尋求協助,卻被集中監禁在島上,連監獄外頭緊鄰的社會都看不到,遑論世界其他地方。他們只看得見彼此,只聽得到彼此訴說的故事。
貝魯斯.布加尼(Behrouz Boochani)是伊朗庫德族作家、記者,為了追求自由,從印尼經海路要逃到澳洲,一路經歷船難、同伴死亡,卻因澳洲政府不人道的難民政策──把所有難民都送往巴布亞新幾內亞的馬努斯島或諾魯等拘留中心──先後被監禁在兩座太平洋小島5年多,透過一連串簡訊,傳送波斯文給英文譯者兼合作夥伴歐米德.托費希安(Omid Tofighian),協力合作造就本書的誕生。諷刺的是,布加尼破例贏得了澳洲最重要的文學及非虛構類雙料大獎,而他仍被澳洲政府拒絕入境。2019年11月,布加尼終於成功逃亡至紐西蘭,以難民身分得到庇護。他獲聘為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以線上論壇及視訊合作),亦受聘於英國倫敦大學伯貝克法學院、紐西蘭坎特伯雷大學等,定期為《衛報》等各國媒體撰稿。
評審們是這樣說的:
「布加尼創作出一部無法簡化而論、融合藝術與批判理論的驚人之作。儘管如此,其本質上可說是對於布加尼所謂馬努斯監獄理論更詳盡的批判性研究與闡述。布加尼藉由對君尊體系(一借用並加以延伸的概念)的爬梳分析,為我們提供新的角度去認識澳洲的作為與澳洲本身。」
「我們瞭解布加尼,不是因為知道他的人生故事,而是透過他求生的堅韌意志、他對旁人的觀察,以及他對於他稱作馬努斯監獄的地方,其心理與權力結構的精闢分析。他的一生經歷與所學,盡皆體現於本書之中。布加尼對於馬努斯島上的生活,提供了唯有內部人才能得知的細膩描述,道出種種殘酷、貶低、屈辱、無時無刻的監視等令人震驚的細節。他在奇異的花朵和馬努斯島的月亮中發現美,在盡可能的獨處時光尋得心靈慰藉。」
日子沒有任何計畫 茫然迷失方向 依然困於驚濤駭浪的心 在新的平原尋覓安詳 但是監獄的平原有如通往拳擊館的走廊 無所不在的溫熱汗臭逼得所有人發狂。
流放到馬努斯島之後已過了一個月。我像是被扔進未知國度的一塊肉,跌入這汙穢燠熱的牢獄中。我跟一大群人同住,他們個個帶著刻劃憤怒、滿是敵意的臉孔。每星期都有一兩架飛機在島上的破爛機場降落,載來大批大批的人。下機幾小時後,他們就會在其他流放者震耳欲聾的鼓譟聲中被丟進監獄,一如綿羊送入屠宰場。
新人抵達之際,監獄的緊繃氣氛到達最高峰,人們彷彿發現入侵者般緊盯不放。他們送到福斯監獄的主要原因是這裡空間大,給新人的帳篷可以搭在偏僻的角落。西側,還有兩棟監獄相對而立,名為德爾塔和奧斯卡。不過從福斯監獄只能望見德爾塔監獄,看上去就像個籠子或擠滿蜜蜂的蜂窩。這兩棟相鄰的監獄裡沒有一丁點可容活動的空間。監獄意味著身體的對抗,人類血肉之軀的衝撞,是人與人呼吸的摩擦,而吐吶的氣息散發大海的味道,那趟絕命之途的味道。
福斯監獄內,有近四百人關押在不到一個足球場大小的區域。一排排寢室和走廊之間流竄著這群權利被剝奪之人,自四面八方來去遊走。飢餓不堪的人們製造各種騷動、挑釁、震耳欲聾的喧鬧,構成了獄中的氛圍基調。每個人都互不相識。這裡就像瘟疫爆發人心惶惶的城市,群眾狂躁不安,恐怕就算有一人站立不動,也會被人群拖著走。
人們的外表反映內心極度的緊張,目光永遠在打量對方。我們之中有一群人,儘管早已遠離在家鄉繁忙市場營生的日子,如今依然把人視為商品,也就是幾乎毫無價值的東西。被囚者四處遊蕩,茫茫不知所向。這些根植於各自特定的國家與文化的男性身體,還需要很長的時間才可能和睦相處。
監獄如同一座動物園,住滿各種不同毛色氣味的動物。這些雄性動物一整個月彼此摩肩擦踵,塞在泥土地面的牢籠裡。獄中人數實在太多,多到有種錯覺他們是棲在樹枝上、坐在廁所屋頂上聊天。每個角落都是人,甚至擠到廁所後面的小泥坑邊。等到日落時分,氣溫稍涼,椰子樹葉開始隨風搖曳,監獄營區才變成適合散步的地方。大多數人喜歡離開自己的房間。這段時間總有幾個年輕小伙子大聲喧嘩,希望主導群眾鬧騰的聲量樹立威信。這座人滿為患的叢林裡,人們透過獨特的方式建立關係。
獲得地位最簡單的方式就是認同某個群體。亦即,加入其他你認為擁有同樣身分、經歷過同樣處境的人。這麼做的動機只有一個:逃離足以將你擊潰的虛無與恐怖感。依賴團體或集體身分認同掩蓋了孤獨,提供某種逃逸路徑,或捷徑。此種集體性首先透過一同乘船渡海的經驗成形。那段艱辛路途衍生的恐懼與痛苦如此深烙於心,使他們可以本能般與渡海旅伴建立群體認同。隨著時間流逝,團體認同的基礎從渡海經驗逐漸轉向其他標誌,例如:語言和民族。一段時間過後,團體的基礎演變為單一標準,即一個人的出身:阿富汗人、斯里蘭卡人、蘇丹人、黎巴嫩人、伊朗人、索馬利亞人、巴基斯坦人、羅興亞人、伊拉克人、庫德人。
幾個月後大家開始交換寢室。被囚者向自己的同胞與說共同語言的人聚集。於是我們小小的監獄進行著某種內部移民。久而久之,共同渡海的經驗漸漸不具關鍵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共同語言的重要性。(儘管如此,共同渡海的人在整段獄中歲月仍會堅持彼此的革命情感。他們會不斷互相提醒,別忘記那段經歷形成的兄弟情義:「要記住,我們是 GDD/MEG/KNS。」渡海的共同創傷始終流倘於我們的血液,每一段海上流浪都創建一個新的想像的國族。)
長時間下來,馬努斯監獄發生的種種事件證明了,兄弟情義是被囚者僅有的慰藉,他們只能對這些兄弟傾吐個人的苦痛。時間愈久,這種情感便愈深化,進而支撐著監獄生態。在這裡,被囚者受到更嚴密的檢視,對於細微變化的察覺能力有如只能仰賴嗅覺的盲鼠一般敏銳。
我們四百人 遭受嚴密看守的四百個失落靈魂 四百位囚徒 期待黑夜到來 ⋯⋯於是便能離開 ⋯⋯繼而進入噩夢之淵。
我們是幽暗洞穴裡的蝙蝠,最細微的震動都教我們驚顫。每天,我們漫無目的反覆步行約一百公尺的距離,走得精疲力盡,就像被迫只能以不切實際且徒勞無用的單一划水姿勢,游過充滿腐臭味的泳道。夜裡,比季風更惡劣的絕望景象吹散所有夢想,一切都在苦澀的噩夢中腐朽敗壞。
監獄裡除了在圍牆和走廊間來回遊蕩的被囚者,還有其他人在內徘徊。監獄的部分區域受到G4S的人監控,G4S是一間負責管理監獄秩序的保全公司,該公司的警衛會針對一些被囚者嚴加控管。或許我該稱呼他們真正的名字:混蛋保全公司。我可以想出更多稱號,不過這最合適。或許也可以叫他們看門狗或攻擊犬。他們每人腰間都佩有對講機。三不五時,好管閒事的警衛就從口袋拿出隨身攜帶的小本子塗寫。每個人、每件事他們都要記。他們的工作準則就是當個混蛋。要在一個必須討厭每個人的地方工作,你得是徹底的混蛋才行。
從第一天起,他們的工作價值就獲得褒揚:「你們是保衛國家的軍隊,這些被監禁的難民是國家的敵人。誰知道他們是誰、從哪裡來?他們搭船入侵了你們的國家。」情勢對他們而言是一清二楚,在這裡,眼前所見的是從各地聚集而來的敵人。老天,你真該看看他們的眼神,多麼冷酷、野蠻、可恨。
入夜後,監獄營區恢復自然狀態。前幾個月營區只有兩支大燈,兩側各一支,為附近區域提供光源。燈理應要照亮空間,不過光線亮度根本照不到福斯監獄。那些夜裡,封閉的監獄宛如恐怖片場景,幢幢黑影糾纏交戰,人們只能靠直覺摸索去洗手間。
一片漆黑中,警衛的到來比任何時候都令人感到被囚的無助。當他們的影子從暗中浮現,壯碩魁梧的身材似乎更顯巨大。他們如充滿敵意的野獸持續看守監獄的每個區域。他們的凝視鑿透黑暗,你似乎無從避開無所不在的掃射。
G4S獄警(在獄中我們只叫簡稱G4S)大多勞累過度,且大半輩子都在澳洲監獄工作,面對各種不同犯人。可想而知,犯罪、刑事法庭、監獄、獄中暴力、肢體衝突、持刀攻擊已成為他們每日例行公事、所思所想的一部分。其中多名警衛是退伍軍人,曾在阿富汗及伊拉克服役多年;他們曾持續在世界的另一頭發動戰爭。他們殺過人。
殺人凶手就是殺人凶手,不容置辯。我曾讀過或聽說,殺人者會變年輕,或他們老得慢。因為這種人對別人毫不關心。殺人凶手就是殺人凶手;他們模糊、放大的瞳孔流倘出暴戾之氣。我深信眼睛反映殺人者的靈魂。
我是在觀察過好幾位G4S後得出此番體會。有次,一位G4S站在血淋淋的場面前;有年輕人在廁所內割腕。警衛轉頭對我說:「抱歉,我不懂你,也不懂這個嚇呆的年輕人。我大半輩子都在當獄警⋯⋯抱歉。」這便是他所能展現的同情限度。對一個畢生浸淫在監獄暴力裡的人,你能有什麼期待?這男人的肚子極大,與身體其他部位簡直不成比例,細瘦的雙腿彷彿只是垂掛在巨大肚皮下面,像是一對黏附於軀幹的噁心下肢。這男人承認他不了解普通人。
顯然,他已努力鞭策自己思考此事,嘗試打從心裡擠出一點什麼,什麼都好。或許他與其他同僚之間的差別在於,他確實承認自己變成一副冷血的機器。也許他認為自己缺乏同理心的原因在於獄警這個職業。除了在這個體制內待了太久以至於異於常人,他恐怕永遠找不出其他解釋。
G4S在每段班次、每個監獄的當值人數多達五十人。晚上七點,數十位G4S警衛會在德爾塔和福斯監獄中間集合,聽長官講話幾分鐘。由於隔著一段距離,很難得知熱烈談話的內容,只看見圍欄後方站著一群穿著相同制服的男人:被動的警衛擠在駐軍地一樣的地方,專注聆聽一位站在椅子上的男人講話。長官講完話,他們立刻變得像一排剛入伍的菜鳥新兵,靠近監獄後全體散開,直接走回被指派的區域。
他們如機器人般,聽命執行每一條監獄規定,規定同時涉及微觀與宏觀層次的控制,從最枝微末節到至關重要的事項皆包含在內。G4S當中也有一大部分是馬努斯島民或莫士比港(Port Moresby)人。監獄啟用後,他們被召來工作。這些人先前都忙著射魚、在叢林裡鋸木,或採收熱帶水果到島上的當地市場販賣。巴布亞紐幾內亞政府與澳洲移民部之間達成的協議規定,監獄必須僱用很大比例的當地人。因此,監獄被迫僱用這些不久前還是我所遇過最自由無拘的人們。但如今,他們被吸納進君尊體系,被吸納進監獄結構及系統性暴力的文化之中。澳洲人試圖將他們硬塞入G4S的企業文化,不過他們與澳洲警衛不同,他們有著自由不羈的靈魂。他們不可駕馭,對於遵循監獄規則及軍事化邏輯並藉以維持秩序毫無興趣。他們與君尊體系是完全相反的兩極。然而澳洲移民部除了容忍他們之外別無選擇。他們無法被規範限制,無法被組織結構約束。他們身上散發著叢林的氣息,讓我想到海中自在悠游的魚。採收水果的人擁有驚人的小腿肌,他們攀爬過最高最原始的熱帶樹木,雙腳踏過多數人類從不曾靠近的沙地。
當地警衛與澳洲或紐西蘭籍警衛之間的巨大差異顯而易見。在我看來,G4S和移民部似乎也以此為根據分派任務。當地人和來自巴布亞紐幾內亞其他地區的人無一例外都位於最低階層。每位巴布亞紐幾內亞獄警都必須遵從澳洲人的命令,不得異議。月底,他們辛勤工作整個月領到的工資只等同澳洲獄警(還是最肥胖笨重的那位)五天的薪資。差別待遇促使他們更不在乎監獄規則,至少盡可能忽視不管。
當地聘僱的獄警與澳洲獄警的區別甚至也反映在制服顏色上。當地獄警穿著紫色制服,他們的職責包括分成小組巡查監獄的各個角落。這是君尊邏輯制定的,彷彿一則公開訊息:「所有人必須明白,當地人在這座監獄的地位微不足道。他們不過是聽命行事罷了。」這一點形塑了監獄裡三組基本元素──被囚者、當地人及澳洲人──之間的關係,最終促使當地人與我們結盟。結盟關係當中還帶有某種友善與同理心。有時,當地人會偷偷抽被囚者贈與的菸;他們會在走廊盡頭或監獄的隱蔽暗角背著澳洲人抽菸,一邊忐忑發抖。有時,他們嚼了檳榔亢奮起來,便開始扯著粗啞的嗓子胡言亂語。
檳榔取自島上種植的檳榔樹,大小約如小番茄,被當地人當作天然興奮劑嚼食。他們會在地上把檳榔敲開,嚼食果實內部的物質,嚼了幾分鐘後和著唾液一口吐出來。他們將檳榔渣吐得到處都是,舉凡草地、垃圾桶、辦公室水泥地,完全毫無節制,因為這是習俗。
獄警嚼檳榔提神時,嘴巴會染得滿口血紅。常吃檳榔的人牙齒總是紅的,也就是說,幾乎所有當地人都有一口紅牙。這是馬努斯島的文化習俗。血紅色的牙齒,宛如剛埋首飽餐,從獵物屍體中抬起頭的掠食動物。我初次跟一群當地人同坐時,感覺就像被真實的食人族團團包圍。他們滿臉皺紋,鬈髮,滿口血紅的咧嘴笑,所以澳洲人才希望藉此嚇唬我們。
如此和善的人民可能是食人族嗎?這些當地僱用的獄警特別親切好相處。這副好心腸反映的獨特特質,來自於自由的天性與不受法律約束的行事作風。他們的存在使監獄生態形成較好的平衡,不過也因為他們到來後人數增加,空間隨之更為局促,環境變得更令人窒息了。
監獄裡瀰漫著強烈的畏懼與宰制感,這種陰魂不散的感受滲透了一切事物。夜晚最深、黑暗最濃之際,你會格外意識到圍牆的力量。被囚者的呼吸吐出原始的恐懼、深沉的絕望,他們緊抓噩夢不放,雙手深深環抱住噩夢,彷彿試圖藉以抵抗即將席捲廊道的狂風。監獄的盡頭持續籠罩著沉重的寂靜,這是一位形銷骨立的囚徒僅有的庇護所。
所以我在這兒,靜靜抽著菸。這時間連老蟋蟀都睡了。我看見監獄上空的椰子樹,它們好像在飛,好像涼風吹散的囚犯的頭髮。但是螃蟹還在沿著長長的圍欄覓食。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