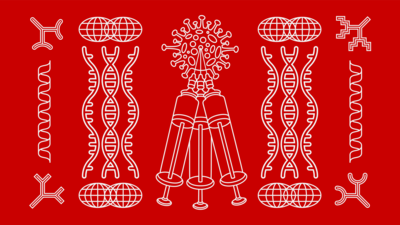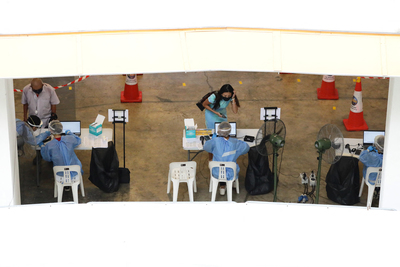10萬劑COVID-19獨立劑型的疫苗,冰存在國光生技台中潭子工廠裡,這10萬個準備抵禦病毒的小兵,能否等來上陣廝殺的戰場,還是一個問號。
「國光生技」是台灣最老牌的人用疫苗廠,但與他們合作生產四價流感疫苗的國際伙伴──法國大藥廠賽諾菲集團(Sanofi)一樣,在COVID-19疫苗研發的第一階段競逐,落入敗部區。兩家藥廠的重組蛋白疫苗跌倒路徑也相似:「臨床試驗劑量計算失誤,沒有激發足夠的免疫反應」,只能退回起跑點再來過。
然而,目前領先集團的國際四大藥廠已開始大規模量產,估計明年(2022)全球可能上看160億劑的疫苗;第一階段落居敗部區的疫苗,「復活」與「逆襲」的機會在哪裡?
72歲的國光生技董事長詹啟賢,國民黨時期擔任過衛生署長(現改制為衛生福利部)、民進黨時期亦獲聘過國策顧問,2008年在蔡英文長年醫療衛生政策核心幕僚李明亮推薦下,接下虧損連年的國光生技,由醫界、政界、再轉入業界。他在國光台北總公司的辦公室,入門處最醒目的是牆上一塊閃亮的高爾夫球場「一桿進洞」的 「見證紀念牌」,顯見他的驕傲與霸氣。
「這次COVID-19疫苗,一開始失敗在哪裡?有沒有什麼檢討和學習?」對於我們的這個提問,詹啟賢初時並不願意回應,「這個問題我不想多說,點滴在心頭。但我們從來沒有停止過。」
去年(2020)COVID-19疫情橫掃歐美,當美國的莫德納(Moderna)、英國的阿斯特捷利康(AZ)、美德合作的輝瑞BNT(Pfizer-BioNTech)陸續宣布疫苗開發的成果。法國擁有疫苗大廠賽諾菲(Sanofi)及研發出人類史上第一支疫苗(狂犬病疫苗)、「世界第一實驗室」之稱的巴斯德研究所(Pasteur),卻遠遠落後領先群,引起法國人極度不滿。
巴斯德去年5月與另一家美國疫苗大廠默沙東藥廠(Merck & Co.)合作,以麻疹疫苗為基礎開發,今年1月宣告失敗、以放棄作結,因為「產生的免疫效果不如自然康復的患者及其他已經核准的疫苗」。默沙東即刻轉換跑道開發COVID-19治療藥物,2款候選療法也已獲美國採購。
至於賽諾菲,攜手英國疫苗大廠葛蘭素史克藥廠(GSK)的蛋白質疫苗,重新設計臨床試驗,以GSK獨有佐劑,決定繼續走到最後;同時與另一家美國Translate Bio廠商合作研發新款mRNA疫苗,預計在今年第3季公布結果。
5月中,賽諾菲宣布蛋白質疫苗二期臨床效果不錯,將展開3萬5千多人的跨國三期臨床。國光生技也對我們表示,7月將在東南亞啟動二期臨床、最快要明年第1季執行三期臨床。
「其實,這次第一時間開發成功的AZ、莫德納,都不是傳統疫苗大廠,真正做疫苗是賽諾菲、GSK,還有像是我們(國光)。輝瑞過去雖有做疫苗,但不是針對大規模的傳染症、而是一般性和利潤高的特定族群,如肺炎鏈球菌這類,走高價路線,這也是它的商業定位,」詹啟賢如此解釋,「真正一直做疫苗的,反而比較謹慎,謹慎不說刻意慢,而是一開始知道風險和責任在哪。像賽諾菲,一開始劑量不足,因為有疫苗研發經驗的會認為,劑量要由小往上調,因為劑量太高、副作用會大。所以一期有免疫反應、但是沒有達到期待,重新調配再做。我們也是這樣。」
在詹啟賢的看法,「為什麼(莫德納、AZ)這些會快?因為不曉得什麼劑量是最好,碰!就丟下去,第一次開發疫苗,非要成功不可。」
國光與子公司安特羅,原本分別開發一款擅長的重組蛋白疫苗、及另一款與國衛院合作DNA疫苗,與高端、聯亞是去年4支國產候選疫苗。動物試驗階段,國光重組蛋白這支表現極好,但人體臨床一期時卻因劑量與佐劑設計問題,沒有出現好的抗體效價,國光原希望計算出調整劑量和佐劑後,繼續爭取進入食藥署緊急授權EUA資格的名單,未獲同意,必須重做試驗。據了解,國光為此再由美國聘請相關專家,加入陣容。「沒有通過就慢慢做,細節我就不多說,」詹啟賢語帶保留。
「COVID-19第一波的疫苗戰,是新科技打敗舊技術,mRNA並不是全新的平台,過去多用在癌症等其他疾病研究,因為有其副作用的疑慮,沒能敢真正使用。但它若要置換一個變異序列,可能只要15秒時間,比傳統疫苗重新培養快速很多,緊急傳染病大流行下,就取得優勢,」長庚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人類免疫與感染醫學實驗室教授顧正崙分析。
今年2月《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也指出,世界三大製藥商GSK、默沙東和賽諾菲第一時間失利,是對新技術(即mRNA)抵抗,優先考慮自家長久驗證的方法。過去疫苗研發動輒8到10年,當時默沙東首席執行官弗雷澤(Kenneth Frazier)表示,要用1到2年半生產出一支全新疫苗的想法「非常激進」。
在業界眼裡,國光雖然具備疫苗從研發到量產的完整能力,並且擁有全台最大的疫苗封裝廠,是他的強項。但因為包袱大,「在策略發展的靈活調度稍弱,也是這次落後在高端、聯亞之後的原因。」一名生技業者如此分析。

詹啟賢說,「第一波已經沒有意義,也來不及。當初目的是萬一全世界都沒有疫苗,要趕快來努力的心態去做,但現在世界都有認證的疫苗了,我們就是按部就班做完它。因為COVID-19已有流感化趨勢,就像我們的流感疫苗也有找到國際巿場,所以雖然慢了,還是看好它長期的發展空間。」
然而,全球疫苗已接種近30億劑,主要的疫苗國際廠產量都在提升,全球疫苗免疫聯盟(Global Alliance for Vaccines and Immunisation, GAVI)估計,明年(2022)一般狀況全球產量約120億劑、樂觀情況可上看160億劑。其中,mRNA平台的輝瑞預估今年可生產近30億劑疫苗、銷售額將達到260億美元(約新台幣7,250億元);莫德納則估計今年約10億劑、明年也瞄準30億劑,《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甚至指出,美國現在是「疫苗淹腳目」,後來者的機會在哪裡?
顧正崙指出,如果再加上全球近200家的小型公司,明年疫苗總產量可能會高達200億劑,「對變種病毒的保護力,將會是關鍵。」
近來,歐盟也押向mRNA、逐步放棄腺病毒平台的AZ和嬌生(Johnson & Johnson),而蛋白質疫苗將則開始加入戰局,疫苗平台明年可能重新洗牌。美國生技公司諾瓦瓦克斯(Novavax)的蛋白質疫苗,日前公布的保護力與mRNA相當,對變種病毒也會有效,但因為副作用低,受到關注。
顧正崙提到,「Novavax研發初期也蠻波折,但靠著獨家佐劑配方,以及用奈米粒子技術把蛋白質段聚合,讓結構更完整、人體細胞吸收更有效,這使得接種後的抗體效價濃度很高,而目前研究發現,如果能有足夠高的抗體,對抗新的變種病毒仍然會有效。」而賽諾菲和GSK合作的蛋白質疫苗,關鍵之一也在於GSK向來獨有的佐劑,其三期跨國的臨床試驗,目前也在擴及變種病毒株保護力測試。
「要進入國際巿場,一定要找到利基,」詹啟賢認為,相較mRNA,蛋白質疫苗便利、平價,仍有優勢,「但很多人以為,台灣的國際巿場理所當然是東南亞,事實上,東南亞的傳染病疫苗巿場很小,部分國家經濟不好,政府沒有辦法照顧到這一塊,那些國家疫苗是有錢人在打,那裡的有錢人往往會選擇歐美品牌,因為某些地方,過去就是歐美國家的殖民地,對歐美品牌比較有信心。」
國光近年與賽諾菲疫苗集團的美國子公司Protein Sciences公司合作、代工充填的重組蛋白四價流感疫苗早在美國上市,也技轉已併入嬌生集團的日本大廠的破傷風疫苗、日本腦炎疫苗等。至於開發COVID-19疫苗,已遲了一年,有什麼利基?

「清真!」詹啟賢寫下這兩個大字。
他解釋,「我認為,我們的利基在於『細胞培養』這一塊,國內其他疫苗廠是以倉鼠卵巢細胞(CHO)養重組蛋白,我們用的是昆蟲細胞(與Novavax相同),回教徒不接受動物東西進入體內、但可以接受昆蟲,他們的長老說,危急的時候也許可以用(動物),但有選擇的時候就要選擇,所以,我們不只工廠相關有國際GMP認證,也有台灣清真產業品質保證推廣協會認證。」
台灣近日的「疫苗殘劑誰能打?」爭議,背後凸顯的某部分,是疫苗原物料生產與儲備的問題,這是台灣國產疫苗更大的困境。
過往疫苗是單劑型,一人打完即抛棄,也能減少感染等問題;但去年疫情吃緊下,大家都搶原物料,國際運送也需要節省空間,採取裝10~12人多劑量瓶裝。詹啟賢說,「我們長期做疫苗,光是流感疫苗一年就製造超過千萬,有長期合約的工廠,這些原物料供應就沒有太大問題。」
但量產能力並非一蹴可幾,「靠的是長年累積的經驗跟know-how,」詹啟賢舉例,輝瑞在去年12月也發現量產有很大障礙,但他們做過肺炎鏈球菌疫苗,有這個基礎再去改進,所以現在的生產量才會變成全世界最大。
「產業就跟沙漏一樣,最上面是研發、然後動物試驗、人體試驗、再到生產,沙漏中間的『瓶頸』,就是量產。突破這個瓶頸要有技術門檻、累積的經驗。你可以蓋一家很大的醫學中心、有開刀房、有設備,可是如果沒有經驗豐富的團隊,就等於沒用。」詹啟賢受訪時特意帶著木製沙漏計時器當道具,想表達的是,「政府發展生技的方向錯了,長年只重研發、不重生產,生技發展一直卡在『瓶頸』。」

曾擔任政府閣員的詹啟賢說,「這個事我講了好幾年,國民黨政府執政時也講同樣的話,主導生技政策都是學術派,政府找過我們(業者)去討論嗎?沒有!這10多年來沒有人找過我們去談生技發展。你看看,美國政府去年要趕快把COVID-19疫苗做出來,他們疫苗專案小組找了很多產業界的人一起去討論,我們有嗎?沒有!至少國光沒有被邀請。」
要建立產業鏈,不是說每一個環節都要自己設立工廠,「全球化發展的環境下,你不可能什麼都都自己來,再大的國家都不可能,」詹啟賢提到,「2003年SARS後,很多人說疫苗廠很重要,當時一窩蜂去蓋,結果,到了2010年一半倒閉、一半被併購。像美國很大的百特藥廠(Baxter)完全退出疫苗巿場,瑞士諾華(Novartis)那麼大,也退出傳染病的巿場。有一陣子流行用細胞培養來做流感,一窩蜂蓋了細胞工廠,世界各地到處都在蓋生物反應器、發酵糟,結果在COVID-19之前倒了一半。」
台灣生技史上唯一成功開發的本土疫苗是腸病毒71型疫苗,由國衛院技轉給高端和國光子公司安特羅,高端日前宣布已完成三期解盲、安特羅則在去年即已送食藥署申請藥證審查。從2003年起啟動,走了18年之久,這是台灣生技的突破、也是台灣生技的心酸。
1998年台灣爆發腸病毒71型大流行,高達140萬名兒童罹病,共有405個孩子併發重症、78名孩子不幸死亡,當年連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都派員來台報導。是這些孩子的生命,促動台灣傳染病防治和公衛重大變革的起點,在那之後,衛生署才把原本分散的防疫處、預防醫學研究所及檢疫總所三單位合併成「疾管局」(現改制為疾管署),讓事權統一、防疫全面;更從幼稚園、托兒所開始推動「勤洗手」的觀念。
台灣也在兒科醫界的努力下,建立出治療指引,大幅降低死亡率,更被世界衛生組織(WHO)引用,嘉惠其他國家。但腸病毒好發在東南亞地區,這個巿場對歐美國家沒有誘因,台灣是全球第一個啟動腸病毒疫苗研發的國家,但5年前被中國超車,中國已開發了3支腸病毒疫苗商品。
國際疫苗到貨量仍不足、國產疫苗又卡在審查的爭議和量產的關卡,國人渴望打疫苗的壓力日增,經濟部、生物技術開發中心、食藥署、國衛院,近來積極盤點資源,再度嚐試開發代工機會。繼去年爭取AZ代工但失利後,近日由國衛院和外交部負責和美方對口,爭取授權代工mRNA疫苗,但據了解,目前美方仍未回應。
一名替國內及國際藥廠做原料供應鏈服務的業者對我們透露,「近來台灣大約有10幾組人找我們,說要做 mRNA,真的把這個想得太簡單。」 在業界有15年以上資歷的他說,傳統化學藥開發很單純,找到原物料和配方,丟入反應器裡去純化,「現在像生物藥、細胞治療、蛋白質等大分子藥,有10數個步驟,都要用不同的反應器和設備,這個巿場不大,所以,每個步驟的儀器可能是不同廠牌,需要進行串聯,不僅技術門檻很高,要把這些備齊都很困難費時。就算流程設備確立,量產後要放大對應,光是確認效果,就要花上一年,」
這位業者指出,「即使台灣順利取得美國授權代工,準備的時程,可能也需要政府目前對外宣布的時間(6到9個月生產3到5億劑),再乘以5倍的時間。」
生技中心執行長吳忠勳提到,在尊重IP(intellectual property,智慧財產權)的前提下,技術產製有幾個考量:一是知道怎麼做、也可以做得出來,但不能侵權去做;二是知道那個技術、但做不出來;三則是根本不知道關鍵技術,「mRNA目前的情況是介於二和三,它的RNA要如何混製?順序?時間?仍是業者的商業機密,就算知道配方,細節出錯,疫苗脂質的包覆率就不會好,所以只能爭取對方授權後,才能代工生產。」
但是,要爭取原廠授權,不是空出廠房、設備和備齊原物料,就有勝算。常出席全球新藥和疫苗大會的日商新藥開發平台Gemseki亞洲地區部長宋豪麟說,「你要證明你有能力和經驗,才可能爭取得到國際訂單。近年看到台廠十分努力,但沒有『履歷』,國際藥廠不會輕易下單或授權,因為產品的品質一旦出問題,是原廠要負責,也關乎他們的商譽;像是台康努力了很多年,2年前爭取到與諾華集團Sandoz AG的乳癌生物相似藥訂單,才有了突破。」
「生產mRNA技術有兩個關卡,一個是核酸合成、一個是脂質體包覆,目前台廠在合成部分,少量也許還可以,但可以做的廠商也很有限;能做脂質體包覆技術的業者,就更少了,」宋豪麟指出。
吳忠勳表示,「平時如果沒有做好準備,沒有量、沒有技術、沒有原料供應,別人不會找你代工。這些資源能量,需要做好規畫、清點,自己生產的產品佔產能多大?如果緊急時刻,哪些能量可以釋放出來?但要建立起商業產能,在特殊時刻才有空間可以挪移,」他認為,「台灣本身巿場規模雖小,但一定要有自己的生技產業,政府可以做的是,建立好制度、規範,鼓勵高科技濃度的事業,不是都要政府去做,而是讓商業自然發生。下一步先讓能力到位,然後讓產業走得穩、走得好,我相信台灣可以做得到。」

mRNA疫苗的快速到位,成功救援COVID-19疫情,其實是一場美麗的賭注。
國衛院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研究員暨生物製劑廠執行長劉士任,去年開發DNA疫苗、技轉國光子公司安特羅,但未趕及食藥署要求在9月30日前打第一針臨床試驗,預期的2億元補助獎金泡湯,一樣未進入申請EUA候選名單,現在以別的零星計畫經費繼續做,「DNA疫苗開發有其意義,因為做mRNA之前,一定要先做DNA。」
mRNA就是將RNA的片段把細胞轉變為製訂的蛋白質工廠,它可以教我們的免疫系統去抵禦病原體、也可以命令細胞產生某些缺失或受損的蛋白質。但劉士任指出,它現在其實不是完美的,因為副作用滿強,還沒找到最好的配方,過去多用在癌症或COVID-19大流行下,感染的風險和副作用相比,也是利大於弊。但你要把他應用到一般疫苗可能會比較困難一點,它和一般季節性流感的副作用比例,是差很多的。」
mRNA是否是最佳的疫苗平台?《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專欄作家巴斯廷(Hilda Bastian),針對日前德國藥廠CureVac的mRNA疫苗三期期中報告有效率僅47%、未達標,但做傳統蛋白質疫苗的Novavax成果出色做出評論:這完美詮釋流行病學家所說的「倖存者偏差」(survivorship bias)──高估某些治療方法、而低估其他治療方法,製藥(疫苗),通常是一場賭注。
「如果說mRNA要取代傳統疫苗,我認為不太可能。第一個原因,成本太高,這一次COVID-19大家花這麼多錢還可以,以後各國會受不了,特別是窮困國家和中、低收入國家怎辦?它成本太高。而且冷鏈問題,仍不方便,」詹啟賢認為。
但作為業者,也不會壓注同一邊。國光仍持續和國衛院合作DNA疫苗開發,同時也在爭取賽諾菲另一支mRNA疫苗合作的可能。

劉士任認為,mRNA的意義,在於它架構了一個治療疾病的新平台,「台灣現在的研究開發,只去為了生產COVID-19疫苗,我覺得利基不是太大。我們應該看到是『疾病』,要看長遠的,比如說未來可能有SARS 3.0、 SARS 4.0,或者威脅來得很快的新興疾病,所以必須要建立這個技術。因為這個技術的好處在於,如果你有掌握這些技術平台,它可以快速應付其他疾病,像莫德納的發展,它不是只有COVID-19的疫苗,有系列的疫苗都在後面排隊等著。」
對於台灣來說,國產疫苗之路仍要先堅持下去,雖然高端、聯亞和國光,迄今距離驗證保護力的三期臨床結果仍十分遙遠、且充滿未知。一名業者表示,台灣的生技發展最大的問題在於,「政府的政策一直很搖擺,又礙於近年爆出幾樁學術技轉扯上司法調查的大案件,讓政府生技投資逐年減少、甚至有些預算不敢執行,研發人員退回來只管研發、技轉後就丟給業者,產學無法串聯。最後業者只能各玩各的,自行找生路,走一步是一步,無法以長遠發展去規畫。」
台大醫院臨床試驗中心主任陳建煒說,以賽諾菲為例,他被法國人視為「國寶」,雖然第一時間研發受挫折,但有龐大的財力支撐,雖然有社會壓力,可是沒有政治上的阻力,得以仍按常規去進行疫苗臨床試驗,繼續把它開發出來。國產疫苗在財力和規模上難以和國際大藥廠相比,「我們可以思考的是,這世界需不需要再多一支完全新的疫苗?短期內,如果能和領先群的國際品牌進行策略聯盟,譬如成為別的領先集團品牌做混打的第二劑、第三劑配合和研究?也是一個方向。」
「無論如何,3支國產疫苗應該都要按常規的臨床試驗去完成,這條路都要完整走過一遍,這次COVID-19也許可以當成國產生技一次重要的轉型。」陳建煒認為。
詹啟賢則認為,疫苗產業不是能速成的,法國那麼大、歷史那麼悠久,不過就一家賽諾菲;英國不過一家GSK,「台灣也要想想資源整合的問題。」
不能速成、但決戰時刻往往一翻兩瞪眼。4月國光法說會上,對於自家COVID-19疫苗進度的落後,再驕傲自信的詹啟賢,也只能低聲向投資者致歉:「對不起,讓大家失望了。」
「疫苗不單是產業問題、科學問題、社會問題、政治問題,還是金融市場的問題,台灣金融巿場捲入太深,大家對疫苗產業是覺得投資賺錢,不會去看一個企業長遠給大家帶來的好處,這也會造成資金排擠,影響產業發展和社會觀感,」72歲的詹啟賢最後說,「做疫苗,真的不好玩,而且責任很重呀⋯⋯。」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