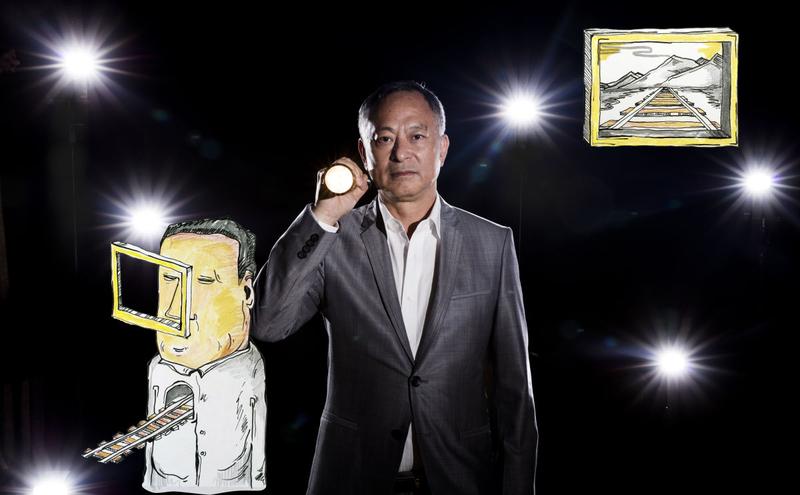8月7號,《中國電影報》引述中國國家電影局,宣稱將暫停中國電影及人員參與2019年第56屆金馬影展。消息一出,輿論譁然。沒有中國的金馬獎,會帶來什麼長短期的效應?我們是否能更看清自己的路?
中國國家電影局宣布今年暫停參加金馬獎,「這是中國特意設下的框架,要陷中國電影人於不義。這禁令損傷的不是金馬獎,而是中國自己的電影創作者,」知名影評人藍祖蔚評論,這就像冷戰時代美國和蘇聯相互抵制奧運會,真正蒙受損害的,是美蘇雙方那些青春有限的運動員。
中國電影無法參賽,這個寒蟬效應也燒到香港。
「香港電影應該是可以去金馬獎的,但是香港電影人整體是可憐的狀態,因為恐懼,不只是恐懼自己的事業,還恐懼自己的人生,」曾以獨立電影《十年》拿下香港金像獎最佳影片的導演伍嘉良接受《報導者》訪談時說。
「電影應該是一個最溫柔、最和平的媒介平台,讓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有了交集的可能。封殺金馬對中國和台灣來說,都是非常可惜的,」伍嘉良說。
中國電影快速成長為全球第二大市場,但電影與文化被國家設下的禁令反而增加。商業片上,香港與中國電影人開始埋下自我審查的種子,而中國的獨立製片,也感受到國家機器的壓迫。
習近平2012年上任後,從2013年起,中國重要的北京、南京、重慶獨立影展,一一被取消。「過去檯面下的干擾、政治操作,現在大辣辣擺在檯面上,」長年跑中國獨立影展的台灣國際紀錄片策展人林木材觀察。
2017年3月1號,中國《電影產業促進法》開始實施,更是加強意識形態審查,明文規定刑罰。
中國紀錄片《大路朝天》導演張贊波稱那一天是「中國獨立電影最黑暗的時刻」。
「像我這樣已經捨棄和商業體制去發生關係的創作者,都感到途徑愈來愈窄,」張贊波告訴《報導者》,他詳讀了一條一條的法令後,真切感覺到中國政府的設計狡猾、用意歹毒。從製作、發行、放映到參展,都要經過審查,否則就是犯法。

《電影產業促進法》的兩個尖牙,第一個是拍攝許可證,第二個是俗稱「龍標」的公映許可證,兩個證各自掐住電影產業鏈的頭尾兩端。要拿到拍攝取可證,劇本得先通過審核。即使拿到拍攝許可證,等到要公開播映,如果沒拿到公映許可證而參加國外影展,就是犯法。
「它可以查你帳戶、查你資金來源,就算你不怕,也沒人敢跟你合作。人家是電影改變國家,咱們是國家改變電影,」張贊波批評。
《電影產業促進法》第49條明文規定「發行、放映未取得電影公映許可證的電影」、「取得電影公映許可證後變更電影內容」、「提供未取得電影公映許可證的電影參加電影節(展)」的行為,將會受到吊銷許可證、沒收影片及違法所得、罰款等,「違法所得5萬元以上,並處違法所得10倍以上20倍以下的罰款」。
先前的《電影管理條例》中也有類似規定。中國的電影藝術始終掙不脫政治這個緊箍咒。
13年前,中國第6代導演婁燁就曾因為《頤和園》沒有拿到「龍標」就參加坎城影展,被罰5年內不得拍片。《頤和園》裡,描述兩名青年跨越十多年的激情,背景穿插著六四等社會事件,這樣從戀愛瞥見政治巨靈的電影,至今中國觀眾無緣得見。今年2月,中國第5代導演張藝謀以文革時期為背景,描述勞改營囚犯溜出農場看電影,與一名孤兒結下不解之緣的《一秒鐘》,也因為中國官方宣稱的技術審查,被迫在柏林影展撤展。
公權力的荒謬令張贊波感到憤怒,但人民的攻擊卻令他感到悲傷。當他8月7號在Facebook直言批評中國抵制金馬獎時,網路一片怒罵,要他「換個國籍」、把他扣上台獨分子的帽子,甚至有網友留言:「你在台獨這種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想要博眼球、搞個性,那我只能問候你全家。」
「我其實只是在爭取每一個人都應該有的權利,怎麼你們倒覺得這個權利可以隨時交出去,」他接受《報導者》專訪時更透露,現在網路上人人喊著要「封殺」、要「舉報」的氛圍,讓他覺得中國整個社會彷彿又倒退回到文革時期。
反觀金馬獎,因為兼容並蓄,匯聚兩岸三地電影創作人才,仍被公認是華語圈最具影響力的電影交流平台。
曾擔任金馬獎評審的導演易智言接受我們採訪時指出,金馬獎最珍貴的,不是獎落誰家的片刻煙花。金馬獎的能量與聲譽能夠累積,是因為在評審團裡就納入香港、中國評審,在評審的過程中,兩岸三地評審對入圍電影能有最真誠的批評與意見交換。彼此歧異的觀點,在金馬獎激盪沖刷,年復一年,涓滴成河。
「如果認為我們只在乎得獎時致詞那30秒,那是把我們電影人瞧小了,」易智言說,與他相熟的中國資深導演如婁燁、王小帥等,倒不是特別在意得不得獎,但是,以電影藝術為終身職志的導演們,總是特別珍惜金馬影展這個影人能坦誠交流的機會。
「我替我的中國朋友感到惋惜,不是惋惜不能參展,而是惋惜了失去這個交流的機會。這種創作者和創作者可以面對面坐下來討論,甚至彼此批評的機會。這種交流,對導演來說,比起得獎,是更大的收穫,」易智言不諱言。
「這個禁令,可能短期內打擊了這一屆金馬獎的廣告、收視率、影響力,但也同時凸顯了兩岸在創作環境與體質的嚴重落差,愈發彰顯出金馬獎的獨立性和公正性,」藍祖蔚受訪時強調,金馬獎不必自亂陣腳,只要去翻翻看金雞獎的得獎紀錄,有多少次歌頌周恩來和毛澤東的作品得獎,就會知道連中國影人自己都不相信金雞獎。
有「華語奧斯卡」之稱的台灣電影金馬獎從1962年創設以來,已舉辦55屆,從1996年開始接受中國電影報名參加。那一年,姜文首度執導《陽光燦爛的日子》,拿下最佳劇情片、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改編劇本等6項大獎,風光無限。
隨著中國成長為電影大國,中國電影也愈來愈常入圍金馬獎。2018年的金馬獎甚至被戲稱為中國年,入圍最佳劇情長片的5部作品,只有《誰先愛上他的》來自台灣,其他4部全部來自中國;中國導演更壟斷了最佳導演的5個提名。
「(金馬獎)這麼多年輕導演的作品,代表著中國電影的希望和未來,」去年憑《影》拿下最佳導演的張藝謀,站在台上頒獎致詞時曾這麼說。
儘管張藝謀口中的「中國」,與台灣紀錄片導演傅榆所說的「中國」,涵義大相逕庭,但對許多中國電影人而言,金馬獎的分量未曾稍減。
在中國,不管是工業式的商業劇情片導演、或是手工式的獨立紀錄片導演,對於中國政府近年來以政治凌駕藝術的政策走向,有的憤怒抗拒,有的不慍不火,但都練就出一身帶著無形手銬腳鍊跳舞的本事。
「金馬獎還是華語圈中最具公信力、最多元、最包容的,」張贊波說,很多在中國被禁、封殺的電影,透過金馬獎有了被看見的機會。
金馬獎,仍是許多中國年輕導演嚮往的舞台。台灣自由的空氣,仍然刺激了當代中國年輕導演的創作。從2010年開始頒發的最佳新導演獎項中,9次中就有4次頒給了中國新銳導演,分別是文牧野、畢贛、陳建斌,以及烏爾善。
「胡波如果沒有來過台灣,就拍不成《大象席地而坐》,」藍祖蔚說。《大象席地而坐》拿下去年金馬最佳劇情片大獎,台上李安溫馨擁抱前來為已逝兒子拿獎的胡波母親的畫面,還留在人心。
兩岸三地的導演一致期盼,這個禁令只是暫時現象。
「我覺得有矛盾、有摩擦是必然,但是中國人要學會不要把所有反對聲音都當成敵人,不要落入政府塑造的這種戰爭思維,政治的黑手不應該伸入兩岸電影的盛會,」張贊波說。
「不同的價值、不同的想像、不同的電影都可以在金馬這個舞台出現,彼此衝擊,很希望這個交流平台不要被一時的政治壓垮,現在香港很羨慕台灣啊,」伍嘉良說。
但若中國抵制金馬獎成為長期現象,易智言認為,沒有中國的金馬獎,就必須仔細思考金馬獎與台北電影獎的定位差異。
而金馬獎也必須持續開放。林木材認為,金馬獎的公信力、多元化不會受損。「中國電影參展數量是最大,但不一定質是最精。金馬獎的探照燈也可以多多照向星、馬的華語片,看到更不一樣的創作,」他說。
當中國封殺金馬獎之後,台灣電影在惋惜之外,還得穩紮穩打,厚積能量,才能持續在中國政治杯葛的陰影下,開出自由的花。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