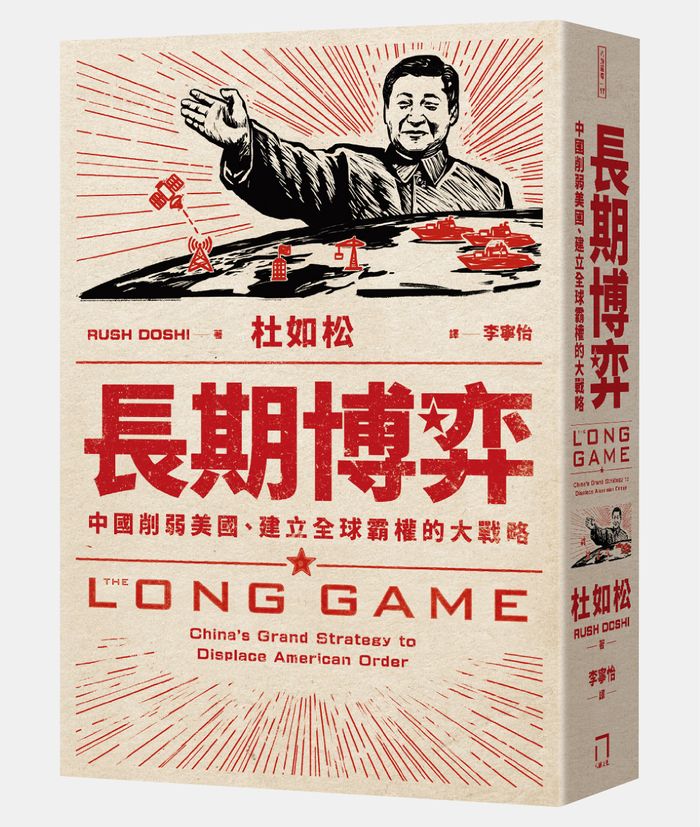書評

杜如松首先定義「大戰略」是一國為達成其安全保障相關目標而刻意規劃的治國方略(statecraft),接著引用沃爾滋(Kenneth Waltz)影響深遠的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指出國際間存在著階級式秩序,霸權會對他國行使權威並產生支配,支配的類型按照國際政治經濟學家吉爾平(Robert Gilpin)的界定,可分成強制力(迫使服從)、誘發共識(提供激勵誘因)及建立正當性(可正當指揮從屬國)三者。
其次,杜如松強調中國的列寧主義黨國體制有利於統合協調、排除內部各方利益掣肘,形成統一的戰略,並可分3個時期歸納為「削弱」(Blunting)、「建立」(Building)和「全球擴張」(Global Expansion)三者。
1970年代美國在「聯中制蘇」戰略下與中國進行合作,此時中國奉行「韜光養晦」方針,遷就無威脅的美國。但隨後經歷天安門事件、波灣戰爭和蘇聯垮台的三重衝擊,轉為認定美國是對中國各領域安全的最大威脅,在美中實力有一大段差距的情勢下,維持「韜光養晦」、但削弱美國在東亞和雙邊關係上對中國可能的箝制。
2008年金融海嘯後中國認為雙方國力大幅拉近,逐漸揚棄「韜光養晦」,積極建立有利於中國利益的國際秩序,推動周邊外交和創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國際組織;2016年川普(Donald Trump)當選和英國脫歐,中國認定西方國家無法應對民粹主義和種族與經濟不平等的挑戰,2020年以來的全球疫情蔓延凸顯中國治理模式優於西方,「東升西降」已是大勢所趨,於是加快全球擴張的腳步,積極尋求主導聯合國等國際組織,與區域(如阿拉伯世界國家和拉美國家等)發展以中國為中心的多邊關係。
最後,杜如松提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政策建議:考慮到中國經濟量體之大,採取對稱手段(例如提出基建計畫大灑幣以抗衡「一帶一路」)並非上策,應該借鏡中國的削弱和建立的經驗,以不對稱的方式遏阻中國擴張,同時強化美國自身實力,以因應中國挑戰美國霸權及其主導的自由開放世界秩序。
此外,杜如松對中國自古在東亞的封貢秩序和天朝上國心態,及清末民初以來救亡圖存的憂患意識所形成的現代中國民族主義隻字未提,或許因為寫作目的是帶出最後的政策建議,全盤性的溯源和追索無助因應眼前迫切的戰略競爭難題。
此外,《長期博弈》字裡行間引用大量中國高層文獻,包括從鄧小平到習近平歷任中共領導人、與錢其琛、戴秉國、劉華清等高階官員的談話或回憶錄、高層會議的官媒報導和國防白皮書等正式文件,這點堪稱本書最大價值之一。
另一方面,書中卻幾乎沒有社會科學主流的量化分析(例如中國的GDP增長率等總體經濟數據,或對外援助金額、海軍逐年造艦數等),分析的對象與研究成果也是陳述中國戰略觀點與作為的演變,並一定程度上把論證的有效性建立在文獻的厚度(反覆徵引官方與學者針對同一概念或主題的類似言論頗有堆砌之感),因此更像是以文獻分析為主流的歷史學研究。
不過,由於中國政治資訊的封閉,外界只能從中共釋出的官方文件和宣傳中的蛛絲馬跡(例如領導人們的談話出現在《人民日報》頭版的次數,或是報導主題的暗喻、指桑罵槐或借古諷今)推敲政局,這種方式常因流於陰謀論和臆測被戲稱為「tea-leaf reading」──亦即猶如用茶葉散開的形狀占卜,但杜如松採用權威的正式文件和具代表性的重量級學者(尤其是具官方背景者)的觀點,使其文獻分析相當有說服力。
最後,《長期博弈》很少陳述美國對中戰略的觀點與作為(彷彿預設讀者已具備相關背景知識),只單方面陳述中國對美國懷有根深柢固的敵意,像是法庭上的一紙訴狀,控訴中國處處以美國為假想敵針鋒相對,也像是民主黨版的懺悔錄(白邦瑞是共和黨籍);不過相較白邦瑞使用「祕密戰略」的副標題,暗示中國的戰略是以隱匿、掩蓋和欺瞞的謀略騙取美國放下戒心,似乎美國有無辜之處,杜如松則更直白地展示中國的戰略野心始終表露無遺。
對生活在台灣的我們而言,中國的霸權與威脅早已是生活中的日常。但對美國人而言──特別是在多年「交往」(Engagement)政策下已有著千絲萬縷的交流或利益──可能仍會感到震撼。例如知名中國研究學者、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21世紀中國研究中心主任謝淑麗(Susan Shirk)便在推薦詞中坦言,本書說服她重新審視自己之前認為中國的外交目標是開放且具有彈性的觀點。
既然中國要削弱並取代美國的戰略意圖從未在中共高層的世界觀中缺位,那麼隨之而來問題便是:為什麼美國在冷戰結束後對中國的潛在威脅視而不見?
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攻勢現實主義理論指出,當一個新興強權崛起時必然會挑戰既有霸權支配的秩序,他在名著《大國政治的悲劇》2014年新版的序言中自述,在1990年代動筆寫作時便注意到中國崛起後將不可避免地循美國稱霸的路徑和美國發生衝突、引發亞洲軍備競賽,亦即中國宣傳的「和平崛起」是不可能的,但這樣的預測在2001年該書問世時並未被廣為接受。
另外,許多人將當今美國對中國威脅形成跨黨派共識歸因於習近平2012年上任後對內對外益發蠻橫的作為,例如經濟脅迫、戰狼外交和關押新疆維吾爾族的所謂「再教育營」。但從杜如松的分析可以看出,挑戰美國其實是中共高層長期以來的共識,因此單單歸咎習近平個人而忽略中國的黨國體制,可能偏離了答案。
對中國戰略誤判的原因應該出在美國自身。例如川普時代的白宮國家安全顧問麥馬斯特(H.R. McMaster)在其《全球戰場:美國如何擺脫戰略自戀,面對全球七大安全挑戰?》中指出,美國在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戰略上往往犯了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戰略自戀論」的錯誤:只從美國角度看世界,認為世局走向將依照美國的決策或計畫而定,低估他國影響力,導致美國擺盪在過度自信(冷戰結束後)和過度畏縮(2008年後)之間;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曼德爾邦(Michael Mandelbaum)在《美國如何丟掉世界?後冷戰時代美國外交政策的致命錯誤》一書中全面檢討冷戰後的美國一系列失敗的外交政策,認為單極獨霸的美國禁受不住敗家的誘惑,揮霍資源投入改造他國、造成自身國力衰退,且相信能透過經貿「和平演變」中國,對第三波民主化和現代化理論過於樂觀,也低估中國抗拒體制被動搖的能耐。
《長期博弈》一書較為可惜之處,是它沒有對美國的戰略誤判和為什麼中國有能耐實現其戰略目的(例如成功取得美國的「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做出解釋,也未比較和評估美中體制差異對戰略競爭產生的影響(中國學者自信能勝過美國的本錢之一是列寧主義黨國體制較民主選舉更易形成長期穩定的戰略)。但杜如松的字裡行間透露出中國巨大的經濟吸引力是導致戰略誤判的原因之一,最後對美國衰退論的討論也表達對美國體制自我糾正錯誤的信心。

拜登政府上任已經一年多,此際恰可檢驗其對中政策與《長期博弈》的政策建議有多少相符,或說杜如松的政策建議有哪些被採用。
但是在今年(2022)5月24日Quad峰會與6月26日G7峰會上,成員國分別提出500億和6,000億美元提供印太和全球進行基礎建設和應對氣候變遷、數位經濟的投資,抗衡中國「一帶一路」意味鮮明,則似乎與杜如松不支持對稱方式的立場相左。
因此在基礎建設計畫上縱然如杜如松所言,通過與在地公民社會和媒體合作,揭露中國「一帶一路」的貪腐、剝削和債務陷阱可以削弱其正當性,但開發中國家對基礎建設的龐大需求不會因此消失,單單抵制或破壞恐怕不足以阻止繼續與中國合作,美國終究必須拿出相當的誘因建立基於規則的自由開放世界秩序。因此,削弱與建立與其說是手段,不如說是描述美中之間的攻守之勢,當中國處於守勢時著眼的是削弱美國的影響力,在國力蒸蒸日上後便轉守為攻。
另外一個檢視杜如松「以彼之道、還施彼身」政策建議的觀察點,是中國籌建非西方國家大聯盟的雄心。
杜如松建議美國應加入或鼓勵盟友(如日本)加入中國主導的多邊進程,在中國的小圈圈內削弱中國影響力,但中國似乎也已有提防,將重心放在美國最緊密盟友圈(如北約和G7)以外的多邊組織,因此在國際政治對中國採取削弱方針的可行性還有待觀察。
最後,誠如遠景基金會執行長賴怡忠指出的,從川普到拜登政府的對中政策態度出現三個轉變:民主黨政府同樣認定美中是競爭關係,但更強調投資和壯大美國自身而非反制中國弱化美國競爭力;捨棄區分中共與中國人民、寄望中國內部改變而表明無意尋求改變中國體制;和對台灣重要性的定位從民主與專制的價值之爭轉為強調地緣政治和國際利益的重要性。再加上拜登多次稱考慮調降對中關稅、仰賴盟友在地緣政治和軍事平衡中國以尋求維持現狀,和出現杜如松主張的不對稱方式思維,顯示美國在攻守之勢中似有戰略收縮的傾向,美中博弈的態勢可能已從過去中國抵禦美國「和平演變」,轉為美國防守中國威權主義擴張與顛覆自由民主體制。
俄烏戰爭爆發後,烏克蘭軍民憑藉堅韌意志和西方軍援,以標槍、刺針飛彈和城鎮戰等不對稱作戰方式取得不少戰果,使得美國更理直氣壯地要求台灣以不對稱作戰的方針建軍;然而正如杜如松指出的,中國自己就是不對稱作戰的老行家,多年來持續精進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能力、2020年更試射有「航母殺手」之稱的東風-21D和東風-26反艦飛彈,想必在無人機等其他武器戰術更無懈怠之理,台灣防衛構想是否應單單壓注在不對稱作戰,值得三思。
其次,台灣可以從杜如松的不對稱方式中學到什麼?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教授郭育仁在華視《三國演議》節目提到2018年訪澳時,澳洲外交部希望台灣能協助開闢中文電視台,打破中國壟斷唯一一間中文電視台的大外宣,筆者不禁思考,既然台灣無法跟中國拼財力,與其耗費鉅資從頭建立《TaiwanPlus》這類新平台卻成效甚微,不如將同樣的大筆預算用在既有媒體從事跨國合作,例如讓《中央社》的報導可以在各國主流媒體轉載(中國多年來深耕大外宣的一環便是由《新華社》與各國主流媒體簽署供稿合作機制),或是補貼外國主流電視台騰出部分時段播放台灣新聞或戲劇節目,效益恐怕都比從零開始建立新媒體平台的效果更好。
同樣的,中國現在積極爭取的太平洋島國中,台灣過去雖遭逢索羅門群島和吉里巴斯斷交的挫折,但仍有帛琉、吐瓦魯、馬紹爾群島和諾魯等4個邦交國,台灣若更積極透過邦交、援助和經貿合作降低該4國受中國的影響,並促使他們在太平洋島國論壇中監督與中國的合作關係,不僅削弱中國的勢力擴張,符合美國利益,也有助提升台灣的地位與價值。
最後,美中博弈未來將是全球政治的主軸,然而中文對多數美國的中國研究者而言仍是不低的門檻,這也是杜如松之輩的優勢;無論在情報或研究,美國勢將需要更多中文人才,而這一點恰恰是台灣資源最豐沛的,如何引進更多台灣人才進入美國學術和戰略圈,是台灣值得努力的方向。
鄧小平的一句「黑貓白貓,能抓到老鼠就是好貓」傳誦多年,稱霸世界多年的美國轉為學習中國稱霸的治國方略,對照清末魏源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諷刺地令人喟嘆;不過畢竟《孫子兵法》首篇〈始計〉篇開宗明義便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叢林中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獲勝與生存比虛榮的面子重要得多,杜如松的建言反映出美國人務實的一面,今天的美國或許最需要的就是能抓到老鼠的那隻好貓。
(編按:本文由八旗文化提供,標題、內文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改寫。)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