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選書摘

在傳統中國,歷史詮釋是各方角力的戰場,對政權的權力合法性至關重要,新王朝會為前朝修史,證明自己有權取得「天命」,施行統治。而到了當代中國,中國共產黨也繼承了老祖先的「美德」,為了穩固政權,他們會不惜竄改歷史,粉飾過錯、隱蔽事實來美化自己的統治。然而,有本在1960年誕生於中國西北鄉間勞改營的雜誌《星火》,改變了這一切。
當時,中國正值人謀不臧引起的大饑荒,全國各地有千萬人死亡,但訊息卻沒辦法讓多數人知曉。有群下鄉的大學生親眼目睹了農民餓死和吃人的場面,也看到了政府如何殘酷懲罰或殺害上訪求救者,他們覺得有必要做點什麼,把正在發生的事情傳出去⋯⋯於是,他們決定辦一本雜誌。
學生們將這本雜誌命名為《星火》,取自「星火燎原」之意。但,這本雜誌沒能出到第二期。幾個月之內,與該雜誌有關的43人被逮捕。3人後來遭處決,其餘人都被送去勞改多年。
50多年後,有一群獨立的中國記者、作家、導演在意外中發現了「星火」的故事,也尋到「星火」事件的見證人跟倖存者。這群自詡為「地下歷史學家」的人們不僅挖掘出「星火」的故事,也力圖挑戰反右傾運動、文化大革命、天安門事件、SARS、COVID-19疫情中官方的歷史敘事,打開中共政權謊言下的事實。
曾任《紐約時報》等多家外媒特派記者張彥(Ian Johnson),在中國生活20多年,他如此描寫:「『星火』燃燒了不到一年似乎就熄滅了。在中國共產黨執政近四分之三世紀的時間裡,它不過是反對黨權力濫用的無數小規模反抗之一,可能轉瞬就被遺忘。但在許多中國人看來,它的故事如今已經成為抵抗一黨專政的代名詞。」
張彥將這群「地下歷史學家」的故事,寫成《星火:中國地下歷史學家與他們的未來之戰》,本文為第7章部分書摘,經由八旗文化授權刊登,文章標題經《報導者》編輯所改寫。
1990年初,中國最著名異議人士帶著妻兒,困守在北京美國大使館中,眼睜睜望著他們的國家在暴力與嚴懲中顫抖。在前一年的6月,北京當局鎮壓學生領導的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殺了數以百計學生,讓更多學生流亡。方勵之逃進美國大使館,等待讓他離境的交易。在帶著家人藏身大使館,於一間原本用作診療室的無窗房間住了13個月後,他終於得以移居亞利桑那州。
跌落失望谷底的方勵之在大使館裡寫了一篇〈中國失憶症〉,解釋悲劇何以不斷降臨他的國家。方勵之寫道,共產黨以絕對徹底的手段控制歷史,讓絕大多數中國人始終不知道它那套永無止境的暴力循環。結果是,中國人只知道他們親身經歷的事。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知道文革是什麼樣子,但對文革前10年發生的大饑荒一無所知。他回憶道,參加天安門抗議的那些年輕人,就連10年以前發生的「民主牆」運動都不知道,更別說文革或大饑荒了。方勵之寫道,由於每一代人都對過去一片空白,遂讓共產黨可以無中生有,任意進行它灌輸運動。
每過10年,這種將真實歷史從中國社會記憶中完全抹掉的事總是一再發生。這是中國共產黨「忘記歷史」政策的目的。為了讓整個社會陷入持續不斷的失憶中,這個政策要求凡是不符合共產黨利益的歷史訊息,不能在任何演講、任何書籍、任何文件,或者其他任何媒介中表達出來。
在方勵之撰寫這篇〈中國失憶症〉時,中國共產黨對資訊的控制幾已堪稱滴水不漏,只有極少數最有關係的人才可能知道這個共和國歷經的種種創傷,而在人口十幾億的中國,這樣的人可能只有寥寥數千人。共產黨發表了一些有關文化大革命的資訊,但它既有選擇性,能夠取得的人也有限。例如大饑荒,或在1950年代初期造成好幾百萬人死難的土地改革等其他事件,在中國都是禁忌。大多數人只知道本身親歷的事,對其他一切幾乎一無所知,而這正是黨的計畫。
相對於過去,方勵之這篇文章這時看起來似乎更切中要害。這時的共產黨擁有強大的技術官僚體系作為管控歷史的後盾,中國領導人已經鐵下心腸,要洗白過去,要創造讓國民銘記在心、信以為真的故事。中國似乎已經徹底染上了失憶症。
但實情並非如此。方勵之準確描述了1990年代初期中國的狀況。不過在接下來幾年,一種新趨勢開始出現,政府不再能壟斷歷史,例如新科技為許多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開創了一種新集體記憶,而為了因應這種變局,共產黨管控歷史的手段也愈來愈嚴厲。
德國的埃及古物學者楊.阿斯曼(Jan Assmann)在古文明的研究中,找出了兩種形式的記憶。一種是「文化性記憶」(cultural memory)。這種記憶用神聖經文與信念將一個社會結合在一起,它們不必真實,而且往往也沒有人指望它們全然精確。但大家共享這些神話與故事,從而聚在一起。埃及人相信法老王是類似神一樣的人。希臘人相信雅典娜是雅典守護神。猶太教、基督教與穆斯林相信「大洪水」,相信諾亞造方舟救了人類。中國人相信大禹治水。這種文化性記憶能答覆有關我們源起的基本問題,從而將人群結合在一起。它們出自學者、聖人或朝廷指定史官等專人手筆,然後代代相傳。
另一種是「傳遞性記憶」(communicative),是人們或他們的家人直接經歷的記憶。這類記憶一般出現在三代內,也就是說這些記憶是一代人,或他們的父母或祖父母的親身經歷,可以直接傳遞,通常經由口述,在家族內或向友人傳遞。這兩種記憶一般不會衝突:文化性記憶講述創造文明的神話故事,傳遞性記憶則是個別人士對現況的敘述。
共產黨將這兩種記憶攪在一起,用神話解釋不久以前的過去。這樣的神話與人們的傳遞性記憶,換言之,就是人們透過本身直接經驗,或透過與仍然在世者的對話,知道的確實屬實的現實,兩者是互相衝突的。直到不很久以前,對共產黨來說這還不是大問題,因為它只造成幾小塊脫鉤群體。儘管或許有數百萬人知道共產黨用極端手段在天安門清場,但黨控制了教科書與媒體,迫使這些群體孤立,與社會脫鉤。其結果是,大多數人相信政府有關天安門事件的說詞。隨著災難目擊證人一天天老去凋零,他們的記憶也逐漸灰飛煙滅,留下來的只有政府的版本。這就導致方勵之所說的失憶狀態。

但在那以後,兩件事有了變化。其一是,一個人就算早已作古,即使不能控制政府媒體,那人的記憶仍可以保存下來,傳給後世。其二是,遭到孤立的群體現在有了串聯的能力。大群民眾於是發現自己並不孤單,發現官方說法與自己親身經驗不符的大有人在。在本書第四章結尾,中國時評人士崔衛平就說,《星火》雜誌的存在意味她與其他異議人士並不孤單,就是這個意思。
造成這種變化的轉折點是數位科技。這指的不是30年前人們心目中的「網際網路」。30年前,網際網路像是一股無法控制、幾近神奇的力量,可以跨越審查、在全球各地傳播真相。但沒多久情況明朗,獨裁國家很快學會運用審查與軟體控制網路內容。
但數位科技讓人們可以運用過去不可能辦到的方式分享經驗。《星火》又一次成為範例。《星火》出刊未久就遭查封,所有複本都被沒收。當文革結束,當事人可以檢視人事檔案時,他們見到警方保存的《星火》複本,用手將它們抄下來。但這些手抄本仍然只是他們的私人珍藏,只在幾十位劫後餘生者之間流傳。
這些記憶研究中所謂「運載群體」(carrier groups)的人群,如果能接觸媒體,原本可以在中國造成立即影響。儘管他們大多不具備這種條件,但由於1990年代數位科技興起,他們的知識仍得以流傳。以《星火》為例,他們可以將這本雜誌轉成PDF檔,用電子郵件傳給其他人。就這樣一點一滴,滾雪球般,這本雜誌的名聲愈來愈廣。原本大體屬於個人記憶的東西成為集體記憶。不過,並非所有中國人都知道這本雜誌,但有相當多的人知道它,而且其中許多是受過高等教育、有影響力的人。
這類科技轉型使許多中國人可以輕易看穿政府宣揚的那套歷史版本。政府的宣傳官員可以用大量官方說詞在媒體洗版,可以設法阻撓他們不喜歡見到的資訊。這種精密的審查形式意味著,大多數人會贊同政府對事件的說詞。但令人稱奇的是,質疑聲浪仍然持續不斷,而這讓習近平這類領導人將控制歷史列為他們施政的最高優先事項。
中國地下歷史學家的崛起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出現在一種嚴密管控的政治環境。但同樣重要的是,它是一股全球性走勢的一部分。事實上,如果我們觀察我們自己的國家,無論在非洲、美洲、亞洲或歐洲,我們會見到我們都生活在一種記憶大榮景中,例如說有愈來愈多書籍、電影、展覽、藝術品正在設法透過過去對現在提出解釋。而且在大多情況下,目擊者對過去的說法差異還愈來愈大。
在西方國家,這股走勢於一次大戰結束後展開。由於識字率普及,出版成本降低,以及電影產業崛起,使數以百萬計民眾可以透過「砲彈休克」(shell shock)概念了解這場帶來巨大創傷的戰爭。就算那些未曾親赴前線參戰的人,也能感受他們這代人承受的戰鬥之慟。這種認同與創傷的融合成為全球常態。在過去幾十年,共同創傷不僅成為代表世代的標籤,還成為代表人群、甚至國家的符號。例如說我們只要提到「納粹大屠殺」就會想到以色列,提到「南京大屠殺」會想到中國,提到「種族滅絕」則會想到亞美尼亞。
這類記憶有的發生在戰場、博物館、小說、詩歌與信件等有形領域。但近年來,這類記憶同時也發生在學者傑伊.溫特(Jay Winter)所謂「記憶場域」,這是由電影、電視或戰爭罪審判紀錄片組成的一種虛擬世界。在大多數案例中,口述歷史在這種虛擬世界的地位更重要,許多人認為口述歷史更能真實描繪過去的事件。
但記憶是個讓人憂心的東西。我們從本身生活經驗中得知,隨著年齡漸長,我們的記憶也不斷變化。這種容易變形的特性在「集體記憶」概念中尤其真切。有人用「集體記憶」表示鐫刻在一個國家集體意識中、一種不變的苦難回憶。但這種做法過於簡單,因為記憶確實是會因時變化的。由法國哲學家摩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原創於1920年代的「集體記憶」一詞,原本有更精確、有用的意義:人群在記憶時,形成一種人數可能多達好幾百萬的集體,但每個人對過去仍然保有自己的專注與解讀。隨著這些人逐漸凋零,集體逐漸解散,記憶也消失了。
就這種意義而言,集體記憶頗能適用於中國的地下歷史學家。他們透過數位科技確實形成一種集體記憶,並且嘗試以群策群力的方式改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再以阿蕾達.阿斯曼的比喻來說,雖說大多數中國人無法進入展館,但這些記憶現在已經搬出庫房,進了博物館的展示櫃。這項過程進度緩慢,歷經數十年。有一個人將這種走出沉默、訴諸言語的過程發揮得淋漓盡致,想了解這項過程,觀察他就行了。他是中國半世紀來最偉大作家之一的小說家王小波。
在整個1970年代末期與1980年代,他們大多是政府官吏,忠心為國,他們或許有異議,但從未動過推翻系統的念頭。但就算只是提出最卑微的一點意見,他們仍不免遭到毛澤東迫害,下鄉勞動,扒糞幹活。許多人寫出後來所謂的「傷痕文學」,回憶像他們一樣的知識分子當年承受的苦難。這些作品幾乎全是自艾自憐、平淡無奇之作,作者會憤憤不平,但對這個殺了千百萬人的系統卻並無反思。
隨後在1992年,一位名叫王小波、名不見經傳的作家,以極其荒唐的手法模擬早先這些作品寫了本稀奇古怪的中篇小說。小說講述文革期間,下放到緬甸鄰近邊區的兩位年輕情侶的滑稽搞笑、荒誕不經的故事。兩人在邊區有了婚外情,遭官員逮到,被迫不斷寫自白書,還被迫在鄉間各處遊街,重演他們的罪行。兩人之後逃入山區,但又折返接受更多處罰,直到有一天終於獲釋。兩人並無悔意,只是感到有些錯亂。
這本小說因為談到性愛,立即爆紅。它無所不在,荒唐而搞笑。除了「性」以外,最令人震驚的是書中對知識分子的描繪。在王小波這本小說中,知識分子幾乎像控制他們的那些黨官一樣壞。小說男主角引誘戀人上床,與在地人滋事打架,在工作時磨蹭閒蕩,像那些折磨他的人一樣詭計多端。小說的書名讓全書更加光怪陸離。它叫做《黃金時代》,讓許多人看了嘖嘖稱奇,無論什麼人,無論什麼國家,哪有可能有這樣的黃金時代。
作者本身情況同樣令人費解。王小波住在北京,在北京工作,但不是國家作家協會會員。他的小說一開始甚至沒能在中國出版。但在台灣出版過後,《黃金時代》開始在中國出版,並且立即暢銷。王小波之後又寫了許多小說與文章。他特別受大學生歡迎,大學生愛他的詼諧、反諷與幽默,當然還有「性」。
王小波受到妻子李銀河的極大影響。李銀河是中國性學權威,曾經研究中國男女同性戀運動,發表相關著述。近年來她致力為跨性與雙性戀者發聲。

王小波與李銀河於1979年相識,隨於翌年結婚。李銀河是毛澤東時代社會學禁令解禁後的新一代社會學者,兩人一起留學匹茲堡大學,李銀河拿到博士學位。兩人回到中國後,共同執筆,寫了一篇開創性的研究報告《他們的世界:中國男同性戀群落透視》(Their World: A Study of the Male HomosexualCommunity in China)。李銀河後來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士,王小波則在人民大學與北京大學任教。
1989年學生運動在一陣波濤洶湧後重歸平靜。像他的友人、前文提到的夾邊溝紀錄片製片人與女權運動學者艾曉明一樣,王小波不清楚這場沒有組織的學生運動會造成什麼後果,大體上對事件保持沉默。
王小波最著名的一篇文章〈沉默的大多數〉就以「保持沉默」為主題。他在文中寫道,在毛澤東統治時代,毛思想、毛理念與毛說的話,夜以繼日、鋪天蓋地而來,讓每個人都閉上嘴。這種經驗留下一道瘡疤。對王小波而言,這道瘡疤意味著,「我不能信任那些屬於話語圈的人。」尋找聲音就此成為他為自己、為中國社會訂下的目標。
他因此找上中國的同性戀族群。弱勢族群也是沉默的族群。他們沒有話語權。社會有時甚至否認他們的存在。於是王小波有了種頓悟:中國社會大多沒有聲音,這不只是性傾向特異的族群,還包括學生、農民、外來人口、礦工、生活在城市中即將拆除的老區裡的居民等等。這些人不僅是少數特殊利益團體,他們代表一大片中國社會。
然後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屬於古往今來最大的一個弱勢群體,就是沉默的大多數。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種多樣,有的人沒能力、活著沒機會說話;有的人還有些隱情不便說話;還有一些人因為種種原因,對於話語的世界有某種厭惡之情。我就屬於這最後一種。而身為這樣的人,我有責任說出我眼見與耳聞的事。
巴黎史學家魏簡(Sebastian Veg)以研究王小波的想法而在中國名聲遠播,他認為,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為王小波帶來巨大震撼,讓王小波質疑自己沒有支持抗議的學生。王小波逐漸覺察到,抗議學生儘管立意崇高,但做法失於老舊過時,他不能支持他們。這些學生自視為正統知識分子,要影響國家,因發現遭到忽視而憤怒。王小波對社會有不同的看法。核心問題在於,中國社會分裂成許多群體,而這些群體都太弱,無力與國家權力對抗。中國沉默的原因就在這裡。他終於知道他必須寫些什麼了。
1991年,王小波完成他自1972年從雲南返回起已經著手的《黃金時代》。他不知道應該怎麼發表,遂將一份抄本送給曾在匹茲堡擔任他指導教授的著名史學家許倬雲。許倬雲把它交給台灣著名中文報紙、每年在台灣舉辦文學獎比賽的《聯合報》。王小波贏了大獎,就此走進他所謂「喋喋不休的瘋人院」──話語世界。
《黃金時代》的成功使王小波成為著名公眾知識分子。只是他的盛名只持續5年,因為他於1997年心臟病突發去世,享年只得44歲。但在這5年間,他率先運用網際網路,在中文媒體發表許多作品。他直接、間接影響了包括艾曉明等一代中國人。在他感召下,閻連科與廖亦武等作家也開始發表文章,描述囚犯或毛統治時代受害人等等社會上最容易受害的人群。中國導演賈樟柯常說,由於受王小波的鼓舞,他的作品主要討論個人的故事,而不是政府屬意的集體敘述。
王小波本人受到許多思想家的影響。在毛澤東治下中國成長的他,年輕時私下閱讀羅素(Bertrand Russell)的作品,開始在內心深處植下個人自由的理念。在匹茲堡留學期間,他也讀了傅柯(Michel Foucault)與他針對個人與國家權力關係提出的敘述。
傅柯不僅影響王小波的思考,想了解王小波本人在中國社會扮演的角色,傅柯的論述也是重要指標。傅柯認為,知識分子會逐漸走出自由、道德、存在等普世性主題,進入他們擁有專業知識的特定領域。他們運用這些專業知識可以有效干預公共辯論,為窮人、移民、愛滋病受害人這類弱勢群體發聲。
在西方社會,這種走勢於20世紀中葉展開,但在中國,這一切直到數位革命出現才成為可能。數位革命使中國思想家不必仰賴政府控制的製片工作室或出版社,也能拍影片、發表作品。自1990年代末期起,這些地下歷史學家製作許多突破性的歷史作品、紀錄片與文章。幾乎完全按照傅柯所說的模式,這些中國知識分子開始運用他們的專業知識在相關領域進行干預。他們一點一滴發掘遭到忽略或遺失的歷史,同時也創造供其他人使用的新資訊。
在這類「草根知識分子」中,我們更容易聽到詩人林昭、作家艾曉明或江雪等女性心聲,更容易聽到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等被囚禁的維吾爾知識分子的心聲,而這當然並非偶然。在以男性為主的儒家知識分子傳統,或講究名氣輩分的中國小說家世界,他們的聲音往往遭到排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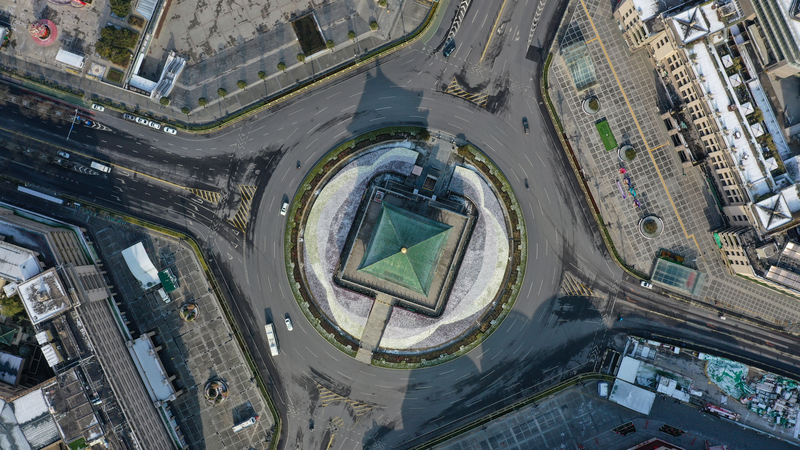
王小波在一篇個人經歷的自述中,談到自己決定挺身發言的另一個重要原因。他為的不是加入憂國憂民的儒家傳統,而是一個自私的考量。他寫道:
「我最希望提升的是我自己。這個理由有些可鄙;它很自私,但也很真實。」
他將這個動機與其他草根知識分子分享。曾目睹繼父在大饑荒期間餓死,由記者轉入歷史研究的楊繼繩,決心以記錄大饑荒史實為終身職志。影片博主張世和曾當過修築鐵路的奴工,後來決定記錄這段歷史。艾曉明眼見婦女遭到壓榨,江雪察覺祖父的死因。還有人因為政府處理新冠疫情手段荒謬,家產遭到沒收,顛沛流離。他們都因為這種種個人理由挺身而出。這些現象或許狹隘、有限,但當人們努力了解、描繪自己的人生時,社會也因此轉變。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