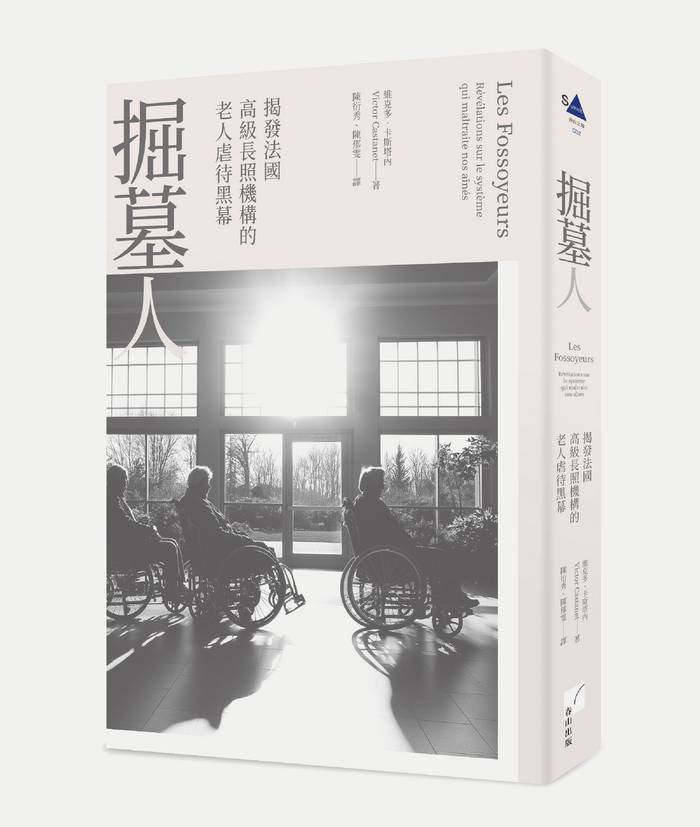書籍導讀

要記住:金錢具有某種生殖能力的與繁殖力強的本性。錢可以生錢,並且後代還可以生得更多。5先令一周轉就是6先令,再周轉一圈就是7先令3便士,如此下去直到變成100英鎊。錢愈多,錢在周轉時所產生出來的也就愈多,收益也就增長得愈來愈快。 ──韋伯(Max Weber),《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我們怎麼會讓這種事情發生?誰該為此負責?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們所有人都有責任,因為我們長期以來對此視若無睹。但除了集體責任之外,我們也要對國家機器,也就是法國醫療體制提出質疑與批判。 ──《掘墓人》,第38章
將「照護」與「產業」連結起來,會得到什麼?法國獨立記者卡斯塔內(Victor Castanet)在《掘墓人:揭發法國高級長照機構的老人虐待黑幕》一書給出了答案:失能照護產業的資本主義精神。
卡斯塔內指出,照護產業化宣稱要讓照護服務更加蓬勃發展,但它未說出口的,是要讓照護能夠「賺錢」。照護可以孳生利潤嗎?如何孳生以及應該孳生利潤嗎?這是我們21世紀正迫切面對的問題。自有歷史以來,照護或照顧勞動所產生的剩餘價值,一直是建立在主要由女性或少數族裔提供的無償勞動,以及被貶低價值的有酬勞動上。如今照護服務發展的面貌愈趨複雜,本書調查法國跨國照護集團歐葆庭(Orpéa)旗下的照護機構,揭露了照護的資本主義帝國繼續以不同的形式,壓縮照護勞動與勞工的權益,進行資本的跨國積累,侵蝕失能長者受照護的權益。
卡斯塔內自2019年花了近3年時間走訪全國歐葆庭旗下的失能長者住宿機構進行調查。1989年歐葆庭設立第一家長者住宿機構,2000年股票上市,成立30年後擴展至歐洲、美洲、亞洲23個國家上千家機構,從家族企業轉型為產業經營的財團。本書出版後,歐葆庭股價下跌、國會展開調查、召開聽證會、2024年3月政府提出「2024至2027全國對抗虐待策略」、歐葆庭集團更名為艾米斯(Emeis)、本書改編的紀錄片(Les Fossoyeurs : au coeur du scandale des Ehpad)已於今年(2025)3月底上線⋯⋯凡此種種均見證了這份獨立調查報導龐大的社會影響力。
然而,這並非法國第一起長者住宿機構震動視聽的醜聞。自2009年即有媒體以隱藏式攝影機報導養老院的老人虐待;2017年起陸續有照護機構工作人員罷工,抗議照護資源不足、勞動條件惡劣,機構及居家照護勞雇攜手上街頭示威,抗議國家未盡責任。為何機構照護的問題如此難解?
書中描寫的光鮮亮麗的長者住宿機構,其實歷經數番重大改革。在過去,俗稱「退休之家」(maison de retraite)的老人集體住宿機構,源自於濟貧救助傳統下的收容所(Hospice),其淒慘、悲涼的印象深植人心,被視為等死之所(les Mouroirs)。自1970年代起,對機構化的社會批判激起了養老院人性化的改革,尊重個體性與隱私的個人房取代了宛如集中營般的多床擁擠於一室。1990年代末機構的醫療化改革,令絕大部分的公、私立長者住宿機構均轉型為醫療化機構(即EHPAD),以因應住民老病的生命歷程演變。EHPAD的財源亦同步改革,機構取得營業許可後,依法與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地方政府簽訂「目標與資源多年期合約」(CPOM),規範機構的財源、照護目標與策略。機構建置需要龐大的資本,特別是土地取得、建築設備與密集的照護勞動力。因此,入住EHPAD涵蓋3項費用成本:
- 「醫療費」(tarif soin):由中央層級的健保直接付給機構,後改為由大區(région)衛生局支付。本項目支付住民醫療費用、機構聘用的照護人事成本和必要的照護用品。
- 「照護費」(tarif dépendance):支付住民醫療之外的照顧陪伴服務,由地方政府的省參政委員會(conseil départemental)和住民共同負擔。法國施行個人化自主津貼(Allocation personnalisé d’autonomie),依失能等級(GIR)補助60歲以上失能者支付居家照護或入住機構的照護費。
- 「住宿費」(prix hébergement):涵蓋住民在機構的食、宿、樂齡活動、洗衣等開銷,由住民自付。經濟困難者可申請社會補助,國家亦有權要求負撫養義務的子女支付。
EHPAD財源規畫的邏輯蘊含了法國將失能照護大幅度公共化的理想。無論公立或私立、營利或非營利機構,以及失能長者,均獲得國家資助醫療照護成本,包含照護人力的薪資(協調醫師〔多為兼職〕、護理人員〔100%〕、護佐〔70%〕)。相較於台灣的長照政策將機構照護視為住民或家屬應自行承擔的成本,法國承認其為公共責任的一環。然而《掘墓人》披露了「老人自主」的公共理想,被失能照護產業化的金融體制轉變為虐待長者的逐利場。
「這裡就像工廠!」是我於2009年在法國EHPAD進行田野調查研究經常聽見的一句話。遇缺不補、勞動條件惡劣、濫用臨時人員,這些問題竟隨著時間日益惡化。然《掘墓人》調查的是導致機構長者遭受虐待的一個整體運作機制,作者稱之為「歐葆庭體制」(Le système Orpéa)。本書所揭露的並非歐葆庭集團特有的體制,而是失能照護產業化的一種典型,指稱一套「利用照護創造利潤」的方法,及其信徒奉為圭臬的照護資本主義精神。卡斯塔內指出,令長者的風燭殘年為照護產業搖錢的「歐葆庭體制」建立在兩大基石上:「成本最佳化」的做法導致勞動條件下降和對長者提供的照護品質惡化,以及挪用和侵占公款。
失能照護產業化的信徒奉行韋伯所稱的「資本主義精神」的邏輯,以理性簿記──本書稱之為「管理模組」(Le Matrice)──來預估住房率、利潤率、最佳化薪資總額,以確保「圈養一群老傢伙」不會虧錢,還能賺翻!透過新自由主義的辭藻──「成本最佳化」、「現代化」、「導入科技簡化人力」──帶來的利潤,從來不會用於補足照顧現場匱乏的人力與資源,而是促進銀髮產業的迸發。集團總部以中央集權遠端操控的方式,開發管理應用程式,由總部控管成本和支出,剝奪機構主任的預算權與人事權。為達績效目標,逐利體制更仰賴回扣機制,集團與特定廠商長期合作,以高比例回扣挪用公款中飽私囊。住在金屋銀屋的老人一天的伙食費縮減為4.2歐元(約新台幣150元),尿布量配給不到3片,即便浸泡在糞尿中亦求助無門,但集團的營業額仍節節攀升。這個虐待長者的體制猶如照護的「鋼鐵牢籠」,集體禁閉著身、心難以自主的老年,被理性計算的斗篷罩得密不透風,命運未卜。
歐葆庭錯綜複雜的金融體制最後生產了什麼?除了機構老人虐待、股東利潤落袋為安,它還生產了勞工的痛苦與憤怒。透過200多份訪談,卡斯塔內走訪歐葆庭集團的醫療總監、機構主任、護理人員、護佐、生活助理、剷除異議主管的「清道夫」⋯⋯他們畏懼遭集團報復仍勇敢發聲,說出對惡劣勞動條件的厭倦、在高層不願涉足的照顧現場承擔照料衰敗身軀卻無法給予住民合理照護的羞愧,甚至面對上級霸凌而心理受創、憂鬱、必須仰賴藥物或心理治療。大型連鎖跨國集團、機構內部的不民主、對員工的監控、扶植企業內部工會,均助長「掘墓人」體制的擴張,更扼殺了小型、非營利照護機構的生存空間。
為何這本書激起法國人的集體憤怒,無分黨派與社會階層?在法國,照護並非是一種給予弱勢的慈善救助,而是公民實現「自主」(autonomie)的理想,期望在生活或心智無法自理的人生階段,仍能維持人性的尊嚴直至生命最後一刻。照護應該是國家的公共責任,建築在人民的集體連帶(solidarité)基礎之上。《掘墓人》撼動法國社會的神經,不僅因為它揭露的照護集團醜聞,更是它讓法國人自主的理想硬生生地幻滅──因為,連財富都未必能買到好的照顧,一舉戳破了新自由主義歌頌的個人主義幻象。平均餘命不斷延長,無法安老的恐懼卻深深糾纏人心。在未來,機構照顧的需求和費用只有增無減,失能照護並非單純「我付了錢你就該給我好的照顧」的交易邏輯,而是多方權力與價值角力的場域,充滿照護、勞動、國家、市場、個人、家庭、性別、族群、障礙交織的多重矛盾和衝突。本書作者卡斯塔內控訴:
這就是把人們的生活納入工業化管理的後果,就像阿達尼先生所說的:這些邁入暮年的長者只剩下一具具肉體,而這些肉體又成了營利工具。尿片不再是護理用品,而是數據,是不惜一切代價必須壓低的成本,護佐、生活助理和機構主任不再只是負責照護住民,保障他們的福祉,還要聽從上司的財務指示,降低成本,追求利潤極大化⋯⋯這個集團要失控到什麼時候?(《掘墓人》,第16章)
- Chon, Yongho (2018) The Effects of Marketization of Long-term Care Services for Older Adults in Korea. Journal of Social Service Research, 45(4), 507–519.
- Harrington C, Jacobsen FF, Panos J, Pollock A, Sutaria S, Szebehely M. (2017) Marketization in Long-Term Care: A Cross-Country Comparison of Large For-Profit Nursing Home Chains. Health Services Insights, 10.
商品化的資本主義精神,將受照護者的「權益」改造成了「利益」。北美、北歐、東亞的長照市場化,無論在社區居家服務或機構照護,均面臨著嚴峻的困境:在創造利潤的前提下,照護品質下降、縮減人力、削減薪資或加班費、運用避稅天堂是伴隨而來的結果,然而國家「根本不是歐葆庭這種大型私人集團的對手」(《掘墓人》,第38章),整個社會集體極其缺乏分析、稽查、監督照護品質與長照市場化運作的能力。
在課堂上我分享於法國失能長者住宿機構進行的研究:在一間養老院實習時,一位老先生坐在輪椅上,無法說話的他示意我參觀他的房間。我踏入漆著溫暖鵝黃色調的牆,橘色條紋窗簾飄逸的房間,搭襯著機構允許住民擺放的少數典雅「個人化」家具。他指引我看望牆上一個大相框,裡面交疊著許多親友的照片,問候著已無法從此地離開的老人,而人手不足的照護者仍忙碌地穿梭於照顧的生產線上。
這是我在法國美輪美奐的照護機構實習的共通記憶。我總為那華貴而孤獨的個人房嘆息,無論人的一生如何,最後尚未必能掙得這一席之地,遑論人什麼都帶不走,個人生命的歷史最終僅能濃縮於此方寸之間。一位同學說:「但起碼他們還有個人房,這在我們這裡不可能。」另一位同學則堅稱長照非得走向營利、產業化才有未來。照護能否營利,猶如本書指出的,這樣的問法其實簡化了問題。我們要問,照護如何、為何營利?它的利潤從何而來,又用於何處?如何確認從人類的失能與照護中,營利存在正當性?如何制止照護產業化附隨而來的異化?正因為人生最後只能留這樣一小方寸的空間,因此我相信,人類對於照護的冀望應該不止於資本主義精神召喚的方向。失能照護體制運作的方式,照護的全球治理,促進老年生命的平等,必須受到世界更多的關注與社會共同體的監督。
(編按:本文由春山出版提供,文章標題與文內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改寫。)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