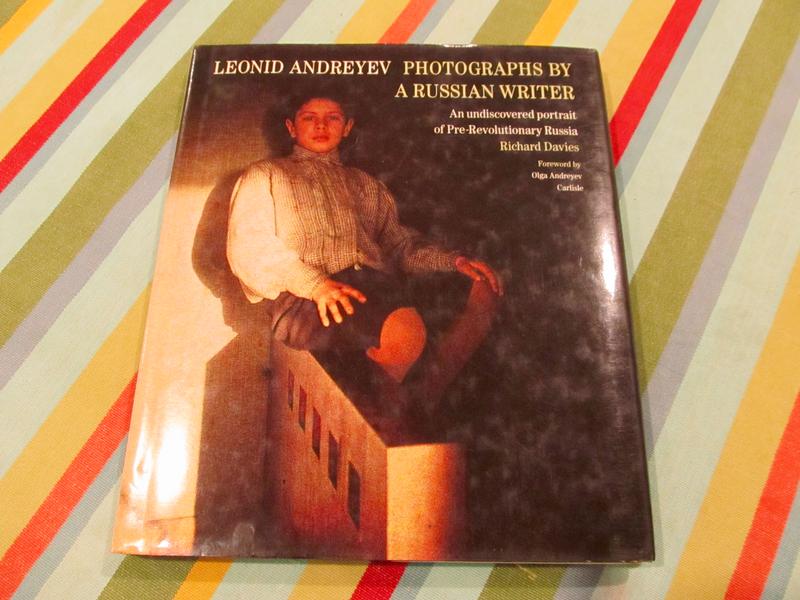【閱讀現場 X 讀字書店】

上網,把(虛擬的)書丟進購物車,結帳,物流配送,小七取件。
人和書的關係,可以無縫接軌、冰冷順暢。
人和書的關係,也可以不止於如此。
走進書店,拿起一本書,撫摸書皮,打開讀幾段,書頁翻飛間,耳邊傳來生祥樂隊的歌曲〈南風〉:「我的鑰匙變孤僻/吵著回鄉找屋/海風北上幫忙敲門/它一身酸臭」,在哀婉的嗩吶聲中,你不經意地看到架上就有一本《南風》攝影集,和許多環境議題的書放在一起。你打開,彰化大城鄉,倚著牆渺小如螻蟻的老婦,下一頁,濁水溪出海口有如猙獰異形盤據的六輕工廠。你因這沉重議題而想得出神,一隻店貓忽焉躍過,扯亂思緒的線頭,你望向櫃檯後方,店員羞澀地朝你眨眨眼,你想和他聊一本書,他卻把你引進閱讀的蹊徑:從一片葉到一棵樹,進而是一整片森林。
11月起,《報導者》在每週末推出書評專欄,由閱讀現場的第一線觀察員:北中南的獨立書店輪流推薦心頭好。
人與書的關係,因為書店,有了景深與溫度,以及更多的可能。
鄰居女孩剛加班完,回家路上先折進書店。我剛烤好包了士力架的小餐包請她,一邊讓她猜內餡一邊聊起近來日常,女孩的戀愛遇到點兒困境,她來問事的(讀字書店,經營滿一年的活動:問事選書)。聊一聊,「欸,妳不會要哭了吧?」我問,「才沒有,」她推推眼鏡。她帶走夏宇翻譯的《夏日之戀》後,好幾個禮拜沒再看見她。
午後,還在大型出版社裡奮鬥的C翹班來找我。因為近來同婚爭議跟烏煙瘴氣的鳥事,我們各自負能量爆表,需要結伴喝點什麼。整個下午我卻疲忙於趕最後一天完成文化部補助的結案報告。
還在台北的出版社當編輯那幾年,跟C常相約在古亭或南門市場站覓食晚餐,也不特別餓,其實只想賴在一起發洩彼此的厭世與憤世。好像記得當下街景在黑暗裡煥發的顏色,也記得迎風吹上髮際、皮膚的觸感;縱使聊過的爛書、好書,對出版環境的期待或灰心都隱隱晦晦地模糊不清了,但你知道有個人一起走的安全感。
趕在郵局關門前寄出文件,傍晚我們就著眷村麵館外帶的油膩炒菜晚餐,喝她帶來的甜蜜蘋果酒。「我訂的書來了嗎?」「咦,哪一本啊?」「我也不記得了⋯⋯」喂,酒精濃度不是才5%嗎?
晚上,同光教會的朋友租借書店場地做小組聚會。請他們喝飲料,卻回收到一大塊成員自製的巧克力蛋糕,「你試試,我加了黑啤酒。」晚餐的漲持續,我端給剛進門的詩人宋尚緯,「看起來很像黑色的發糕,」他說。「小聲一點,」我說,「你這個失禮的傢伙!」兩個人卻忍不住在他們就著iPad吟唱詩歌時「議論」蛋糕。看起來最年輕的那個成員,離開時買走《小王子》。
晚一點,來了時運不濟、聽起來儼然就被職場霸凌的「樹」,不知道為什麼覺得好像應該煮點薑茶。他的女朋友「書」沒過多久也進門,我們喝薑茶也喝啤酒。書是譯者,最近從台北搬回桃園,因為太常來書店還曾請她以專業幫我選食譜書、當過幾日書店的緊急小幫手。但喝酒的時間好像總比聊書的時間多。
樹的學生時代是社運青年,出社會後不好不壞地在安定工作裡適應世界運轉的方式;我笑他是中產階級,他一臉震驚,恍然大悟的模樣。為他幻想中的自傳想了個書名:《別傻了,你就是中產階級》。他就像我概念裡被陽剛教育訓練成型的男生,不是我平常有機會與之為伍的人。我們常笑著指稱他恐同,我明白這是成長環境使然;但那日他跟我們幾個人為婚姻平權公聽會早起集結青島東,還跑去附近的護家盟鬧場,驀然覺得這世界似乎還行。「老闆,我的《文案力》跟《異境之書》來了嗎?」「有喔。」「可是我們現在沒錢,而且有人要失業了,先幫我留著好不好?」「我知道啦。」
再晚一點,習作咖啡部的店長小戴趁著自由日(不用照顧小孩)也帶朋友來,加入喝酒陣仗,每次他都說:「沒辦法,沒地方去。只有你的店開最晚。」一路聊到打烊時間已過。小戴再買了一本明明對我說過他看不懂的海明威,兩人搖搖晃晃又去找地方喝最後一攤。
有一陣子我常常很焦慮,不確定自己到底準備把書店做成什麼模樣;股東跟老闆總一股腦胡亂給我自信:就以「臭臉店長」闖出名號吧。如今想想,也許就是「這世界上總有一個地方可以容納你」的那個地方吧,有人一起走的那種陪伴。喔,隔天鄰居女孩出現了。「怎麼樣,有用嗎?」「沒用啊!不能解決我的問題。」「哈哈,變成詐騙集團了我。」「但我非常喜歡。」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