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投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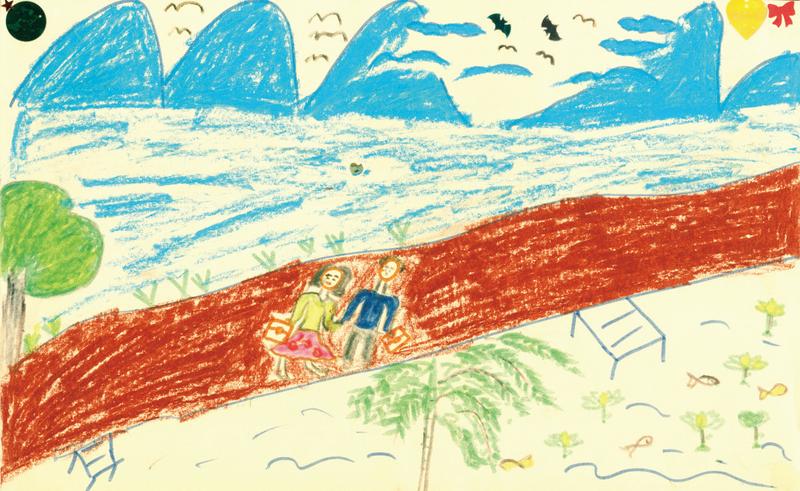
在台灣,每40人就有一位是來自東南亞的移工。這群異鄉人懷抱理想、飄洋過海來到台灣勞動、生產、貢獻,但不是每個人都能盼到美好結果,移工在台被騙、被剝削的事件至今仍時有所聞。
處在弱勢的人要為自己發聲向來都不容易,為此,善牧基金會希望藉由採訪所服務「南投庇護所」兩位移工朋友的故事,透過移工的表述,一步步去追溯那些關於勞動與移動、夢想與失望的印記,提供讀者另一種視角,期待能促成台灣社會對於「人口販運倖存者」有更多的理解和對話。
從高鐵台中站開了半小時車程,景色急速變換,稻田愈來愈多、房子愈來愈矮、人煙愈來愈少,目的地南投庇護所就座落在南投鄉間的山腰邊,清幽宜人的環境讓人一下子忘了這裡其實是戒備森嚴、專門安置人口販運被害人的庇護所。
到訪那一天是假日,M和S老早就坐在大廳等著我們到來。M縮在椅子上看上去有些緊張,S盯著電視正在看足球賽轉播。社工說:「台灣的電視節目移工看不懂,所以他們大多看體育台,球賽沒有語言的問題。」M和S有許多雷同之處,兩人都來自印尼,同樣有著黝黑的皮膚、微捲的頭髮,都是父親,移動的原因也一樣,都是為了心愛的家人。
M首先受訪。他坐在長桌的一端,與另一端的我們對望,一股緊張氛圍融在空氣裡,社工趕緊跳出來幫M解圍,說他是害羞的人,不擅言辭,我們連忙安撫。
孰料,M話匣子一開,思緒便如泉水般湧出,一口氣說了好多話,像是想把曾經存在的記憶和情感一次宣洩出來。以下是M的故事:
44歲的M,來自印尼西爪哇省,已婚,育有一兒一女。
M說,在印尼,到他這個年紀很難找到工作,短短一句話便道盡遷移者的無奈。M原本在家鄉的磚頭工廠打零工,但收入不穩定,為了養家,他只好出走,聽人說去海外就有機會成功,所以2年前M來到台灣。
M來台第一份工作在漁船上。他萬萬沒想到,等待自己的竟是一片黑暗。
當時正值冬季,也是捕烏賊的季節,船上只有雇主、M以及另一名印尼籍漁工,他氣憤表示:「船上只有2名漁工,卻要做7個人的工作,」不僅如此,M的雇主還不准他們戴手套工作,原因是烏賊價錢好,不能弄傷,M說:「徒手抓烏賊,很癢,很難受,後來我累到生病,向雇主討藥吃,雇主卻說他不想知道我生病,如果我不做就回印尼,我聽了,心好痛。」
工作究竟有多累?M說,那時候沒日沒夜工作,連吃飯的時間都被剝奪了。「雇主只給我們生麵,我們煮麵的方式就是把麵放進塑膠袋、倒入熱水,放在雨衣口袋等麵燙熟,然後趁魚網撒出去後的10分鐘等待時間迅速把麵吃掉。」
那麼,睡覺呢?M說,跟吃飯一樣得自己找空檔休息,「我常常在分裝魚的時候不小心睡著,沒辦法實在太睏了,一次短短10分鐘,就這樣『睡覺』,若被雇主發現便會招來一頓痛罵,雇主常用恐嚇的語氣跟我們說:『沒趕在幾點做完,就把你們丟到海裡。』」M餘悸猶存地說。
這樣的工作環境,M無法忍耐下去,領到第一份薪水的那天,他離開了原本工作的漁船。
「當時的我只有2個選擇,生和死,我完全不會說中文,雖然害怕我還是決定逃走,因為我寧願死在街頭被發現,也不想留在船上被虐待死,沒有人知道。」
於是M上了計程車,他不知能去哪,他連自己身在何處都不清楚。計程車司機開了2小時車程在高雄將他放下。「下車時我身上只剩台幣1,800塊,之後我在街上遊走,累了就睡在超商門口,可是心情舒暢許多,我心想被警察抓好過被雇主送回印尼,那樣太沒面子了。」
後來,在街上巧遇的印尼人把M引薦給台灣仲介。M嘆了好大一口氣才繼續說:「我又碰到愛罵人的老闆,然後莫名其妙被解雇;陸續換了幾個工作,逃跑都是因為沒領到薪水,我不懂,為何這樣的事情會一再發生?語言是我最大的障礙,我無法表達,我很生氣,但誰能幫助我呢?」
「一個人再厲害,都會有失誤的一天(印尼諺語)」,M說這句話就是他的寫照。他無奈地說:「大老遠跑來台灣,為什麼運氣那麼差?但是,我還是保持勇氣,因為⋯⋯不想講了⋯⋯。」淚水在M的眼眶裡打轉。
社工見狀,趕緊遞出面紙,緊緊握在M手上。
經社工解釋,我們才曉得M離開印尼後他的父親生重病,急需醫藥費,正在唸大學的女兒也等著他寄學費回去,被雇主積欠薪資的M心急如焚,他把僅剩的錢寄給母親讓父親治病,自己默默承受女兒對他的不諒解。社工說:「第一次會談,M為了父親過世的事,在會議室哭了好久。」
社工知道M對於無法回去見父親最後一面一直耿耿於懷,她特地幫篤信回教的M查詢去台中清真寺的交通路線,社工說:「這是我唯一能為他做的,我只希望他心裡能好過一點。」
M最大的夢想是養羊,庇護期間M透過社工媒合目前在蘭花園工作。「M是每個月存最多錢的移工,我相信他蓋羊舍的心願一定可以達成,」社工語帶驕傲地說。
社工說,採訪前一天,M的案件第一次開庭,所以談起家人他才會那麼激動。問M,是想家了嗎?他說:「想家,但是我還不想回去,我想在台灣多賺點錢,女兒跟我要黃金首飾,我本來打算等這個月領錢,沒想到⋯⋯」M再度哽咽語塞。
出庭前夕,M拿到一封信,是社工託通譯寫給他的。社工表示,擔心M因案件結束,被害人身分異動,隨即會被遣送回國,因此想提醒M:「要學習當一個爸爸,而不是把自己當成提款機,要教育孩子更甚於滿足孩子的欲望;還有,要試著去修補與家人碎裂的關係,雖然心仍受著傷,為了不要留下遺憾,還是要努力看看。」
聽完社工這段話,我有點明白,為何M要犧牲難得的休假,接受我們的採訪?「因為M曾說,社工比他的家人還要像他的家人,把他的問題看得很重要……,我覺得,M是想要回報社工對他的好。」

想要說謝謝的人還有S,他也是這位社工服務的個案。
來自印尼蘇門答臘島的S,30歲,已婚,育有一兒一女,來台灣一年兩個月。
S向銀行貸款蓋房子,在印尼賺錢很困難,朋友說台灣的工作好、薪水又高,於是他跟著一群不認識的印尼人來到台灣。
下了飛機,一名男子對照手機裡的照片找到S,「我上了他的計程車,司機把我載到雲林某處的西瓜園,」S說,工作沒多久他覺得奇怪,其他印尼移工看見警察來查拔腿就跑,還要他跟著一起躲起來,「我才知道持觀光簽證不能在台灣工作。」
我們追問:「當下會害怕嗎?」S說:「怕啊!可是,想到在印尼欠下那麼多錢,我只能硬著頭皮面對。」
S認為台灣老闆與印尼老闆最大的差別在於,台灣老闆很兇、不通人情,「台灣老闆總是不斷催促我們快一點、快一點,工作量很大、很辛苦,生活除了工作和睡覺,幾乎沒有自己的時間,」最讓S憤怒的是,領到的薪資只有當初談好的一半,「我不會說中文,也已經找不到印尼仲介,能寄回去的錢很少,我很難過。」
S越說越激動,為避免尷尬,我將目光轉向桌上的哆啦A夢玩偶,想起社工稍早向我們介紹,「哆啦A夢擺在會議室是要讓移工朋友發洩情緒用的,」心裡忍不住一陣感慨。
不甘現狀S後來決定逃跑,台灣仲介安排一台計程車載他到另一個農場,只做4天就被抓了,接著被送往南投庇護所。這段時間,社工除了幫S整理剝削史,也協助他在紙箱工廠找到一份工作。
談起在庇護所的日子,S這才卸下防備露出難得的笑容,「要謝謝姊姊(社工)幫我找工作、教我管理金錢,在這裡學到的生活紀律,對我幫助很大。」
S說,欠銀行的錢已經快還完了,如果能在台灣存到錢,他打算回去之後蓋雞舍做生意,我們獻上深深的祝福。
社工笑著說:「前幾天S跟我分享手機裡小孩的相片,還說,回印尼之後,他要像親戚一樣跟我保持聯絡。」順著小孩的話題問S:「會想家嗎?」S點點頭,我們接著問:「有沒有想對家人說的話?」S停頓一會然後說:「我有家庭,我想要給我的小孩、老婆幸福,」可能是想起遠方好久不見的家人,說完便逕自哭了起來。
「一講到孩子S就會掉眼淚」,S曾向社工透露心裡的不安,「離家時S的女兒還在襁褓中,S深怕女兒不認得他。」
不只有S,每位移工都有說不盡的遺憾。拿著家人照片的雙手,溫馨的背後是離鄉背井在異地打拼的辛酸。
每位移工的背後都是一個愛的故事,「家」是海外打拼的他們守護的目標。「一心為家人,這樣的愛,相信你我都能懂,移工朋友走在愛的道路上,若能得到台灣人的友善支持,他們一定會覺得安慰,」南投庇護所主任真摯地說,「不要把移工朋友想壞了,一開始就猜疑他們會偷東西、會偷懶、會逃跑,其實只要我們給移工朋友多一點關心,多了解他們的想法,相信他們在台灣都可以過得很順利、很幸福。」
(作者簡介:主要協助弱勢邊緣者培力、建立自我價值與尊嚴。目前在台共有39個服務據點,服務對象包括:受暴婦幼、高風險青少年、未婚媽媽、棄虐兒、原住民家庭、單親家庭、新住民家庭、人口販運被害人等。http://www.goodshepherd.org.tw/)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