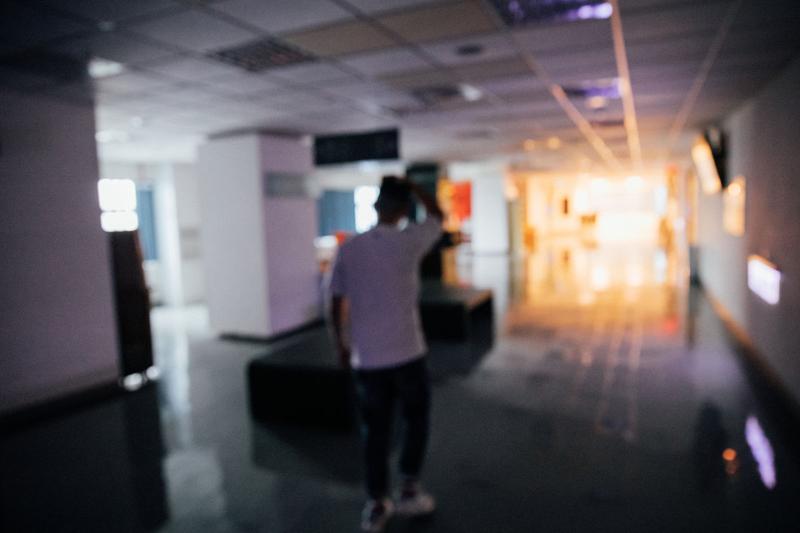在路上,是狀態、過程、是進行式。對創作者而言,在(創作)路上的所感所思,難以向外人訴,可能痛,但快樂著,或許焦灼難耐,卻無可自拔。
那滋味究竟哪般,誰不好奇?【在路上】系列專題今天登場,試著將那模糊失焦的拉近清晰。

2016/01/23,淡水,6度,雨天
身處創作期的編舞家跟孕期中的媽媽一樣,易感、多慮,滿懷興奮期待又緊張著面對「結果」的時刻,懷胎新作《十三聲》的雲門2藝術總監鄭宗龍,正在這條路上。
隨著雲門舞集落腳淡水,鄭宗龍也移居此處,年少輕狂時,春風少年的他經常混跡淡江大學附近網咖。再一度置身舊地,當時的血氣烈性已如煙惘然,曾駐足笑鬧的街頭店舖,徬徨飛掠過的堤岸碼頭邊上,如今都成了創作焦慮期的安胎定神所在。
「不進排練場工作時,或者結束工作後,我喜歡晃進市場、走上老街,一路沿著河岸,放空,或者想事情,在碼頭邊躺下,吹風,瞇一下。空白的時候、不知道怎麼接著走下去的時候,去龍山寺上個香、抽籤,往往就豁然開朗。」
在霸王寒流襲台前的一日,鄭宗龍的《十三聲》發展到了尾聲,整部作品的樣貌,只差最後一個段落,但,他腦中所有畫面卻也隨氣溫急降凝凍成了一片白,就像考卷寫到最後一題時,墨水乾了。
他踏進龍山寺,抽得的籤是這樣寫的:「於今此景正當時,看看欲吐百花魁,若能遇得春色到,一洒清吉脫塵埃。」柳暗花明,註定好了的。他想。
鄭宗龍身上有一股優雅的浪蕩江湖氣,獨行市井中,不語的模樣深沈肅殺,但路經廟宇時必然的駐足、合掌頷首,虔敬有禮;迎面市場裡招呼叫賣的大媽大嬸時,他的好嘴問候與條直古意的笑,更讓人想起,他的確從小就在艋舺街頭幫忙家裡擺攤做生意,最生猛的街頭百態與江湖事,是一路伴他成長的。
還記得2014年,鄭宗龍剛接下雲門2藝術總監,本來面對媒體就寡言內斂的他更顯謹慎沈穩。那陣子的他,只要站出去發言,幾乎都是「夾緊屁股」的貫注全神姿態。
笑鄭宗龍當時一點都不像他自己,每次說話活脫是林懷民上身,他害羞,但跟著大笑,「林老師是一個楷模,被影響,一定的,我當時真的很有意識的在模仿。但說實在,面對人,我常常會尷尬。」走過那一段,鄭宗龍反倒更明白自己,一份源長自體內深處的創作渴望,開始像爪撓著他、勾抓住他。
從2014年《杜連魁》、2015年《來》,鄭宗龍都轉用了廟會陣頭、乩童起乩等肢體元素,但他直言,「《杜連魁》是不知道做什麼的、七來倒八(台語)的作品;《來》又太重複自己,有體無魂(台語),很失敗。」其實,時序若推得更早,2003年《似相》中歌仔戲小生演員謝月霞的聲嗓唱念、2011年《在路上》的陣頭腳步,老早揭示了鄭宗龍的心之所向。
他本來沒怎麼意識,甚至想逃,感覺這麼「台」的元素、這麼理所當然的成長經驗,讓他太自卑。是在《來》演出結束後的回家路上,鄭宗龍回頭跟坐後座的媽媽討論舞作,聽媽媽開心說自己看得懂台上那些動作,又憶起過往街頭記憶,話匣子一開,鄭媽媽說出早年艋舺有位名喚十三聲的奇人,說那人一登場,能演男、唱女、扮小、裝老,獨挑大樑分飾多角,故事被他說演起來精彩無比。
幾乎是那個瞬間,他身上那道無形封印解開了,「我一聽這故事,就說,好!我就用他來編舞。」十三聲的無所不能為,是無限的自由,是台灣庶民的韌性精神表現,這讓在創作路上,一直反覆摸索猶疑的鄭宗龍,終於篤定了,「我們面對自己,總是空白,因為自卑、從不面對,我想,從自己開始、從自己出發,不論過去再多模仿、再多學習,走過看過再多異國風景,我知道現在自己要過自己的關了。文化走到最深處,都是一樣,只是表現形式不同。」昂然自信說完,下一秒他又害羞了,「啊,還是會歹勢啦,這,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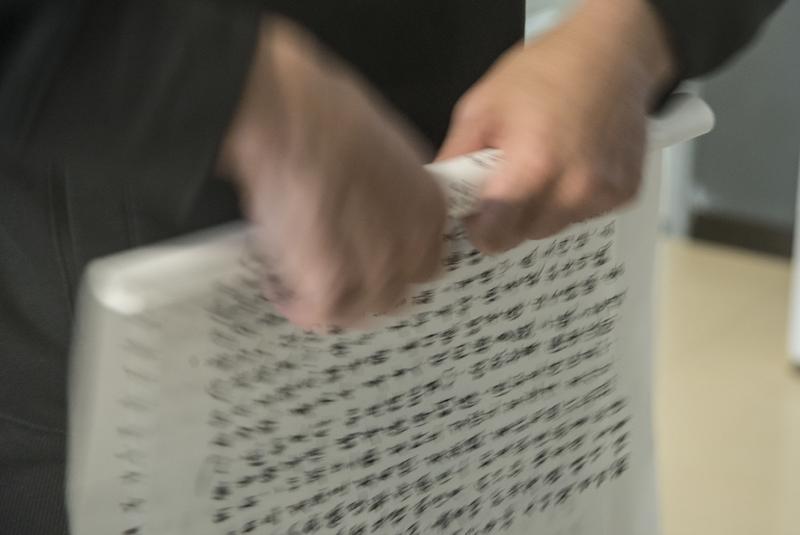


雲門2《十三聲》演出時間:2016/3/11-4/3,台北、台中、嘉義、高雄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