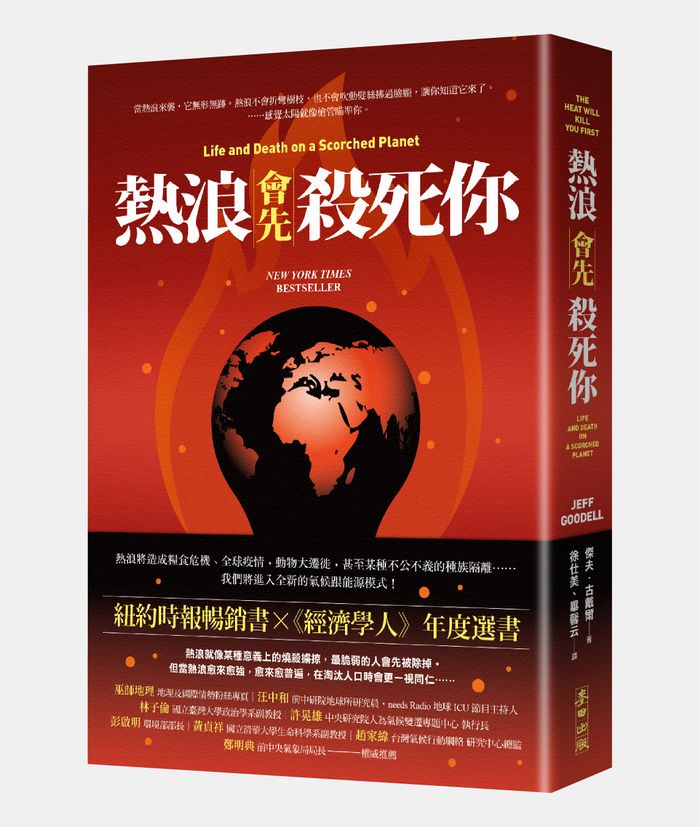精選書摘

本文為《熱浪會先殺死你》部分章節書摘,經麥田出版授權刊登,文章標題經《報導者》編輯改寫。
熱浪將造成糧食危機、全球疫情,動物大遷徙,甚至某種不公不義的種族隔離⋯⋯報導氣候變遷議題長達十餘年的記者古戴爾(Jeff Goodell),揭露極端高溫如何展現超乎想像的威力,我們已經進入一個新的氣候跟能源模式,急需新的社會和文化轉型。他呼籲,我們愈晚行動,代價就愈高。
隨著安.伊達戈(Anne Hidalgo)當選巴黎市長,為巴黎降溫的行動自2014年展開。60多歲的伊達戈是難民的女兒,他們家為了躲避法西斯主義而逃離西班牙。祖父是西班牙安達魯西亞(Andalucía)的左派份子,在弗朗西斯科.弗朗哥(Francisco Franco)獨裁統治期間被判死刑(雖然最後免除死罪)。伊達戈在14歲歸化為法國公民,開始工作時是擔任針對工廠的勞動檢查員,在1990年代成為利昂內爾.喬斯班(Lionel Jospin)總理的政府顧問。
巴黎在昔日是美妙的步行城市,伊達戈接任市長的時候,這座城市塞滿了汽車,內城區瀰漫著致命的空氣汙染,自行車道很罕見,所剩無幾的樹木看起來病懨懨的。伊達戈首先鎖定汽車與卡車,打一場她所謂的民主戰爭,把巴黎還給巴黎市民。她關閉巴黎中心地帶塞納河畔兩英里長的車行道,改造成河濱公園。里弗利街(Rue de Rivoli)是這座城市的主要商業街道,也變成自行車林蔭大道,只允許數量有限的某些汽車行駛。在巴黎的兩處主要廣場,共和廣場(Place de la République)與巴士底廣場(Place de la Bastille),車流限縮在一側,多出來的空間變成大型步行區,供熙熙攘攘的人群行走。她在這座城市裡創造了超過250英里的自行車道,本人經常被拍到騎腳踏車到市政廳上班的身影。
「我的工作是改造這座宏偉非凡的城市,但不造成破壞,」伊達戈曾經說過,「把它變成適合居住的城市,並且是鼓舞人心的模範城市,而不否定它的歷史。」
但是,伊達戈的企圖心在2018年受到阻礙,當時有成千上萬名巴黎人穿上黃背心,走上街頭抗議燃料稅調高;這些人大多是住在市郊通勤到市區工作的勞工階級。這些抗議如雪球般愈滾愈大,震驚全法國,馬克宏(Emmanuel Macron)總統差點因此下台。
動亂之後,伊達戈把目標從汽車轉向樹木。她並沒有完全放棄對抗汽車的戰鬥,在為2024年奧運預作準備的期間,她努力推動禁止大部分汽車與柴油卡車進入內城區。但是她發現為樹木奮鬥是比較好打的仗,而在她前後的許多政治人物也都發現這一點。畢竟,誰不愛樹呢?而且巴黎鐵定需要更多樹。雖然這座城市有很多公園,但樹冠覆蓋率在全世界各城市中敬陪末座,只有9%,相較之下,波士頓是18%,奧斯陸是29%。2019年的夏天,伊達戈啟動都市森林行動,誓言要「大幅綠化」這座城市的校園,以及4個地標:巴黎市政廳、里昂車站、巴黎歌劇院後方的廣場、塞納河岸的小路。
從公關的角度來看,伊達戈宣布都市森林計畫的時機再恰當不過了。2019年6月25日,距離都市森林行動實施還不到一個月,巴黎測到至今為止的最高溫度:攝氏42.6度(華氏108.7度)。想要讓城市降溫,還有什麼方式比種樹更好、更無害的呢?

樹木是氣候戰爭中的超級英雄。它們會吸收二氧化碳,釋放氧氣,在進行光合作用的同時可以過濾空氣。它們吸收土壤裡的水分,透過葉片散發,過程中順便使空氣降溫(可以把它們想成迷你冷氣機)。當然啦,它們為大大小小的生物提供庇蔭,也為周遭的土壤遮陽,有助於降低蒸散作用,減少土壤水分的損失。曾經在城市公園散步的人就知道,植物對於生活緊張的都市人也能帶來心理健康方面的好處。樹木與我們在深邃時光中一起演化,是我們數百萬年來倚靠、攀爬、崇拜的生物夥伴。
巴黎市計畫在2026年之前種植17萬棵樹,這是伊達戈都市森林倡議的一環。聽起來似乎數量很多,從某些角度來說的確如此。但讓我們以客觀的方式來看。紐約市已經種植了100多萬棵樹,而且還會持續下去。米蘭的都市森林計畫每年種植30萬棵樹,目標是讓這個城市在2030年有300萬棵新種的樹。為了讓你有個概念,從全球的尺度了解這些情形的意義,在此提供以下數字:地球上大約有3兆棵樹,算起來每個人分422棵樹左右。人類要為每一年消失的150億棵樹負責,而每一年種植或發芽長出的新樹約莫有50億棵,因此每一年的樹木淨損失是100億棵樹。雖然人們可能也很愛樹,整體而言,我們沒有善待它們。自從人類文明開始以來,地球上樹木的數量減少了46%。
儘管如此,17萬棵樹仍是不小的數目。討論到讓一座城市降溫,樹木很重要。2022年的夏天,有一位研究者發現,巴黎歌劇院前的地面溫度是56度。幾步之外,義大利大道樹蔭下的人行道地面,溫度只有28度。
但是,在快速變遷的氣候下,樹木不是解決都市高溫問題的簡單答案。首先,比起讓樹活下來,種樹容易得多。民眾喜歡捐錢種樹,政治人物喜歡有人拍到他們在種樹的照片,但是找到維護這些樹的經費則困難得多。在洛杉磯,市府官員估計,光是種植一棵橡樹並維護5年的花費是4,351.12美元。接下來的問題是,誰來負責照顧這些樹。以鳳凰城為例,該市沒有專責的部門或機構擔負維護樹木的任務,這表示樹木通常沒有得到應得的照顧和關注,尤其是在它們種下後的頭幾年。根據鳳凰城一位愛樹人士的說法,這座城市的行道樹平均壽命只有7年。
「鳳凰城過去曾有很多漂亮的大樹可以提供遮蔭,但他們在1960年代把樹都砍掉了,因為擔心消耗太多水,」鳳凰城的永續長馬克.哈特曼(Mark Hartman)在我幾年前初次到訪時告訴我。
城市裡的樹木即使得到良好的照顧,生活條件仍然很艱難。狗撒尿在它們身上。樹根被柏油和混凝土蓋住。戀人在樹皮上刻自己名字的起首字母。酒醉的司機開車撞它們。在雅典,有一種甲蟲入侵當地,正在摧毀公共廣場上提供庇蔭的桑樹。梣樹在美國的芝加哥與密爾瓦基(Milwaukee)等城市是遮陽的主要樹種,一直受到光蠟瘦吉丁蟲(emerald ash borer)的肆虐,那是一種2000年代初來到北美洲的吉丁蟲。有一項研究認為,到了2050年,光蠟瘦吉丁蟲可能害死美國140萬棵行道樹。在奧斯丁這裡,高大的橡樹與長山核桃樹經常讓人砍掉,好空出土地給那些科技業老兄蓋大房子與游泳池。法律與規則都阻止不了他們砍樹,即使他們必須付一些罰款,那又怎樣?
決定要種哪些樹,也不是簡單的事情。為了避免病害與入侵物種造成的大範圍損失,多樣性很重要。但是,當今城市裡的氣候,將不同於2050年時的城市氣候。樹木專家與都市規劃者自然會看得更長遠,看看哪些樹可能適合未來的條件。在巴黎市中心,隨處可見的二球懸鈴木(London plane tree,又稱英國梧桐)已經奄奄一息,無法抵抗暖化的氣候,目前有關單位正在以常綠樹、橡樹與幾種七葉樹取代。在土桑,棕櫚樹已經遭到淘汰,改種扁軸木(paloverde)與牧豆樹。為了幫助人們選擇能在嚴酷氣候下生存的植物,澳洲麥夸利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的研究人員發展出名為Which Plant Where的程式。在自家栽種植物的園藝愛好者可以上網,輸入地點,程式就會推薦,比如說,在2040年的氣候中可以生長得很好的植物。
2011年,乾旱與極端高溫的雙重壓力在德州害死10%的都市樹木,將近600萬棵樹在短短幾個月內死亡。接下來的幾年,情形可能會更糟。有一項最近的研究叫做「全球都市樹木清單」(Global Urban Tree Inventory),是涵蓋164個城市的4,734種都市樹木的資料庫,認為在中等氣候暖化的情境下,到2050年,四分之三的都市樹木可能會死於同時發生的炎熱與乾旱。

還有公平的問題。基本的事實是,富人得到好樹,窮人得到雜草。墨西哥市就是很明顯的例子。不久前的夏季某一天,我在市中心附近的波朗科區(Polanco),沿著馬薩里克總統大道(Avenida Presidente Masaryk)散步,在高大藍花楹的深色低垂樹蔭下,經過愛馬仕(Hermès)和卡地亞(Cartier)的店門口。這提醒我們,這座城市擁有的豐富歷史包含了公共花園、公園與樹木林立的廣場。但是,圍繞著內城的一些雜亂區域,情況就很不一樣。我的岳母這次和我們一起旅行,她成年後有很長的時光是在這座城市度過的,就生活在貧民區,她說:「其實這才是大多數人生活的地方。」貧民區的景色是由混凝土,還有苦苦掙扎的瘦弱梣樹構成的。
美國森林協會(American Forests)是提倡健康森林與生態系的非營利組織,他們的一項研究認為,奧斯丁市的樹木覆蓋情形,是美國所有都會區中最不平均的。在我們這一區,1940年代不起眼的房子一幢幢拆掉,蓋起玻璃麥克豪宅(McMansions),有14英尺高的天花板與黑色屋頂,還有高大的橡樹與長山核桃樹提供遮蔭。但是,如果我騎腳踏車到東邊的社區,就能看到那裡的樹更小棵,陽光更熱,溫度更高;20世紀初,黑色居民在那些社區遭受種族分區法律(也就是紅線制度)壓迫。如同許多城市,奧斯丁的市府官員和志工發起植樹活動,嘗試消除這種樹木不平等,想讓樹蔭民主化,普及每一個人。
許多新都市主義者(New Urbanist)抱持更大的目標,都市森林是其中一環,他們想要把自然元素帶回城市,包括河川、溪流、公園、花園、動物、整個生態系,這些事物都被冷酷的混凝土與四處蔓延的柏油覆蓋或趕走。南韓的首爾投入9億美元的經費,拆除高架道路,讓穿過市中心的清溪川河道重見天日,這樣做不只開發出眾人盼望的綠地,也可以讓河川附近區域的溫度降低將近6度。雅典為了把回收水引入城市灌溉公園和綠地,計畫整修羅馬皇帝哈德良最早在西元140年建築的輸水道。紐約市建立高架線(High Line),也就是在西城的高架步道,提供人們遠離都市混凝土結構的翠綠花園。巴西的古里提巴(Curitiba)有時被譽為地球上最綠的城市,每個人分到的綠地超過50平方公尺(相反的,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每個人只有2平方公尺)。「我們為自然設計空間,」 巴西的一位官員說。
在某些城市,設計自然本身就是極度人為的事情。在新加坡,你很難找到一寸稱得上「自然」的土地。但自從1960年代以來,政府刻意主導,一直努力讓這座城市因應上升的溫度。公路覆蓋了茂密的樹冠,都市公園不斷擴大,人行道種植成千上萬棵樹木。我最近一次到訪,在市中心散步時,看到許多蔓藤與植物從窗戶垂下,讓我覺得自己好像身處叢林裡。新加坡的WOHA建築事務所設計的市中豪亞酒店(Oasia Hotel Downtown)是27層的綠色高樓,外頭圍著網格鋁板,讓攀援植物可以沿著建築物生長。這些植物與鋁板有防晒功能,可以吸收熱並成為天然的遮陽設施。
這些綠色植物當然有助於新加坡為其居民創造涼爽的環境。但是我們很難說,像新加坡這樣的城市真能幫助地球降溫,因為它們的煉油廠與供應鏈遍布全球,產生巨大的生態足跡。「新加坡之所以能把自己建成一座花園,是因為它的農田和礦場都在別的地方,」賓州大學的景觀建築教授理查.韋勒(Richard Weller)寫道,「我會說新加坡是古馳生物多樣性(Gucci biodiversity) 的一個案例,這種多樣性分散人們對於它們投資位於加里曼丹(Kalimantan)的棕櫚油田的注意力,加里曼丹有全世界少數僅存的大型雨林之一。」

改造巴黎的重點是香榭麗舍大道(Champs-Élysées),這條連接凱旋門與協和廣場的林蔭大道是深具代表性的地標。我在1990年代初首次拜訪巴黎,驚訝於這條著名的大道竟然如此俗麗,以及觀光人潮之多。這裡很像時報廣場,但是情況更糟,雖然你可以從紀念碑與成排無精打采的樹木,看出它曾經是恢宏的步道。這幾年來,香榭麗舍大道日漸沒落,讓大道旁的地產業主與企業老闆憂心,於是他們委託巴黎頂尖的建築事務所PCA-Stream來重新想像這條林蔭大道,改造成符合伊達戈的涼爽綠色城市願景。
PCA-Stream的共同創辦人菲利普.基安巴萊塔(Philippe Chiambaretta)看待城市的方式與大多數人不同。對他來說,城市不只是物體與人類的集合,也不是一部巨大的機器,而是一隻不斷蔓延的巨大生物。「城市會有代謝的流動,」他告訴我,「事物正在新生,能量流入流出,城市總是在生長──或者死亡。」50多歲的基安巴萊塔在我們對談的那天戴著彩色圍巾,談起巴黎歷史與現代建築同樣興高采烈。「如同其他生物,城市可能處於健康平衡的狀態,也可能是不健康的失衡狀態。一座發燒的城市,如同一個發燒的孩子,就是生病了。」
基安巴萊塔和團隊花了4年的時間,從各個角度研究香榭麗舍大道,運用跨領域的方法,涵蓋人類學、哲學、物理學與經濟學。最終,他的團隊提3億美元的計畫,要把香榭麗舍從一片荒漠改造成伊達戈所說的「一座非凡花園」。這個計畫會縮減幾個車道,把空間留給自行車道及更寬廣的人行道。刮除黑色柏油,改鋪淺色的地磚,這樣可以反射陽光。收集雨水,重複使用。在開闊的土地上種植1,000多棵樹,讓樹根可以交往(「我們現在知道,樹木會交談,我們為此做了安排,」基安巴萊塔解釋)。總之,除了讓香榭麗舍大道變得更安全、更環保、逛起來更有趣以外,基安巴萊塔估計,這樣的改造將使這個區域的人行道溫度降低4度以上。
這就是城市的特色。它們可能是具有自己的代謝流動的超生物,但改造城市需要時間,除非你有拿破崙三世這樣的皇帝主導,或者像羅伯特.摩西(Robert Moses)這樣的權力掮客(摩西是20世紀中葉的都市規劃者,用冷酷無情的方法重塑紐約)。假設巴黎這座城市有充裕的金錢與穩定的政治領導。曾寫書探討巴黎如何因應氣候變遷的立爾金(Franck Lirzin)計算,如果巴黎人以每年1%的步調改造這些歷史建築,那麼需要75年的時間才能全部更新,為它們加上隔熱裝置。基安巴萊塔說,香榭麗舍大道計畫可能最快要到2025年才能啟動,並且需要10年的時間完成。「如果一切順利,我們可以在2035年完工,」基安巴萊塔告訴我。而且這只是為了一條林蔭大道的一個(大)街區。
但或許最大的阻礙來自於,建築師和都市規劃者的宏大願景,與真能建設出什麼的現實之間的落差。牽涉到許多不同利害關係人的大型公共工程計畫經常會有這種情形,而且要是那些大型公共工程挑戰到民眾對於城市應有怎樣的外觀和感覺的期望,更是如此。基安巴萊塔在巴黎嘗試為他的香榭麗舍大道計畫尋求政治支持時,已經面臨這種狀況。「我們想要在協和廣場鋪上淺色地磚,讓那裡看起來比較不像熔爐,保護古蹟人士看到這一點說:『不不不,你不能改變路上的石頭,那是巴黎之所以為巴黎的原因!』」基安巴萊塔告訴我,「而愛樹人士說:『不不不,你不能移走原來就有的樹,即使它們生病了。如果你嘗試砍掉任何一棵樹,我們會把自己綁在樹上,並且打電話給媒體!』所以,最後會建出什麼,我們能走多遠,我還不知道。我們可以拯救未來,也可以拯救過去,但是我們無法兩者兼顧。」
立爾金擔心法律規章會發生同樣的情形,讓變更市中心的奧斯曼建築困難重重。「因為熱沒有在短時間內罷休的跡象,人們將不得不採取什麼行動,」立爾金說,「他們會做的事情,可能和全世界的人正在做的事一樣──買一台冷氣機,裝在窗戶上。對巴黎來說,這將是災難。不但會增加用電需求,進而提高停電的風險,而且看起來很醜。」

還有其他方法可以讓巴黎降溫。立爾金指出,許多公共建築已經使用區域冷卻系統(district cooling system),系統中循環的水在流經建築物地底的管道時可以冷卻下來,而冷水流經建築物時可以帶走熱。這種系統可以推廣到巴黎的其他地區以及私人住宅。但這將會是一項重大的任務。
建築物也可以進行改造,讓它們完全不需要人工冷卻系統。法國的拉卡頓與瓦薩爾(Lacaton & Vassal) 建築事務所在2021年獲得普利茲克獎(Pritzker Prize,相當於建築界的諾貝爾獎),擅長用新方式重新思考老建築。他們最著名的一項專案是改造波爾多(Bordeaux)的503間公寓,原本這些是功能不佳又很醜陋的混凝土國民住宅,後來變身成明亮、寬敞、通風良好的住家。他們以便宜的方式進行,讓住戶不會流離失所(事實上,住戶在整建期間甚至不用搬出去)。這項專案的費用大部分由法國政府支付,政府的這項努力改善了老舊建築物裡的居民的生活,值得稱許。那麼,政府何不擴大規模,對巴黎每一幢老舊建築物進行奧斯曼式的改造?
這並非異想天開。畢竟,法國正在花400億美元,把巴黎地鐵的路線擴展到內城以外,增加125英里的軌道(大多在地底),建造68個新的地鐵站,這將使得住在遙遠郊區的民眾更容易進入市區,不需要開車。這種擴張計畫稱為大巴黎快線(Grand Paris Express),預定2030年完成,到時候將會使路上減少15萬輛車。
「現在的挑戰是短時間內進行奧斯曼改造,但不用槍枝,而是透過民主程序,」年近40歲的亞歷山大.佛洛宏丹(Alexandre Florentin)說,他是巴黎市議員,代表第十三區,這裡是該市最多的亞裔移民人口居住的地方。愈來愈多的巴黎年輕人認為,高溫是這座光之城(City of Light)的致命威脅,佛洛宏丹是其中之一。他說,不光是鍍鋅屋頂的問題。事實上,學校沒有隔熱裝置和冷氣,醫院的建築抗熱效果很差,他那一區的巴黎人大多沒有學過如何因應高溫。佛洛宏丹憂慮這座城市正邁向世界末日般的未來:夏季停電、急診室人滿為患、食物短缺、人們逃出城時造成交通大阻塞、消防員在撲滅凡仙森林(Bois de Vincennes)野火時死於中暑。「我們已經進入新的氣候與能源典範,」佛洛宏認為,「我們需要一種社會與文化方面的轉型,程度之大,恐怕是過去20年當權者無法想像的。」
這種轉型要如何發生?「你必須發起一場政治運動,」佛洛宏丹告訴我,「人民必須強烈要求。」而且不能讓維持現狀也是一種選項。無論如何,就像中緯度的每一個城市,巴黎肯定將因極端高溫而改頭換面,和這座城市過去幾百年來因為戰爭、疾病、商業而改變面貌一樣。佛洛宏丹推動市議會成立一個15人的委員會,稱為「攝氏50度的巴黎」,這個委員會將在全市舉行公開會議,並向市議會建議應對極端高溫的最佳策略。「在巴黎,我們有三種選項,」佛洛宏丹直言不諱,「烤焦、逃跑,或者行動。」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