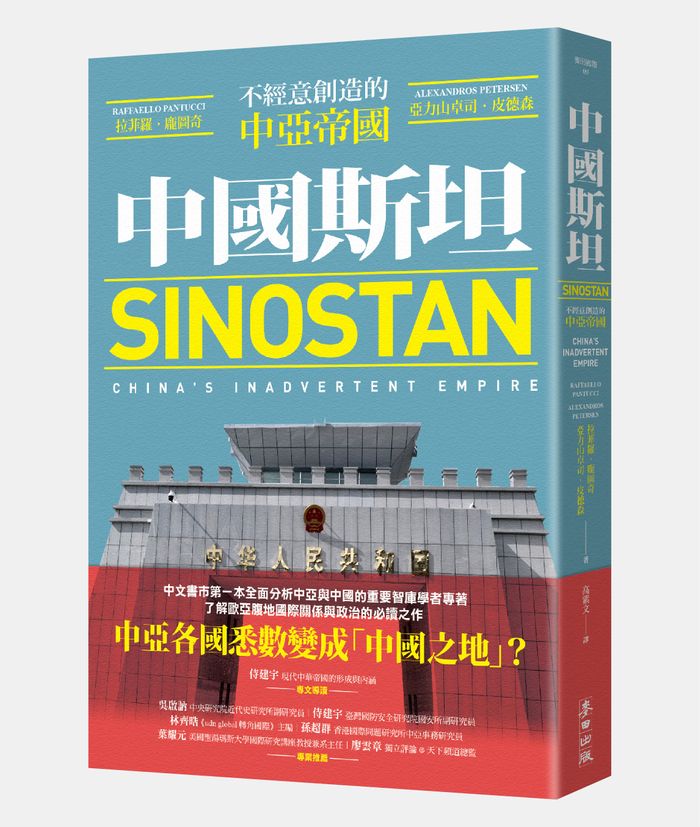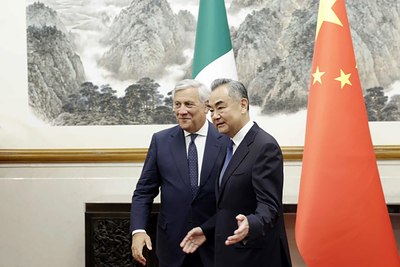【精選書摘】
本文為《中國斯坦:不經意創造的中亞帝國》導讀,經麥田出版授權刊登,標題與文內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所改寫。
中國的地緣經濟願景如何打亂全球經濟?中國科技如何改造世界?在這些引人注目的議題之外,中國的影響力一直悄悄向中亞地區擴張、滲透與深入。在這裡,習近平首度提出宏大的「一帶一路」倡議,打算建造通往西邊的新絲綢之路。在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中國的新外交願景造成哪些後果?
兩位外交政策專家──拉菲羅.龐圖奇(Raffaello Pantucci)與亞力山卓司.皮德森(Alexandros Petersen)在《中國斯坦》一書中,訪問絲綢之路市集裡的中國商人,翻越偏遠險峻的山區隘口;他們同情阿富汗考古學家,必須負責保全擁有數百年歷史的佛教古蹟,防止古蹟在採礦工程中遭到破壞殆盡;他們訪問滿懷熱血學習漢文的中亞年輕人,同時造訪中亞五國的首都,訪問官員、聽官員訴說他們親眼見證北京日益改變中亞地區。其故事和經歷,闡明了中國的外交政策倡議如何在中亞當地推動,以及如何影響住在這個中國「不經意創造的中亞帝國」裡裡外外的人們。
而這一切,真的是在中國政府「不經意」間創造的嗎?
這本書是兩位作者十多年前就開始的研究計畫,但是過程中一位作者不幸在阿富汗遇難本書作者之一亞力山卓司.皮德森(Alexandros Petersen),生前在阿富汗與中亞的大學任教,在歐亞大陸居住與遊歷甚廣。2014年1月,他在喀布爾的餐廳用餐時,遇上
自殺式炸彈與掃射攻擊而罹難,該次事故總共造成21人死亡。
學界對中亞的理解非常「離地」,非常欠缺即時與務實在地的理解。在2011年,美國曾經意圖一勞永逸地解決阿富汗問題,當時的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公開提出「新絲路倡議」(New Silk Road Initiative),想要經由阿富汗,連結中亞與南亞,透過基礎建設與貿易來繁榮此區域,根除貧窮與恐怖主義亂源。但是面對阿富汗塔利班的騷擾攻擊,最後無法落實而放棄。 中國版的「一帶一路倡議」與美國的「新絲路倡議」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中國想要確保新疆的「安全與發展」,所以路線規劃不同,中國的兩條陸路「絲綢之路經濟帶」,一條從中國新疆往西北進入中亞,經俄羅斯進入歐洲;另一條也從新疆出發,往西南進入巴基斯坦,再出印度洋;唯獨繞過阿富汗。美軍在2021年完全撤出阿富汗後,中國也開始必須面對此問題。出版這本書的另一個目的當然也在提醒美國與世界其他強權,不要輕忽歐亞大陸中間地帶的重要性。
地緣戰略學者麥金德(Sir Halford John Mackinder)在百年前就提出歐亞大陸是一塊「世界島」,而「心臟地帶」就是現在中國意圖染指並掌控的中亞。麥金德當時指出,掌控心臟地帶的的人,就掌控了整個世界島,稱霸世界。習近平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可說只是一個架構,內容多是拼湊與匯集正在、或意圖進行的各種對外投資與基礎建設項目。不可諱言,在俄羅斯還以為中亞是自己的「勢力範圍」之際,北京嘗試在不直接觸怒莫斯科的經貿先行方式下,蠶食中亞。從蘇聯30年前瓦解以來,不能否認中國的確用心經營中亞,但是作者實地考察一圈後,可能還是看不清楚中國擴張的具體戰略計畫。本書作者用「不經意創造的帝國」(inadvertent empire)來形容中國在中亞地區的擴張,但是北京真的是如此無心與被動嗎? 中國為何經營中亞?關鍵在新疆
《中國斯坦》在書中第一章與第二章介紹中國歷史上與中亞的關係與新疆背景的描述,沒有直接討論傳統中華帝國起伏變化的內涵,只是勾勒過去中原政權與中亞地區的互動。書中認為大清帝國擊退準噶爾,征服新疆,最初目的是要牽制遊牧民族的威脅,而不是擴張領土(註)這樣的傳統歷史史觀詮釋最近20年出現爭議,大清帝國的天下觀與治術是否與前朝斷裂,日本與美國學界都有不同的論點出現。有人稱這些討論為「新清史」,也有人批評是一種史為今用「修正史觀」,一般簡單的介紹,例如可參見James A. Millward,
“The Qing Conception of Strategic Spac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 Research, August 23, 2023. 。
中國官方在1990年代多使用「疆獨」來稱謂「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可能是因為類比藏獨、台獨、蒙獨的稱呼而來。事實上新疆不像西藏、蒙古,不是一個族稱;更不同於台獨,台灣有著日本殖民史與獨特的政治認同建立過程。新疆的主體民族被中共定義是維吾爾,追求的應該是「維吾爾斯坦」的獨立運動。但是新疆一半人口是中國在不同時期因為不同理由從其他省分遷入,而且由於20世紀蘇聯與中共的意識形態與民族識別過程,蘇聯的中亞地區與中國新疆識別出多個跨界民族,如果維吾爾捨用「東突厥斯坦」這個歷史探險家給予的稱謂,很可能新疆/「維吾爾斯坦」因為民族認同差異將會四分五裂。維吾爾人過去多聚居新疆南部塔克拉瑪干沙漠周邊的綠洲城市,19世紀開始逐漸往新疆北部遷徙。
習近平時期更強調新疆「安全」議題,擔心中國邊疆被「外部勢力」利用,或以恐怖主義的形式襲擊,進而挑戰中國主權。2012年開始,媒體披露新疆持續出現幾十起的「恐怖襲擊事件」,2013年10月北京天安門金水橋撞車襲擊、以及2014年3月更發生昆明火車站屠殺,直接觸動並衝擊中共以往首重「經貿」的新疆治理策略。《中國斯坦:不經意創造的中亞帝國》的作者認為,中國對中亞外交政策的源頭在於鞏固中共在新疆的政權,照顧國內需要;國內利益大於外交利益。換句話說,中國對中亞政策是新疆治理策略的延伸。於是新疆的「安全」重於一切,經貿只是一個達到「安全」目標的手段。習近平要完全控制政治權力與意識形態,再確保經濟發展。按照作者的說法,中國在中亞於是成為一個「不經意創造的帝國」,隨著經貿連結漸趨牢固,中國在歐亞大陸的影響力難以忽視。
帝國:形塑一套價值與秩序的霸權
當前政治與國際關係學者,總是掉入「國家」這個範疇,迴避國家其實可以嵌套在帝國概念中。事實上,帝國的政治常常與某些國家相關的概念連結,像是民族、聯邦/國協、政治聯盟、或說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或「一國兩制」下的主權行使,息息相關。帝國因此不應僅是廣土眾民的「大」國家,帝國其實彰顯出一套特定價值與秩序,用以作為擴張或鞏固權力的正當性。於是,帝國最近十多年史學界熱衷於帝國研究,關切美國是否可以稱作帝國,又與過去傳統帝國有何不同,又應該有什麼啟發,像是Jane Burbank and Frederick Cooper及Niall Ferguson的著作。這裡限於篇幅,不檢討史學辯論的看法,採用的是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的討論,參見Michael Doyle, Empir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帝國不是多民族、多盟邦屬國的大型國家而已,帝國傾向形塑並管理全球秩序,以利擴張與發展。國際關係在過去百年的假設都可能有失誤,國家並不平等,國際法的實踐只是一個理想。同時,國家的權力不應只強調軍事力量,否則國際關係的討論就偏向強權政治。至於霸權的概念又太過強調強國與弱國之間的強制影響,忽略這個影響過程其實已經將國界淡化到幾乎沒有實質意義。
帝國不僅是一個政治體制,更是一套國際秩序與價值。換句話說,國際關係學科討論的國際無政府秩序、兩極秩序和多極秩序,其實應該都是帝國面對壓力,所理解並投射出來的世界觀;也就是該跟哪些對手,又應該怎麼競爭或平衡權力的問題。
過去帝國的發展模式可以歸結於現代工業大都會因為發展需要,而向外擴張「都會中心論」(metrocentric empire)。馬克思與列寧於是論證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但是帝國發展還有「邊陲為重論」(pericentric empire),強調帝國擴張到周邊是理所當然,因為那些邊陲地區沒有清楚的政府掌控,或政權高度分裂、經濟型態單調不能自給自足、再加上當地社群沒有清晰的政治忠誠或認同分裂,這樣的邊陲社會情勢有利於帝國擴張。(註)David Lake, “Imperialism: Political Aspects” in Neil Smelser and Paul Balte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1st Edition (Oxford: Pergamon, 2001), pp.7232-7234.
帝國擴張統治的過程中常有各式各樣的「地方中間人或代理人」,他們被賦予權力,不同的邊陲也與帝國中心有各種價值標準不同的契約關係;一旦這些中間人或代理人沒有辦法履行他們的承諾,或帝國中心改變策略,他們地位就會被取消,或轉嫁給他人承擔。帝國統治形式非常多樣,在「都會─邊陲」的基礎上,也可能變成是網狀結構。(註)討論「地方中間人或代理人」在美國統領世界政治數十年的格局,可參見Daniel Nexon and Thomas Wright, “What's at Stake in the American Empire Deb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1, No. 2, 2007, pp. 253-271。
從歷史上來描述帝國內網狀結構的串連,可參見Tony Ballantyne, Webs of Empire: Locating New Zealand’s Colonial Past. (Vancouver: UBC Press, 2014)。
帝國不見得都是「自上而下」,也可以非典型地平行交換,甚至「由下而上」。帝國的邊緣總是被爭奪競逐,也可能影響帝國間的政治(註)Sindre Gade Viksand, “Contentious colonies: The Positional Power of Imperial Peripheri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6, No. 5, 2020, pp.632–651.
至於今後是否有可能在新疆和中亞地區形成跨境的帝國間邊陲,對中國的帝國統治政策進行反噬,則有待觀察。值得注意的是帝國邊陲與底層的發展經驗,邊陲地區能否發展出自己的社會意識,在社會菁英與群眾智識上形成反帝國主義,進而駁斥帝國價值與秩序霸權的生活方式,攸關帝國命脈是否能夠維繫。當然帝國中樞的焦慮也來自底層,擔憂權力脆弱或不及的領域,甚至被其他帝國所利用。(註)這樣的研究愈來愈多,參見例如:
- Adom Getachew, Worldmaking After Empire: The Rise and Fall of Self-Determin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 Mark Condos, The Insecurity State: Punjab and the Making of Colonial Power in British Ind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中華帝國的擴張邏輯與當前挑戰
帝國總是會逐漸發展出一套自己價值規範與行動綱領,這也是帝國的最高戰略指導原則。時至今日,無論中、美、俄羅斯帝國似乎都與自由主義結合,追求自由貿易,將商業利益極大化成為帝國的信念。同時開始劃分陣營,簡單來說還是以「文明」與「不文明」之分來詆毀可能被有效控制的對手,帝國運作的邏輯就是要誘導或強迫,去推動「文明」的價值與交往方式,進入改寫邊陲地區的商業行為、法律仲裁、改寫社會倫理所有的文化面向。對待「不文明」的野蠻群體或國家,可以發動戰爭,殖民地官員或代理人也可以協助用特殊,甚至不符文明的方法去轉換當地社會結構與內涵。帝國與邊陲來往的經驗還可以納入國際組織,嘗試建立集體的價值與秩序。(註)Martin J. Bayly, Taming the Imperial Imagination: Colonial Knowledg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Anglo-Afghan Encoun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換句話說,隨著中國的國力上升,中國進行著帝國式的擴張,其實並非「不經意創造」。中國為了新疆與邊界安全、為了消化多餘的工業產能、為了持續並鞏固已有的經濟繁榮,同時又不要直接惹惱把中亞當成禁臠的俄羅斯,利用從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的資本,投資中亞天然資源,以「一帶一路倡議」全盤推動基礎建設,廣設孔子學院與攏絡中亞菁英,都非偶然。這些內容在《中國斯坦》一書的第三章到第五章多所描述。第六章討論上海合作組織(簡稱上合組織)的時候,作者提及中國學者浮誇地推銷「上海精神」,吹噓這是國際關係維繫的新態度。實際上,上合組織嚴重缺乏制度能力,當然很可能是因為另一個帝國俄羅斯的暗中阻撓。但是隨著時間過去,中俄兩個帝國的實力此長彼消,尤其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發生後,上合組織反而可能成為中亞周邊區域包容最廣的國際組織,未來會否在中國的操弄下,逐漸擴大地緣政治影響力,還在未定之數。
國際關係是在歐陸帝國中建立,但現在大家迷惑於一個由主權國家組成的世界。國際關係學科原本是帝國研究,涉及各種殖民事務的管理、理解帝國內外關係、處置帝國內部多元民族與社會差異。(註)Robert Vitalis, White World Order, Black Power Politics: The Birth of Americ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7)
《中國斯坦》一書指出中國已經透過貿易市場、修築道路與各種基礎設施、傳統與電子物流來連結中亞,所有的規格都指向以中國為準,而不是俄羅斯。儘管俄羅斯也在2011年提出,並在2015年正式組建與運作類似歐盟結構的「歐亞經濟聯盟」,一個由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亞美尼亞5個前蘇聯國家組建的關稅同盟。莫斯科想要在經貿上拉緊前蘇聯國家,但是成就有限,無法藉此限制住中國向中亞的經貿擴張。目前中亞各個國家從中國進口的貨物逐年增加,而且積欠中國的外債還在上升。
第七章描繪中國在中亞的安全足跡,儘管中國安全部隊與中亞鄰國合作的最終目的是要解決中國對新疆安全的顧慮,也就是維吾爾武裝分子的滲透,但是中國與中亞各國的軍事交流日益加強,則是不爭的事實,還在日益強化。(註)如同作者所說,北京的策略是「只做不說」,緩慢改變當地情況,等到木已成舟成為公開的祕密後,改變已然發生,水到渠成也無法抗拒;這其實就是中華帝國擴張的邏輯。 《中國斯坦》在第八章指出中國對阿富汗的擔憂有四點:
- 伊斯蘭主義的暴力恐怖襲擊從阿富汗輸入到中國,當然指涉的就是維吾爾武裝分子。
- 阿富汗動盪威脅到中亞周邊地區,並影響中國在當地利益。
- 中國擔心毒品從阿富汗流入中國。
- 中國懼怕阿富汗成為美國的代理人,憂心美國或印度假手激進團體攻擊中國。
中國的確還在摸索阿富汗,尋找一套風險管控的架構。阿富汗不只有塔利班政權,還有蓋達組織、伊斯蘭國呼羅珊分支(ISKP)、巴基斯坦塔利班,他們都可能利用懂得中文的維吾爾武裝分子,去鎖定並襲擊中巴經濟走廊的工程項目與人員。這些不同的伊斯蘭恐怖主義組織都想要向中亞擴散,維吾爾武裝分子更意圖回流攻擊新疆。阿富汗可能是目前中華帝國向中亞地區擴張的立即挑戰。 20世紀初的國際關係學者爭論如何管理殖民地、如何防止戰爭,但是在傳統帝國的需要下,他們都認為國際事務的核心問題是種族/民族治理。一直到兩次世界大戰後,冷戰浮現之際,國際關係學者自我麻醉式地開始討論兩極國際體系、國際組織與國際政權、國際互賴,其實他們先驗思考與知識都源自從美國或歐洲看世界。但是《中國斯坦》讓國際關係學科再度回歸帝國研究,作者提供豐富的田野調查資料,讓我們有機會再度思考中華帝國的再崛起形式與內涵。
《中國斯坦:不經意創造的中亞帝國》, 拉菲羅.龐圖奇(Raffaello Pantucci)、亞力山卓司.皮德森(Alexandros Petersen)著,高紫文譯,麥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