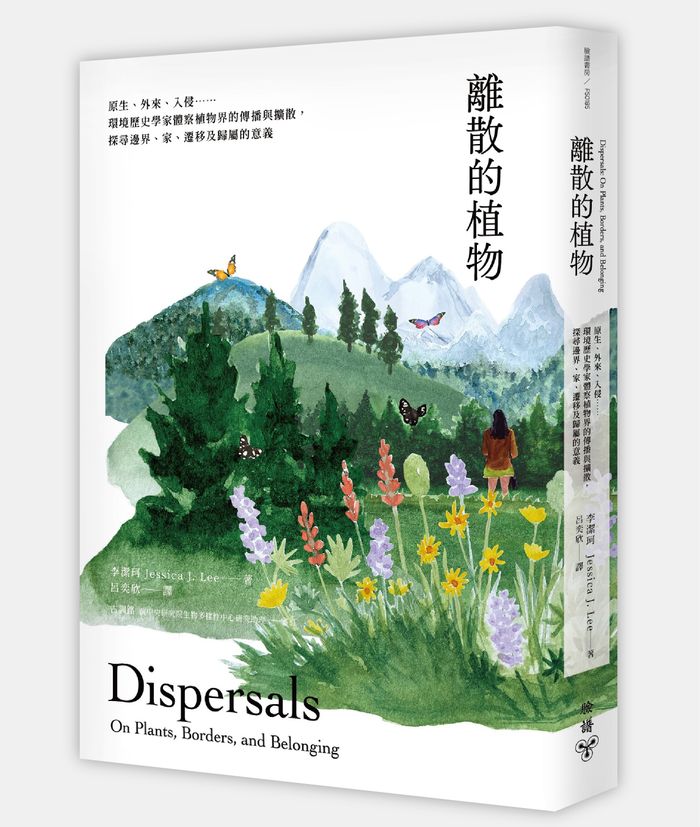精選書摘

人們往往認為植物是靜態的,而「生根」不僅會用來形容植物,有時也描述歸屬於某個地方的某些人。然而,植物可能會意外離開原生地、隨著壓艙水飄洋過海;抑或被遠赴異國的採集者刻意蒐羅來改革母國糧農生產;又或者,在全球化世界中,離鄉背井的移民帶上植物,便將小小一部分的原鄉一起攜往他方。 加拿大籍、台英混血的背景讓作家兼環境歷史學家李潔珂(Jessica J. Lee)對「遷移」、「流徙」、「原生」、「外來」等概念格外敏銳。在《離散的植物:原生、外來、入侵……環境歷史學家體察植物界的傳播與擴散,探尋邊界、家、遷移及歸屬的意義》寫作期間,她偶然因故被迫在2個國家、3座城市、4所不同住宅間輾轉遷徙,觀察人文世界折射於自然環境所呈顯的風景,也反思人類建構的社會與野生環境之間的交互影響。
本文為《離散的植物》第二章〈邊境之樹〉書摘,經臉譜出版授權刊登,文章標題經《報導者》編輯改編。
柏林是座蓋在沙上的石之城。人行道上的卵石以不規則的角度排列,或灰色、或赤褐、或白鑞、或棕色。城市原本有混凝土牆穿過,那是毫無計畫、匆忙建立的牆體,陰暗的疆界圍牆與圍籬長達百哩。未翻新的老公寓是奇特的米灰色調(greige)──塵土與黏膩煙霧的顏色。一年中,許多時候天空看起來都一樣,銀色,不飽和。但我漸漸把柏林與一種奇特的粉紅色聯想起來:像吊鐘花(fuchsia)的夕陽霞紅,或櫻桃在白色冰淇淋上蕩漾的漣漪。這城市的春天有撩人的顏色,就像泡泡糖或五彩紙屑。花朵如雲一般籠罩著樹木。
我在這座城市的第一個家是位於街角的老公寓,就在貝瑙爾大街地鐵站(Bernauer Straße U-Bahn)旁,它讓我想起《竊聽風暴》(The Lives of Others)這部電影。房東是個美國藝術家,他以復古的東德家具裝飾房子,房間也沒有翻新。樓地板並不穩固,灰泥剝落(在這城市就能以「創意」一詞簡單帶過),從陽台可眺望柏林圍牆原址步道。我搬進去的那天,房東讓我看地窖──他說,這裡的人曾經挖掘逃難隧道,講得好像這樣會讓人更想租──並朝著公寓的儲藏間一比。我忍不住盯著牆,看著磚與灰泥補過的部分。我再也沒走進地窖。
在柏林這座城市,有牌匾標示著圍牆過去的範圍。我在湖中游泳而過,好奇哪個邊界是在水中劃定的。圍牆路這個空間會讓我們悲痛,在某些方面也應該如此。但我後來得知,春天時,這裡也是櫻樹(cherry tree)生長的地方。
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日本朝日電視台發起一項運動,共捐贈10,000棵櫻花樹給柏林,種在圍牆原址留下象徵意義的空間:花朵表示讓分裂的城市再度統一。後來,柏林的其他街道也種起櫻花。櫻花樹排列在我住的老社區街道邊、種在我上一棟公寓的院子裡,也點綴著附近公園的草坪。春天時,在圍牆最多人造訪的地段,明亮的花朵在樹上成簇綻放,呼喚當地人走出冬天那片沉重的灰暗。
我住在那裡,度過了6個春天;那段時間裡,生活的喜悅超乎我的想像。在櫻花樹間漫步尤其愉快。每一年,我都想要用力吸收櫻花的色彩與美,彷彿這樣就能繼續享受一整年。在這一度讓人覺得沉重得難以承受的城市,櫻花超乎想像輕盈,甚至毫無重量。

我說的是櫻花(cherry blossom),但植物學上的科名是源自於薔薇(rose):薔薇科(Rosaceae)。薔薇科通常美豔動人,許多薔薇科的花朵與果實相當馳名,例如玫瑰、花楸(rowan)、覆盆子(raspberry);山楂樹與繡線菊(meadowsweet)。薔薇科名列世上最具經濟與美學價值的物種,有蘋果(apple)、扁桃(almond;杏仁果)、杏(apricot),還有李子(plum)、桃子(peach)、梨子(pear)。櫻樹是薔薇科李屬(Prunus),其中包括結出果子的品種,以及具觀賞價值的品種。櫻樹的歷史可說是遷移的歷史:會結出食用果實的歐洲栽培種被定居殖民者帶到北美,而耐寒的北美木材櫻樹則正好反其道而行。至於觀賞用的通常會以日文:sakura為人所知,也同樣展現出轉瞬即逝的特性。這些樹都是旅行過的樹。
櫻花的種類很多:中國、韓國與日本的野生山櫻花(wild mountain species)已培養出400多個品種。要精準追溯這些櫻樹的譜系與命名,向來非常複雜,觀賞用栽培種櫻花比較常被歸類為里櫻(Sato-Zakura)。雖然確切名稱很難明確說明,但一般種植在城市街道上的是各種山櫻(Prunus serrulata)的品種,以重瓣有摺邊的花朵聞名;中國櫻桃(Prunus pseudocerasus)則有扁平攤開的花朵;江戶彼岸櫻(Prunus × subhirtella)是在冬天綻放櫻花;或者最常見的染井吉野櫻(Somei-Yoshino;Prunus × yedoensis)則有粉嫩的粉白色花瓣。
雖然西方人屢屢感到新奇,但櫻花長久以來皆在日本文化占有中心地位。因此在1893年,一本寫給日本年輕植物學家的手冊在解釋樹木解剖學時,僅以櫻花為參考點,說明其葉子、根、樹枝,把櫻花樹當成日本樹木的原型。櫻花也有專屬的慶祝祭典,這樣的慶典說明了櫻花數個世紀以來,在農耕文化宇宙觀中的地位:健康準時開花,代表這一年稻米會豐收。在8世紀之後,日本皇室開始舉辦年度花季,「花見」在城市居民之間也愈來愈受歡迎,許多人會吟詩作對,談起花朵轉瞬即逝之美。經過幾個世紀之後,這個春日活動就專屬於賞櫻,也就是欣賞日文中所謂的「花之王/花之后」,即使花見活動過去尚納入許多其他花朵。
到19世紀晚期與20世紀之交,日本在第一次中日戰爭獲勝,因此鄰近日本的台灣落入其掌控。1905年,日本也占領韓國。正當日本占領附近鄰國的範圍達到巔峰之際──與西方的殖民行為不無類似──也與歐洲和北美強權培養關係。贈送櫻花樹成為日本外交的重要元素。1909年,美國旅遊作家伊萊莎.斯基德摩爾(Eliza Scidmore)長久以來深愛櫻花,遂建議第一夫人海倫.塔夫脫(Helen Taft)在華盛頓特區種植櫻花。兩年前,威廉.霍華德.塔夫脫(William Howard Taft)與妻子一同前往日本時,海倫就深受櫻花吸引,於是很快接受斯基德摩爾的建議,與日本大使館著手安排。投入了龐大的外交努力──包括1909年冬天,2,000棵櫻花樹初次啟航,但抵達後才一個月,就因為病蟲害而得焚毀──計畫終於啟動。第二趟是由東京都贈送櫻花,代表日本給予美國的贈禮,在1912年達美國。那一年,總共有3,000棵樹沿著華盛頓特區的潮汐湖(Tidal Basin)與波多馬克河(Potomac River)種植,代表締結友誼之禮。白宮後來回贈山茱萸。

在我稱為家鄉的城市,也曾經獲贈樹木:1959年,第一代日裔加拿大人與日本領事館共同推動計畫,贈送多倫多2,000株染井吉野櫻。2019年,英國獲贈超過6,000株的櫻花樹,首先在倫敦幾座皇家公園栽種,另外還有許多是在全英國種植。幾千株在前柏林邊界種植的櫻花,只是栽種的眾多櫻花的一部分,後來尚有許多櫻花以友誼與外交之名種植、包裝、搭船或飛機,足跡遍及全球。
不過,櫻花的象徵未必那麼一目了然。櫻花代表生命力,這個意涵延續了好幾個世紀,然而在19世紀末,櫻花飄落的花瓣恰恰變成相反的意思:死亡。「日本軍國主義最重要的比喻,」人類學家大貫惠美子(Emiko Ohnuki-Tierney)說,「是說一個人要像飄落的美麗櫻花瓣,為天皇而死。」
隨著日本帝國勢力擴張,櫻花的黑暗理想也擴張了。19世紀末的哲學家與軍國主義者西周(Nishi Amane)明確把櫻花定位為與牡丹(peony)和木槿(rose of Sharon)相對立──後兩者分別是中國與韓國的象徵──指出櫻花會在凋零之前,就好好從樹上飄落。西周的思維對於皇軍的基礎而言很重要。他認為,櫻花代表日本這國家與人民的美德與優越特質。到了第二次中日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櫻花與帝國的連結鞏固了:日本軍機上畫著一朵櫻花圖徽,女人也帶著開著櫻花的樹枝向飛行員揮舞道別,而特別攻擊隊的飛行員會在胸前別著櫻花,飛向死亡。
櫻花不僅被當作象徵:日本在其占領的韓國與台灣等領土,都種下許多真正的櫻花樹,還找出原本已經種植的櫻樹,予以維護。這種對於地景的干預,是希望把殖民地變成日本的土地,繼而啟發人民的轉變。所以他們在韓國原生的濟州櫻(king cherry tree;Prunus×nudiflora)之間,又種植了各種日本櫻。1995年,日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投降了50年之後,首爾景福宮將日本人種植的櫻花砍除。殖民遺緒依然和櫻花有象徵性的密切連結,即使其美麗仍舊受人歌頌。
在台灣,山櫻花(Prunus campanulata)是原生物種,而染井吉野櫻則在城市種植,在宮廟與佛寺都見得到蹤影。然而,台灣的季節和日本並不一樣,當地顯然溫暖得多,早在1月底或2月中櫻樹就會開花,通常會碰上春節(農曆年)。
在日本投降、把台灣交給國民黨──另一群殖民者──之後的幾十年,我家人會發現自己就身處於這些樹木之間。在冬季步入尾聲、春季即將來臨的交界時節,我母親會跟著父母踏上陽明山賞花,那時幾乎整個台北的人都出動了。我母親的童年不算快樂,然而這段記憶卻格外突出。他們很少全家出遊──外公在空軍服役,住在車程好幾個小時之外的地方──但是每年賞櫻的行程,我母親就會有雙親相伴。外公會讓母親坐在他肩上。對母親來說,櫻花代表的就只是輕輕盈盈,代表著愛。她不會想到花瓣飄落,或是任何死亡氣息。
以大自然的遷移來服膺帝國主義與國家主義,並不是日本的專利。環境史學家克羅斯比(Alfred Crosby)曾提出知名的主張,認為探索時代不僅把「新世界」的植物,例如馬鈴薯(potato)、番茄(tomato)與菸草(tobacco)帶回歐洲,也把歐洲植物種植到新獲得的殖民地土壤。歐洲赤松(Scots pine)、蒲公英(dandelion)與常春藤(English ivy)都從歐洲來到北美,而在印度,非原生種的引進則可追溯回英屬東印度公司的植物園。殖民地建立了,殖民者惦記著的家鄉植物也跟著到來。
透過神話創造與象徵主義,自然界就代表著人類力量的理想:櫻花象徵日本對天皇的忠誠,橡樹(oak)則代表英國的堅忍。白頭海鵰象徵美國人的自由精神,但在德國,鷹依然帶著有問題的形象:帝國鷹(Reichsadler)從19世紀末以來就是力量的象徵,如今因為過去納粹曾引以為象徵,新納粹主義者又持續沿用,因此不免遭到污名化。這兩種鷹並不相同:原本帝國鷹的圖案經過重新設計,至今依然會用新的設計樣式,是老鷹張開優雅有弧度的翅膀。但是納粹的符號則剛好相反,是一隻僵硬的老鷹站在納粹萬字符上,翅膀在地平線上奮力張開,從過去到現在都傳達著深刻的恨意。
人類以外的自然界──從花到鳥類──依然承載著人類歷史的包袱,在我看來似乎不公平。這樣頂多是把人類的敘事放到一個遠比我們更複雜的世界。不過,經我們改變的世界已無法逆轉;人類在世界各地移植與引介物種時,鮮少會顧慮到以公平為準,而我知道這樣的思考方向是太天真了。羅瑞.薩伏依(Lauret Savoy)曾在她思慮縝密的回憶錄《痕跡》(Trace)中寫到,人類企圖在「一個蒐集人類的殖民世界,也從中蒐集異國動植物」,藉此為自然賦予秩序。在人類的行為之後,樹木提醒我們,自然不是中性的,荒野不會是一片空白。不過,我還是好奇這些我們打造出來的象徵,會如何回應我們訴說與之相關的故事

科學家如今透過櫻花,發現到比過往的意象更關鍵、更有潛力的東西。隨著地球暖化,櫻花儼然成為人為氣候變遷的哨兵。
東京靖國神社是專門紀念為帝國捐軀的軍人的地方,這裡有一株櫻花樹成為所有櫻花樹的代表。靖國神社的櫻花標本木是有幾十年樹齡的染井吉野櫻,會用來衡量櫻花季的起始點與盛開期。但是一棵樹木不足以衡量世界的變化,因此至少從1930年代開始,日本科學家就已開始整理櫻花祭的資料:櫻花祭的歷史時間點可以提供獨一無二的洞見,說明長久以來的溫度變化。關於日本櫻花祭的敘述,也比開花樹木的常見資料集要久遠得多,從15、16世紀開始就有豐富的紀錄,有些甚至可以追溯回九世紀。這些紀錄追溯到的時期,是櫻花曾標記著農業年度,以及象徵生命力與浪漫的年代,還有承擔著軍國主義陰暗色澤的那幾十年。從幾個世紀前的日記與宮廷紀錄,都可看出以前氣候較涼爽的痕跡。
資料顯示,櫻花通常從3月底到5月初開放6個星期。就如同歷史上的開花時間點往往可以預示農作豐收或欠收,過去的櫻花樹也給了我們顯而易見的警告。到了1980至1990年代,櫻花樹開始一直都比過去1,200年還要提早開花。
2019年12月,在全世界的人幾乎都待在室內前的幾個月,人在柏林的我常出門走走。大部分的日子,氣溫離冰天雪地還很遠。連續兩年冬天,我都把我的派克大衣留在真空袋,放在床底下;第二年根本沒有下雪。樹木回應了。這年,附近公園在秋天開放的櫻花,比我過去看見的都還要盛開。一年前,我讀到日本的櫻花樹在10月開放,因為那一年來的氣溫在極端氣候之下欺騙了櫻花。我無法不去想,在秋天看見櫻花色彩有多奇怪。我家附近公園的櫻花在年節假期都有開花,冬天開了整整10個星期。這些花朵比春天的要小,大概只有四分之一,但是形狀完整,花瓣緊密堆疊,綻放冷光。白色花瓣取代雪花,在1月鋪滿地面。
等到櫻花再度於3月綻放之際,新冠肺炎疫情已經來襲。先生與我戴上口罩與墨鏡,沿著圍牆路的櫻花樹下遛狗。在灰濛濛的天空下,粉嫩花朵令人著迷。這是一塊留有失落痕跡的土地。樹木將樹根延伸到土地之下,或許漫不經心地,在路面撒下花瓣。那年春天,我訝異發現,櫻花能承載加諸其上的歷史重量,即使是那麼短暫,之後才翩翩飄落。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