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太安毒產地在短短5、6年之間,從中國廣東沿海轉移到緬甸撣邦,市場開始失控和翻轉;跨國運毒集團將安毒從金三角、中南半島、順著海路送往台灣、東南亞、大洋洲及東北亞,以「千里長征」方式走私致命的毒品。5年來,台灣販毒集團在各國被查緝的規模,一次比一次大;而光台灣,吸食安非他命被捕的人口從每年2萬多人快速成長到3萬多人。
運毒鏈裡,不同國籍職掌不同,台灣毒梟不但吸收製毒師、亡命之徒、買漁船組跨境走私船隊,更懂得市場行銷,展開了「一條龍式」的販毒產業鏈。這已讓聯合國毒品與犯罪問題辦公室(UNODC)點名台灣,澳洲、日本、印尼等國也注意台灣毒梟和漁船的運毒能量。
面對日益嚴重的毒品問題,被視為反毒戰神、同時是新世代反毒策略主要撰寫者,剛卸任的前高檢署檢察官王捷拓受訪時說:「對境外的主導機關是誰?主政機關是誰?沒有!」他點出目前多頭馬車的情況。
司法互助困難,緝毒機關紊亂,如何截斷一條龍的販毒產業鏈?
烈日穿過熱帶叢林,士兵們捲了捲袖子,試圖讓身上濕黏的制服變得舒適一些。休息時間裡,不少人將步槍擺在身旁,點起雪茄享受執勤外的悠閒。座落於緬甸北部撣邦的山區,士兵身後是一座他們所把守的化學工廠,這裡常年來被反抗緬甸政府的軍隊把持,是一處連政府與法治都無法企及的國中之國。
工廠外的士兵以撣族語交談,台語則此起彼落地在工廠內響起,幾位台灣人拿著燒杯與容器,正神情嚴肅地混合著化學液態原料。身為工廠裡的製毒師,他們趕工製作的是被簡稱為ice、冰毒、安毒的甲基安非他命(Methamphetamine)。不出數個月,這些產品就會跨越4,000公里抵達周邊國家的黑市,不分種族地區,層層被交易到中盤、小盤和施用者的手中。
在這條毒品的千里長征之路裡,有香港人、中國人、泰國人、大馬人、日本人、緬甸人的參與;但其中,台灣人的「貢獻」卻是不可小覷。
一份報告,多少解答了幾位警官的疑惑。

2019年的3月與7月,UNODC位於泰國曼谷的東南亞區域辦公室發布〈東亞與東南亞合成毒品報告〉(Synthetic Drug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東南亞跨國組織犯罪:演變、成長和影響〉(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in Southeast Asia: Evolution, Growth and Impact)兩份報告,皆點名「台灣跨國犯罪組織(TOC)」在這個區域的毒品販運鏈中佔有「重要角色」(significant role)。
但這個「重要角色」是指什麼?為了進一步理解台灣被點名的背後,《報導者》聯繫了3個月,終於越洋採訪到撰寫報告之一的UNODC研究員沈仁植(Sim Inshik)。
韓國裔的沈仁植透過視訊受訪。他曾服役於韓國海軍情報單位,在UNODC已工作7年,常飛到北京、東京等地交換情報,對亞太販毒體系有相當程度的瞭解。在報告中,他們首次點名台灣。對此,沈仁植解釋,雖然在撣邦製作安毒的製毒師來自各國,但台灣籍的製毒師有純良的技術,讓他們成為亞太安毒供應鏈裡的要角。
實際例子也說明了沈仁植的想法。2015年,數輛載著26公噸安毒前驅藥物麻黃鹼的卡車,在泰國與緬甸撣邦邊境被查獲,3位台灣籍製毒師也在車隊之中,這是緬甸官方首次發現台灣販毒組織涉入撣邦的毒品製造與運輸。
不只是製毒師,台灣人也扮演精明的「交通」,亦即毒品運輸者。
印尼國家緝毒局主任赫魯.威納科(Heru Winarko)接受《報導者》合作夥伴《Tempo》採訪時指出,雖然輸入印尼的毒品並非來自台灣,而是從緬甸進口,但負責運毒的大多數都是台灣漁船跟台灣人。而印尼至今因販運毒品被判死刑的總人數123人裡,就有21人是台灣人,佔了總數的六分之一。(延伸閱讀:〈印尼監獄中的台灣死囚──千里運毒的漁工和男人們〉)
5年來,台灣的販毒集團也一次又一次地在各國打破當地紀錄:2016年台灣籍嫌犯運送600公斤安非他命進入沖繩遭捕,成為日本當時破獲毒品數量最高紀錄;2017年台灣籍嫌犯運送超過1,000公斤安毒運入印尼,創下印尼史上最高的查獲量;2018年,韓國警方在仁川破獲的安毒販運也再度刷新紀錄,循線追蹤後發現,同樣是台灣販毒組織所為。
然而台灣人在亞太毒品走私鏈的角色大增,是在近5年才發生的轉變,這多半導因於亞太毒品主產地的變化,從中國廣東一舉移到緬甸撣邦。

「風險是毒品生意的靈魂,要避開風險才能獲利,」在調查局主責查緝毒品超過20年的前毒品防制處處長、今年(2020)剛轉任為毒防處研究委員的單培祥,一語道破亞太毒品販運鏈在這幾年改變的根本原因。
安非他命在亞太地區氾濫的狀況從2014年之後開始失控,最主要是安毒產地轉移到了緬甸撣邦的山中。「以前抓幾百公斤就是大案子,現在抓上千公斤也是很常見了,」單培祥指出,雖然2014年以前在中國廣東省沿海地區的博社村裡,幾乎是全村都在製毒、販毒,被戲稱為「製毒村」。2014年初,中國官方動用3,000多名警力,一舉剿滅此村。
「製毒村」被消滅之後,逐利的販毒集團逐漸轉往一個周遭國家力量無法企及的地點,也就是長年遭到地方反抗軍把持的緬甸撣邦山中。「那是一個沒有風險的地方,你愛做多少就做多少,幾百公斤、幾噸的量都出得來⋯⋯等於是有當地政府(地方反抗軍)保護你。現在的狀況比在中國大陸更嚴重,產製等於是無法可管,」單培祥點出了這個關鍵性的改變,而這個改變也翻轉了亞太毒品市場。
根據UNODC年度毒品報告顯示,2013年亞太安毒市場有150億美元(約新台幣4,500億元),到了2019年則暴升至610億美元(約新台幣1兆8千億元),成長近4倍。

地點的改變,除了降低安毒的生產風險,也改變了毒品運輸的方式。
以往安毒生產地聚集在中國廣東沿海村落,運輸都是以一次幾十或上百公斤為主,在商船的貨櫃中夾藏毒品,銷往台灣、韓國、日本等目的國;因距離較近,往來次數頻繁。但隨著製毒大本營轉到撣邦山區,出海的路途從近百公里一下增加到上千公里,遙遠的距離讓運毒風險徒增,毒梟們因此想盡辦法提高產量來吸收被抓的風險,這導致近幾年亞洲毒品走私的數量,很快上升到以「公噸」為單位計算。
2019年《路透社》(Reuters)一篇調查報導中發現,在緬甸撣邦,一個有台灣人涉入的販毒集團,標榜著只要有金主下訂安毒,集團絕對「使命必達」。若毒品運送中途遭到執法人員破獲,集團會自行吸收損失、再次運送,直到成功抵達目的地為止。
雖然跨境走私演變為「千里長征」,但販毒集團依舊利用中南半島鬆散的法治,以行賄打通關,安毒因此順著海路被送往大洋洲及東北亞等目標國。有20年緝毒經驗的蕭瑞豪指出,對販毒集團來說,10次運送只要有2次成功就可以賺回成本,更何況成功的機率遠比預估的高。這就是2014年之後,甲基安非他命在亞太各國氾濫的主要原因之一。
管不到的製毒工廠、擴大的產量,造就了販毒集團有恃無恐。
沈仁植指出,亞太的販毒集團並不是將個別國家看作市場,而是把整個亞太地區當做一個完整的市場。在這個市場內的集團並不是如歐美毒梟電影中互相殘殺、或是擁有嚴密的階層組織,更多的是互相合作,有錢大家賺。
「尤其是最上面的源頭,他們根本就是生意人,不是幫派、不是凶神惡煞,」單培祥也點出,亞太毒品販運鏈裡分工細節,各司其職:金主負責出錢下訂單,製毒師負責在撣邦製作毒品,「交通」負責利用漁船運送毒品,抵達目的地國家後還有當地的犯罪組織負責銷貨。但這些角色通常不會知道其他人的存在,只負責自己的工作。這些不同國籍、功能職掌不同的組織相互搭配,專業化的分工讓走私更為順暢,同時也加大了各國執法單位的查緝難度,讓緝毒上的「斷鏈」成為常態。
製毒風險劇降,製程加速,造就供給量的上升;大量安毒流入市場,又導致價格下降,這意味著吸食的門檻放低。低價促銷的現況,就像一場毒品大拍賣,不僅一舉擴大了需求,也拉抬了供給。
根據UNODC統計,東亞、東南亞與大洋洲3個區域總共有1,200萬的安毒使用人口;台灣自身也深受其害,每年因吸食安非他命被逮捕的人數,2014年有2萬多人,2017年達到3萬7千多人,近年則維持在3萬人左右。施用甲基安非他命的初犯人數佔一、二級毒品初犯者的比例,從2009年的43.6%上升到2018年的85.1%,顯示安毒對台灣的危害持續增加。大批施用者的面貌也在變化,有職業者以及高教育程度的施用人數,快速上升中。高檢署多次強調安非他命是台灣主要毒品問題,應專案解決。
即便各國政府努力緝毒,向毒品宣戰,一次燒毀數十噸毒品,印尼、菲律賓當局當場擊斃運毒者的新聞也屢屢躍上國際,但這個暴利市場,依舊未能阻絕運毒集團的猖獗。
一位曾經做過小盤運毒的受訪者告訴我們,走私毒品在台灣的上岸處,中部多在梧棲港,南部則在東港。一旦接獲上岸通知,港口邊就會湧進十多輛準備接貨的轎車;貨進來的那幾個晚上,各地中盤會啟動自己養的年輕人,讓他們開車或騎車出去銷貨。只消一晚,車子座位底下的腳踏墊就會擺滿一綑又一綑的現金。
因為暴利,包括台灣在內的販毒集團也搶進緬甸撣邦分一杯羹。
在亞太地區安毒風暴裡,台灣販毒集團不僅被UNODC點名,菲律賓也同樣將矛頭指向我們。
過去3、4年,菲律賓總統杜特蒂(Rodrigo Duterte)在國內掀起一場又一場的掃毒戰爭;但2017年,在取締反毒揚起的煙硝和鮮血中,杜特蒂卻特地點名台灣:「他們(台灣毒梟)在公海上製造『沙霧』(Shabu,類安非他命),然後把毒品丟到海裡,一個個寫著漢字的空箱子,實際上是來自台灣,全部都是。」就在菲國司法部成立120週年慶祝活動上,杜特蒂如此指出。
杜特蒂公開指控台灣人的介入,導致菲律賓成為亞洲毒品轉運站。然而杜特蒂所說的台灣人是誰?橫跨多國的毒品交易是怎麼被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清楚標記?

一位緝毒近20年的警界高層透露,從源頭叫貨、海上走私到異地販售,一條龍模式正為台灣的國際毒梟們帶來鉅額利潤。而當中最知名的,莫過於林孝道這個名字。
從金三角產地的接洽開始,到毒品在海上的轉運、靠岸搶灘、上岸販售,林孝道建立的販毒網絡一手包辦全部工作。「像人家販毒報酬都是領現金,林孝道不是。他是收取整批貨的15%,就是因為能夠自運自銷,一條龍式全方位發展,」曾與林交手的台東地檢署主任檢察官黃榮德形容道。
台灣級別最高的警官、現任警政署長陳家欽,在2000年任職於高雄刑警大隊時也與林交手過,警職生涯裡,他始終將林孝道視為盯哨對象。
靠著靈活的販毒手段,林孝道還一舉從台灣打進了國際賽場。
刑事局偵三隊是專門打擊毒品跨境走私的專責單位,多年的查緝過程中,他們發現林孝道販毒的觸手早已伸入亞洲毒品最大產區:緬甸撣邦。憑藉著與當地交好的關係,林將毒品賣到中國、日本、韓國、澳洲,南亞的巴基斯坦、斯里蘭卡,歐洲的荷蘭,更接觸中南美洲的毒梟,試圖擴展生意範圍。一條龍式的毒品走私鏈不只讓偵三隊傷腦筋,包含前陣子點名台灣的菲律賓政府、美國緝毒局和澳洲、泰國、中國、日本等地的緝毒單位都密切注意林孝道的一舉一動。
從林孝道架起的一條龍運毒模式裡,可一窺台灣人在亞太毒品販運鏈的角色。

50歲出頭的屏東里港分局偵查隊隊長陳忠義與林孝道年紀相仿,他幾乎見證了這位國際毒梟發跡的過程。一下將時間拉回1980年代末期,陳忠義說,當時年輕的林孝道還只是一名靠賭維生的街頭混混。在台灣錢淹腳目的時期,每個人身上多少都有一些錢,林孝道看中了這點,便不斷用「詐賭」來賺錢。
千禧年左右,靠著台灣師傅的傳授,林孝道成了出色的製毒師,開始到東南亞國家製作安非他命牟利,並且逐步搭建自己的販毒網路。因他製作的成品好、純度高,即便缺乏與當地人溝通的管道,但高超技術屢獲肯定,不僅發了一筆橫財,也讓當地販毒集團執意把他留在境內,甚至一度限制他的行動。
靠著走私賺進大把鈔票,這位國際毒梟更進一步砸錢與政商兩界建立密切關係,甚至打算效仿鄭太吉的行徑,一度準備出馬參選屏東縣議員,直攻議長寶座。但因牽扯多起毒品和偷渡案件,他最終打消了搶攻政壇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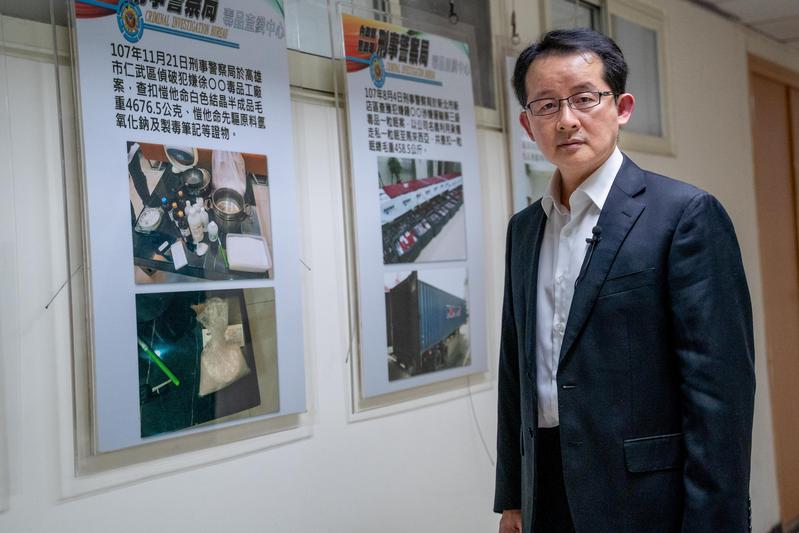
高調作風讓林孝道一直是執法單位的鎖定目標。只是在貓捉老鼠的遊戲裡,他始終在黑白兩道遊走,並設斷點自保。去年兩起破紀錄的毒品案件中,藏身在背後的林孝道都扮演了關鍵角色。
2019年5月,台東地檢署查扣了中型漁船藍悅號所走私的829.44公斤安非他命;幾天後,在當地漁船金海銘號上又發現了627.92公斤的愷他命(又稱K他命)。短時間破獲1.5噸重的毒品創下國內查緝紀錄,主導買賣的張姓與廖姓販毒集團也隨即落網。
兩起案件牽涉不同的販毒集團、走私不同的毒品,平行間並不存在關聯性;但再向下追查,兩起案件就像弧線,交錯在林孝道的身上。負責支援該起案件偵辦的蕭瑞豪就發現,兩案查到最上端其實存在著交集,基本上幕後的人一致、貨源相同,境外組織幾乎是同一掛台灣人,最重要的海上運毒也都是由林孝道負責打點。
經由中、大型漁船走私而來的毒品,大量流入台灣黑市中。據警方統計,近3年,林孝道所涉及的重大走私毒品案起碼4件以上,走私毒品超過3,000公斤,當中又以安非他命為大宗。
「光他一人就佔了全台三分之一的毒品源頭,」在破案記者會上,陳家欽疾言厲色地指出。以刑事局統計數據來估算,2018年查緝毒品總量高達7,992公斤,等於光是林孝道一人,一年就走私了2,600公斤以上的毒品入台,可供1,000萬人吸食。

靠著販毒,林孝道積累了數百億元的資產,這讓他得以出手闊綽吸收各路人馬為他賣命,建立分工專業的毒品帝國。
審訊期間,曾多次與林孝道交鋒的台東地檢署檢察官許萃華透露,由於林操作的都是跨國毒品買賣,無論交易時間、價錢或交貨地點,都需要懂得當地語言的人來協助溝通。因此他花了不少精力在尋找會日文、英文或緬甸文的雙語人才,以按月給薪的方式將這些人納入毒品交易中。
除了朝專業化發展,他的毒品網絡更具備組織化的動員能力。以「屏東王」自稱的林孝道,在當地收了數十個忠心耿耿的小弟,這些人幾乎都是從十多歲就開始被栽培成為組織的一員。他們的任務在於承擔風險最大的分段運輸工作,人多勢眾也能減少黑吃黑的可能,讓交易順利。
此外,跨境走私多半牽涉眾多國家,特別需要有人在各國之間幫忙打點運輸事宜。應對這個需求,林孝道特別在中國雲南和泰國邊境建立了一處基地,大量吸收亡命之徒,並將這些人派往各地作為聯絡人員,以確保運輸順利。
得以建立如此綿密具規模的犯罪組織,許萃華指出,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林孝道會在人極度需要幫忙、走投無路的時候給對方金援。「像通緝犯逃亡在外的,他會給錢讓這些人在外面重新開始,還會幫忙負擔逃犯的家計;一次給個3萬、5萬、10萬都是常態,因此光一個月給旗下兄弟的開銷大概就要3、400萬元起跳,這些受了恩惠的人自然甘願為他賣命,」她解釋道。
槍與毒常相伴,穿梭在國際叢林裡的林孝道並沒有忘記這個真理。為了護衛自己的毒品帝國,早年他採取「以漁換槍」的模式:由於他在菲律賓擁有漁業公司,便以漁獲賣的錢來換武器,並僱用數十名菲律賓南部民答那峨島的叛軍。長槍、短槍、手榴彈和火箭砲武裝了他的走私漁船,近年更直接靠著販毒的鉅額利潤來購買這些服務。
為躲避查緝,林孝道甚至將這些遠洋船隊隱藏在法規背後。在專業的指點下,他旗下船隻的船籍多半登記在蒙古或玻利維亞等內陸國家,再不然就是透過代理商登記掛籍在巴拿馬等地;由於缺少船籍國的監督,他的船隊形同「幽靈船」,在公海上肆無忌憚地走私毒品。
當中,規模最大的漁船噸位高達700噸,上面搭載了海水淡化系統,由菲律賓叛軍武裝,不固定船隻進行補給,形成半自給自足的狀態;一年幾乎300天以上都在公海中航行,作為毒品跨境運輸的海上中繼站,被視為林孝道的「海上毒品要塞」。
然而利用遠洋漁船走私毒品,並非林孝道一人的專利。今年司法機關也成功破獲另一位操盤北部毒品交易的台灣毒梟,以同樣手法在寮國、柬埔寨、越南等地經營毒品走私事業。
無論是林孝道或是其餘尚未落網的台灣毒梟,透過漁船在海上接應自緬北出產的毒品,再一路運回台灣或是銷售到其他國家,無數條航行軌跡構成了這條影響亞洲各國的毒品販運鏈。多年來他們在亞洲毒品販運上的著力甚深,都相當程度地解釋了「台灣跨國犯罪組織」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為了釐清台灣跨國犯罪組織對各國的影響,《報導者》花費數月聯繫日本駐台警察聯絡官及去年開始駐台的美國緝毒署(DEA)官員,但因事涉敏感資訊,最後他們只給予官式回答:「日本與台灣執法單位密切合作」、「美國緝毒署感謝台灣夥伴在雙邊和多邊調查上所做的貢獻」。
運毒產業的跨國合作特色,讓美國、日本、澳洲這幾個安毒最終目的國,開始警醒。由於受害深,他們紛紛在近年主動加強與台灣的合作。
美日警官之所以駐點台灣,是發現台灣人在金三角有長足的關係──不只是敢冒著高風險製毒,也透過遠洋漁船的運輸優勢,賺取極高價差。

這段歷史的痕跡,得從現今的產茶勝地、泰北的美斯樂(Mae Salong)中找出端倪。1994年,調查局派出第一任法務祕書,駐點在泰北城市清邁,當時重點任務指明需嚴密監視毒品產出地點美斯樂,因為在20世紀末期,全世界的海洛因有60~70%是來自這裡。該地的海洛因以磚塊的形式輸出,標上醒目的「雙獅地球牌」商標,好證明毒品的高純度,博取買家信任。
身為早期派駐的人員,調查局國際處科長賀宗正在2000年就駐紮過泰國。回憶起那段過往,他指出,國民政府在美斯樂留下孤軍部隊,坤沙與羅星漢兩位孤軍領袖兼毒梟,在當時大量種植罌粟提煉海洛因,以此獲取暴利當作軍費,據地為王。而他們都是華人血統,講的是中文。
「那時在泰國北部只要會講中文,就會被懷疑跟不法勾當有關係,尤其是毒品,所以常有人被掃射、被暗殺甚至被丟炸彈,我在餐廳吃飯都要坐在面對出口的座位,隨時注意周遭,」賀宗正回憶,法務祕書的工作就是將當地華人的情資交回台灣,同時也跟泰國緝毒單位合作。當時台灣緝毒單位跟泰國官方的互信仍然薄弱,很多關係必須由法務祕書來突破和建立。他也指出,在那3年裡,他曾經到過緬甸十多次,就是希望跟當時極度親中的緬甸軍政府打好關係。
在泰國政府軟硬兼施下,美斯樂於2005年試圖擺脫毒品形象,孤軍後裔將原本的罌粟田轉型種植咖啡豆,希望一改泰國國內對泰北華人的負面看法。也因為這樣,調查局在清邁的據點在2014年撤裁。同時因毒品轉至緬北撣邦,調查局在2017年於緬甸仰光設立據點。
「撣邦北部的人有90%都會講中文,因此他們合作的國際販毒集團都要會說中文,」韋恩指出,撣邦的反抗軍需要軍費跟緬甸政府對抗,所以跟來自台灣、中國、香港等地的華人販毒組織合作,以抽取稅金、提供人力、軍隊護送運輸,甚至幫助建立工廠等合作方式賺錢。
對在亞太各國賺取的暴利的華人販毒集團而言,提供給反抗軍軍費的支出有如杯水車薪。在軍隊協助下,販毒集團得以毫無顧忌地建立販運網絡,這也使得安毒產量飆升。

狡猾的販毒集團不斷在各國司法管轄區域內流竄,這讓意識到問題的國家紛紛重啟合作,試圖圍捕這些現代的毒品海盜。順著這股趨勢,台灣政府也在2017年頒布四年一期的「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將「溯源斷根」列為緝毒行動的重點,同時啟動了一系列的變革,著重打擊境外毒品問題。
而今年初,林孝道的落網總算讓這個政策注入一劑強心針。
今年2月,台東檢警宣布瓦解了林孝道的販毒勢力。趁著他攜家帶眷到花蓮住宿遊玩的期間,大批警力已經完成蒐證,一舉湧入飯店外圍,逮捕一身悠閒裝扮的林孝道。
對於破案,陳家欽在記者會上直言,此案象徵打擊毒品犯罪的能量達到新的里程碑,過去毒梟集團在每一個環節都會設置斷點,導致無法追查毒品來源和貨主;這次透過與國際的合作,才能有效打擊毒品源頭。
而在負責承辦此案的黃榮德看來,林孝道的落網則是反映出新世代反毒策略確實起了效果。
他說,以往各機關辦理毒品案件,因為沒有單位統一指揮,所以不一定會有縝密的計畫,往往是抓到其中一個嫌犯就趕快開記者會,這導致最上頭的毒梟得以有時間滅證、進而逍遙法外。而新的策略裡,由高檢署負責指揮國內所有緝毒機關,把多頭馬車的韁繩抓住,辦案的火力集中,也可以減少洩密,這讓這些毒梟來不及反應,大大提升破案可能。
「像是去年9月,大批海洛因一漂流到海灘上的時候,林孝道其實就有警覺。那時他們的軍師就叫他趕快逃,但因為我們檢警都遲遲沒動作,他就鬆懈下來了,」黃榮德回憶道。
就在林孝道鬆懈的期間,檢警也與泰國警方展開合作,向上追查供貨給林的上游。多次召開跨國緝毒會議後,泰國警方鎖定了長年往返泰緬的另兩名台灣人嫌犯,趁著出入境時接連將兩人緝捕歸案,移交台灣警方處理,提供了更多林孝道販毒走私的直接證據,讓檢警得以一舉瓦解他所建構的勢力。

林孝道的落網,顯示了追查源頭、國際合作的成果,這都是「新世代反毒策略」希望帶來的直接改變。只是,對外合作卻一直是台灣緝毒單位的罩門。
被視為反毒戰神、同時是新世代反毒行動策略的主要撰寫者,前高檢署檢察官王捷拓在去年底提早退休,在接受我們專訪時,指出兩大痛點。
第二個痛點則是境外緝毒機關紊亂,他說,「對境外的主政機關是誰?沒有!現在的狀況是多頭馬車。境外的案件每個機關都想搶主導權,外國單位要找誰合作都不知道。到底是該找調查局,找海巡署,還是找刑事局?」
王捷拓也指出,雖然「新世代反毒策略」初步在國內有不錯的成果,但在國際反毒工作上,台灣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因為緝毒機關紊亂的情形還是存在,國內案件可由高檢署主導,一旦涉及境外毒品案件就缺少單一窗口。此外,牽涉國際情勢跟政治,台灣跟國外的司法互助很差,這減少了更多合作辦案的可能。
通過林孝道案的偵辦過程,就清楚印證了這項問題。由於該案嫌犯之一潛逃泰國,刑事局在與泰國警方交涉時,就因司法互助的簽訂與否有所齟齬。當時台灣官方希望兩邊能簽定司法互助協定,方便交涉與移交嫌犯;但泰方卻不希望如此,理由很簡單,「因為一簽中國就會打壓」,最終合作還是靠著私下協議來完成。
另外,身為UNODC研究員,沈仁植所透露的謹慎態度,也進一步說明了這種限制。在接受《報導者》採訪時,只要沈仁植一提到台灣,都會小心地加上「台灣,中國的一省」(Taiwan, province of China)幾個字。即便雙方僅是聚焦在被視為「萬國公罪」的毒品問題上,國際政治的影響力仍清楚地透過此種方式展現出來,這多少弱化了台灣在與他國合作緝毒的努力。
整體而言,為解決境外毒品問題,王捷拓認為,成立專責的緝毒署有其必要。
然而從緬甸撣邦一路橫越亞洲,這條橫跨4,000公里的亞太安毒販運鏈,穿越了十多個國家,牽起了數百億美元的安毒經濟網絡,身處其中的台灣犯罪組織扮演了關鍵角色,我們該如何洗刷這樣的汙名?
是走向專責機關,建立對外的單一窗口,還是按照既有制度,臨時編制往前走?面對國際毒梟所建立綿密的跨境販毒網絡,政府機關正想盡辦法補破網,試圖用高檢署領頭的緝毒大軍來奮力迎擊。
負責主導對抗這場「毒品戰爭」的政務委員羅秉成在專訪時直言,毒品戰爭是一場不容易的戰役。(延伸閱讀:〈反毒邁入2.0,政委羅秉成:要洗刷毒品中繼站汙名,也要抑制毒品再犯〉)
「有些時候台灣會被當作毒品的中繼站,或是在東南亞路徑上的一站。但是我認為,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就是要洗刷我們的汙名,」羅秉成認為,是否能成功撕下台灣身上的毒品標籤,還得看高檢署統合六大機關(檢察、警察、調查、憲兵、海巡、海關)的功效能否發揮。畢竟台灣的外交處境讓我們鮮少與國外有正式的司法互助協定,只能憑藉駐外單位與國外的情資交換。
資源匱乏的狀態下,想要徹底截斷製毒、運毒到販毒的一條龍產業鏈,打贏這場跨國的毒品戰爭,台灣需要的不只是深入社區的防治與查緝,也需要主權國家間的協同圍堵。而這條漫長的征途,台灣才正在路上。
(閱讀英文版,請點:Manufacturing, Trafficking, and Selling: The Role of Taiwanese Cartels in Asia’s Meth Supply Chain。)
深度求真 眾聲同行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今年是《報導者》成立十週年,請支持我們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度過下一個十年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