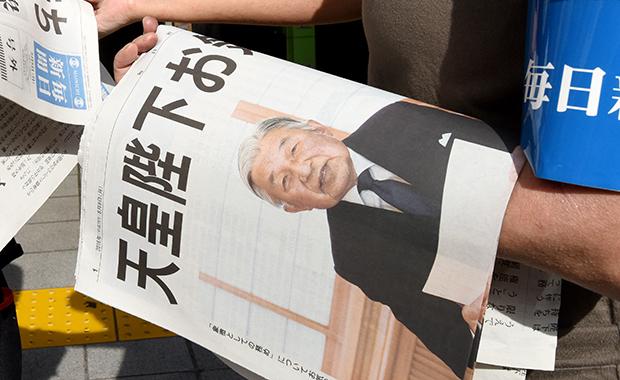《報導者》日前刊出〈無國籍的移工孩童〉專題,揭露台灣有數百位無法取得國籍身分的孩童,引發各界關注。其實,無國籍新生兒的問題在國際上很常見,鄰近的日本與台灣的情況相似,兩國的國籍法同樣為屬人主義,有許多菲律賓女性移工與日本男性所生下的小孩,同樣面臨國籍的問題。
究竟,無國籍的議題如何解?我們專訪長期關注此議題的早稻田大學副教授陳天璽,她著有《無國籍:我,和那些被國家遺忘的人們》一書。她曾是無國籍者,也是非政府組織「無國籍網絡」創辦人,為無國籍者提供法律諮詢,致力於減少日本無國籍者所受到的歧視。
繃緊的空氣,連心跳聲都聽的格外清楚,海關通道上傳來急促的腳步聲,幾位台灣的海關人員盯著我的中華民國護照, 然後異口同聲的說:「不行喔,妳沒有簽證,所以無法入境。」
我站在原地,對著「國境」另一頭不安的父母親大聲喊著:「我不能入境。」
這是發生在我大二那年的春天,我和父母親前往菲律賓參加華商會議,回程日本時過境台灣,媽媽對我說:要不要順便回台灣見見大哥。到了台灣之後,爸媽很順利地入境了,我卻被擋在國境之外。
之前我都說是回台灣,這是我第一次知道,想回也回不了。媽媽在海關另一頭安慰我:那好吧!我打電話給二姊,讓她去羽田機場接妳。
就這樣,爸媽進了台北,我在桃園機場大廳等候下一班飛機回日本。到了羽田機場的海關,我拿著無國籍的證件進去,日本的海關看了證件,又抬頭看看我,把我的外國人登錄證收過去,接著把我叫進一個小房間說:妳現在回台灣吧。
剛才台灣不讓我進去,現在我回到日本,我是有日本永久居留證的人,妳叫我回台灣?海關說:「妳的永久居留證過期了,妳就是不能進來。」
我從未想過,有一天,我會被夾在國與國的邊境之間,體驗了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的感受。我那時感覺自己像一粒灰塵,每個地方都要把我掃出去,沒有人需要我。
那是我第一次實際感受到,哦,原來「無國籍」這三個字是這個意思,沒有一個國家需要我,也沒有一個地方我可以回去。
混亂的思緒跌入過去,想起我為什麼會成為無國籍呢?

我的父親出生於中國的黑龍江省,母親則來自湖南省,他們在國共內戰的時候離開大陸到了台灣,我的5位哥哥姐姐都在台灣出生長大。50年代,父親拿到獎學金赴日本留學,隔幾年,他在橫濱中華街找到工作,橫濱華僑也希望他留在日本,於是母親帶著5個孩子赴日,一家7口在7個半塌塌米的公寓展開新生活。
我出生在1971年,隔年,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同時跟中華民國斷交。我們家面臨國籍的選擇,到底是入日本籍?還是要取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
但是,我的父親出生於東北的地主之家,外公則是國民黨的軍人,所以他們才在國共內戰時離開中國大陸。因為這層背景,我的父母親沒有選擇這些國籍,我們家因此變成「無國籍」。
從小,我就知道自己和別人不一樣。例如,年滿16歲居住在日本的外國人都要申請外國人登錄證。我第一次拿到登錄證時,上面寫著我是無國籍,我就問我爸爸:我為什麼是無國籍,我們不是中國人嗎?
他跟我說了一些外交上面的事,當時的我還不能夠了解。最後我只記得父親說:妳就挺著胸,妳要有自信,走到外面人家就會認識妳「陳天璽」。
上大學後,因為我讀國際關係,經常需要出國,出國旅遊需要攜帶好幾個證件,像是中華民國的護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的僑居民旅遊證,還有日本發給無國籍人士的再入國許可書。從小,因為無國籍的身分需要填寫表格,我被訓練的很會處理文書作業,而且只要按部就班申請,出入國並不會受到阻礙,因此,即便是「無國籍」我也不以為意。
直到大二被堵在國境之外的那場意外。那份強烈的委屈,事發後我仍不敢跟朋友說,況且我也覺得沒人能體會這種感覺。在那之後,我只想快點離開日本,我認為我之所以有這些被歧視的經驗,全是因為我生活在排外的日本,如果能到民族大熔爐的美國,可能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了。所以我就留學到美國。
取得博士學位後,我不想回日本,想到一個新的地方重新開始。我想到聯合國工作,可能到那裡我就不必顧慮國籍的問題,所以我應徵了聯合國。
到了聯合國面試,面試官問:妳是日本人嗎?我說,不是。他再問:那妳是中國人嗎?我說,實際上我沒有中國國籍,面試官說:那妳到底是哪裡人?
我說我是無國籍的。他說,我想聘用妳,但我們需要聯合國會員國國籍的人才能聘用,妳先去辦個日本籍,再回來跟我應徵吧。當時我發現,即使聯合國也不能包容我這個無國籍的人。
那次的挫敗,觸動我心裡最深的傷疤。突如其來的無力感,竟是20多年累積的挫折砌成的。
高中時,我知道自己與身邊的同學不同,想要融入班上卻又做不到。因為,我一直藏著祕密,我不敢讓別人看到我的身分證件,即使身邊親近的朋友,我也不讓她們知道我是無國籍。
上大學申請留學獎學金,卻因「無國籍」而四處碰壁。所有的獎學金條件都有國籍這一項,發給日本人的獎學金僅限「擁有日本國籍者」,發給外國人的獎學金,則需要提供證明身分的文件。
到美國參加新生酒會,大家都以「where are you from?」取代問候。可以翻譯成「妳從哪裡來的?」,也可以是「妳是哪國人?」之意,我總以「 I am Chinese.」輕鬆帶過,狡猾地迴避了國籍的問題。
從小因為無國籍受到歧視,我告訴自己,我必須比別人加倍努力,未來有天能憑藉自己的專長,活躍在國際的舞台上。沒想到這些年的努力,在聯合國門前竟是不堪一擊。
我要面對自己一直不敢去碰的無國籍問題。我開始研究全世界無國籍者,去過很多國家聆聽他們的故事,然後把這些故事都寫在一本書上。

逾期居留的外國人所生子女,在最近成為無國籍兒的主要原因,代表案例是小安德烈。他在1991年於日本醫院出生,母親據說是居住在日本的菲律賓人,生產前她委託一對美籍的牧師夫婦收養腹中的孩子,生產後數日,小安德烈的生母拋下他出院,從此行蹤不明。
安德烈的出生登記上,沒有父親的資料,母親僅聽說是菲律賓人,因此他的國籍被登記為菲律賓。這對美籍牧師夫婦依照約定照顧小安德烈,某天,他們要帶小安德烈回美國度假,前往菲律賓大使館辦理護照,結果,菲律賓政府拒絕發照,並回覆:如果生母不親自出面,提供護照或相關證明文件證明小安德烈是菲律賓國籍,菲國政府無法發行他的護照。
最終,日本政府認定其為菲律賓國籍,但菲律賓政府不願發給國籍,小安德烈在互踢皮球的情況下成了無國籍。
日本的國籍法採屬人主義,出生時父或母是日本人才能取得日本國籍,但是國籍法中亦提及,若「在日本出生,父母均不詳」的情況下,孩童可取得日本國籍。因為這條規定,小安德烈的養父母提出確認國籍的訴訟,他們主張小孩的父親不詳,也無法確定母親的身分,因此應被認定為日本籍。
經過4年纏訟,最高法院最終判定小安德烈為日本國籍,日本舉國譁然。在安德烈事件之後,日本社會也開始關注日籍父親與外籍母親「私生子」的國籍問題。
許多來自菲律賓的女性到日本從事表演工作,她們大多在俱樂部或酒吧當陪酒女郎,自1980年代末期開始,日本男性與菲律賓女性所生的小孩急遽增加,這些小孩被稱為「JAPANESE-FILIPINO CHILDREN」。當父母未婚生子,這些小孩的國籍也會有問題,安娜就是這樣的孩子。
她的媽媽是菲律賓人,爸爸是日本人,她在日本出生長大,但是她的父母沒有結婚,安娜是所謂的「私生子」,母親沒有把她的出生報給政府,所以她就成為無國籍。
在安娜8歲的時候,警察逮住她的媽媽,準備遣返她們回菲律賓時,才發現安娜是法律上的透明人。安娜回到菲律賓後,一句菲律賓話也不會說,突如其來的壓力,讓她一下子瘦了8公斤。

無國籍者的生命故事,經常勾起我深埋的記憶。過去我每每被無國籍的問題困擾時,總是哭著入睡,若能像我一般哭到把枕頭都弄溼,然後睡一覺又醒來的傻大姊個性,那也還算是幸福的。在我接觸的無國籍者中,日日為此所苦而誤入歧途,或精神上承受巨大壓力而罹患精神疾病的大有人在。
因此,我在2009年成立一個非政府組織「無國籍網絡」。一方面希望給予無國籍者支持力量,取得國籍的路相當漫長,我要讓他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有許多無國籍者同樣在路上;另一方面,我這幾年到處去演講,希望讓大家知道無國籍者是如何生存的。
無國籍者經常被誤會成是非法的人,可是就因為有國籍制度,才會產生無國籍的人。像我從小到大沒犯過法,我是因為外交關係、安德烈是被生母遺棄,而安娜則是因為國家國籍法的衝突才變成無國籍。台灣無國籍孩童的情況和日本很相似,只不過日本比台灣早了10年,這些無國籍的小孩都長大了,我們今年才處理一個無國籍的女孩在日本上大學,協助她取得居留證也幫她募集學費。
這是全球都在發生的故事,我希望大家能更理解無國籍者,給他們自信。不管我是什麼國籍,我的名字「陳天璽」是在前面的,而不是我的國籍代表了我;我的朋友認識我,是承認我這個人,而不是因為我的國籍。
其實,在流動頻繁的移民時代,國家的邊界越來越模糊,不過,我們的國籍法卻始終僵固。反而,無國籍的人像一面鏡子,讓大家知道我們的國籍制度有些缺陷,也讓我們去反思,到底我們的國籍制度合不合乎這個時代?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