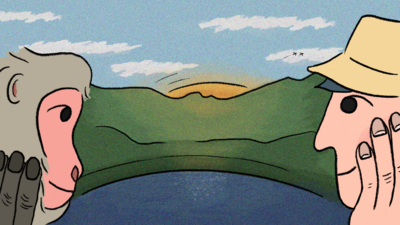George Chan/獵殺與救贖──澳洲袋鼠的命運之舞
(※本文內含動物傷亡影像,建議讀者斟酌閱讀)
深夜,澳洲內陸,一隻袋鼠被強燈照射致盲呆站原地。
「轟!」
獵人扣動扳機,在百米外的袋鼠應聲倒地,眼珠暴凸,頭顱上的細孔正淌血。
「我不是瘋狂殺手。」獵人一邊解剖袋鼠一邊說,「我愛袋鼠,我尊重袋鼠。」
袋鼠是澳洲最重要的象徵和「國寶」,牠們的雙腳只能往前蹦跳不能後退的生理特性,使牠們被放上了澳洲國徽──寓意澳洲是一個永遠邁步向前的國家。據統計,澳洲人口約2,700萬,而這片土地上生活著約5,000萬隻袋鼠,平均近一人2隻。
袋鼠無處不在,同時造成了大量交通意外,在澳洲的公路上袋鼠的屍體隨處可見;農民將袋鼠視作「害獸」,在領地外架起鐵絲網防止袋鼠入侵與牛羊爭搶牧草,此舉又進一步將袋鼠推向公路,造成更多路殺。
然而,並非所有人都對袋鼠抱有敵意。



在昆士蘭州內陸人口僅有100餘人的Muttaburra小鎮上,袋鼠救援義工金・帕爾默(Kim Palmer)和她的兒子基蘭・帕爾默(Kieran Palmer)兩人共收養了超過50隻袋鼠。
金正在廚房裡準備給袋鼠的食物。她逐個清洗袋鼠使用的奶瓶,再用一個大桶把袋鼠專用的奶粉和水按比例攪拌混和,用針筒將奶按需要注入奶瓶。


「其實只有袋鼠寶寶需要喝奶,但我還是希望能讓每一隻袋鼠都能吃得上,就當是零食一樣,能補充一點營養。有些袋鼠已經長大了,奶就吃得少一點,主要還是吃草;那些寶寶還無法吃草,就要喝多一點奶,」金說。
兩人在屋內摀著袋鼠寶寶的眼睛給牠們餵奶,模擬袋鼠寶寶在母親袋子裡喝奶的情形,讓牠們更有安全感。餵完寶寶們後,兩人捧著奶瓶走到屋外的沙地,聽見聲音的袋鼠們馬上向兩人跳過來,他們放下奶瓶親暱地撫摸著袋鼠們。就如同寵物一樣,這一隻隻袋鼠,都有著自己獨特的名字。
金取來一大捆乾草放在地上,袋鼠們低頭吃草,她又喚來十數隻袋鼠來到她與基蘭身邊,一人手持3、4個奶瓶,給這些大袋鼠餵奶。金與基蘭顯然有著很多心事,在餵奶時也總是緊皺著眉頭,若有所思地低頭望著這些袋鼠。唯一一件令他們稍微開心的事情,只有當袋鼠朝他們跳過去,親吻他們或者討抱抱的時候,他們才會稍微展露笑顏,然後與袋鼠面對面地親吻或擁抱。
養育一隻袋鼠一年需要花費約1,000澳幣(約新台幣21,000元),當中包括了醫療和糧食等各種雜費,同時由於未能覓得合適的野放場所,金不忍心選擇「硬放」,即冒著獵槍和路殺的風險隨意找個地方把袋鼠放走。隨著收養的袋鼠愈來愈多,金的經濟負擔亦愈來愈重。她說:
「我在過去6年裡成功野放了差不多100隻袋鼠,而一個袋鼠獵人花一、兩晚時間便能夠輕易地將這成果抹去。我們只是在幫助一個個的個體,但對整個族群來說,我們產生不了什麼影響。我恨,我瞧不起那些獵人,但可能我們和獵人同樣希望能有一個健康的袋鼠族群。沒有健康的袋鼠族群,袋鼠獵人也就沒有工作了;但同時我們現在做的事情需要付出成本,我們絕不會想見到被野放的袋鼠最後被運到袋鼠卡車上。只是如果沒有其他的辦法,我們也只能把牠們帶到叢林裡,放走,然後結束這一切。」
基蘭接著說:「如果我現在跑去殺了一個袋鼠獵人,可以拯救的袋鼠比我一輩子都多。」


就在救援義工金所住的街道另一側,住著袋鼠獵人羅傑・海頓(Roger Haydon)。羅傑起初並不願意接受我的採訪,並表示媒體和動物權益組織一直在嘗試抹黑這個行業,摧毀他們的生計;雖然最終被說服,但同時警告如果發現我是動物權益組織的臥底,將會在狩獵時將我拋棄在荒野之中自生自滅。
懷著忐忑的心,羅傑開著一輛專為捕獵袋鼠設計的袋鼠卡車帶著我駛入漆黑的夜裡。這輛袋鼠卡車只有兩個座位,後面是一排排鋼架,置放著掛鉤,車頂有盞探照燈,可以透過手柄操控照明方向。羅傑將擋風玻璃放下,將步槍架在司機和副駕駛座之間,開始今晚的狩獵。羅傑戴著風鏡,一手握著方向盤,一手控制著探照燈,左右來回地掃視,嘗試尋找目標獵物。
袋鼠並沒有想像那樣多,每隔2、3分鐘只能見到1、200公尺距離外有零星的3數隻,但羅傑並沒有一發現袋鼠便馬上停車開槍。
「那隻太小了」、「那隻是母的」、「那隻不可以殺」、「那隻無法瞄準」⋯⋯羅傑認真向我解釋每次他不開槍的理由。
差不多半個小時過去了,羅傑尚未開他的第一槍,因為法律規定,亦因為羅傑個人的「道德標準」。就在我困惑的時候,羅傑突然煞車,「就是那隻了!」然後用探照燈直照前方100公尺處的一隻袋鼠。
袋鼠被強燈照射致盲,呆在原地一動也不動。
「轟!」羅傑開了第一槍,袋鼠應聲倒地。我們開車靠近,袋鼠的眼珠暴凸,頭上有一細孔正在淌血,Roger用鉗子剪斷牠的脖子和雙腳,用鉤子把牠的跟腱掛在卡車的後方。

並不是每一發子彈都能精準命中袋鼠的頭部。有一槍命中了袋鼠的下巴,牠奄奄一息地躺在草地上,羅傑拿來一根鐵棍猛地向牠砸去,牠整個身體彈了起來又重重地倒下去,又一記猛棍,又再彈起倒下,3、4棍之後袋鼠沒有再動了。理論上來說,如果沒能一槍斃命的袋鼠是需要記錄在案的,但很顯然這對獵人們來說太麻煩了。
殺戮一直持續到凌晨4點,羅傑已收穫了17具屍體。他快速地用刀子把袋鼠的頭顱割去,再從胸部劃開到胯部取出內臟,然後將它們丟到草地上。
羅傑手上的刀一邊飛舞,一邊說:「我愛袋鼠。牠們給了我自由,想工作時就開車出來打獵,看看星星看看銀河,不用看老闆臉色,這是最自由自在的工作。我不是一個瘋狂殺手,我打到我需要的數量,足夠支付我的燃料和子彈,我就會停手。我們尊重袋鼠,這是我們的生計。」
處理完這些屍體,羅傑開著車把袋鼠肉送到冷凍庫裏。




史蒂夫.加里克(Steve Garlick)教授是澳洲動物正義黨(Animal Justice Party)的創辦人,他在澳洲新南威爾斯州(New South Wales)與首都領地(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的邊界上營運著一所救傷中心,在過去25年裡共拯救了超過5,000隻袋鼠。目前共收養了約90隻袋鼠,週末固定有獸醫駐守,為野生動物進行檢查和手術。許多袋鼠的腳上和尾巴上都纏著繃帶,一跛一跛地走著跳著,順利康復者將會被野放回歸野外,而無法康復的將會留在救傷中心終老。
加里克表示,澳洲是全球物種滅絕量最多的國家,其中一個主因是政府只關注選票,救傷中心所有的救援費用全是他自掏腰包或來自公眾的捐款,而政府並沒有提供過絲毫幫助。加里克在過去20餘年與動物權益組織多次發起法律行動希望可以制止政府的殺戮,縱然每次都鎩羽而歸,但他與他的支持者們未曾放棄。加里克雖在8年前宣布從黨內退休,但動物正義黨仍積極參選每一屆選舉,希望繼續為動物發聲,更成功在新南威爾斯州與維多利亞州(Victoria)各取得一席議員。加里克憤慨地說:
「人類能投票,但動物不能,所以政府不在意動物的死活。農民總在抱怨袋鼠把草都吃光了,造成環境問題,影響他們的生計,所以要去射殺牠們。但袋鼠已經在這片土地上吃草吃了百萬年了!卡車司機說袋鼠撞到了他們的車,不,不,不,是你撞到了袋鼠!政府受到了壓力,那些都是有投票權的人,袋鼠不能投票,所以你猜政府會怎麼做?澳洲曾經有過百萬隻無尾熊,是因為人類的撲殺所以數量才會銳減,直到牠們快絕種了人們才想起要保育。50年後袋鼠也會落到一樣的處境,我們以後不只是要到動物園裡面才能看到無尾熊,袋鼠也一樣。」
談起袋鼠獵人,加里克顯得十分憤恨,形容他們為一群「自私、愚蠢、殘忍、貪婪、未開化」的「原始人」:「『這些野生動物不屬於任何人,所以我可以把牠們殺掉去換錢,沒有人會在乎』──政府不斷推動這種觀點,說在野外有很多袋鼠,袋鼠獵人可以處理這些『問題』。問題是為什麼我們會發放執照給人們去殺戮這些動物?」

各州政府每年都會進行一次袋鼠數量統計並訂出各區可以狩獵的袋鼠品種以及狩獵配額,一般是該地袋鼠總數的15%左右,而昆士蘭州在2024年的狩獵配額有逾200萬隻,但分配到Muttaburra小鎮的配額則只有每兩週150隻。要取得狩獵執照,要通過測試在100公尺外將5發子彈全部命中一個直徑為75毫米的標靶,並需要取得土地擁有者許可,才能進行狩獵,並且只能夠將狩獵所得售給持有牌照的指定經銷商。
大衛.柯頓(David Culton)是Aramac小鎮上資歷最老的袋鼠獵人,營運著多個冷凍庫。他強調自己「崇拜」袋鼠:「牠們每天只吃草但卻如此強壯。只要吃袋鼠肉,你就不會罹癌,而且活得充滿力量。」他拉起上衣展示他腰間的刺青,是一隻跳躍中的袋鼠媽媽,袋裡還裝著一隻袋鼠寶寶。
「我是個有道德的獵人,我從來都不對母袋鼠開槍,因為多數時候牠的袋裡都會有袋鼠寶寶。我在路邊如果見到有需要被拯救的袋鼠,我甚至會把牠們送去鄰鎮的救援義工家裡。」他望著我真誠地說:「獵人不需要殺那麼多的袋鼠,每晚3、40隻就已經很足夠了。」
工人們在貨車與冷凍庫之間架起軌道,然後將冷凍庫裡的袋鼠一隻隻推向貨車,這些袋鼠肉即將要被送往肉廠。一個冷凍庫可以裝下超過百隻袋鼠,裡面有一股奇特的血腥味,牠們的頭顱和腳掌被切下來,雙爪交錯地倒吊在裡面,頸部的傷口已凝結成血塊,只能勉強憑那碩大的尾巴認出這是什麼物種,一點袋鼠的樣子也沒有,景象十分嚇人。
「有時候我會覺得這個行業毫無前景,有時候又會覺得充滿希望。」當被問到行業前景時,Roma市的肉廠老闆艾倫.布雷迪(Allen Brady)沒有正面回答。
在肉廠裏,工人們正忙碌地分割著袋鼠。肉廠老闆布雷迪表示,90年代末是袋鼠產業最好的年代,那時的袋鼠皮肉都值不少錢,但自從2014年俄羅斯恢復袋鼠肉進口禁令,善待動物組織(PETA)和綠色和平(Greenpeace)等組織亦在歐洲市場施加了很大的壓力,使袋鼠產業飛快的萎縮。目前肉廠的產品有90%最後都成了寵物食品供應本地市場。
「你肯定看到過那些農民建起的鐵絲網,他們說是為了防止野犬入侵,胡說八道!農民只想把袋鼠趕盡殺絕。我不覺得袋鼠有多泛濫,現在是剛剛好。你需要有足夠數量的袋鼠才能讓整個行業裡的所有人生存下去。」
袋鼠產業是一個隨著政策走的行業,在澳洲國內外並非必需品,而動物權益保護的呼聲又日益增長的情況下,袋鼠業者只能盡力開拓寵物食品的市場。
「小狗很喜歡吃袋鼠肉,我們會成為寵物食品產品最大的供應商,」布雷迪說。

當我離開那殺戮戰場,回到雪梨的家中,那身血腥味卻揮之不去。我時時會回憶起在這幾千公里路上遇見的,被烏鴉啃咬的袋鼠屍體;回憶起袋鼠獵人說起他們對袋鼠的尊重時的誠懇,下一秒幻聽袋鼠中槍後的哀鳴;回憶起救援義工對袋鼠族群現況的悲觀和憤慨,心中暗諷這些不過是薛西弗斯式的無用功。
這些袋鼠的命運不由自主,被救援、被野放、被獵殺、被製成商品。即使野放後,袋鼠幸運地不被獵殺或躲過車輪,那也只是幫助了寥寥可數的個體,對整個袋鼠族群的數量,產生不了根本的影響和意義──畢竟在荒野草原和沙漠裡,還有過千萬隻袋鼠在蹦跳著。不過,加里克看著我的雙眼,說著他認為的拯救袋鼠的意義:
「我不關心數字。我只關心是否有動物正在受苦受難,我們是否能夠做些什麼去幫助牠們,然後將牠們送回牠們原來生活的地方。如果可以,那我們便成功了。在數據上看是毫無意義的,但我只在乎在某時某地正在受苦的那隻動物。」
有人認為袋鼠數量泛濫成災,有人認為袋鼠族群數量受到危害;有人以獵殺袋鼠來謀生,有人以拯救袋鼠為己任。儘管意見立場天差地遠,但或許這個故事裡,沒有人做錯了什麼。袋鼠也沒有。
家中的角落放著一隻袋鼠的毛絨玩具,那是當時報導東協(ASEAN)特別峰會時澳洲政府為記者們準備的紀念品。牠不會與牛羊爭搶牧草,也不會有獵槍對準牠的頭顱,沒有人會討厭這樣人畜無害的毛絨玩具。人與動物間的瓜葛永遠糾纏不清,但願袋鼠能永遠在這片土地蹦跳著。

1996年生,香港出生長大,於2022年移居澳洲雪梨,目前是自由攝影工作者,專注拍攝澳洲各地的新聞與人文議題。
Instagram:@WhoIsGeorgeChan
【歡迎影像專題投稿及提案】 請來信[email protected],若經採用將給予稿費或專案執行費。
用行動支持報導者
獨立的精神,是自由思想的條件。獨立的媒體,才能守護公共領域,讓自由的討論和真相浮現。
在艱困的媒體環境,《報導者》堅持以非營利組織的模式投入公共領域的調查與深度報導。我們透過讀者的贊助支持來營運,不仰賴商業廣告置入,在獨立自主的前提下,穿梭在各項重要公共議題中。
你的支持能幫助《報導者》持續追蹤國內外新聞事件的真相,邀請你加入 3 種支持方案,和我們一起推動這場媒體小革命。